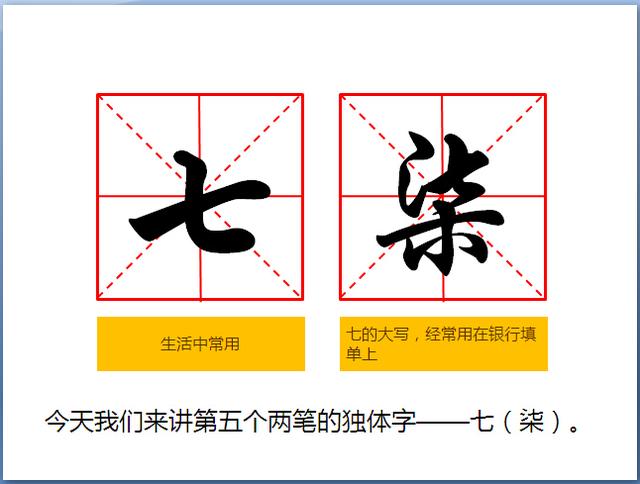打摆子福建连城话怎么讲(老成都说四川话摆几个龙门阵)
打牙祭

打牙祭这个词组不仅流行于四川,流行于西南,并且,也广泛地被其他省区的人所认可,所引用,等于是地方粮票全国通用。过去,一说到打牙祭这几个字,我们就会红光满面,热血沸腾,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渴望,嘴巴头也就会满口生津,“泪”如涌泉;而现在,我们差不多天天都在打牙祭,反而忘却了这个很传统的词语了,这几个打成捆子关系亲密的字离我们是越来越遥远,遥远得如同我们穿叉叉裤的睡娃儿时代。
打牙祭的说法源远流长,可以考证出起码源于民国之前、之前的封建社会。
“牙祭”咋个打?这就得从“牙”从“祭”说起。
那时,生产力低下,再加之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弄得“牙”冤枉天天守门把关,常常是一点点油水都沾不到。老百姓总觉得对不住一天到黑辛辛苦苦嚼糠咬菜的“牙”,时常寻思弄点“油大”来祭祭“牙”这尊菩萨,免得它瘦得只剩下白生生或者是黄焦焦的骨头。
朝思暮想,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端阳、中秋,或者是初一,或者是十五,盼得来锅头、碗头、筷子头有了“油大”,平头老百姓就要“打牙祭”了。

但则见,“油大”一沾唇,便身不由己,被“牙”一口咬住,三十二位牙兄牙弟高矮不打让手,咬、撕、扯、嚼、磨,牙法娴熟,上下同心协力,又快又稳又准又狠,硬把一坨“油大”咬得嚼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油水四溅,祭得门牙、大牙、智齿均油光水滑,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吃不尽肥肉瘦肉决不下战场。
此时,唾液急如泉涌,喉咙伸出手来,生拉活扯将今非昔比、面目全非的“油大”扯进咽喉,又匆匆忙忙吞将下去。忙中自然免不了小有遗憾,竟留得三两丝或一两点肉渣在牙缝之间藏身,也就只得权作“打牙祭”的纪念物,权作进贡五脏庙路过牙关时的回扣。水过地皮要湿,肉过牙该沾油,牙也就当仁不让地笑而留之了。
“打牙祭”至此,告一段落,未尽之兴,未了之愿,未歼之敌,还待下坨分解。
这正是:提起“打牙祭”,千头又万绪。过去的日子,想起就怄气——不晓得为啥子,总之难得打牙祭?如今天天有肉吃,“打牙祭”已成了历史,成了过去。
生活就是打戳戳

“打戳戳”不是“打乱戳”。“打乱戳”多指闯荡江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吃一嘴算一嘴;“打戳戳”则多是指“打临工”,找一个算一个,“戳”一下算一下。
当年,一位朋友,因“病”暂居姐姐家中。那些年月,要找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比李太白惊叹过的古时的蜀道更难。他寄人篱下,日子自然过得艰难,心情更是糟糕,便想出去“打戳戳”挣点散碎银两,好看到姐夫的脸色“阴转晴”,自己也过几天“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虽然那时一切小商小贩都被明文取缔,但他已是成了被逼慌了的兔儿,也就慌不择路,走上了“黑道”——他借了姐夫一辆破旧自行车,到附近乡场上去买了些黄鳝,再骑回城里,专走背街背巷去“剐黄鳝”卖。弯腰驼背地剐,双手沾满无辜黄鳝的鲜血。黄鳝也是生命,也有它的生存权,它在被强力强权宰割之时,不能开言,无法控诉,就只能在剐它的木板上又蹦又跳地表示强烈抗议,喷得这位知青朋友一身、一脸都是血点点。他也并不在乎,当了泥鳅就不能怕泥糊嘴,当了剐黄鳝的“刽子手”,就得不怕一身沾满了黄鳝的鲜血。血沾得越多,他越高兴,衣服上,脸上的每一个血点点,都说明他又赚了几分或是几厘人民币。

天天早出晚归,从市区到乡场,再从乡场到背街背巷,他亡命地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骑起自行车开跑。一两个月下来,他收获不小,果然挣了一大把散碎银两。他便给了姐夫60元钱,把姐夫借给他的那架“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响”的“全响牌”买下了,姐夫姐姐都很欢喜,说他有出息了,他更是高兴。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谋生糊口的劳动工具兼交通工具了。
哪晓得这位朋友刚买断自行车产权个把星期,就痛失街亭,误走麦城——在乡场上被当地"乡群众专政指挥部”的人没收了他的“作案”工具:自行车和黄鳝筐筐。他不服,就像黄鳝在剐它的木板上一样,又蹦又跳外加上他有嘴巴又在大声喊黄,鸡蛋碰石头,被扎扎实实捶了一顿,弄得鼻青脸肿怒火满腔眼泪汪汪地又是走路,又是赶公共汽车,天都黑了才狼狈而归。
后来,他又在街道运输组打零工,拉过木料,拉过石灰;再后来,又挖过烂泥巴,掏过阴沟,卖过凉水;总之是东一下,西一下,八方“打戳戳”。
再再后来,他买了推子、剪子、梳子,天天串院坝走宿舍区,上门剪头。只剪脑壳不刮胡子不修面,也不洗脑壳,不吹风搽油,称为“剪素脑壳”。大人一角钱一个脑壳,娃娃只收八分钱;两弟兄打伙剪,两个脑壳打伙优惠一分钱,只收一角五。

一天晚上,他来我家耍,经济基础可以了,就整起了上层建筑,说他在体验生活,二天要当诗人。说到说到的就很动感情地朗诵了他的一首自由诗——“呵,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打戳戳’/呵,生活,/生活咋个说/生活就是剪素脑壳……”
打滥仗

“打滥仗”词义模糊,涵盖的内容很多。多用于20世纪或20世纪之前,21世纪少有人使用了。属于失业率较高,但还有上岗可能的一类词语。这不,我这篇短文就通知它说:你资格老,经验丰富,本文又请你来上班了!
比方说:龟儿杂牌军又在打滥仗了——意思是杂牌军把“仗”都打“滥”了,年年打、月月打、天天打,打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又比如说,哪家的娃娃从小就不学好,长大成人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想做,弄得来只有流落街头,伸起两只手,讨口度日。街坊邻居看到他长大的老大爷老婆婆为之叹息道:这个娃娃才是擀面棒搅屎——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小时候不听老人言,到今天必定受饥寒,弄得来只有当叫花子,到处打滥仗。
过去好多跑江湖的,比如择字、算命、卖唱、卖打药、卖烟花爆竹、卖针头麻线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的,说得好听点,统统叫作四海为家找钱吃饭,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得不好听点,或者是自嘲的说法,也统统叫作“打滥仗”。

(图为四川谐剧创始人王永梭先生表演的卖膏药的江湖流浪汉。《卖膏药》是谐剧的创始作品,原创于一九三九年)
——这些说的是早些年的事。现而今社会飞速发展,很多语汇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今有的“打滥仗”也打得今非昔比,打得有点高级了。
我的一位文友,笔杆子有点写得,人也很能干,干了些实事,当上了该地方的官员。据我所知,此君为官期间,颇有政绩。然而,官场风云变幻非一介书生所能驾驭,为官有功无过的他,竟然仕途受挫,说得清楚点,就是被洗白了。此君义愤填膺,一纸数行呈送上峰,便义无反顾,捏起两个砣子,辞职下海远航去了,又是赴海南,又是闯北海,一去就是三五年未闻音讯。一日,我接到此君从本市打来的电话,说是刚从海边归来,诚邀亲朋好友一聚,以慰多年思念之情,要我一定到饭店餐厅共饮几杯。我应邀赴宴,见此君亲友高朋满座,他老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名片上头衔一串,又是老董——董事长,又是老总——总经理,又是啥子执行董事,外搭常务副总经理,看得人眼花缭乱。酒席宴上,大家无不赞叹,都说是当年把你洗白歪打正着,硬还整对了的;还是你老兄拿得横,无官一身轻,下海风又顺,简直可以说是我们“识字”分子的光辉榜样了。此君仰首饮下了一杯杜康,摇摇头,微微笑,做谦虚状曰:过奖了,过奖了!兄弟是离乡背井,亡命天涯,八方打滥仗!哈哈!简直是打滥仗!

这位老董兼老总兼啥子执董的“打滥仗”,在他是有若干曲折故事——诸如抛妻别子,诸如离婚再娶或不娶,诸如商场情场名利场都是战场三位一体硝烟滚滚的,而在未下海的人听来,却只当是“打滥仗”的新解。
鸡肚不知鸭肚食,条条蛇都咬人。不是万般无奈,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亡命天涯”,八方“打滥仗”为好——一位戴眼镜的朋友席后对我说道。
徐建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任编辑,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副会长、秘书长,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