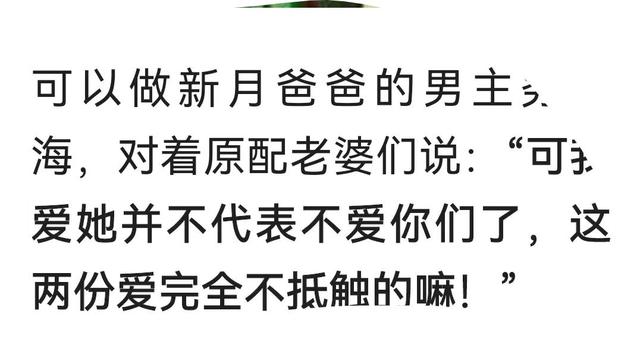豆瓣上看日志的人(豆瓣日记:我是你的谁)
本文作者“CUT”,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巴赫曼与策兰:《心动时刻》
前言
这段爱情故事很长时间鲜为人知。期间少不了传出一些虽小小的谣言。现在,英格堡·巴赫曼和保罗·策兰在1948年至1967年期间的来往信件,镜像地向公众开放,他们悲惨的、辉煌的、独一无二的爱情才真正地公之于众,两位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留下众多线索,不再是学术上含混不清的轻声细语,而是爱的语言,是远比美好更可怕的爱情故事。
无论怎样,在两位诗人身上,爱情和失败是同义词,爱情的殉难超越一切失败之上,他们的经历、所讲述的故事,比所有的爱情故事更强烈。任何一个像保罗·策兰一样、深入到历史最深处的人,完全无力逃脱父母遇害的死亡经历。另外,与这种深渊比起来,还有一种更深的深渊,当他与首批奥地利纳粹的后代、诗人英格堡·巴赫曼一见钟情时,那个深渊早就在等待着他们。
永远的陌生人
在噩梦序曲之一的,小说《玛丽娜》(Malina)中,英格堡·巴赫曼将策兰描画为一个身着黑色斗篷的陌生人形象,将自己爱情命运与策兰的犹太人命运联系起来,包括策兰驱逐出境和跃进塞纳河结束生命的故事,联系起来:“他在放逐过程中溺水身亡,我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就像爱生命,甚至重于自己的生命。”
这些句子仅仅只是文学创作呢,或者还是真情实感?真实生活中的巴赫曼,和众多的凡人一样,爱自己多一些,等待和期望遇到一个非常自信的男人。因此,第一次遇见策兰,她的感觉非常好;尤其是他与生具来的奉献精神、他虔诚的所做所为,恰好是她生活重心、即她的写作中,最不确定和缺失的部分。在写给策兰的信中,巴赫曼总是热切地和他讨论着诗歌,但是策兰对此反应却很冷淡,甚至是比较潦草和零散。
一封1961年写作的、从未发出的信,主要内容是了结和终止他们的关系;除此之外,她非常坦白地问策兰,“经过这么多年,我是你的谁?在你眼中,我是谁?”: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策兰诗人偏执狂的反抗,而且更是质问和抗议他作为一个永恒的受害者的地位:“你有一切的选择权,是否作为一名受害者生活,但是你选择了以受害者身份生活着……你活着就是想成为一个惭愧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在这种生活中,她也未能幸免地成为了受害者,也带着惭愧地心情生活着,策兰不仅在生活中一直都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她在众多幻想的男人中选择的一个牺牲品。
首位出现在巴赫曼视野中的男人,应该是来自克恩顿州的、纳粹作家、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佩科尼格(Josef Friedrich Perkonig),青少年时期的巴赫曼非常崇拜他,出现在巴赫曼青年时期的作品《致费礼兹安的信》中,只是后来在她的传记中此人完全消失了,因此外界并不熟知。外界公认的、巴赫曼首次堕入爱河的男子是,二战时流亡瑞士的汉斯·威格尔(Hans Weigel),此人二战后再次回到奥地利维也纳,成为了当时战后文学教皇,而巴赫曼收集了所有的威格尔创作的、认为对自己有用的文字。但是没过过久,巴赫曼就兴趣索然,因为1948年,她与逃离罗马尼亚的、无国籍诗人策兰首次相遇,两人一见钟情。
1948年5月20号,她写给自己的父母的信中说,“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策兰”和她“非常幸福地”相爱了,他“用众多的罂粟花装饰房间,现在那里被花海淹没”,成为了一片“罂粟花田”。三天后,在巴赫曼22岁生日时,策兰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在埃及》(In Ägypten),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这些被公开的信件,里面内容充满了心爱的陌生人之间的庆祝,以及只能用被谋杀的痛苦来装饰的情人之间的爱情:
你应该将你身边的陌生人装饰得最美丽 你应该用路特,米利亚姆和娜奥米的痛苦装饰她们。 —— 《在埃及》节选
Du sollst die Fremde neben dir am schönsten schmücken. Du sollst sie schmücken mit dem Schmerz um Ruth, um Mirjam und Noemie.
即使九年后,在写给巴赫曼的信中,策兰再次回忆起这首诗歌时,写道:“我每每读到时,就设想着你进入到这个诗歌中:你是我生命的源泉,支撑着我继续写作、说话、活着”;同时对于他,她永远是陌生者,而他同样也是她的陌生人。

保罗策兰
我将一切压成赌注
1948年6月底,策兰离开了依旧充满二战遗魂的维也纳,流亡到巴黎,后来决定定居那里,当时巴赫曼正在为她的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紧张工作着;在她寄往巴黎的第一封信中,非常坦白地表示她有时真的不想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对于我来说,你来自印度、或者一个更加遥远的、黑暗的、棕色的国度,对于我来说,你是沙漠和大海、以及所有的秘密。”但是随后,这个带着深厚奥地利君主制印记的女孩,将自己的幸运寄托在一座城堡上:“我应该拥有一座城堡,让你来到我身边,让你成为我的永远幸福的主人,让我们用很多地毯、挂毯和音乐来装饰它,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和得到爱。”很自然的,幻灭会紧随其后:“现在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平淡、陈旧、疲惫和磨损的,然而我所渴望的,都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之间的通信受到各自情绪周期影响,出现长时间的、冷战式的沉默。策兰在写于1949年8月20号的信中,向巴赫曼解释了自己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几个星期短暂生活,你到底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从你的稍纵即逝的语句上,我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英格堡?也许这是我们两人的错误。现在我只能安慰自己,或许我的沉默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由它产生的、施加在我身上的黑暗,更为古老。”
她的回信却是平淡无奇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以及将来去向如何。对此我还是很开心。我很了解你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人……你应该能这样想,对于我来说,有了你也不等于我不能与任何男人有任何关系,……但是一种无疾而终的结果,会让我你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同时,她也向他承认了,她“将和某人一起做一次巴黎私人探访”,期望这些字里行间的内容能够给予策兰一点安慰。1950年9月,她突然决定搬到巴黎和策兰一起:“对于即将到来的将来,我的感觉十分复杂,时常高兴时常恐惧,更多的是恐惧。请尽量地一定对我好,不要抛弃我! 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迷茫的梦,你不存在,巴黎不存在……”

巴赫曼
两人性格非常相像,不知道如何给予和放弃,巴黎共同生活的时间最终成为一场灾难。当时,巴赫曼写信给与她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斯·威格尔,信中她抱怨说,策兰和她共同生活的尝试斯特林堡戏剧性结束了。1951年6月,已经回到维也纳的她写信给策兰:“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即使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刻,即使当时我们成为最仇恨彼此的敌人,我们依旧感觉到幸福?为什么你感觉不到,我依旧怀着一颗疯狂的、即困惑、又矛盾的心情想回到你身边,而这颗心依旧会对你不利?我爱你,又不敢、不愿意爱你,这种爱实在太多太重;但是我爱你超过一切……”策兰回信内容却是充满了父亲式关爱,讲述着古老的智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一些经验教训,一些事、一些感觉,即使是最真实的部分,也是无法再次得到或收回,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真切地回忆再次拥有。另外——不仅如此——你还需要宁静,英格曼,平和和坚定,而且我相信,你无法在其他人那里找到这些,而只有在你自身上发现。英吉,和你同时代大多数人相比起来,你的生活所得比他们多得太多……现在,你应该少一些要求……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在你得到一定成功之前提醒你:生命是短暂的,成功尤其如此,如你这样、拥有天堂般美好生活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去生活,去对待成功。”
热恋期间,保罗策兰曾送给巴赫曼戒指,后来又想收回,于是,1951年9月,巴赫曼只是将戒指寄回去,把早已写好的信留了下来,在信里她写道:“我无话可说,我的良心由戴着这个戒指的死者组成。”一年之后,策兰和吉赛尔德莱斯特兰奇结婚,他们在1951年11月相识。吉赛尔,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一个外国人,来自一个法国天主教贵族家庭,家族祖先画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的时代。她非常善良,愿意为策兰无私地圣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她无法独自以自身的力量挽救策兰。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在大家阅读巴赫曼与策兰的通信时,也可以同时阅读策兰和妻子吉赛尔之间的信件来往,(法国德苏伊勒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策兰生命中最后二十年期间的所有生活细节),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无常的命运如何将这两位伟大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巴赫曼与策兰在《第47小组》聚会中
“我将我的所有压成一张赌注,而现在我却失去了它……我我什么愿望都没有。请不要害怕担心,如果我重提那些陈年旧事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过去”,1952年春,在给策兰的信里,巴赫曼写道。当时,结婚后的策兰恳请巴赫曼不要重返巴黎,并且要求放弃这段情谊,(“友谊也无法改变已成的事实”)。在这个从策兰那里开始的、“可怕的、不可宽恕的”阶段,巴赫曼陷入了沮丧压抑状态,此时的她唯一能做的,只能调整自己在策兰生活和创作中的位置,成为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利用她在德语文坛上的所有影响和关系来扩大策兰诗歌的影响,树立起策兰在德语文坛上的稳固地位。1952年5月,她安排策兰到尼恩朵夫参加文学创作集体《第47小组》的文学活动,在那里他们再次见面,但是首次交谈,(他)“摧毁了我过去一年的所有希望和努力”。当时策兰朗读《死亡赋格》,与《第47小组》中某些国家民族意识的作家发生严重冲突,(“你的朗读,仿佛是戈贝尔在演讲”,其中一个人大声喊到),结果策兰反过来指责巴赫曼,认为她残酷地抛弃了他和他的诗歌。巴赫曼在1952年7月10写给策兰信中质问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我明白之后、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找到其他人,并且指责我,在这种德国“丛林”中没有和你站在一边。……。告诉我,你早已离开了我,我应该怎样和你站在一起。”
1952年11月,在《第47小组》秋天一次活动日中,巴赫曼遇到了年轻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泽(Hans Werner Henze),这位年轻人与生具来的感恩、贵族、机智、热情、童心傲慢等气质深深吸引着巴赫曼,她毫无犹豫地接受他的邀请去到意大利。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亨泽的音乐可以证实这种生活仿佛一种永恒庆典,尽管这种庆祝生活完全没有牵涉到性。不仅亨泽的歌剧能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美妙生活,而且巴赫曼的一些最美妙的诗歌中,也能看到这种永恒庆典生活的轨迹。
“有些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一直不要返回到‘欧洲’ ”,1953年,从福廖-伊斯基亚,她写信给策兰时说,随后提到,她“独自生活”。事实上,策兰过了很久才听说亨泽,而亨泽却从未听到过策兰的名字。巴赫曼非常喜欢在一种严格保密地情况下,同时拥有好几种不同的恋爱关系,这是一种疯狂的、甚至非常危险的举动,喜欢这种疯狂危险游戏的人,往往会得到最不幸的后果,巴赫曼也不例外,到最后,特别是认识并且爱上了有嫉妒世界冠军之称的马克斯·弗里施后,她不得不为所有疯狂行为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亨泽与巴赫曼的性别取向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还是考虑到婚姻,两人拥有一个共同心态,他们视共同生活为兄弟姐妹般的生活,视为已经铭记在心的、保留一个无所畏惧空间的承诺,视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反抗爱情中、快乐恐惧时刻相随的“黑暗大陆”的新世界。

策兰与妻子吉赛尔
放逐与迷失,一直在家
随后几年,策兰和巴赫曼之间通信来往中断,直到1957年10月,在伍珀塔尔举行的精神复兴协会会议上,两人再度重逢,一时间,两人之间再次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令人陶醉的爱情回来,然而一同到来的还有很久以前的、所有的害怕和恐惧情感。团聚激发了策兰创作激情,短短几天,他就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对巴赫曼的爱恋,这些诗歌中最美好的一首,应该是《科隆,安霍夫》(Köln, am Hof),当时两人入住在位于科隆大教堂附近、安霍夫大街上、酒店里,那里成为了两人共同的家,那个失去了很久的、从一开始他们都不曾拥有过的、共同的家:
放逐与迷失 一直在家 —— 《科隆,安霍夫》节选
Verbannt und Verloren waren daheim
1957年10月28号,巴赫曼从慕尼黑写信给策兰,引用了法国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诗句“我们两人都还在”,策兰曾将此诗句翻译为德语“一次又一次,我们两人”。这是一封充满绝望情感、又混合着希望的信件,同时又恳请策兰不要抛弃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策兰和吉赛尔已经分居),希望他们能破镜重圆。信中写道:“每当我想起她和你们的孩子——而且这些将一直存在在我的脑海中——我便无法拥抱你。”
在同一封信中,巴赫曼问恋人说:“难道我们只是梦想者吗”,那么只有这样,她才能不放弃,将她与策兰之间非常真实的爱情关系延续下去。后来发生的事情,减轻了他们的一些顾虑,吉赛尔·策兰阅读英格堡·巴赫曼的诗歌后,在巨大震惊的同时,也得知了两人真切爱情和巨大痛苦,因此特地恳请丈夫去到他的情人身边去。(在她写给策兰的日记中,吉赛尔写道:“多么可怕的命运。她如此地爱着你,她受尽了折磨。你对她怎么可以如此残酷无情。现在我站在她一边,而且接受你再次见到她,我会保持冷静的。你欠她实在太多。”)
这对相爱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激动、刺激、误解、痛苦和疏远等等情感波动后,最后还是向现实屈服:英格堡·巴赫曼回到那不勒斯亨泽的身边,而保罗·策兰与吉赛尔的婚姻继续下去,与此同时,两个女性之间开始了信件来往,但是对1958年7月访问巴黎时、英格堡·巴赫曼首次遇到的、马克斯·弗里希反应冷淡。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巴赫曼依然无法将策兰从内心深处完全抹去,同时开始了和弗里希在苏黎世和罗马两地的共同生活;在首封苏黎世来信中,她就谈到了自己“闲散、怀疑和抑郁”等情绪,随后几乎所有的信中,不仅恳请与策兰的团聚,而且请求策兰成为见证“我内心中的荒原”,以及“粉碎了我的所拥有一切的”衰竭的见证人。
到此,也许大家会疑问,为什么策兰成为“彻底瓦解了我和我的一切”的原因:外表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件爱情事件,但是对于他而言,却触及到了犹太人灭亡的中心创伤,其中他的父母成为了牺牲品,不仅是他的作品《死亡赋格》,而且是他整个创作的深渊。

爱情,一件美丽拘束衣
诗集《语言铁网》出版后,君特·布勒克在柏林《每日镜报》上发表了潜意识地反犹太主义思想的诗歌评论,策兰气愤地认为这是一种“严重亵渎”;与此同时,策兰还深受来自诗人伊凡·戈尔的遗孀克莱尔·戈尔的、臭名昭著的抄袭指责的影响,她指责策兰的诗歌创作从里到外、从次要到核心内容,都抄袭自她已经去世的丈夫的诗歌。策兰不得不使用所有的力量为自己辩护,在德国寻找反对布勒克和克莱尔·戈尔的盟友。同时,他感觉到自己最亲密地朋友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这种感觉让策兰陷入了一种更加绝望的偏执情绪中。为了获得帮助,他不得不公开地发出恳请和声明,甚至绝望地请求巴赫曼新同伴、明星作家弗里希帮助。但是,弗里希在收到策兰三封请求信后才姗姗答复,信中内容更是深深地伤害到策兰,弗里希在回信中说,策兰创作时使用死亡集中营是非法的、甚至可怕的,因此他对布勒克言论的愤怒,只是作者虚荣和贪婪共鸣产生出的、小小火花而已。(策兰在自己的日记中列出了“懦弱,虚伪,耻辱”等字眼。)
尽管马克斯·弗里希喜欢用一种良好的外表来粉饰自己个人深渊,但是英格堡巴赫曼非常清楚,弗里希自己也是一个受过伤的人,而且出于对某人的忠诚,也不允许她,按照策兰所希望的那样,为了策兰而完全利用弗里希。因此,不仅弗里希,而且巴赫曼也错过了策兰所谓的“求救呼喊”(“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不在你身边……而是……在文学中”),导致他要求她停止给他写信、或者给他打电话。尽管得到如此要求,1959年11月18号,巴赫曼依旧写信给策兰:“从你上封来信以来的日子,极其可怕,现在,一切都处于摇摆不定中,濒临破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无止尽地伤害着对方。这里我不能也不应该发言,但是我必须谈论我们,在我们的立场上,我必须谈论。你和我之间,无法再次错过了,这样会毁了我。”
1960年2月,在忠诚与爱之间的冲突威胁压迫下,她终于选择了忠诚,放弃了爱情:“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到如今我们的爱情走投无路,似乎到了尽头。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后来,出现了两次机会,他们可以再度重逢,首先在苏黎世,两人都拜访了刚刚在梅尔斯堡接受德罗斯特奖的诗人耐莉•萨克斯,随后的一次,英格堡在弗里希的陪同下抵达巴黎,此行目的主要谈论针对克莱尔戈尔对策兰的剽窃指控的防御策略,但是策兰和巴赫曼各自坚守着承诺,在彼此的心中相会。“毫无轮廓和目的,更加重了交谈的不幸感”,策兰在日记中记载了那次苏黎世会面的情形。

告诉我关于爱
这时,巴赫曼自己也慢慢地发生了改变,那种“超越同情心”的感情和友谊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在她经受了无数次来自策兰的侮辱和威胁后(策兰曾经称她为凶手),连对策兰的怜悯也几乎消失了,1961年9月,她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气和力量,写了那封永远没有邮寄出去的、伤心至极的分手和最终了结的信件,其中指出:“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总是痛苦万分,有时候甚至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无法恨你……很多时候也会想到吉赛尔,非常佩服她对你的坚定和宽容,而你恰恰最不坚定、也最不宽容……对我来说,她的舍己精神、她的高贵骄傲、以及她的忍耐比你的抱怨,更有意义。你用你的不幸折磨她而得到满足,但是她永远不会利用你的不幸得到满足。我要求能够独自确认对一个男人的要求是否足够,但是你总是和我唱反调,这多么地不公平。”
1965年11月24号,策兰试图谋害妻子未遂,随后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恢复出院。但是,1967年1月30号,策兰再次企图谋害吉赛尔和儿子艾瑞克,又一次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最后一次强行入住精神病学院接受治疗后,策兰于1970年4月20日在塞纳河投河自尽。
诗句“爱情,一件美丽拘束衣”来自策兰诗集《线程太阳》,要想了解诗句背后的可怕事实,并不被需要知道诗人强行入住精神病院治疗,因为英格堡巴赫曼与策兰之间的来往信件,都是证明了这个悲惨的事实。
巴赫曼与弗里希之间的关系以惨败告终后,所有的城堡最终只是一座座空中楼阁,而在后期盛宴中,她喜欢将仇恨性言论喷洒其上:在小说《玛丽娜》中,弗里希是一个恐怖角色“岗兹先生”;而保罗·策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黑暗中渴望的身影,却是那般美好,是他在第一次见面时为她而呈现的、一直到她死亡之前、都无法从现实中抹去的美好形象。
1973年,在策兰去世3年之后,在罗马,巴赫曼死于一场火灾之后,终年47岁。
“策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流血的伤口”,这是来自另一位伟大的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的感叹。人们都会爱上一个伤口,尤其当这个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尾声:
最后,关于这本书的版本,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书中的评论往往令读者失望。
其次,随书同时选录的吉斯勒·切兰·莱斯特兰奇写给英格堡·巴赫曼的信件,其翻译不仅不通顺,甚至出现了语法错误,比如“请您从您那里给我写信”这样的错句。
最后,最让人气愤的还是,芭芭拉·韦德曼和贝特朗·巴迪欧所写的夹生半调的后记:对于两人来说,写信和写作一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后记中使用到的德国官方法律术语、比如“在这方面”等等,与一本诗人通信集的用语和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同样的,“伴侣”一词,也应该留给婚姻机构使用,而不应该出现在这本书中。
(全文完)
本文作者“CUT”,现居Bern,目前已发表了304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CUT”关注Ta。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