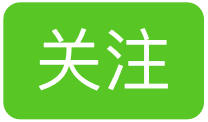杨公忌日是没有道理的(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禁忌,是人们为了避免遭受灾祸、凶厄而对某种特定的时间、地点、人以及其他自然事物所作的禁止性规定。规避凶恶,追求福祉,是古人遵循禁忌之初衷,故许慎《说文解字》释“禁”为“吉凶之忌也”,足见禁忌的遵循与否,与国家、个人的吉凶祸福密切相关。而时日禁忌之目的,即在于选择良辰,规避凶日。关注时令的阴阳家宣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在面对未知恐惧时,普通民众自然乐于逃避灾祸、接受福祉,故时日禁忌在汉代社会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汉代社会迷信时日禁忌的现象及其影响,王充《论衡·讥日》篇有生动的描述:“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由此可见,汉代的“世俗之人”,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皆遵循时日之禁。而且,尽管王充称信仰日禁者为“世俗之人”“俗人”,但这种信仰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续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之执掌曰:“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刘昭注引《汉官》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四人日时。”则国家诸礼仪之执行,亦需择卜时日,且设有专门之职。而在王莽时期,甚至还曾向全国发布诏令,规定:“冠以戊子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为忌日。”故王充又云:“故世人无愚智、贤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惧信向,不敢抵犯。”

《论衡·讥日》,宋乾道三年绍兴府刻宋元明递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随着以《日书》为主的数术类简帛的不断出土与公布,《日书》及相关数术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这使我们对时日禁忌这一汉代信仰世界中的重要类别有了十分真切的了解。不过,学界的目光似乎过于聚焦于《日书》及相关宗教信仰的研究,而很少关注时日禁忌观念的另一个侧面,即汉人对时日禁忌观念的反思、质疑与批判。随着对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研究热度的下降,这种对古代信仰的批判性研究似乎已经逐渐式微了。然而,在关注宗教信仰的内涵与细节的同时,古人对这些宗教观念的省思与批评仍值得重视。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土壤之上,人文理性精神才得以增长。因此,本文将结合《日书》等新出简帛数术文献与传世典籍,并将目光聚焦于汉代的日者、士人及知识分子,藉以探讨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应对、质疑与批判,以期更为完整地展现汉代时日禁忌观念的真实图景。
一、日禁之密与“不得择日”下日者的救禳汉代日者流派众多,又各有不同的禁忌系统,若兼顾诸种流派,往往会造成无良日可择、无凶日可避的局面。如《史记·日者列传》载汉武帝取妻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以至于“辩讼不决”。由褚少孙记载的这一汉代故事可知,一个随机的“某日”,便至少有四家日者认为是不吉的。而随着出土《日书》的大量公布,我们对禁忌繁密的现象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王子今曾统计过《日书》中所列行忌凡14种,发现“不可以行”的日数总和超过355天,排除可能重复的行忌,全年行忌日达165日,占全年日数的45.2%以上。除《日书》外,马王堆帛书《出行占》等数术文献也载有众多的行忌之日,足见当时出行禁忌之严苛繁密。当然,若事非紧迫,自然可以等待良辰吉日,加以防范。如杨树达曾注意到,受时日禁忌之说影响,西汉末年以后颇有停丧不葬之风,以至于有留殡至三四百日而始葬者。然而,若遇事急迫,有不可不为、不得不为时,便只能触犯禁忌。这在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的汉代社会,无疑会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造成巨大的压力。

马王堆帛书《出行占》
面对日禁过密造成的困境,秦汉时代的日者已经开始反思、应对。如在遇到有急难之事而“行不得择日”时,往往会采用某种方术进行救禳,以消解灾祸。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简六七贰曰:
禹须臾行不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乡(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曰:“禹有直五横,今利行,行毋(无)咎,为禹前除道。”
关于“行不得择日”,姜守诚解释道:“《禹须臾·行不得择日》篇讨论的就是无法出行择吉情况下的应对措施及防御性手段。准确地说,出行时无法择日或不得已必须在凶日时涉足远行等场合下所进行的禳解方术,是对无法出行择吉情况下的一种变通处理方式,藉此祈求路途平安无虞。”至于具体的救禳方式,则包括走禹步、画四纵五横及相关咒祝语。类似的厌劾方术,又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出邦门》篇:
行到邦门困(阃),禹步三,勉壹步,謼(呼):“皋,敢告曰:某行毋(无)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地,掓其画中央土而怀之。


日本阴阳道文献《小反闭作法并护身法》中的“四纵五横”、“禹步”图及咒文
此外,额济纳汉简亦有相似的方术,简2002ESCSF1:2:“欲急行出邑,禹步三,唬‘皋’,祝曰:‘土五光,今日利以行,行毋死。已辟除道,莫敢義当,狱史、壮者皆道道旁。’”则在“欲急行出邑”时,亦可通过禹步及相关祝语来禳解出行之不利,从而将出行的凶日变为“今日利以行”,最终实现“行毋咎”、“莫敢我当”之目的。不过,相对于秦简,汉简的具体操作方式(特别是祝语)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
此外,又有根据五行相胜理论,在“有行而急,不得须良日”时的救禳方术。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它”部分的简三六三曰:
有行而急,不得须良日,东行越木,南行越火,西行越金,北行越水,毋须良日可也。
陈炫玮认为:“出行者只要在欲行之方向,摆上此方位五行属性之物,然后越过它而行,那么出行即可不待良日而行。”至于具体跨越何物,则难以获知。
除周家台秦简外,相关方术又见于汉简。如北大汉简《六博》篇简二六 “急行,不得须良日,东行”的简文,便保留了该方术的序言及东行部分。额济纳汉简2002ESCSF1:4则有“南方火即急行者越此物行吉”的简文,尚存“南方”部分,足见这一方术在汉代流传范围之广泛。而见于孔家坡汉简《五胜》篇的类似方术,则为我们提供了利用五行相胜从而实现“毋须良日”的另外一种操作方法。《五胜》篇曰:
东方木,金胜木。□铁,长三寸,操,东。南方火,水胜火。以盛水,操,南。北方水,土胜水。操土,北,裹以布。西方金,火胜金。操炭,长三寸,以西,缠以布。欲有□□行操此物不以时。
如陈炫玮所言:“本篇的内容主要是讲述五行相胜之法,其基本结构为凡前往某方时,行者身上必备某物,而此物与所往的方向在五行上属相胜关系。”如欲往东方,由于金胜木,当携“铁”而行,从而可以“不以时”,即不考虑时日禁忌。
总之,在遇到急事而不得不出行,即在“行不得择日”“不得须良日”时,日者可以通过举行某种救禳厌劾仪式,以消除出行遭遇凶日时可能面临的困厄与灾殃,从而在“不须时”“不以时”的情况下,也仍旧能够“无咎”。而日者的这种救禳方法,大概是笃信时日禁忌之人所惯常采用的。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即在遭遇急迫之事时采用厌胜的方法消除凶厄。当然,采用厌胜救禳以解决日禁繁密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并不曾真正质疑时日禁忌的合理性,只不过是日者应对时日禁忌繁密的变通处理,仍不过是“从此一迷信圈,跳入彼一迷信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六博》篇中的“不得须良日”
二、“不问时日”:不拘日禁的士人群体如果说日者在面对时禁过密时采取的措施是厌胜救禳,属于自身对时日禁忌之术的某种改良与完善的话。那么,同样是面对时禁过密,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时日禁忌的合理性了。就目前文献所见而言,这种质疑大概在墨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据《墨子·贵义》篇载: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墨子·贵义》,明嘉靖三十一年芝城铜活字蓝印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按照日者之说,甲乙日不可东,丙丁日不可南,庚辛日不可西,壬癸日不可北,从而造成禁锢天下之行者的局面。墨子认为这是“围心而虚天下”,故不用日者之言,直接抛弃了时日禁忌之说。尤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提出的“围心”说。所谓“围心”,吴玉搢曰:“围心即违心,古围、违字通”,即违背“心”而遵从日禁,这显然是王充“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之说的远源。所谓“考于心”,又见于《对作篇》:“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徐复观认为:“考之以心,是心知的合理思考、判断。若傅会一点地说,这是合理主义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的行为、判断,首先应该求之于“心”,而不是“围心”去依从时日禁忌。新近公布的周家寨汉简《日书》,则为我们理解墨子、王充之说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简七八曰:“天固不建龙日,毋央罚。人者以□自置龙日,□之所央者有矣,心之所忌者因有忌矣。”整理者解释道:“所谓龙日(忌日),不过是人们心有所忌,自行设置的忌讳,不信也罢。”因此,“忌日”的生发,乃是出于“心之所忌”,而并非天道自然。而“心之所忌”,便是未曾“考于心”而“围心”了。由此看来,当时已有士人与日者认为,时日禁忌既非天理自然,本身也不会带来祸殃。而之所以有忌日者,乃是人内心自我设立之禁忌,即“心之所忌者因有忌矣”。也就是说,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自然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从而可以不拘时禁。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作用下,或者基于共通的理念,汉代出现了很多“不问时日”的士人。如《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载刘君阳之事曰:“《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闘争。按:刘君阳为南阳牧,尝上朔设盛馔,了无闘者。”《论衡·辨祟》篇亦有“上朔不会客”之说,《协纪辨方书》引《堪舆经》则曰:“上朔日忌宴会。”则“上朔”为会客、宴会之忌日,且又能引起争斗。然而,刘君阳于上朔设宴,最后却并无凶咎,这一事例遂成为应劭否定时日禁忌的正面例证。相似的事迹,又见于《后汉书·郭陈列传》: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乃子诉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

《后汉书·郭陈列传》,北宋刻递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葬日是秦汉时期尤为重要的时日选择类目。根据刘增贵对传世文献、碑刻文献所载死日、葬日的考察,发现“其与《日书》虽然不能说完全符合,但大体合辙,只是遵从者或多或少、采取的禁忌各不相同而已”,由此益可知“《日书》之类的数术书提及的时日禁忌,在当时的确被广泛使用”。然而,吴雄母亲去世后,却“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当时的巫者都认为犯此大忌,恐当族灭。但吴雄一族的命运却恰与巫者之预言相反,“三世廷尉,为法名家”。吴雄的故事,也被视作“不问时日”的典范而受到后人称赞。实际上,在东汉时期流行的薄葬论思想背景影响之下,不遵从葬日的例证尤多。如赵咨欲行薄葬,即遗书敕其子胤曰:“勿卜时日,葬无设奠。”赵岐死前亦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即日便下,下讫便掩。”范冉亦“临命遗令敕其子曰:‘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所谓“即日便下”“气绝便敛”,与“不问时日”“勿卜时日”一样,都是不拘日禁的表现。
与吴雄“不问时日”一事类似的,还有《意林》引《风俗通义·释忌》篇所载“五月到官”事: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今年有茂才除萧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视事五月,四府所表,迁武陵令。余为营陵令,正触太岁,主余东北上,余不从,在事五月,迁太山守。
依据俗谚,若五月到官上任,会对仕途产生消极的影响。而《风俗通》所载五月到官之茂才,很快就由萧令迁为武陵令。实际上,这位茂才除了五月到官之外,还在“破日入舍”。“破日”为建除十二辰之一,据孔家坡汉简《日书》,破日为凶日,“毋可以有为”,则这位茂才所犯日禁颇多,却对其仕途毫无影响。
此外,应劭亦以自己“触犯太岁”,最后却迁为太山守一事作为佐证,足见应劭亦是“不问时日”的。
与吴雄、应劭这种“不问时日”而有美好结局者相反,后汉桓帝时期的陈伯敬则是遵循时日禁忌却反而命途多舛的典型。其事亦见《后汉书·郭陈列传》:
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
《风俗通》之佚文亦有“汝南陈伯敬,行必矩步,坐必俨然,目有所见,不食其肉”之语,可见陈伯敬行动必合乎规矩,举凡一切禁忌皆避之。为了严格遵守“归忌”日,以至于留宿乡亭,暂不归家。然而,与不问时日的吴雄等人相比,严格遵循禁忌的陈伯敬却没有好的下场,至老只博取了个孝廉的功名,最后还坐罪被杀。以往的讨论者往往将陈伯敬视为汉人之典型,但从“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的叙述来看,当时不拘时日禁忌者,恐怕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而以陈伯敬作为反证,无疑能够进一步坚定这些“罔忌禁者”“不问时日”的信念。
类似的例证,又有张竦避“反支”一事。《汉书•游侠传》:“竦为贼兵所杀。”颜师古注引李奇曰:“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与陈伯敬遵守“归忌”相似,张竦所遵者为“反支”,但并没有躲避凶祸,反而被杀身亡,从而被桓谭批评为“通人之蔽”。
大体而言,吴雄、茂才、应劭之事迹可以概括为“触忌而获福”,而陈伯敬、张竦则是典型的“择日而得祸”,这显然与民众追求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的目的相反。这种反证,无疑会对汉人的信仰世界产生某种震动。面对“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终凶”这些书于史册的凿凿事例,热衷于数术之学的颜之推也只能给出“拘而多忌,亦无益也”的结论。总之,东汉时期,“不拘日禁”大概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流行的观念,且至少已经影响着一批开明的士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倡与表彰。如对于赵咨“勿卜时日”的行为,时人已有“明达”的称誉。由此益可知,东汉“时人”对“不问时日”“不拘日禁”的士人,是持赞许态度的。
三、人事:儒家传统的“吉人”“凶人”与“吉日”“凶日”迫于情势之紧急而“不得择日”时日者采用厌胜救禳仪式,说明当事者本身仍旧是信仰时日禁忌的。而“不问时日”“罔忌禁”的士人,则开始进行理论反思,强调“考于心”而不“围心”,遂能够基于自己的理性判断,从而做到“不问时日”。在这两种处理时日禁忌的态度之外,又有一种强调“人事”作用的观点。卢藏用《析滞论》曾提出:“昔者,甲子兴师,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异制胜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济。”“人事苟修,何往不济”的态度,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时日吉凶的理论基础,认为“人”自身才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种观念,在秦汉时期的《日书》中就已经存在了。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稷辰》篇曰:
正阳,是胃(谓)滋昌,小事果成,大事又(有)庆,他毋(无)小大尽吉。利为啬夫,是胃(谓)三昌。时以战,命胃(谓)三胜。以祠,吉。有为也,美恶自成。生子,吉。可葬貍(埋)。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为也,美恶自成”一句。王子今认为,所谓“自成”之“自”,当指《日书》使用者自身。《日书》作为问吉凶宜忌的择日之书,竟然有强调“自成”的辞句,是值得注意的。而能够“美恶自成”的关键,乃在于“有为”,即尽“人事”。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周家寨汉简《日书》中的两段思辨性文字,在时日禁忌信仰中引入了“吉人”“凶人”的概念:
凡人固有吉凶,吉人昜(易)为日,凶人不可为日,吉人举事抵凶日,而其事多利。
故人有善日不善日。为吉人,日则善日矣;为凶人,则不善日矣。
整理者认为:“以上简文大意是人自有善恶,与日子吉凶无关,为善者好择日,为不善者难择日。好人举事即使撞上了凶日,事情照样顺利。”在整理者看来,“吉人”为为善之人,“凶人”则为为恶之人,“吉人”“凶人”本身才是决定时日吉凶的根本。这种观念,与儒家传统的“吉人”“凶人”之说相符。
吉人、凶人,最早见于《尚书•泰誓》:“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孔安国注曰:“言吉人竭日以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恶。”其所谓吉人,乃是为善之人;凶人,则是行恶之人。而在荀子看来,吉人、凶人又可以与君子、小人相对应。《荀子•非相》篇曰:
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
冯友兰认为:“这里所说的术,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他在行为上所走的道路。一个人如果选择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正确的道路,这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人;善人也是吉人。至于形象是个什么样子,那是无关重要的。”以相术而论,决定吉凶的并不在于长短、大小等等“形相”,更重要的乃在于“心”和“术”。若心术为善,即便形相恶,亦可以为君子;若心术为恶,即便形相善,仍旧不过是小人。而君子则吉,小人则凶。由此,君子即是所谓吉人,小人则为凶人。
而在论相术的其他文献中,也有与《荀子》近似的说法。据《吕氏春秋•贵当》篇载: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观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荣矣,所谓吉人也。观事君者也,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臣也。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证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庄王善之,于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荆楚之善相人者,其相术也不是观人之相貌,而是观人之友。其友若皆品行纯良孝善,则可谓之吉人。相应地,则有所谓吉臣、吉主。实际上,观人之友,亦不过是根据“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之法则,相人之善恶而已。
由此可见,在儒家语境下,吉人、凶人才是决定吉日、凶日之关键,而吉人、凶人的确定,则在于为善、为恶,是基于道德层面的判定。为善则为吉人,为恶则为凶人。故若“有为”、“人事苟修”、“竭日以为善”,则会无往不利。正如周家寨汉简《日书》所言:“吉人举事抵凶日,而其事多利”,此即所谓“吉人自有天相”。而这种强调“人”的主动精神的做法,正是自董仲舒以来“用儒家仁义学说和积极作为的观念改变了阴阳家使人处于过分拘谨服从的被动状况” 的做法,是儒家对于“使人拘而多畏”的阴阳家的改造与超越。至此,时日丧失了决定吉凶的主导地位,时日禁忌之术的理论根基亦就此消解。
四、命运:王充的宿命论及其对时日禁忌的批判东汉时期,曾兴起过一批相对于正统儒家而言的“异端”思想家。我们发现,这些思想家对于时日禁忌之说,皆持反对之意见。如前文所引应劭《风俗通义·释忌》篇,即搜罗了不少“不问时日”的士人事迹。又如前引《新论·识通》篇,桓谭亦以“通人之蔽”来批评张竦拘泥于“反支”这一日禁之事。此外,桓谭在《新论》一书中还对王莽“信时日”一事有所批评,认为“不可称道”。而对时日禁忌批判最多且最为系统的,则属王充。作为“疾虚妄”的一部分,王充对汉代社会所流行的时日禁忌深恶痛绝,并撰有《讥日》《辨祟》《难岁》等专篇加以批判。在这些篇章中,王充讥讽信仰日禁者为“俗人” “世俗之人” “俗儒”,并将信仰禁忌之世称作“衰世”,好求福祉之君为“不肖君”,足见其对时日禁忌之术的鄙夷。然而,正如王充之人格与思想充满着矛盾与混乱一样,其对时日禁忌的批评亦杂乱而充满矛盾,且终究无法逃脱宿命论之束缚。
(一)王充对时日禁忌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王充对日禁之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讥日》篇中,尤其是着重批判了“葬历”“沐书”“裁衣之书”“工技之书”等等“日禁之书”。关于这一点,前人多有评述,也曾总结归纳过王充所使用的论辩方法,并认为王充对禁忌的批评“内容之详尽,批评之透彻,均属前所未有” 。然而,尽管王充的识见已经远远超出了时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由于王充知识结构及逻辑思维存在某种缺陷,这些讥讽之言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从而造成了王充“疾虚妄”的低效率问题。
比如,王充运用“验之于古”的方法,考察了春秋时期的葬日,从而得出春秋时期“无葬历法”的结论,并据此否定择取葬日的合理性。他论辩道:
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刚柔;刚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合于葬历,验之于吉〈古〉,无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天子、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数,案其葬日,未必合于历。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鲁小君以刚日死,至葬日己丑,刚柔等矣。刚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当以雨之故,废而不用也。何则?雨不便事耳,不用刚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鲁人之意,臣子重慎之义也。今废刚柔,待庚寅日中,以旸为吉也……然而葬埋之日,不见所讳,无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备具,孔子意密,《春秋》义纤,如废吉得凶,妄举触祸,宜有微文小义,贬讥之辞。今不见其义,无葬历法也。
所谓“日之刚柔”,即指刚日、柔日,又称作男日、女日、牡日、牝日。按照秦汉简《日书》中的规定,子、寅、卯、巳、酉、戌为刚日,丑、辰、申、午、未、亥为柔日。就葬日而言,《日书》规定:“牡日死必以牝日葬,牝日死必以牡日葬。不然,必复之。”“以女子日死,死以葬,必复之。男子亦如是。”足见葬日需讲究刚柔相合,否则会有凶咎。王充认为,若求证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的葬日,发现并不合于葬历。为此,他举出了鲁小君本当己丑(柔日)葬,却为了避雨而改为“庚寅”(刚日)葬这一例证。并认为,当时只是以晴天为吉,并不讲求刚柔日相合。于是,王充得出了“葬埋之日,不见所讳,无忌之故也”、“无葬历法也”的结论。然而,王充用汉代的葬历考察春秋时期实际葬日这种“验之于古”的方法,却是存在问题的。时代在更替,数术方法本身也在演变。即以葬日而言,春秋时期的“葬历”是以“柔日”为吉的。顾炎武指出:“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这正说明春秋时期是恪守“葬历”的;偶有例外者,也不过是因为遇到特殊情况而不得不从权处理。只是与秦汉不同,春秋时期的“葬历”并不讲求“奇偶相合”,而是单纯的以“柔日”为吉,故所卜葬日皆为柔日。由此来看,王充认为春秋时期“葬埋之日,不见所讳,无忌之故也”的结论,显然要大打折扣了。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他否定汉代的“葬历”。
此外,对日禁事项设置的合理性,王充也提出了质疑。如对于“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之说,王充论辩道:
夫衣与食俱辅人体,食辅其内,衣卫其外。饮食不择日,制衣避忌日,岂以衣为于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衣服,货也。如以加之于形为尊重,在身之物,莫大于冠。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是于尊者略,卑者详也。
王充认为,既然裁衣有禁,那么与之类似,且又更为急切、尊崇的饮食、造冠何以不设禁忌?在这里,王充虽然引证了《尚书·洪范》之“八政”,又强调了等级尊卑之说,但其论述仍旧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如“人道所重”之“饮食”,本是百姓日用之需,一日两餐,不可断绝,本就不存在“选择”之可能,这显然不属于“选择术”之范畴。至于王充所谓“造冠无禁”,则又显示了他对“日者之术”的掌握是不全面的。据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凡初冠,必以五月庚午,吉。凡制车及冠……申,吉。”这里的“制冠”便是“造冠”,由于简文残缺,“制冠”可能是以“申”日为吉。由此可见,日者对于“造冠”,亦是设置有禁忌的。实际上,针对日禁事项设置的缺陷,日者是可以修补完善的。如王充曾在《讥日》篇中质疑“沐日”的合理性,他认为,既然沐、洗、盥、浴都是洁净身体,就不当独为沐设置日禁而不及洗、盥、浴。而在清人所编《协纪辨方书》中,“民用三十七事”即有“沐浴”一项,这自然可以回应王充的质疑。
王充将某些日禁归结为礼法上的需要的做法,颇值得重视。《论衡•讥日》篇曰:
礼不以子、卯举乐,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书,子、卯日举乐,未必有祸,重先王之亡日,悽怆感动,不忍以举事也。忌日之法,蓋丙与子、卯之类也,殆有所讳,未必有凶祸也。
《礼记·檀弓下》亦曰“子卯不乐”,郑玄注曰:“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所以自戒惧。” 郑玄认为子、卯为“疾日”,当本自《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之说,杜预注曰:“疾,恶也。纣以甲子丧,桀以乙卯亡,故国君以为忌日。” 疾日即恶日、凶日。王充认为,作为忌日的子、卯“未必有凶祸”,只是因为这是“先王之亡日”,故为后人所重,不免“悽怆感动”,以至于“不忍以举事”。由此看来,王充将子、卯视作了某种纪念日,这与先人卒日之“忌日”相同,自然应当禁止举乐了。通过追溯忌日之渊源,并将这一忌日的形成归结为礼法上的需要,王充将忌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否定了。而这种方法,无疑是值得认可的,甚至与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路径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问题是,作为凶日的子、卯并非源自纣、桀之亡日。
纣亡于甲子虽见载于《史记·殷本纪》,而桀亡于乙卯却不见诸史籍。据此,黄晖认为:“桀亡非乙卯,则子卯之忌,不因桀、纣。”而随着近年来数术原理研究的推进,《日书》等数术文献中的时日禁忌,大都是根据阴阳五行、干支之间所存在的相生相克等关系生成的,而不是基于后人附会的历史典故。所谓“子卯不乐”,实源自子卯相刑之说。《汉书》载翼奉所上封事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张晏注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为忌。”翼奉、张晏之说,皆本自汉代流行的刑德之术。自马王堆帛书的三种《刑德》公布之后,太阴刑德术的数术原理已经十分明晰。具体而言,即当太阴在子时,刑在卯;相应地,当太阴在卯时,刑在子,即所谓“子刑卯,卯刑子”。子为水,在北方,即北方之情;卯为木,在东方,即东方之情。东方、北方之情为“好”“怒”,“好行贪狼”“怒行阴贼”,二者并行,故谓之“二阴并行”,以故王者忌子卯日。这种从刑德术的原理来推测子卯为忌日的做法,显然更为合理。因此,尽管王充对于子、卯之忌的解释十分通达,但若追根究底,王充对这一“忌日”“未必有凶祸”的判定,仍有一定的缺陷。

马王堆帛书《太阴刑德大游图》
(二)吉人、凶人:王充的宿命论及其对时日禁忌观念的消解
由于王充在《讥日》篇的具体辩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而尚未能彻底否定汉代的时日禁忌观念。不过,从王充的宿命论出发,却可以从根本上对时日禁忌的合理性进行消解。作为区别于正统儒家的“异端”,王充对于吉人、凶人的看法亦与儒家主流不同。在讨论卜法、蓍法时,王充提到了所谓的吉人、凶人。《论衡•指瑞》篇曰:
王者以天下为家。家人将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见于人。知者占之,则知吉凶将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为吉凶之人来也。犹蓍龟之有兆数矣。龟兆蓍数,常有吉凶,吉人卜筮与吉相遇,凶人与凶相逢,非蓍龟神灵,知人吉凶,出兆见数以告之也。虚居卜筮,前无过客,犹得吉凶。然则天地之间,常有吉凶,吉凶之物来至,自当与吉凶之人相逢遇矣。
王充的核心思想在“逢遇”二字。他认为,吉人卜筮,则与吉相遇;凶人卜筮,则与凶相逢。而这里的“遇”“逢”,实际上是《论衡》一书反复论述的宿命观。《逢遇》篇云:“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由此可见,王充的“遇”“逢”,是一种极为偶然的状态,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不与任何事物发生关联。吉、凶与吉人、凶人之相逢遇,亦是如此。在《卜筮》篇中,他又论述道:
然则卜筮亦必有吉凶。论者或谓随人善恶之行也,犹瑞应应善而至,灾异随恶而到。治之善恶,善恶所致也,疑非天地故应之也。吉人钻龟,辄从善兆;凶人揲蓍,辄得逆数。何以明之?纣,至恶之君也,当时灾异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贤者不举,大龟不兆,灾变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龙兴,天人并佑,奇怪既多,丰、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体,所致无不良;凶人之起,所招无不丑。
在王充看来,吉凶并不是像一般论者所说的“随人善恶之行”,只不过应吉人、凶人而至罢了。而所谓吉人、凶人,则是由运命注定而成的。《命禄》篇即认为:“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命,有盛衰之禄,重以遭遇幸偶之逢。”则吉凶之人,不过是运命安排,与善恶无关。故而《卜筮》篇又云:“实遭遇所得,非善恶所致也。善则逢吉,恶则遇凶,天道自然,非为人也。”即排除了“人”在面对吉凶时的任何作用,从而归结为彻底的宿命论了。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因王充……没有人伦道德的要求……连由行为善恶所招致的吉凶祸福的因果关系亦加以推翻了。”因此之故,王充乃“剥夺了人一切的主体性,一听此机械而又偶然的命运的宰割”。马克亦指出:“生命的指引、道德品性、智力和才干依赖于自然秉性,它们对于遗传的宿命不起作用,宿命使个人成为他们本来的样子。”显然,这与儒家传统强调“人事”(也就是为善、为恶)对于吉凶的决定性作用正好相反。而讽刺的是,一旦陷入到了宿命论之中,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反而被彻底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根基亦由此而推翻。故王充又引《论语》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苟有时日,诚有祸祟,圣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说?”则其宿命论之根基,反而又建筑在圣人的言论基础上了。

《论衡·卜筮》
基于王充宿命论之下的吉人、凶人之说,我们或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理解周家寨汉简《日书》中的吉人、凶人与吉日、凶日。如简六所言,“凡人固有吉凶”,则吉凶是人生来所固有者。在这里,我们似乎并不能够找到“为善”“为恶”的道德因素,亦无法发现“有为”“人事”在其中的作用。简四又曰:“故人有善日不善日。为吉人,日则善日矣;为凶人,则不善日矣。”则善日、不善日,与吉人、凶人是固定相配,这与王充“故吉人之体,所致无不良;凶人之起,所招无不丑”是大致相同的。周家寨汉简《日书》简四又曰:“吉人举事抵凶日,而其事多利。”王充《论衡•初禀》篇则曰:“吉人举事,无不利者。”二者也十分契合。由此而言,王充虽然一直在反对“日禁之书”,但其关于吉人、凶人的观念,又可从早期《日书》中找到某种渊源。或者,在王充所读“日禁之书”中,亦有与周家寨汉简《日书》相近之内容,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触发了王充之思想。
当然,王充对于时日吉凶的否定,是可以直接由其宿命论所导出的。既然人之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人力丝毫不能改变之”,则显然无法通过选择时日来“趋吉避凶”,以此改变已经确定了的命运。至于其命运观之形成,则又与其“仕数不遇”“涉世落魄”的人生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于对命运的无助,王充一并连时日信仰这一精神慰藉也取消掉了。
结语时日禁忌观念的形成,源自于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而得出的农事节律,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在讨论阴阳家的时令思想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即云:“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则四时八位等节令,是不可不顺的。比如错过农时,便会影响一年之收成,故而“时间”确然蕴藏着吉凶祸福。然而,时禁太多,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亦使“人”本身的作用降低,故《汉书·艺文志》又云:“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寖以相乱。”因此,汉代的知识分子才会一再地强调人事的作用。
实际上,从睡虎地秦简《日书》“有为也,美恶自成”的文字来看,秦汉时代的日者也在强调人事的作用,这与时日禁忌本身的逻辑并非完全矛盾。如蒲慕州所言:“一切吉凶之事都和时日有相互对应的关系,而且这关系是可以为人所明知的……既然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神密可言的世界,人所要作的只是遵循《日书》中的指示,即可趋吉避凶。”由此可知,时日禁忌术“不是一种完全的命定论。人对于自己的命运仍有一定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便体现在人们可以通过《日书》提供的简明指导以“选择”时日,从而达到趋吉避凶之目的。因此,从人可以“选择”的角度来看,仍旧在强调“人”的自主性。
当然,人生之遭际逢遇、祸福吉凶,又并非自身所能够全部决定的;而即便求诸时日选择,也往往有着“讨求无验”的结果。因此,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整个社会,个人的能力往往十分有限,故常陷入被动之中。宿命论之观念,即由此而兴。王充藉由宿命论来否定时日选择,无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人对于吉凶祸福的掌控,而将人生全部交由渺渺难测之命运。
而在现实人生之中,无论是强调人事还是命运,都容易陷入困境。因此,王符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潜夫论·巫列》曰:“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行者,己之质也;命者,天之制也。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在王符看来,人之吉凶还是应当以“行”为主,取决于自己的事物,人是能够决定的;同时,由上天所宰制的命运,则非人力所能及,只能听天由命,即所谓“尽人事,听天命”。而这恐怕也是汉代社会所能形成的最为通达的吉凶观念了。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