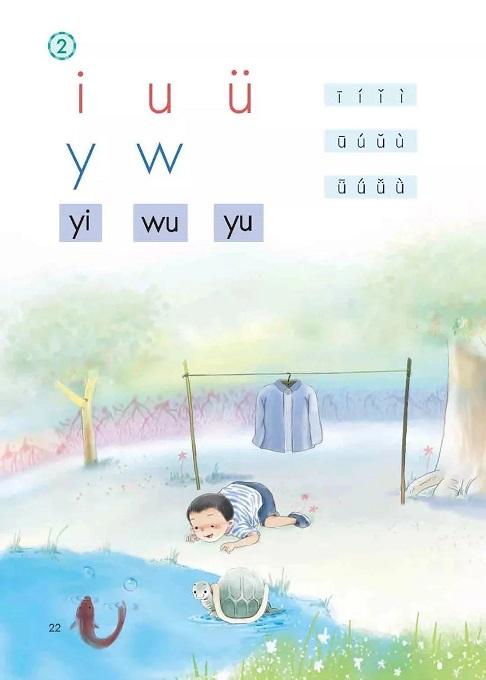三分钟看懂土耳其历史(土耳其一次流产的改革实验)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而言
彼时奥斯曼土耳其的宪制改革
过于早熟了
而对于擅长动员人们的情感
和记忆资源的民族国家来说
它又过于老派和温吞水了

说起土耳其改革与革命,人们习惯于把时光聚焦在1840年代开始的坦齐马特改革,以及“一战”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的改革与革命。而《帝国的伙伴》则把读者的视角拉回到18、19世纪之交,延展和丰富了人们关于土耳其自救求存的认知视界。比如帝国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建立新军以取代不堪大用又尾大不掉的禁卫军等诸多剧目,早在19世纪初即已上演。而作者的土耳其人身份,对土耳其文献的使用,则更凸显了“在土耳其内部发现历史”的说服力,以此来彰显所谓去西方中心论的论述方式。

不过,去西方中心论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视角。相反,本书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将18、19世纪之交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危机及其应对,纳入到当时全球范围的治理危机浪潮中,从而使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的那场改革与革命拥有了更多的全球史意义。奥斯曼土耳其当时面临的危机确实有其具体的国际语境:沙俄和奥地利的进逼令其腾挪空间日益逼仄,既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也渐显左支右绌之局。这是奥斯曼土耳其追求构建新秩序的主要外因。而在构建新秩序的过程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奥斯曼土耳其或借力于外国势力,或被外部势力所掣肘,这些都凸显了改革和革命的国际语境与国际推手。
既有的格局与秩序难以为继,变革图新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既有利益格局的搅动,都必然会带来各种反弹。不过反弹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那些预期自身利益会受损的群体,自然会致力于破坏和颠覆构建新秩序的努力,而那些预期新秩序对自身利益有所增益的群体,则更倾向于火中取栗襄助新秩序,并引导其向有利于自己群体的方向演进。
除了利益之争,令情势更为复杂的是,新秩序应为何种模样,各个利益群体并无共识,也很难有共识。对中央而言,自然是广辟财源,将各种利、权集中到中央手里为要。手中有钱有权,才能建立并扩充新军,一来提升应对外寇的效能,二来取代不堪大用而又尾大不掉屡有不臣之举的禁卫军,三来震慑日渐坐大并渐有离异之心的地方显贵。这种秩序被作者称为帝国的秩序。
这当然是中央的一厢情愿。地方显贵和中央层面的重臣中,都有不乐见中央集权、断了自己财路和独立性的人士,他们不反对提升国力和帝国的威望,但希望通过地方与中央“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式来构建新秩序,并在此过程中捍卫、增进自身的既得利益。这种愿景被作者称为显要的秩序。
而改革矛头所指的禁卫军和作为新增税收主要担当者的平民及商贩等群体,自然对改革怀恨在心,前者更是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来发动一次又一次针对改革和前两种秩序构建的抗争。他们所构想的通过集体推举的领袖来管理公共财政的愿景,被作者称为社群的秩序。
秩序之争与利益之争相交织,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大戏便徐徐展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路人马怀着不同的秩序构想和利益预期展开了一场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合纵连横与抗争博弈。如果化繁就简的话,主要的剧目是这样的:一开始禁卫军和地方显贵都反对中央层面的改革,后来地方显贵发现可以借反禁卫军作乱为自己开辟新局,便以勤王的名义控制中枢,并与中央达成共襄改革利益互保的协议。但这种散发着宪制气息的新秩序,随着关键外省显要的失势很快就被颠覆,禁卫军的地位得以复原,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然而显要秩序的挫败,并不意味着社群秩序的坐大。借禁卫军上位的新苏丹隐忍未久,便发动了坦齐马特改革,而且为了破除再建中央集权秩序的阻力,首先把屠刀挥向了已成为帝国大患的禁卫军,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层面的军事异己势力,为后续的诸多改革打开了一片天地。
历史似乎从来都是更多属于胜利者的。但在历史的种种尘埃落定之前,其实历史曾经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发现历史“规律”更为有趣的,是回到历史现场检视其丰富多元的可能性,以及背后的诸多推手和博弈。
这种回视会拓宽人们对历史的认知,避免黑白分明的判断。具体到本书涵盖的时段,各群体间的冲突就远非改革与反改革的理念之争,而更多是利益之争。反对改革者未必就是反动派,赞成改革者未必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至于屡屡互为奥援的禁卫军、宗教团体和平民百姓,虽然左打皇权右诛显贵,也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更多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民粹派,虽然可以自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显然代表不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正确的历史方向。
同样复杂的画面在大清国的最后时光中也曾经出现。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作者周锡瑞同样刻画了朝廷、地方缙绅阶层和平头百姓围绕清末改良与革命的种种博弈,并一改往昔人们对改良派缙绅阶层的正面看法,认为他们一方面从中央推动的改革中上下其手多方渔利,且不吝于将诸多改革举措的沉重成本转嫁到农民和贩夫走卒等平民阶层身上,一方面又窃取后者因不堪忍受种种剥夺发动起义的成果,借机在与日益虚弱的清廷的博弈中占取先机。
总的来说,18、19世纪之交的奥斯曼土耳其宪制改革更多是一场早熟的重构央地关系的实验,其观念资源还是囿于皇朝政治、伊斯兰共同体等比较前现代的范畴。重读这段历史,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知和检视东南欧历史沿革和巴尔干问题由来的机会。在此次传统观念范畴内重构央地关系的努力夭折后,走现代意义上包容性宪制之路的改革后来也推出过几次,最后因为内外情势交困都未得善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的步伐此时已经远远滞后于沛然莫之能御的民族国家的勃兴,相对于需要精巧设计和复杂博弈的兼顾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利益的多民族联邦制,构建民族国家显然更能同时满足地方领导人的雄心和在地族群对自由的热望。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而言,彼时的宪制改革过于早熟了;而对于擅长动员人们的情感和记忆资源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又过于老派和温吞水了。包容性宪制之路既已不通,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带来的内外压力下分崩离析也是应然的结局。这不是一个帝国的失败,落入此命运陷阱的还有和它缠斗多年的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在其中一些地方,人们仍能听见失败帝国冗长的历史余音。
作者苏琦,授权转载自公号中国新闻周刊

18世纪和19世纪初,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包括落入转型危机的奥斯曼帝国。为应对政治动荡、体制危机和民众叛乱,奥斯曼帝国设计了各种改革方案。帝国成了一个政治剧场,其中各种政治行动者发起了斗争、合作和竞争。
本书研究了三种相互竞争的秩序,“帝国的新秩序”“显要的秩序”和“ 社群的秩序”,或者说集权–官僚的、分权–契约的、参与–民主的。为了解决危机而签订的《同盟誓约》则意味着奥斯曼历史中的一种激进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探索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放大了过去被忽略的地方政治文化实践,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