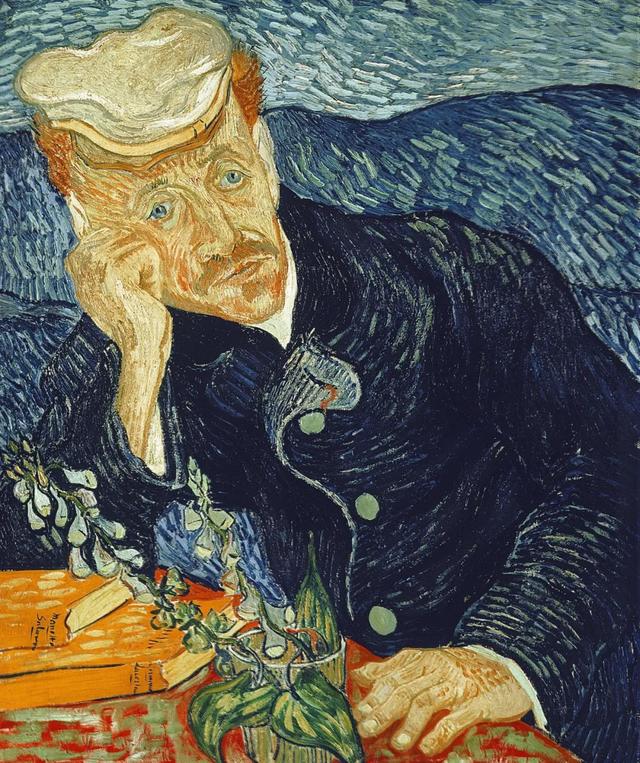请人吃饭不能三个菜(一顿乡宴三段怪谈)


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山谷里面花开花落,没有人看见它们,那它们白开花、白落;因为它不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 许倬云

「院落里鸟拉的屎都是靛青色的,桑葚遭殃!」
汪婆斜睨着眼,指着溪边街石桥对面竹林角落的那片空地,「喏,就是那里歪,都被气套了(吃掉了)。」她与我讲话,操着蹩脚的普通话,最后实在没忍住,落出几句土话来。那头一株桑树,不知是谁家的,通常没人会把桑树圈在庭院,觉得「桑」同「丧」,忌讳得很。汪婆不管,树长在自家门口,她不舍得砍。鸟雀更不管,起头是一两只来吃,第二天就是四五只、六七只,绿豆鸟来,戴胜鸟来,绶带鸟也来,成群结队,呼朋唤友,妻妾成群。

上个世纪末,因瓷器资源匮乏,徽州地区的人们在购置瓷碗后,会请专人在碗底刻字,方便相借、归还。
「沃滴很(坏得很)!体们(它们)一定是说好哩滴!」她一说话,戒指在她绛紫色刺绣马甲的映衬下抖落出暗银色的光,似乎在跟叶下的桑葚果儿们比较着光泽。
「你听,滑儿,滑儿,滑儿叫的,是绿豆,聪明,吃枇杷,钻掉一圈,只留籽和柄挂树上。吃樱桃,吐一地的籽,还把籽嗑开,吃里头的肉。戴胜更沃,好好的桃儿,就吃熟的那半边,一棵树全给我气套了。」最后这几个字她咬得恶狠狠的,仿佛所有闻风而来的鸟都是她的仇敌。
「体们也晓滴吃落昏 [注:在徽州话中,吃落昏是吃晚饭的意思。],太阳公公要落山,就来吃晚饭咯。」果树里是不一般的热闹,数群鸟雀从不同方向赶来落席。噼里啪啦,半树樱桃籽嗑完;窸窸窣窣,一群白头翁占领了半片出墙的枇杷;最后,它们朝桑葚而去,只有这里无人用竹竿支起塑料袋和稻草人,任它们风卷。
她手里的罗边碗已是盛了第二碗白粥,七十五岁,食量不减,门口石阶上垫一块白蚁蛀过的残木,往那儿一坐,用一双竹筷往嘴里赶粥,吃到最后碗底见一个「竹」字,那是她名里的单字。
乌昏中,远处枫杨林的绿影像在化脓,顺着树干缓缓流腻进河里。空气里兰芷草的香味飘浮在河面上层,在日光明灭交替时与水雾一道往上走,穿过苔藓、绣球、芍药、君子兰那些低浅贴地的花草,困住行人的脚。香味不从这些花里来,抬头才见出处。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广玉兰已成参天之势,花朵有碗口大,钝重如瓷的花瓣落在草窠里,怀着一汪水,身上有一些褐色的折痕,像用旧了的瓷碗。

徽州宴席通常在黄昏时举办,摆放于院落中,一般规格为八碗八碟。
「婆,罗边碗有没有?婆,莲花碗有没有?婆,葵花碗有没有?」我恬不知耻地朝她问,看了看挂在墙上那几幅黑白相片中的人影儿,又不忘添上一句:「婆年轻时候漂亮,一定是溪边街上一枝花吧。」
「咹,是有人夸我漂亮呐,我去跟你寻碗。」她不问缘由,哼着《天涯歌女》的调子转身就往厨房走。六点来钟,不开灯,在黑暗的灰尘里摸索,橱柜下层的木栅里碗叠着碗,她掏出四只硕大的葵花碗,「喏,拿好。」接着又转头摸索,「啊呀,莲花碗米有哩(没有了),不好意思,对不住 。」
我被她的一句「对不住」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讪讪地不知道回些什么。这是一个会给陌生人打水洗脚的女人 —— 一次一个外来摄影师在村里采风,暴雨如注,躲在汪婆的屋檐下,浑身湿答答的。汪婆拉她进来,说「紧啦侧,紧啦侧(进来坐,进来坐)」。人家听不懂,还是被她拉在木凳子上坐下。汪婆拿出一捧直掉渣的冻米糖,互相推辞,最后被讪讪地收下。汪婆拖着缓慢的步子去屋外天井的煤炉上「呜呜呜」烧开一壶水倒进搪瓷盆里,又掺了点井水,给人家端去,这回人家更难为情了,「不要紧,内内脚(热热脚)。」汪婆放在人家脚底,人家不好推辞,脱下鞋袜,汪婆又把湿鞋袜放到煤炉边上烘烤。
这不过是前两月倒春寒时候的事,雨停后那人走出屋子去街边与年轻人说,热脚的时候要落泪。
我还是讪讪地站在那里说:「没关系,没关系,多谢,多谢。」
她一低头向前探着,那眼神仿佛在看鸟吃桑葚,要看穿我的魂:「不要倒套了!你考,界个地佛系你个个倒嘞滴壳子(不要打掉了,你看,这个地方是你哥哥打掉的口子)。”
用了二十年的碗,一个裂口都记恨在心,真是个计较的阿婆!

青姨一只手拽着风干猪头耳朵的根部,一边说:「看!多漂亮的猪头。」
那猪温顺地闭上了眼,是双眼皮,睫毛长长的,嘴角向上翘起,微笑着,脸上的皱褶也不妨碍它的美妙。
「猪耳,切片用老酒蒸一蒸,咬起来咯吱咯吱的,香!」「猪舌,切片蘸酱油醋,有韧劲,香!」「猪鼻囱, 切丁蘸辣椒酱,弹弹的,香!」「猪头肉,肥的部分半透明、亮晶晶,下酒,香!」
一只猪头,她如数家珍,仿若世间挚爱。而在每一个厨娘叱咤风云、掌握厨房生杀大事之前,都是一个姑娘,提不动猪头,也欣赏不了它的美。

如今村中居住多位老人,七八十岁,身体依然康健,每日自己下地劳作种菜。
在青姨还是青姑娘时,每日在溪边打水洗菜,一身蓝布衣,两个麻花辫,路过的青年经过风雨桥都会驻足坐在木椅上与她谈心。「阿青,上我的车带你买发卡。」「阿青,中街新开了一家馄饨铺,我带你去。」青姑娘不应,只是低头洗菜,心中早有自己相好的人,不日便置办喜宴,请来「裱画先生」写了大大的喜字贴在门上,又画了两只相好的野鸭贴在床头。
磨难在后头。生孩子那夜,青姑娘在手术台上耗尽了三个小时,最后生下一个不哭不闹的婴儿。没听见哭啼,她脑袋嗡地一下,自己就先哭了。
「救救她。」
产科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其他人还在愣神,她已经迅速擦拭完婴儿,一遍遍进行着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10 分钟后,手术室里更安静了,20 分钟后,旁边的护士已经在慢慢收拾东西,大夫说:「再救一会儿,再救一会儿。」一下下按下去,一口口吐进空气。在按压了 30 多分钟后,她感觉到微弱的气流呼到她的脸上,「回来了。」她对旁人说。
医生的睫毛上都是一层汗珠,脸上的毛细血管洇开一片绯红,青姑娘哭得更厉害了。

老式木制橱柜有自己的逻辑,上层放置当日剩菜,下层放置干净瓷器,侧面可插入刀具,挂置竹筷和勺。
那个孩子的百岁宴办得比她的婚宴还热闹,她请来整个医院的医生,并找来十里八乡最有名望的厨娘,却自己买菜、借碗、烧火、做饭,统领厨房,当起了厨娘。她记得那天的宴席很给颜面,天气预报说落雨,结果是场太阳雨,落昏时候,一片血红夕阳。她站在野地里,面对几十桌的客人,发表了长长而颤抖的感言。那天,所有人都夸她做的菜味好,她沉浸在自己制造出来的巨大而从未拥有过的灶膛之乐中,似乎,之后置办的所有宴席都是为了复制那天的欢愉。
夏季清晨的菜场,五点钟有杂鱼小贩刚刚从河里回来,在马路边的蛇皮袋上放着马头鱼、溪石斑、翘嘴白;六点钟隔壁村的老奶奶会骑着自行车到裁缝店的门口卖苋菜和芋头,买一把回去,拍几粒肥白的大蒜子清炒,紫红色的汤会把米饭染成浅粉色;七点钟郑叔的肉铺会为她留好猪舌和猪肠;七点半,卖鱼的摊位热闹非凡,上学的孩子都站在腥气的血泊中欣赏那一刀划过的痛快与哀艳。

本地常吃笋,村中就有大量竹园,或者在庭院中种植小片竹林,将鸡饲养其中。
她深谙菜市场的味觉密码,一边斩着鸡肉,一边得意洋洋地问我:「你知道,买鸡的时候是应该买肚子里有蛋的鸡还是没蛋的鸡?」
「有蛋的!」我也为自己的聪明而感到骄傲。
「傻子,鸡肉多少钱一斤,鸡蛋多少钱一斤,你按买鸡肉的价格买了鸡蛋,亏不亏!」
她显然用这个问题完美地问倒了很多人,并获得了一声颇为悠长的「哦」以示赞赏。为此她一把捞起自己厚厚的头发,层层叠叠盘绕在头顶,做了一个完美的髻,仿佛是五月末还未开的栀子花苞,螺旋状的一层压住一层,使她的脸庞完整地露了出来,这是一张圆润如玉盘的脸,是逼着人去赞美的佛面,那张脸仿佛在说 ——
我喜欢热闹啊,我喜欢人。

天井深处、檀木椅上,一清癯老头坐在那里。街上的人都传他养了只乌龟精,专在小孩睡觉时吃他们露在被子外的脚趾和手指。
14 岁那年,爷爷领我进去,我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一副菩提祖师发脾气时的脸,白髯遮挡颈部,几粒白饭结硬后扒在须上,实在有些好笑。

西溪南村前是大片枫杨林、湿地与河流,由此与外界隔离开。
那屋子前方有一破败庭院,一株枇杷有气无力地将枝桠伸向长满青苔的地面;左边的石墙上密密麻麻爬上了墨绿色的薜荔果;右边的空地上是二十多个一米直径的石球,荆棘丛生,有几只蝴蝶双宿双飞地消失了。突然,一只狸猫衔了半个鱼头从荆棘丛里跳出来,藏在枯死的枇杷硬叶下,微微佝偻着背,一边吃一边发出低吟喵语,像人在说:「这鱼眼,真好吃啊真好吃。」
天井内有两口大缸,温热的日光印在白墙上一粼粼水波,满屋子幽深的水草横行。一只缸内清水见底,里面是螃蟹和小虾,另一只缸内有一嶙峋太湖石,虎耳草伸出一枝白花,我走过去要端详,却看不见底。这时噗通一声,有东西落入,才瞧见石山上趴着一只小龟与水色石色融为一体,滑溜溜的头上有一道橘红色的眼线,一直画到耳边,另一只已伸展四脚,逃窜入金鱼藻中。我吃惊地退了半步,传闻不虚,他果然豢了龟精!
「小心把你肉吃掉!」闻声,那些遁形的龟一个个游出来趴在石头上,以一种虔诚的姿态布满石头的洞穴,硕大的鲤鱼也摇曳着金身,带着让人膜拜的光。
「它们认得你。」爷爷说。
「我每天给它们吃肉,怎么不认得。」老头说。
后来我再路过,老头以吃枇杷为名将我哄骗进去:「我家是进过神仙的,龙的第六个儿子霸下 [注:又名赑屃、龟趺、填下、龙龟等,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为鳞虫之长瑞兽龙之九子第六子,样子似龟,喜欢负重,碑下龟是也。] 来找过我。」「是龙?」「是龟。」「它住这缸里?」「不住。」「这些是它的儿子?」「不是。」「那霸下呢?」

村中有三四户人家饲养黄牛或水牛,早晨由主人牵至枫杨林水边吃草,夜间牵回家。
二十年前的傍晚,老头照例从缸里捉出两只螃蟹清蒸,早上有小伙摸了一碗螺蛳送他,为求一枚刻章。他应下,那时大家对他毕恭毕敬,称他为「裱画先生」。字画装裱、金石刻印、中堂对联他都不在话下。摆宴席,家家户户去请他,让他坐在入门处的桌子,收钱的人喊话「溪边街汪婆,贰拾圆」,他便工工整整在红纸簿上录下,一手好看的欧体楷字,神气极了。录完,将客人递的几十只香烟用一卷红纸包起装进裤兜里。攥着一只紫砂壶,仰起头嘬着壶嘴「啧啧」出声,抬起的手掌下是一片红纸染色。
他穿过庭院里的酒桌,走向主人为他安排好的上座,全桌的小辈等他拿起酒杯和筷子。八个冷碟上齐,那桌人便开始听他说书,从《水浒》讲到开国元勋,喝至兴头,一人在那用筷子敲着桌面唱《锁五龙》:「好海量,酒来!」自己一边应和着。
那日落昏,他将桌子摆到院墙树下,两只螃蟹、一碗番茄蛋花汤、一份田螺韭菜是从隔壁青姨那里取的经。路过的汪婆往门内探了探头,「吃酒呢?」「咹,吃点。」这是他每日的习惯,吃河鲜,喝小酒,借着月光将螃蟹剥得干干净净。
老头喝得昏昏沉沉,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入了床铺。半夜醒来,月亮已掉入树丛,隐约瞧见窗下椅子上坐着庞然大物,长长的影子将近遮挡了一半屋子的清光。它惬意地翘起一只腿悠闲地晃着,四肢和头顶是一层坚硬的鳞片,身体却是软乎乎地瘫着。手托着下巴,用细小的鼻孔闻着桌上的芍药,眉目软成一道柳叶,陷入沉醉。

初夏,荆棘丛中蝴蝶成双结对。
「你醒啦。」它继续欣赏芍药,用指尖一戳,落了半扇花朵。
「你是?」老头假装镇定,刚抬起半身就被寒冷的水汽激得瑟瑟发抖。在暗处,他看见一副巨大的龟壳,上面还耸立着高高的石碑。他似乎是明白了,「你是龙的儿子?」
「算你读过书。」庞然大物傲娇地转过头,架起的那只脚幽幽地前后摆动。
「霸下老爷,今夜找我何事?」老头努力做到不卑不亢,却也无法抵抗自然权威的压力,毕竟那长须都比自己长几分。
「别喊我老爷,我比你还年轻八岁。找你来,修石碑。」霸下用指尖指了指它脱下的那副装甲。
老头裹紧了衣裳,下床走近借月光。「唔,这是《余清斋》碑石,不是已经损毁了?」
「百年前被我爸爸藏了起来,现在让我们修缮完好并物归原主,我就来找你了嘛。」
老头的睡意全无,「它是神」,他在心里已经翻滚了好几个过场,「但,神能脱下外衣?」他看着这尊衣不蔽体的身躯,毫无尊严可言,柔软的肚腩,甚而比人脆弱。应该惧怕的是不是?但老头兴许是酒劲还在,面对这样的神物,他站着思索了两分钟,向前伸着脖子低头问它:「你饿不饿?吃不吃螺?吃不吃鸡子?吃不吃桃酥?喝不喝茶?」
「要的要的,你们进贡的红烧鱼块总是很好吃的,还有那红烧肉、酱猪舌、炸圆子、米粉糊、笋干猪蹄、红烧鸡……」
老头愣住了,心想这厮可没少吃人间宴席,自己可难养活它的肠胃。木讷了一会儿,便从厨房里托着红漆木盘走出来,上面一盏枇杷、一碗螺肉、一个茶叶蛋、一碟桃酥、一杯猴魁。
霸下原本都将塌陷睡着于木椅,这时眼里泛起光泽,胡须惬意地慢悠悠往上爬。它舔净了螺肉的汤,囫囵吞下枇杷核、桃酥落了一腿、茶叶蛋的蛋壳碎渣踩得咯吱作响,猴魁倒没喝多少,嫌烫。「好吃是好吃的,就是清淡了些,不比我去年八月八吃到的那些圆子、鲤鱼呐。」

厨娘端着水芹菜炒豆干、红烧鸡、豆干辣椒炒茭白、卤猪舌,正要端上宴席餐桌。
另一边的蜡烛已经点燃,像灶膛火一样映红了白墙,老头剜了它一眼,一边叹气心想这还是个没养成性的神,一边堆垒几个木椅往上爬,用湿抹布从上至下擦拭石碑。这是他临过上千遍的碑文,哪里有点破损心里仿如明镜。当年的太平军肆虐村落,入村处的树林深凹处埋有百人白骨,他不愿开灯,只拿了一根蜡烛贴近了看。看见的是梅溪草堂的残垣断壁,听见的是孩童妇孺的哀鸿遍野,他止不住地流泪,最后索性借着酒意哭倒在墙角。
「哎,怎么还哭上了?」霸下叹气,人呐,真脆弱。
泪珠啪啪啪打了几下地面,老头用毛边纸擤了几次鼻涕,倏忽一下站起来,将屋外的刻刀全都搬进卧室,一开始是嘶嘶嘶的摩擦声,后来变成了剁剁剁的刻刀声,最后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古怪鼾声,石灰一层层被挫在地上,由水青的岩石变成灰青的粉末。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虫啊蛙的都停止了鸣叫,阳光透过竹林,换来了公鸡的一声啼鸣。
「我饿了。」霸下在摇椅上躺了一夜,这时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叫吵醒。
「哦,该吃天光 [注:在徽州话中,吃天光是吃早饭的意思。] 了。」老头在碑前刻了一夜,起身时眼神依旧是凝固的,整个身体毫无知觉地去往厨房。不一会儿,端来白糜与雪菜。
「简单吃些。」老头的心思全在石碑,断然不会费心思在做菜上。
霸下不依,尤其是闻见了隔壁青姨家飘来的梅干菜香,坐不住了。但看着老头已然凝固的眼神,犹豫再三还是没发出脾气,再次叹出一口气,人呐,有血有肉的人。

徽州传统宴席八碗八碟。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三日,老头终日刻碑,霸下终日等饭。终于在黄昏将近时,老头喜笑颜开地对它说:「吐水吧!」
「你怎知我会吐水?」
「天天在院落里翻江倒海和缸里的虾蟹们玩,当我没看见?」
「嗨呀。」霸下被说得不好意思,眼后泛起一道红晕。走下摇椅,深吸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重得很呐!」它匍匐下身,柔软的身体钻进龟壳的时候,屋内掀起滚滚波涛,石碑上飘来一朵乌云,稀里哗啦下了一阵大雨,整饬的字迹在水波纹路的青石上显现,一只龙从乌云中钻出,绕着石碑在房顶上翻腾。
「那是你弟弟负屃 [注:古代中国神话中的龙的第八个儿子。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老头抬头看见洁白的龙身时隐时现。
「是呐,我们该去交差了。」霸下的声音被石碑压得老态龙钟,说一句话都会在房内发出嗡嗡的回响。
「这就要走?」老头这回只能趴下身子侧过脑袋来和它说话。
「穿上这层甲,无事我就脱不下了。」霸下显然不舍这三日的闲暇。
「还没请你吃圆子、鲤鱼、红烧肉呢。」老头回想起这几日的冷淡,忍不住摸了摸霸下的脑袋,一层鳞片下是柔软又皱褶的肤质,凉丝丝、滑溜溜的,像在摸一摊水。
「不急,别哭,走啦。」霸下实在不敢瞧老头涨红的双眼,哼哧哼哧转过方向,负屃兴风作浪,在它的引擎之下,倏一下飞走了,桌上的那瓶芍药被震得将将离开花萼,碎了一地。
老头见屋里只剩石灰与水迹,丢了魂。扶着墙壁走向摇椅刚要躺下,「咦」地一声,上面长了一层潮湿黏腻的青苔,一群蚂蚁煞有介事地搬运椅子上掉落的绿豆糕碎渣,他摇摇脑袋心想,「哎,还是个没心没肺的神。」
第二日,报纸、电视和广播纷纷报道碑林中《余清斋》碑石的乍现。与此同时,他听见院内传来哗啦啦的水声,那只缸居然在咕嘟咕嘟自行往外喷水,数十只小龟和锦鲤浮在水面上游泳,每一只小龟都有一道殷红的眼线。
老头嗤一下笑了,撸起袖子逮了一条鱼走向厨房,将一把长须抡到脑后,「人呐,神呐,皆是贪吃鬼。」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