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豆瓣评分(成吉思汗大交换)
本文作者“维舟”,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根据《红星照耀中国》的记述,彭德怀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起自己的身世:他自幼富于反抗精神,六岁丧母之后又进入一个新学堂,接触到一位提倡不孝敬父母的新派激进老师,这与他的想法一拍即合。当他回家说起这些话后,其祖母“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逆子。有一天晚上,他因为无法忍受祖母抽鸦片烟,起身把她的烟盘踢掉,她为之大发脾气,要求全族公审,将他溺死。然而,当他后来从军当上了团长之后,荣归故里时,也是这个祖母率全族迎出数里地,竟当众称赞他“从小就很孝顺”!
这是在我们评判历史时时常出现的现象:后面发生的事,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较早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一点,对蒙古帝国史而言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虽然它开创了一个空前(很有可能也是绝后)辽阔的陆基帝国,但那是以中国、波斯、阿拉伯及东欧等诸多古典文明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的。这种评价典型地反映在它的奠基人和化身成吉思汗身上——他常常被诸如伏尔泰这样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谴责为嗜血好战的野蛮人,就算有值得歌颂的地方,那通常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然而,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史的兴起,这种看法已被视为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将这个征服帝国视为全球化进程的最早开辟者,成吉思汗也就顺理成章地从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伟人。
在翻开梅天穆的这本《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时,这是应当首先注意的一点,因为此书原本就是应“全球性”(Globalities)丛书主编邀约而写。也就是说,梅天穆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出发点在于他认为“除了刚过去的200年,我想不出哪个时代能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蒙古征服”对他而言和撰写《世界征服者史》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完全不同,其意义不在于一些君主的辉煌征战事业本身,而是这一征服给欧亚各地带来了冲击、促进了交流,推动了历史发展,最终塑造了我们当下这个世界。在此他改变了“蒙古征服”的定义和传统理解,而视为“将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的扩散都融入一炉”的过程,这个新的解释实际上非常接近于“全球化”本身。他甚至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口吻问道:“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哥伦布会出航吗?别忘了,他当时是试图抵达中国面见大汗的。”
从世界史的视角来考察这段历史,诚然能极大地开拓我们的视野,尤其对于常常无意识中从“元朝史”的角度来看待“蒙古帝国史”的中国人而言(在国人眼里,成吉思汗也常只被视为“元朝始祖”),更能超越时空限制来重新思考“蒙古世界帝国”的意义。梅天穆在此强调的是蒙古帝国的到来衍生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尽管它迅速走向分立,但仍然对欧亚各地带来深远的冲击,并促进了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观念的流通。他十分精到地分析了“蒙古治下的和平”时期在贸易、战争方式、行政管理、宗教、疾病、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共七个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他所说的“成吉思汗大交换”(这个术语显然是向克罗斯比发明的“哥伦布大交换”一词致敬),从而强调了经此过程之后,世界已经与蒙古帝国之前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关于这些,我们当然能轻易列举出一大堆:蒙古人改进了中国式的驿站系统并将之推广到整个欧亚;他们将中国传统的“牌子”带到了各地,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护照制度;更不用说蒙古所向无敌的军事制度和技术所带来的深远冲击,促进了从东南亚到俄罗斯的军事变革浪潮,尤其是极强的机动性、技术和纵深作战的结合。蒙古人自身没有取得科技突破,没有创设新技能的工匠,也没有伟大的诗歌或剧作,但他们却充当了极好的桥梁作用,让各种物资和文化、技术得以在欧亚大陆的辽阔地域内不受限制地流通。其中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们将宋代中国出现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传播到了西方,包括由印刷术而生的纸币和纸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大体上技术是从东方传向西方,而人员(主要是中亚人,当然也包括马可·波罗这样的欧洲人)则是从西方流向东方。
因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梅天穆所描绘的这一“成吉思汗大交换”的宏大画面中,交换是不平衡的。像前人一样,他当然意识到,蒙古帝国对各地造成的深远冲击有所不同:中国、波斯、阿拉伯、罗斯等古典文明均遭毁灭性打击和完全占领,但西欧则由于东欧的屏障和窝阔台之死而幸免于入侵,除了黑死病这样的间接传播造成的伤亡,蒙古帝国对西欧而言可以说是毫发无损,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宛如天赐礼物。概言之,当时的西欧和日本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可以安全而有选择地对蒙古的冲击作出回应,但在直接受到其铁蹄征服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便我们承认蒙古征服重塑了世界,也应看到,它所留下的遗产是不一样的,至少对中国来说,那种货物和文化的跨区域交流是次要的、局部的,更深远得多的倒是这样一个政治遗产:重新统一中国并锻造了中华民族。
由于将“征服”仅仅视为是一种“交流”(这就好像把“抢劫”视为“强制性交换”),梅天穆低估了蒙古征服对不同地方的深远破坏——这种破坏不一定是带来变革和新机遇的“创造性破坏”,有时它确实就是让当地一蹶不振的彻底破坏。在他心目中,蒙古征服本身毫不重要,只要它能直接“造成世界史上伟大历史变化”——换言之,这是一种进化论史观,相信只要能带来整体进步,就可以不择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它整体上推动了历史发展,但对不同地区的人而言,“蒙古治下的和平”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也是不均等的。另一位蒙古学家Jack Weatherford尽管在所著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也推崇备至,但也承认13世纪的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文明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水平都要高出许多,“因此他们受到的损害也就最大。蒙古入侵者在此地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然而梅天穆走得远得多,他坚称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催化了变迁,“而且并没有导致世界各地区的倒退”,将那些说法贬低为民族主义者的托辞,理由是“若没有蒙古征服,很多进步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这倒说得好像有了蒙古征服就会有进步似的,但问题是:这些进步是出现在被蒙古征服的同一个地方吗?
如果我们追问:“成吉思汗大交换”是谁和谁在交换?主要是谁在得益?那么或许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实际上“蒙古征服”所起到的作用与“丝绸之路”非常相似。按照如今许多内陆亚洲史和世界史学者的观点,“丝绸之路”也是当下“全球化”的前身,促进了货物、思想、宗教、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只不过对“成吉思汗大交换”而言,需要抹去其中的血腥与破坏才能专注于“交流”层面,或是像梅天穆这样运用修辞手法,将“征服”直接等同于“交换”。不仅如此,这两种观点虽然都兼顾到了沿线不同文明与国度的参与,但或明或暗地其实是将中国和西欧视为交流的起点与终点,潜藏着“蒙古征服/丝绸之路对西方意味着什么”这一终极预设。他所说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西方视角的全球化”,以技术、文化等的西传为重心,而不注重这一交流对东方的影响——这对西方而言的确算是沟通了东西方,但在中国,这往好里说也只是一种“浮在表层的全球化”。其实,对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那些具体的技术,而是一种对东方(具体来说是中国)的向往,但蒙古人却无法在中国人心目中激起相反方向的冲动。
虽然梅天穆主张在说“蒙古人开启了全球化”这一点上“应该克制一些”,并将目光聚焦在那些与蒙古人活动直接相关的历史影响上,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他更关注那些“产生了好影响”的交流上。这不仅遗漏了那些“未得到交流的事物”(例如中国的筷子和缠足),也略过了那些“产生了坏影响”的互动——就像“哥伦布大交换”与殖民历史交织在一起,蒙古征服也和许多黑暗的事物不可分割。不过,像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这样的发明,尽管也曾传入中东,但只有在西欧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才爆发出巨大的变革能量,这意味着接受技术的社会条件至少和传播的技术一样重要,否则就算遇到了新技术也不会催生变迁。就此而言,世界之所以在那之后跨入了近现代的门槛,蒙古征服所带来的冲击最多只能算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事实上,任何一个帝国在统一辽阔地域之后,都会起到蒙古帝国类似的作用,或有意、或无意地促进跨区域的流动性,就像亚历山大帝国也曾把希腊文化带到东方,但这之所以不能被追溯为“全球化”的事件,似乎仅仅是因为它还不够辽阔,并且不凑巧地没能触发一个现代化进程。很多历史变化确实是非意图后果,但我们也不应以这些后果来为更早的历史作辩护——否则,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殖民征服也带来了全球化呢?甚至日本人如果在太平洋战争中获胜了,也可以说自己带来了和平,解放了亚洲人民,促进了整个东亚的商业与文化交流。正如美国汉学家米华健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些西方作者赞颂成吉思汗开启了文艺复兴、创辟了当时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但一个问题是:“当时的蒙古人也会致力于‘连接文化,建立信任’吗?”
毫无疑问,这不是蒙古人开创这个帝国时的动机,因此,要说13世纪的蒙古人“体现出了一种虔诚和执着的国际主义者的热忱。他们不仅试图征服世界,而且还试图制定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还说“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见《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这不免让人感觉走得有些远了,毕竟这是一个征服帝国,而不是一个商业性帝国。蒙古帝国确实提供了一种通达欧亚各地的安全流通环境,但与其说这是他们为了促进陌生人之间经济交易和文化交流而开辟出来的有制度保障的特殊空间,倒不如说是他们政治统一的副产品;因而当后来的政治分立破坏了这些之后,也没有人试图去重建经济自由的制度环境。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但却被梅天穆遗漏的是:蒙古人那种亲商的、世界化的政治取向,是游牧传统中的开放性的必然结果,因为历来的游牧帝国都依赖商贸关系来获得外部物资,甚至还会雇佣商人作为自己的大使,不过这种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
这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最大的陷阱:当我们在说“蒙古人开创了全球化进程”时,那个“全球化”和现代人所说的“全球化”真的是一回事吗?“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毕竟是1961年才出现在英语里的,用于描绘一种19世纪以来不断加速的流动性,而且是以现代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化环境作为支撑的;在用于八百年前的蒙古帝国时,这就有一种“将古代炼丹术追认为早期化学史”的感觉。当说到蒙古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时也是如此:那仅有一种表面上的相似,而与现代宗教宽容政策并非一回事。那并非基于公民个人权利,也不是政教分离原则下不同宗教享有同等的法定权利,而是一种一元本体论的信念,即认为不同宗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我们看历史时,看到的往往是“存在于历史中的现代”,而正是这左右着我们对它的评价。在被问到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时,周恩来曾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回答:“现在还为时过早。”他说得对,蒙古帝国即便在八百年后的今天,全面评价它的遗产或许也还“为时过早”,因为不同时代的人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段历史。
已刊2017-12-26《经济观察报》书评版,题目改为《成吉思汗与欧亚大陆的交易》 ------------------------------------------------------------------------------------ 勘误:
地图p.1/2:图上所示年代在1200-1260年间,但里海以西有“莫卧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疑误;安纳托利亚半岛下方有“西里西亚”(p.101也提到),这一古地名是Cilicia,但汉译地名“西里西亚”一般是指中欧的Silesia,而这个中东的亚美尼亚公国则通译为“奇里乞亚”;又图上许多地名、部落名均采用蒙古时代译法,但并不统一,如“格鲁吉亚”当时称“谷儿只”(正文就译作“谷儿只”,如p.50),阿塞拜疆则应称“阿哲儿拜占”等 p.3:东亚研究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林霨 p.18:《大将军速不台》(Genghis Khan’s Greatest General: Subotai the Valiant):直译应是《成吉思汗最伟大的将军:勇士速不台》 p.32:蒙古草原中部的色楞河、鄂尔浑河以及图拉河流域:一般译作“色楞格河”、“土拉河” p.43:在10世纪辽朝崛起之前,宋朝也曾统治过华北地区:此语有误,辽朝建国比宋朝更早,而宋朝失去华北地区也是在1127年北宋被金朝灭亡之后,故似应是“在12世纪金朝崛起之前” p.50:罗斯,译注:元代称“斡罗思”。按书中一般使用元代时译名(再加注今译名),但罗斯却使用现代译名,再加注元代译名,体例不大统一 p.67-68:[1258年蒙哥汗率军从陕西攻入四川]他连下成都、铜川以及数个山城:铜川在陕西,此处既说的是侵入四川,则此地名应是潼川府 p.74:[忽必烈]任命学者编纂前朝(金和宋)的历史:其实最初翰林学承旨王鄂提议撰修的是辽金二史,但忽必烈在位时虽然接受建议,但因正统问题未解决,始终未正式任命学者开始编纂 p.116:只有希瓦汗国维持了表面上的自治,直到十月革命爆发。1912年,希瓦汗国的成吉思汗系统治者被赶下了汗位:按,既说维持到十月革命(1917年),则不可能1912年就覆亡,前一页p.115列出该汗国覆亡的年份是1920年,是 p.116:察合台系莫卧儿人:“莫卧儿”一般是对译印度的莫卧儿(Mughal)王朝,对中亚的察合台系,通常译作“蒙兀儿”(Moghol),如国内之前出版的《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 p.123:当时日本流行的观点是相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日本武士转世:按,日本传说名将源义经未死,而逃亡到大陆,到蒙古人中成为成吉思汗,后来为向源赖朝复仇,其后人入侵了日本。这里“转世”的原文疑是reincarnate,除了“转世”外也有“化身”、“变身”之意,此处应取后一层含义,因为这个传说并不是说成吉思汗是源义经的转世灵童,而就是未死的源义经本人化名 p.123:在乌兰浩特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成吉思汗庙(面积超过762平方米):这里应该指的是庙殿建筑面积,现在一般记录是822平方米 p.125:蒙古国在1912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1921年 p.128:1941年,苏联考古学家打开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跛子帖木儿墓——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误,p.90写明帖木儿“在出身上比较偏向突厥,而不是成吉思汗家族”,虽然这是引文,但宜注明。又p.182谈到“巴布尔是帖木儿的后裔,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很容易让人以为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再到巴布尔是直系血缘传下来,但实际上巴布尔是父系源出帖木儿,母系源出成吉思汗 p.145: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下文有时又将怯绿连河译成“克鲁伦河”,如p.285:“汗廷当时位于漠北蒙古的克鲁伦河附近的巴尔斯和坦” p.201:北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为免与“北卡罗莱纳州”这样的州名混淆,应译作“佐治亚州北部”为宜 p.225:将统治者的名字纳人伊斯兰教的礼拜五宣讲(khutba)中:“礼拜五”是基督教的说法,此处按伊斯兰教的说法严格来说当作“主麻日(或聚礼日)呼图白” p.244:窝阔台之子阔端(1206-1251年在位):这是阔端的生卒年,他作为蒙古帝国的宗王也谈不上“在位” p.295: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按此书是佚名元人所著,何秋涛只是道光年间获得此本,故此处似应注明何氏是整理编定者 p.296:[云南]当地人口主要由彝族、藏族及多种泰语族群构成:英语所说的Tai,国内对应的应是“侗台语族群”(包括傣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等) p.320:河南和四川菜中的辣椒: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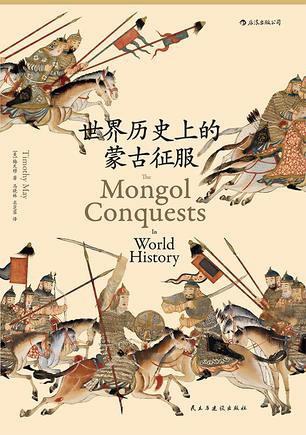
(全文完)
本文作者“维舟”,现居上海,目前已发表了281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维舟”关注Ta。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