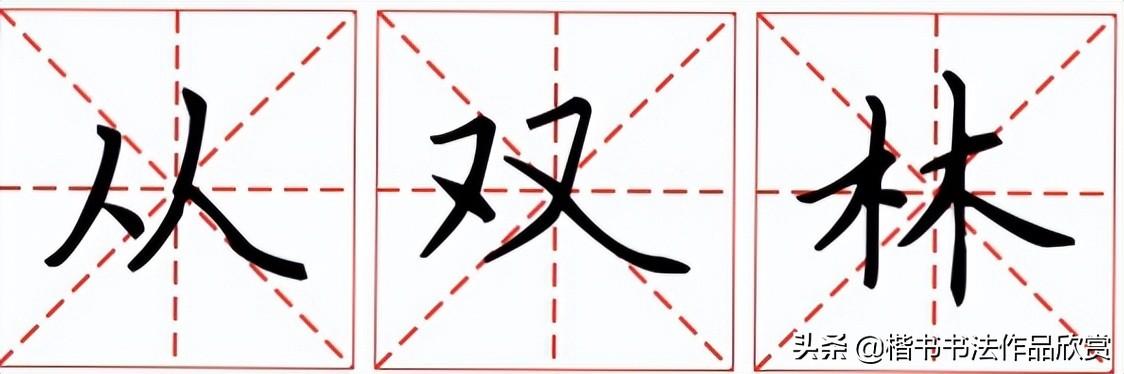麻烦是不是词语(妇女是一个麻烦的词语)

1857 年 3 月 8 日,美国纽约的纺织女工为抗议不平等的工作环境和低薪走上街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际妇女节于 1975 年 3 月 8 日确立。作为女性运动的主体,“妇女”仿佛自带着一种被固化的女性形象,对此,美国女性主义研究者朱迪斯·巴特勒用她的理论警示我们对“妇女”身份的误用。
在她的早期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的第一章节中,她质疑了人们对妇女主体本身的理解方式,指责女性主义在为了满足政治意义下作出的粗糙表达。在她看来,“妇女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即使在复数的情形,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争论的场域、一个焦虑的起因。”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美] 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凤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

“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
大体来说,女性主义理论假设存在有某种身份,它要从妇女(译者按:涉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政治范畴的“women”译为“妇女”,而在第二章、第三章精神分析话语及其他语境中则译为“女人”。)这个范畴来理解,它不仅在话语里倡议女性主义的利益和目标,也构成了一个主体,为了这个主体追求政治上的再现。然而,政治(politics)和再现(representation)是争议性的词语。一方面,在追求拓展妇女作为政治主体的能见度与合法性的政治过程中,再现作为一个运作的框架;另一方面,再现是语言的规范性功能,被认为不是揭露、就是扭曲了那些关于妇女范畴我们所认定的真实。对女性主义理论来说,发展一种全面或是足以再现妇女的语言,对促进妇女的政治能见度似乎是必要的。有鉴于在广泛的文化情境里,妇女的生活不是受到错误的再现,就是完全没有得到再现,这点显然益形重要。

朱迪斯·巴特勒在演讲中
近来,这种普遍存在的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之间具有关联的观念,从女性主义话语内部遭到了挑战。对妇女主体本身的理解方式,不再限于稳定或持久的框架。有大量文章对“主体”作为再现——更确切地说是解放——的终极代表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什么建构了、或者应该建构妇女范畴,这些文章彼此之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政治和语言再现的领域先设定了一套主体形成的标准,结果只有被认可是主体者才能得到再现。换句话说,必须先符合作为主体的资格才能得到再现。
福柯指出权力的司法(juridical)体系生产主体,然后又再现这些主体。司法性的权力概念似乎以完全负面的方式来管控政治生活——也就是说,通过一些具有历史偶然性、并可以撤回的选择的运作,对与那个政治结构相关的个人进行限制、禁制、管制、控制,甚至“保护”。然而受到这些结构管控的主体,由于它们服从于这些结构,因此是根据这些结构的要求而形成、定义以及复制的。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把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语言与政治之司法建构,它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再现政治的结果。结果女性主义主体成了那个原本应该是推动其解放的政治体系的一个话语建构。如果这个体系证实了是根据一种统治的分化轴线来生产性别化的主体,或是生产那些被认定为男性的主体的话,那么从政治上来说这就大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加批判地诉诸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解放”妇女,显然是自砸阵脚。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大师
“主体”的问题对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女性主义政治,因为司法主体一律是通过某些排除性的实践生产的;这些排除实践在政治的司法结构建立完成之际就不再“彰显”。换句话说,主体的政治建构是朝向某些合法化以及排除的目的发展,这些政治运作被某种把司法结构当作基础的政治分析给有效地遮掩以及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了。司法权力无可避免地“生产”了一些东西,而宣称它只不过是再现它们而已;因此,政治必须关注权力的这个双重作用:司法的与生产的。事实上,律法生产“律法之前的主体”这样的概念,而后又将之隐藏,为的是把这个话语结构当作一个自然化的基本前提调用,然后用它合法化律法本身的管控霸权。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现是不够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
事实上,妇女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一个在律法“之前”的主体,等待在律法里再现,或是被律法再现。也许主体,和对一个时序上“之前”(before)的调用一样,都是被律法建构的,作为律法取得合法性的一个虚构基础。关于普遍存在的认为律法之前的主体具有本体完整性这样的假定,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它是自然本质的假设——亦即那构成古典自由主义司法结构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t)神话——残留于当代的痕迹。对一个非历史的“之前”的一再操演调用,成为保证人的前社会本体的一个基础前提;而个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统治,从而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合法性。
然而,除了支持主体概念的基础主义虚构以外,女性主义在假定妇女这个词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这方面,也遭遇了政治上的问题:妇女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充分得到了它要描述和再现的对象的同意;即使在复数的情形,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争论的场域、一个焦虑的起因。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的书名《我是那名字吗?》所暗示的,这个提问正是从这个名词可能有的多重意指产生的。如果一个人“是”女人,这当然不是这个人的全部;这个词不能尽揽一切,不是因为有一个尚未性别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别的各种具体属性,而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语境里,性别的建构并不都是前后一贯或一致的,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因此,“性别”是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会里分离出来,它是在这些交会里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

1914 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的德国海报
认为女性主义必定要有一个普遍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所谓跨文化的身份上的政治假设,通常伴随着这样的概念: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可以在父权制与男性统治的普遍或霸权结构里找到。近年来普遍父权制的概念广泛受到批评,因为它不能解释性别压迫在它们存在的具体文化语境里是如何运作的。这些理论是考虑到了各种不同的语境,但这不过是为一个从一开始就预设的普遍原则,寻找一些“例子”或“例示”而已。这种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受到批评,不仅是因为它试图殖民、窃用非西方文化,用以支持一个高度西方化的压迫概念,也因为这些理论有建构一个“第三世界”、甚或一个“东方”的倾向,在其中性别压迫很微妙地被解释为一种本质的、非西方的野蛮性的症候。女性主义急切想为父权制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特质,以强化女性主义所宣称的它具有代表性的表象,有时候这促使了女性主义者过于急功近利地祭出统治结构在范畴上或是虚构上的普遍性,而据此生产妇女共同的屈从经验。
虽然普遍父权制这样的主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具有公信力,但是想要置换由这个框架推演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关于“妇女”的设想有某种普遍的共通性这样的概念,一直是要困难得多。当然,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辩论:妇女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共通性,而且是先于她们的压迫?或者,是否单单她们的压迫经验本身,就足以使“妇女”之间有某种结盟?妇女的文化是不是有某种独特性,独立于迫使她们臣服的霸权、男权文化之外?妇女的文化或语言实践的独特性与完整性,是否总是以某个比较优势的文化结构为参照,因此也局限于这个框架?有没有“独特的女性”这样的领域,它不仅因此与男性领域区分,而且在这样的差异里,它可以从“妇女”的某种未标记的、假定的普遍性上辨识出来?男性/女性的二元分立不仅成为使那独特性可以被辨识出来的独一的架构,并且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也使得女性的“独特性”再度完全脱离了语境,而在分析上以及在政治上,与阶级、种族、族群等建构,以及其他建构“身份”、同时也使单数的身份概念成为错误命名的权力关系轴线分隔开来。


历史上的女权运动
我认为一般所假定的女性主义主体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实际上因为它所赖以运作的再现话语的种种限制而有所松动。过于急促而不成熟地坚持主张有某种稳定的女性主义主体——理解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妇女范畴,必然造成对这个范畴多重的排拒。即使这建构是为了解放的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这些排除的领域还是显示了这个建构的强制性与管制性所造成的后果。的确,女性主义阵营里的分歧,以及矛盾地来自“妇女”——女性主义宣称它所代表者——对它的反对,显示了身份政治必然具有一些局限性。有人建议女性主义可以试图扩大它所建构的主体的再现范畴,但反讽的是,由于这样的提议拒绝考虑这些再现主张的建构性权力,结果使得女性主义的目标面临了失败的危险。以纯粹“策略”的目的而诉诸妇女范畴的做法,不会使这个问题得到改善,因为策略总是有超出它们意图的目的之外的意义。在这里的情形,排除就可以算作这样一种无意为之而适得其反的意义。为了符合再现政治上女性主义必须表达一个稳定的主体的要求,女性主义因此使自己受到了粗糙的错误再现的指责。
显然,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拒绝再现政治——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一样!语言和政治的司法结构构成了当代的权力场域;因此,没有一个理论立场是外在于这个场域的,我们只能对它自我合法化的实践进行某种系谱学的批评。基于这样的情况,重要的出发点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历史的当下。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建构的框架里,对当代司法结构所生产、自然化以及固化的身份范畴做出批判的论述。

2017 年 2 月 7 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性举行“无上装”游行示威,要求平等和妇女权利
或许在这个文化政治的关键时刻,在一些人所说的“后女性主义”的时代,我们有机会从女性主义观点的内部,对建构一个女性主义主体这样的指令进行反思。在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才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在其他基础上复兴女性主义的再现政治。另一方面,为了使女性主义从必须建构一个单一或持久的基础这样的必要性里挣脱出来,我们也到了该考虑某种激进批判的时候了,因为单一或持久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一直被它排除于外的那些身份位置、或是反身份位置的挑战。把女性主义理论建立在“妇女”作为主体这个概念上的排除性实践,是否悖论地破坏了女性主义拓展它所主张的“再现”这个目标?
问题也许要更为严重:把妇女范畴建构为一致的、稳定的主体,是不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reification)?这样的物化不是正好与女性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吗?在何种程度上,妇女范畴只有在异性恋矩阵(the heterosexual matrix)的语境下才获得稳定性和一致性?如果稳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期待某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来挑战性别和身份的物化,这种政治形式将把可变的身份建构当作一个方法上和规范上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一个政治目标的话。
追溯那些生产并隐藏合格的女性主义司法主体的政治运作,正是一种探讨妇女范畴的女性主义系谱学的任务。在我们质疑“妇女”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努力过程中,可以证明不加置疑地调用这个范畴,使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再现政治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把再现的对象扩及一些主体,而这些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在排除那些不符合对主体的一些心照不宣的规范要求的主体之上,这有什么意义呢?当再现成为政治唯一的重心时,这在不经意间维系了什么样的统治与排除的关系?女性主义主体这个身份不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如果主体的形成是在一个权力场域里发生,而由于对这个基础的主张,这个权力场域在一般的规律下是被掩盖的话。也许非常悖论地,只有不再一味认定“妇女”这个主体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再现”对女性主义是有意义的。

编辑丨是鸭
图片来自网络
点击上图,购买全新上市的《单读 19 :到未来去》

▼▼“再现”这个目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