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脑容量有限(很可能是脑细胞的)
记得年轻时看张德芬的书《遇见未知的自己》,刚看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女主角若菱在和老公婚姻危机之际,误闯入山路边神秘小屋,遇见老人,引导她问自己是谁,结果,身份,名字,工作,经历,身体,行为,思想,信念,价值观,甚至灵魂也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我是谁。
当时的我认为这是在玩文字游戏,是一个个的逻辑诡计,我是谁?我不就是大脑中认同的我吗?纵然我身体在变化,名字,身份都可以变,思想,信念也可以改变,我还是能够意识到头脑中有一个我呀。于是带着这样一种疑问,大概翻了翻情节,草草看完,感觉女主角也没费什么劲,就赢回了破碎的婚姻,赢回了工作,这也太超现实了吧。
多年后,在社会与家庭中磕磕碰碰,阅历渐丰的我开始学习心理学,进行个人成长,慢慢地开始接触到和自我有关的概念,直到前不久遇见心理学的一本书《自我的本质》,我这样一个杠精理工女眼前一亮,对了,这才是我要找的东西。

我是什么?还真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概念,因为我,或者我们用心理学的术语—自我的形成,即有生物学基础,又有环境等社会性影响。这两种因素最终都会通过大脑不断自结构化而体现出来:即大脑是‘自我’的发源地。
心物二元论反驳这个观点,但是包括作者胡德在内的一众脑神经科学家倾向于“自我”产生于大脑,做一个思想实验就很容易证明心物不是二元的:身体可以换,但无论是换手换脚还是换某些器官,大脑都还是认为这个我还是以前那个我,而如果换掉一个大脑,大脑则会迷失掉以前的那个“自我”。
怎么理解自我的形成呢?也许用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知识来打比方更能够帮助理解人类的自我是什么。
一台新买的电脑,必须要装载操作系统软件,比如windows,才能得以运行,这就好比婴儿生下来,大脑中(主要指大脑皮层)已经有很多基础神经模式的存在了,这些基础神经模式就是“自我”的底层操作系统。这就是自我的起点。
就好像只安装了操作系统的电脑基本没有什么用一样,实验证明,小婴儿出生的头两年也是没有‘自我’的概念的。就像我们的电脑要一点一点按需求安装应用软件一样,婴儿也在发出自己的各种需求信号,获得照顾者的关注,并且在与外界的交互中,在各个感官的敏感期内形成感知功能。在此阶段,大脑里的神经元连接在发展期迅猛增长,同时,不被使用的神经连接则被修剪掉。这倒也符合奥卡姆剃刀法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婴儿的视觉敏感期,如果不幸得了白内障,那么过了敏感期,即便白内障消除,眼睛器官的功能是完好无损的,却无法辨识物体—因为那些视觉功能所调用的神经连接由于不被调用则被剪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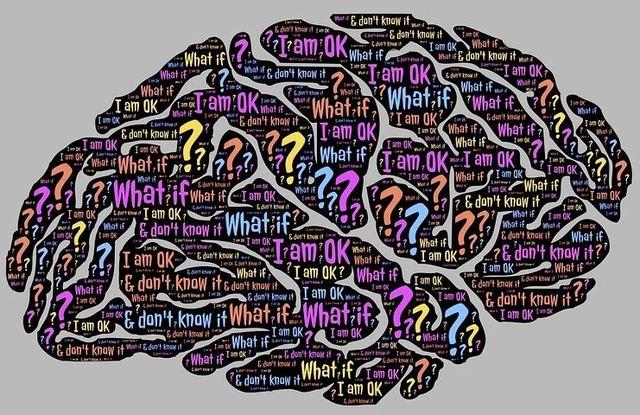
先天的大脑已经准备好了,后天呢?大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加工的世界,环境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书中这样解释:
为了生存,我们的大脑模拟着世界。这种模拟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大部分加工所需的信息都已经受到破坏。而我们的大脑会以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为样本,填补缺失的信息并解释干扰信息。
由于缺乏可供精确加工的信息、时间或资源,我们只能运用基于经验的猜测能力来建构自己的现实世界模型。不仅是外部世界,这一过程同样作用于内部工作中,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头脑内无意识地进行的。
“我们”是谁是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是一种由大脑创造的建构叙事。
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一个像大脑这样的生理系统是如何制造出类似于可被意识到的自我这类非生理体验的。
不过,我倒是有个比喻为什么生理系统的大脑可以制造出非生理体验的自我,那就是不妨用互联网业界常用的“涌现”来表达一种混沌之中出现的秩序现象,只是“涌现”本身也不大好理解,又需要一层比喻:
我们想一下霓虹灯,每一个小灯泡都是只有亮,灭两种状态,外加一种颜色,但是整片的霓虹灯却能够随着每一只小灯泡的亮或灭,让霓虹灯展现出不同的花纹。
每一个灯泡是物质的,实体的,个体层面的,但是所形成的花纹,我们叫做“斑图”(pattern)却是超越个体的,产生于新层次上的非实体的一种“软件”,这也许可以理解大脑虽然是生理的,实体的,但是神经元及神经元之间的电信号连接却会在高一级层面形成出无限种pattern,而pattern是转瞬即逝,不可保存的。你可以想象,某一时刻的pattern可能叫做“害怕”,下一个时刻的pattern展示出“快乐”。
关于大脑里的神经元的活动,胡德在书里是这样形容的:
每一个神经元可以同时和其他几千个神经元连接,它是否激活是由到达的信息集的活动决定的。当活动的总量达到引爆点,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向与它连接的神经元发放一种引起连锁反应的微弱电化学信号。
事实上,(大脑的)每一个神经元都如同一个微型处理器一样,计算着所有与之相连的神经元的集体活动。这好比在一群人之间传话,有的神经元像帮你传话的朋友一样友善,它们被激活了;而另一些神经元则处于抑制状态,它们试图让你保持静默。
既然我们的情绪,感知,思想都是类似于斑图的转瞬即逝的留不住的软件,那么可以想见,没有一个不变的意识上的自我,所以胡德颠覆性地认为自我是幻象。
“幻象”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它只是不像看起来那样。我们都能真切体验到自我的某种状态,但这些体验只是大脑从自我利益出发而创造的假象。
比如下图,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地把它加工成一个白色的正方形。
而书中,关于自我的定义是这样的:
首先,自我是源于大脑对内部世界的一种“设定”。设定有一个自作主,自受用,能稳定不变的“我”,再在此基础上构建自我的模型。
第二,自我不是一个单独的部分,而是感觉,知觉,思想相互堆积捆绑的整体,自我是在这些捆绑在一起的体验中浮现出来的。
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三个名词:感觉,知觉,思想以及三个动词为堆积,捆绑,浮现。
感觉,知觉,思想这三个名词讲的是,自我是由什么“原材料”构成的,说的是What。
堆积,捆绑,浮现这三个动词表明了有了上面构成自我的“原材料”,具体怎么形成自我的,它是动态的,过程的,讲的是How, when,显而易见自我的原材料通过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对外界的反应体验的不断堆积和调整,这些感觉知觉思想的原材料经由大脑神经系统对外部世界进行加工,捆绑,逐渐形成其关于现实世界的模型,以体验的浮现让我们知道“那是我”。
另外,书中还介绍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心理效应,如从众效应,禀赋效应,变色龙效应以及相应的各种实验等,无一不是为了揭示我们的大脑是为了求“存”,而非求“真”,在为我们创造假象。
04 认识到自我是幻象有意义吗?
既然我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模型,这个模型则给予我们掌控感,让我们也可以理解,预测他人。而变幻的自我其实也恰恰心理治疗得以起效的原因,那就是:每一个时刻的我们其实都是在建构着适配于那个情境的故事以便让我们心里好过些,让我们依然保有生存下去的意义。心理治疗也就是帮助案主梳理过往,重构积极的故事,找回生存的意义和勇气。
《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作者,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就是一个意义疗法的奇迹。纳粹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弗兰克尔用自创的意义疗法,找到了苦难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爱的意义,超越了炼狱般的痛苦,得以存活,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
电影《美丽人生》更是讲述了纳粹集中营里一个父亲为儿子把一切苦难重新靠着强大的意志和想象力建构为战争游戏的故事,令人唏嘘,更令人感叹。
回到开头我所提到的张德芬那本书里的“我是谁”,如果能够认识到自我不过是不断变化的,并没有一个真正恒常不变的我,甚至是倾向于“无我”,那么受伤害的那个“我”又是什么呢?佛家上我们叫它为“小我”,而苦苦限于“小我”的陷阱里,便是“我执”,而世界上总有一些”比自己更大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和它联结,就能够逐渐体验到“真我”“大我”“宇宙能量””超意识”等—换一个容易理解的词,那叫做“爱”。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