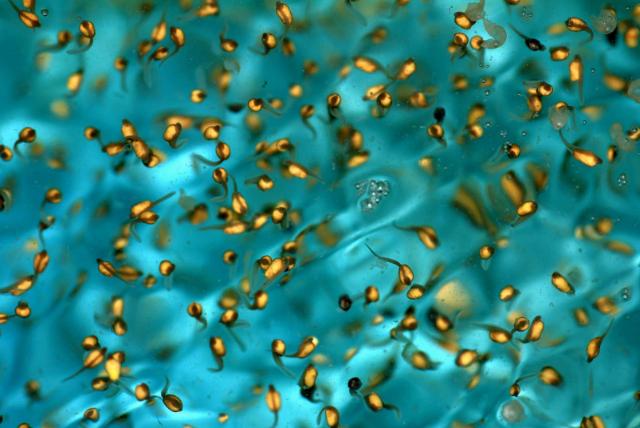科学哲学神学到底是什么关系(科学的尽头是神学)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其中的神学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简中网络,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往往被佛道或者一些“萨满”追随者的话语权所“霸占”,更有甚者,这句话索性被直接改成“科学的尽头是佛学”,乃至于被很多人胡乱理解和解释,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句话中的神学,应该作何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出处,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说的,也有人说是特斯拉说的,也有人认为是牛顿说的,也有可能不是上述三人中任何一人所说,而是某种以讹传讹,但其来源是西方的(或非本土)的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今天要讨论这句话,并非因为它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口,而是因为这句话确然有其深意,而要大致还原其本意,我们必须进入西方智识世界的深处一探究竟。
西方智识史上的神学
在“擅长”望文生义的简中网络,神学往往因其“神”字而被很多不学无术之徒和“迷信”、“神秘”以及“神棍”等类似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这种肤浅的认识,完全和其真正的原意背道而驰。
自古希腊哲学的肇始,哲人们就在不断的思考世界的源头,宇宙是如何产生的,人又是缘何而生?其中的滥觞包括泰勒斯的万物本源是水,阿那克西米尼的干燥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纯净的火,恩培多克勒综合水火土气的四元素说等。但早期的哲人在探讨本源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或者说习惯,就是都指向某种经验的物质。
随着思辨能力的不断发展,哲学家们的“抽象”之能力越来越强:巴门尼德首先提出了不可变的“一”;而受东方特别是埃及神秘主义的启发,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认为数字才是万物的源头,柏拉图深受其影响(早期的柏拉图显然可以被视为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将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置于一个崇高的神圣地位,还在自家学院入口的门楣刻上了“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标语(这让笔者无端联想到了但丁地狱门口的“入此门者,当抛弃一切希望”)。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许多和老师截然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的关注重点并非亚里士多德的本源观,而是其对各种学科的集大成的探索,以及在深入探究基础上的分类整理。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留下了《物理学》、《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包括优太莫和尼各马可)等各个学科的“专著”。在这些研究“具体”某个领域的专著之外,他还有一本以给学生上课的讲义辑合而成的《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合集中,他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研究一切种类的原因是一门还是多门“科学”的任务?
研究实体的第一本原的“科学”是否也应研究如何证明第一本原?
是否有一门研究一切实体的“科学”?
研究实体的“科学”是否也研究其性质?
我们绝不能以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解上述问题中的“科学”,为避免混淆,可暂做“学科”理解。在其纷乱混杂的讲稿中,现代研究者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结出了亚氏为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所规定的主题:其一是对第一本原(实在)及其原因的探究;其二(如果有可能),是对实在的本质(属性)的探究。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即“著名”的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metaphysics,物理学之前。但似乎略显矛盾的是,他又在形而上学 的最后一章详细讨论了另一门“科学”,并将其称为形而上学的“巅峰”和“桂冠”,即神学。根据亚氏的分析:
“物理学”研究可以分离存在,但不可无运动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并非现代的物理学,对亚氏而言,研究动物和植物分类的学科,也可以纳入物理学的范畴);数学研究的是既无运动,也不分离存在,且留置于质料中的对象;如果存在一门既无运动,又分离存在的纯形式的存在,这就需要“神学”进行研究了。
大体的说,在亚里士多德并非非常清晰的分类那里,形而上学研究普遍的存在和它们的原因,物理学研究具体的,经验的“可动”的存在,神学,则研究的是作为形而上学中存在的一个“特例”,是研究兼具实体性、独立存在和无变化的“存在”的“科学”,即亚氏笔下的第一推动力。
在亚氏看来,“神学”考察的对象要比形而上学更为卓越,如果说物理学是亚氏体系中的形而下,那么神学就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这也正好符合作为本文主题的这句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其认识论途径是这样的:从身边的经验的事物,逐渐认识普遍的存在,再到最完美、最终极的第一推动力。
当西方步入基督教时代后,神学的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是研究圣经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logos也就是上帝之道或上帝之言(word)的学问。基督教学者研究圣经,也并非总是从外在的“理性”出发,比如在教父时期有两大学派针锋相对: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倡导以字面意思解经的“循规蹈矩”的安条克学派和鼓吹以灵性和寓意解经,更接近神秘主义的亚历山大学派。
对基督教学者而言,上帝或第一本原,已经籍着基督进行了自我启示,这种启示要远超过人类可怜理性的任何研究和把握的努力。于是,亚里士多德对“特殊存在”的研究已然有了“现成的答案”,神学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转变成了用哲学和逻辑研究圣经的启示,并将其准确传达给普世。在教父时期,能被称为神学家的教父寥寥无几,除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圣约翰,只有纳西昂的圣格里高利和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等极少几人才有“神学家”的头衔,以彰显他们为奠定三位一体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科学”science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的skhizein,以及古印欧语的词根skei或skai,意为将对象“撕裂”、“切割”、分类,进而衍生出将深入剖析对象进行研究之意。这种含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现代的科学,其实仅仅指的是以实证和归纳为基础的对客观规律的研究行为,是所有研究活动中的一个分类,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就要从前者的意义上去理解,神学,即研究“神”或“第一推动力”的“科学”。
近代科学肇始之初,科学和神学的界限也不像现在如此“泾渭分明”。牛顿在晚年研究的,就是此类的神学(这同样适用于莱布尼茨、笛卡尔、伽利略的类似研究),但却被简中网络望文生义的群体无聊的贬低为“迷信”,中世纪炼金学者的理论依据,则是相信一切事物在根源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们也许采取了错误的手段,但他们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则未必是错误的。

现代科学的产生,可以笼统的“归功于”奥卡姆那把犀利的剃刀,这把剃刀,蛮狠的剔除了形而上学和神学对一般事物研究的指导。换言之,“现代科学”是在充分认识了自己的“局限”之后才产生的,它只对可以通过实验和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的客观对象发表意见,而对无法或很难真正把握其本质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置之不论(或者说,知趣的不发表意见)。用更接地气的话来说,科学不再涉及诸如“灵魂”、“上帝”之类的话题,而是将这类无法证否的话题完全留给宗教和神秘主义。因此,在涉及灵魂和死后生命之类的话题(或诸如此类的“神学”话题)时,简单的斥之为“迷信”或“不科学”,是简单粗暴且毫无道理的。
往往这样说的人,既不了解科学,也不了解宗教,要么是这个时代培养出的,为现代科学所展现出的直观生产力和爆发力所震慑的迷信科学的“科学”信徒;要么仅仅是只能以“科学”和“迷信”(或唯物论和唯心论,大体而言,那些言必称唯物主义如何如何的人,对哲学和科学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认知)这样劣质的二分法认识世界的没有思想可言的可怜虫罢了。
综上,以西方的智识史发展和认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言,神学始终是科学的终点,因为神学要探索的,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因,是一切科学的原因,以及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人类理性和智识活动最大的目标,即是催迫人类进行探索的源动力,也是人类想要得到的最高答案。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神学”既是动力因,又是目的因,它不断催迫出人类的好奇心,并让人类在好奇心的趋势下不断攀登,尽可能接近那不可言说的至高原因。
如果将佛学也理解为神学的一支,那么科学的终点是佛学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很显然,说这句话的人,显然不是从本文所阐述的意义上去理解神学的,而中国化的佛学,是一种逻辑被大大弱化的所谓佛学,其丝毫不具备西方神学所有的智识和逻辑传统,故而,这样的佛学,或者道教学说,再或者接近于萨满的世界观,则离开本文所说的“神学”更远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