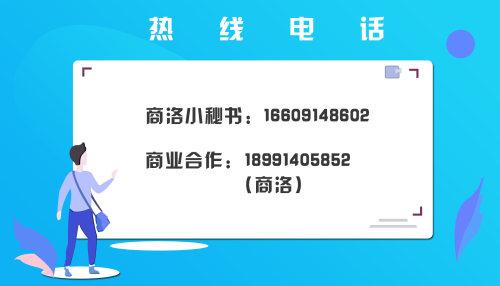学术论文写作的注意事项是什么(学术写作大讲堂)
【专家介绍】朱国华 ,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

要回答我们该使用何种形式的语言进行学术表达这个问题,也许是不易寻找到正解的,因为问题本身可能就意味着一个语言的圈套——我们假设可以存在着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性质的学术 语言体系。但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显然不能认为,学术的语言表述对于学术探讨本身所获得的意义是无关宏旨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假装自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的语言表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无论怎样孤芳自赏,毕竟还是希望自己的论著为人所阅读,而对绝大部分学人来说, 更为迫在眉睫的情势是,我们的表达必须要得到杂志社或出版社编辑的认可。编辑如果厌恶我们的言谈方式,我们甚至可能连学人也做不成。至少在中国大陆,根据我有限的认知,眼下还没有普遍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因此学术杂志的编辑就掌握着生杀予夺的话语权,换句话说,编辑对于学术语言的偏好实际上就影响着我们对于学术表达的自我意识。我这里无意说,编辑是一种代表着特殊利益的学术人, 他们所欣赏的学术语言风格因此也具有特别的趣味,因为编辑的学术眼光毕竟也是一定的学术场域所形塑的结果——,我是想说,考虑到编辑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我们可以暂时把编辑对于学术语言的期待视为我们今天学术共同体集体无意识的某种外在表现。尽管这一简单推论可能化约了学术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但我们不妨把许多编辑对于学术语言的要求视为一个方便的切入点。编辑当然并非一律,偏好也不尽一致,但就我熟悉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们对学术论著的晦涩难解大多是深恶痛绝之的。在这方面,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人文编辑室主任赵明节先生的以下看法还是具有代表 性的:“长期以来,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们的学术著作大多面孔严肃乃至刻板,语言瘦硬生涩。尤其是那些涉及西方学术的著作,不少不仅‘涩’,而且‘晦’,让人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大概著作者本来也没怎么弄明白,一味引用、推演,越闹越糊涂。这还是就内容比较优秀的著作而言,排除了那些仅仅为出版而操作的所谓‘著作’。我就纳闷了:这些著作者是不是诚心要让人望而却步、莫测高深?否则,为什么要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弄得那样云遮雾障甚至面目可憎呢?难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吗?我真的很怀疑,有些著作者是不是有意为之,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问。我总在想,即便是很专业的学术问题,难道就不能用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表述出来么?有什么道理是不能用通俗平易的语言表达的呢?换句话说,我们的专家、学者在锐意学问的同时,是否可以磨练文笔,使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与学问同步提高?”“我非常景慕那些学问好、文章也好的大学问家,任是再复杂、艰深的学理,他都能清楚明白地讲给你听,表述出来不着痕迹,读者接受起来也不费劲。”
这里面实际上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可以理解为一个相当简单的文体层次上的批评,即认为今天许多学术著作的晦涩难解是蓄意为之的,目的 是为了通过表达上的“陌生化”手段(借用一下新批评派的词汇)来欺骗读者,并获得非法的认同。事实上古人常常用这套话语系统来指摘某些文人行文不老实、故弄玄虚的修辞作派。例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写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明人宋濂在《文原》中说:“予窃怪世之为文者,不为不多,骋新奇者,钩摘隐伏,变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读,且曰,不诘曲聱牙,非古文也。乐陈腐者,一假场屋委靡之文,纷揉庞杂,略不见端绪,且曰不浅易轻顺,非古文也。”从这种角度上来说,这一类文体性批评对眼下学术写作不能不说是切中时弊的,的确,我们某些学人的文章刻意摹仿那种蹩脚的翻译语言,其结果是佶屈聱牙,“用汉字写外国话”,其生硬的欧化句式有时简直不知所云。撇开文体恶劣到难以卒读程度的那些文章不提,某些文字功底不错的学者,也不由自主地喜欢将各种希奇古怪而自己未必理解的词藻概念随处播撒,自以为是一种装点门面、提高身价的手段。布迪厄分析了这种“拽词”行为的潜在动机。他指出,教授们故意使用一些高深莫测的概念范畴,旨在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并通过将此学术语言设置为跨入学术场域难以通过的高门槛,设置为预测学术水平高下的区隔工具,拒绝学生的轻易进入,从而维持其学术权威的形象,并牟取符号利益。但是吊诡的是, 布迪厄本人也常常用这种极为拗口的语言来进行学术写作。我们可以比较他在访谈录中比较浅易直白的口语表达与缜密凝重的书面写作之间的不小差别,就会发现,这两者顶多后者逻辑更严密一些,而传达的意思未必有非常大的出入,那么,布迪厄何以采用这样一种繁复冗长的句式来进行他指斥为隐含着教授的符号权力的学术表达呢?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方面。这第二个方面,与赵明节先生所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恰好是相对应的。从赵明节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他相信“任是再复杂、艰深的学理”,如果侥幸碰上文章好的大学问家,在原则上他是能够“清楚明白地讲给你听,表述出来不着痕迹,读者接受起来也不费劲”。换句话说,学术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媒介,它本身是一种空洞透明的中介,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它本身是不 具有独立意义与价值的。使用通透的语言表达,而不失思想的深邃,我认为牟宗三先生对“玄学”之 “玄”的解释颇能切合此层含义:“ 玄者黑也,水深了才黑,所以玄表示深profound的意思。又表示不像分别说那么清浅,好像隐晦obscure。其实玄既不浅也不隐晦。”牟宗三先生这里没有提到学术的语言表达,但是这里他无意中把学术语言预设为水一样清澈无碍的介质了:思想的表达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只是当它达到了一定深度才给人感觉是隐晦的。学术语言的妙处是否在于让人忘记了它的存在呢?从旨在去名执、离言缚的老庄禅理的角度上来说是这么一回事。在这里,我们似乎无需引用那些诸如“舍筏登岸”、“忘筌取鱼”、“得意忘言”之类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
语言从它所表征的思想内容中被无情地抛弃了,但语言是否确乎无足轻重呢?一种深刻的想,是否可以不倚重特定的言说方式也能成功地传达自身?进一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语言,尤其是旨在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性把握的社会理论,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一样,只要表达精确、清楚,它本身的风格特征可以忽略不计呢?笔者 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相对而言,我们可以把概念所强加的同一性指称自然的或物理的事物,并保持言说的相对有效性,但是,对于具有千姿百态、各各不同的人类社会,我们会发现,要把握社会的个人、社会实践或社会总体,任何既定的语言系统都可能是不够用的,其表征功能总是不能完全满足将其客观阐 释的需要。然而在任何社会,总是存在着一整套用来描述现实的话语系统。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中国古代的汉儒或是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他们都可以用一种清晰、简化、浅近的语汇来描述世界,他们的语词在体制的支持下得以不断的再生产和再阐释,已经变成了日常化和自然化的语言,被认知为具有普遍性、中立性、客观性和共享性的交流语言本身,从而难以与意识形态脱尽干系。换言之,简单、通俗和同一化的日常语言背后常常隐藏着权力关系(请想一想“农民工”或“白领”这样的常用词引起的联想),它的表征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却以“清楚明白”的方式冒充自己为理想的纯净的语言,并自以为可以表征一切事物。因此,追求自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操控,首先必须要破除日常语言能自然而然表征现实的神话和默识(doxa),必须要从貌似透明的语言幻觉中走出来。事实上,“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几乎总是述行(performa-tive)的:它包含着希望、劝诫、责备、秩序,等等。”语言以某种不言自明的隐蔽方式参与构建了社会现实。
要粉碎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语言的符咒,要抵抗以常识面貌出现的日常话语背后的压抑性符号系统,就必须拒绝其清晰性的承诺,因此,一种有效的社会理论必须人为地创设出某些概念术语,创设出某些特殊的表达式,由此才可以突破既定规则系统对我们进行的无意识操控,并表征日常语言所无法表征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布迪厄采用费解的学术话语是有意为之的,是可以得到其合理化阐释的:“虚假的清晰性经常是统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认为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人的一种话语,因为一切都恰好如此美好。保守的语言总是求助于常识这个权威。”同时,“生产一种过于简化和具有极度简化作用的关于社会世界的话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你正在提供可以被用来危险地操纵这个世界的武器。”这样,布迪厄某种程度刻意造就的艰涩文章,并非像葛兰西那样,以支离破碎的语言避开黑暗的政治当局对自己红色写作的关注,也不仅仅是 拒绝别人漫不经心地阅读自己,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乃是这种政治批判意识的策略考虑。
但是,所谓策略的考虑,难道不是另一种工具主义的观察学术语言的方式么?用自己质感的风格化的语言技术颠覆依附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化的浅易的学术语言,这种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对学术领域的移植,如何能够保证其爆破工作的有效性,并保证自身不会被收编为另一种形态的意识形态工具呢?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的著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被安置到教育体制的语境中被师生作为知识而传播,并因此取消 了其指向实践的政治冲动效应。所以,我们还应该进入另一个层次,思考一下学术语言本身是否即是学术内容的一部分,或者说,思考一下学术语言所采取 的形式是否即意味着学术论述的内在构成要素。
那么,我们说学术语言转化为学术内容,那该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意味着一定的学术思想总是呼应着与之相应、不可更易的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 举例来说,尽管庄禅哲学强调着对语言的不信任的态度,但实际上,语言即便对它来说也绝非可有可无的中介。像“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这种 “……,即非……,是名……”的表达式,在短短五千言的《金刚经》中出现凡28次。似乎可以说,《金刚经》的般若智慧,如果不借助这种奇特的句式,不仅 无法呈现其圆融辩证、合乎中道的神髓,而且佛学的真理本身就难以传达:因为显然,如果不借助于似乎悖谬的双重否定,体悟不即不离、诸相非相的解脱之境是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简单的事实对应于简单的话语方式,而社会现实实际上是复杂的,因此它也吁求着我们采用复杂的方式来表征它。数学的或物理学的事实,是提纯化、模拟化和理想化之后被构建出来的简单事实,因为它撇除了任何偶然的或主观的因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线性公式的形式予以表征的;但是社会事实如果剥离了偶然的或主观的变量,被形式化、抽象化为一些定理或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是如其所是的社会事实。
《德国悲悼剧的起源》的开头,本雅明尖锐地批判了19世纪以来哲学通过系统化的概念以几何学的方式来捕获真理的努力。他认为,这种数学式哲学写作越是清楚地表明一劳永逸地解决表征问题乃是 真正知识的标记,越是表明它与真理领域的无缘。因为哲学写作的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面对表征问题。把握真理的语言本身绝非无关宏旨:“如果哲学作为真理的表征,而不是作为获取知识的前导,如果哲学仍然要忠实于其自身形式的法则,那么,形式的实 践——而非在系统中的预示——就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那么,这种形式该是什么样呢?本雅明认为,中世纪的用于神学研究的那些论文由于其隐含的神秘性质,颇可以作为范例。数学这样的领域追求的是知识,它是某种占有,即意识对客体的掌握;而真理必定是一种自我表征,因此它必然内在于形式之中。真理作为某种绝对的、神圣的、纯粹的本质,与知识不同,不是任何科学演绎或逻辑推论可以轻易接近的。因此,要表征真理,迂回枝蔓和断片残章式写作形式就是必然的。没有目的意图和线性逻辑控制的文笔,犹如丧失串线的念珠,四散开来,每一个获得解放的念珠都吁求着读者不断停下来静观沉思它的光辉。只有这种跳跃性的文体才能打破知识连续性给我们造成的真理假象:“思维过程不知疲倦地创造种种新的开端,以迂回的方式重返其原初的客体。这种连续的停顿是为了换口气,是最适合于思辨过程的一种模式。”换句话说,将在时间中推进的线性句式,割裂为一簇簇空间化的句群,也就是所谓星座式的或单子式的写作方式,才是促使我们领悟真理的恰当的表征方法。本雅明滞重深奥的语言风格本身就实践了他的这一理论观点,他的追随者和批评者阿多诺,在许多写作中,如《启蒙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或《美学理论》,也采用了这样的写作风格。因此,“晦涩”一词我们不妨可以分解为晦与涩两方面:晦暗,是因为我们不可以清楚地直观真理,这也就促使我们更深地接近它;生涩,是因为增加感受的难度可以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停下来陷入 沉思。这样,与清晰的话语相对应的是不加反思的常识,而晦涩的话语意味着表征真理的可能性,它对于简单清晰度的拒绝,乃是为了进入更深层次的清晰:“清楚地叙述的最佳方法其实就存在于以复杂的方式所作的叙述之中。”
让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学术界流行的对于晦涩文风的批评,只是从最初步的中小学语言教学意义的文体修辞角度来说,才是具有其完全的合理性 的。学术语言之所以常常显得费解,对有的论者例如布迪厄这样的人来说,是因为浅近易懂的常识性语言背后可能掩藏着权力支配关系,因而必须要采用炸毁日常语言的技术手段,来让被意识形态催眠的 读者重新得以唤醒。在这里,晦涩的语言是一种政治批判的策略;对另一些论者例如本雅明来说,语言不是工具,它本身就是构成真理性表征的内在组成部分。知识可能必须求助于采用均质、空洞和同一的数学语言,因为它旨在占有对象;对真理则只能表征,而与连续的、线性的、逻辑的推论式论证不同,真理的表征呈现的形式是断裂的、迂回的、神秘的、残片状的、无固定意图操控的,引起读者反思的。我想补充的是,对较多处理某一些涉及经验定量分析、侧重实证性的社会科学,清晰透明的学术语言是更有意义的,而对于与自然科学距离更远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处理社会世界的理论命题,布迪厄或本雅明对于晦涩语言的辩护,对我们来说,至少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版权归原作者和编辑部所有,编选时有改动)
【学术写作大讲堂】,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