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代会文案(十代会特刊文学)



随着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第十次全国作代会于14日至17日召开,五年一度的文学界盛事如期来临。从九代会以来,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了众多反映时代呼声、扎根现实生活、弘扬中国精神、激发文化自信的优秀作品。近日,本报公号以一组“文学五年”为关键词的系列文章为大家分享了作家、评论家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文学新人、跨界创新等话题方面的阐述,打开了五年来活跃在文学界的重要现象与议题。
十代会的召开是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文学界面对的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心怀“国之大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格局,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文学的力量,众多引领未来文学界发展的新议题、新思想将在此萌发生长。
为此,本报最新一期特刊邀请程小莹、陈丹燕、孙惠芬、葛水平、韦伶、张庆国、张莉、李德南八位作家、评论家从不同角度讲述文学与时代共振、讲好中国故事、青年精神等话题,传递“文学,在这里发声”的辽阔声域与前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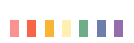

青年写作与
问题意识
文 / 张莉
期待青年作家们更为新锐的写作,无论是从社会问题意识还是文学表现手法上,我们都需要新的、有强劲能量的写作。
最近两年,我开始关注青年写作问题。这与我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教学经历有关。每个学年,讲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我们课堂上都会有热烈讨论,甚至课后我也会收到年轻人的来信,他们会谈林震的意义,会谈到林震所带来的困惑和思考,谈林震为什么要这么做和为什么不那么做……很显然,林震是能够长久引发青年读者共情的人物形象。在当年,王蒙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只有22岁,这是典型意义上的青年写作。这也让人深刻意识到,真正的经典意义上的青年写作,所关注的问题绝不只属于一个时代,它也会在未来激荡每一代青年人。

正是基于对我们时代青年写作的关注,2021年,我在《长江文艺》主持了“新现场”专栏,邀请青年一代批评家聚焦“90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们。从5期到12期,专栏先后关注了陈春成、周恺、王侃瑜、王占黑、修新羽、渡澜和杜梨等六位作家。之所以挑选这六位作家,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有着不同的美学追求,读者从他们的写作中可以看到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丰富面向。
作为2020年横空出世的全新面孔,陈春成带来惊喜,它让人看到一种优美的语言传统正在青年一代作家笔下“复活”。读周恺的《苔》,会想到李颉人的《死水微澜》,那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坐标。它让我们认识到这位作家于语言深处和历史深处写作的野心,也认识到这样的文字既是传统的也是别开生面的,有属于我们时代的文学质感。
《长江文艺》
“新现场”专栏


作为科幻作家,王侃瑜的写作是基于女性视角的所见,但这样的所见也并不是外在的、观念化的写作,相反,这样的所见深植于文本内部,与情节和人物共生,也因此,读她的作品会有共情,会和人物有共同的震惊和喟叹。王占黑的写作特点在于回归生活,回归生活的逻辑、生活的伦理。日常与烟火是她写作的底色,而就在那种“不奇”中,这位年轻作家写出了另一种活色生香、另一种风生水起。
修新羽的《城北急救中》,书写了我们时代在边缘处努力生存的男女青年,尤其是那位女主人公,她清醒冷静,落落大方,即便贫穷困窘,也不自怜自艾。读《城北急救中》时我想到鲁迅的话,“正因写实,转为新鲜”——正是因为对“切实”的尝试,才使得修新羽的写作“别开生面”。渡澜让人想到先锋派写作,她的笔下万物有灵,人和事有如童话寓言般存在,尤其是她的语言,直截而简洁,比喻奇诡。杜梨关于颐和园的非虚构作品引发关注,她细致而贴近地描述颐和园里游人们的众生像,书写了那些北京人生活中跳脱、欢乐而又有趣的一面,同时又穿透了那些表象。
当然,最近几年编选“年度小说二十家”、“年度散文二十家”及“中国女性文学作品年选”时,我也收录了当代文坛出现的更多新鲜面孔,这些青年写作带来了欣喜,但是也不得不说,很难用年龄或代际指认青年一代的写作,他们的风格和审美各有不同,越来越有气象。

青年写作其实历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今年上半年,在接受记者王青采访时,我们谈到了青年一代的写作。她谈到了围绕青年写作的两个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他们更注重私人性的“我”,而失去了对更为宏大的精神力量与信念的追寻;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天青年一代的文学书写太过强调现实的议题性,而丧失了所谓的“文学性”。她问我对此有何看法。
这些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如何理解作家书写“我”?关注“我”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不是说不能写“我”,或者不能写个人化的生活。但很多作者只是关注一个物质的“我”,那是没有精神能量和深度的“我”。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的创作者是把“我”给降维了。写“我”也可以写出尖锐、深刻、强大的主题,因为“我”是“我”和历史、“我”和时间、“我”和命运之间重要的连接。如果对于“我”要成为何种意义上的“我”、何以成为“我”能有思考、有反思、有质询,那么,“我”也会盛载更大的精神潜能。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作中,林震是站在“我”的角度的思考,是关于“我”与世界、“我”与社会的思考,是关于“个我”与“公我”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个人经验,但更属于时代经验。2020年陈春成的《竹峰寺》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当然在于与众不同的语言追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追求里,作家塑造了一个有意思的“我”,“我”身上有历史的沉淀,也有与世界的若即若离。作家在写我们时代的“我”,但这个“我”并没有被降维。
我们讨论的关于青年写作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实议题,其实这也是新文学发展脉络里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是典型的有着现实议题的写作。但是,那些作品中,大概也就是鲁迅的作品留了下来,因为它是艺术性和社会问题的完美结合——真正的社会问题写作并不能只是关注一时的社会问题,而是关注长久以来我们要思考的精神深处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青年在课堂上依然热烈讨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想,正在于小说关注问题的普泛性与持久力。但同时也要强调的是文学品质,作品要有思考、有问题意识,同时也要写得好。
文学在整个社科领域的影响力变弱了,电视剧或者电影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力毋庸置疑。这跟所谓的从文字/纸质传媒到影像传媒的变化有关,但问题是,哪怕是影像时代,文学原本也该是很多影视剧改编的原动力,但今天我们却越来越难看到纯文学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作品。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家介入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严肃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风起云涌。当年,邹倚天塑造的“红衣少女”安然,那个健康的、有生命能量的女性形象曾引领过一个时代,而后来我们很少看到这样性格鲜明、多元的女性形象了。现在,相比严肃文学,反倒是网络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够戳中大众,很多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能够抓住大众所关心的问题,何以如此?我想,是因为网络作者比纯文学作者更渴望抓住我们这个时代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期待青年作家们更为新锐的写作,无论是从社会问题意识还是文学表现手法上,我们都需要新的、有强劲能量的写作。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出版社资料

秋季文创与2022年订阅已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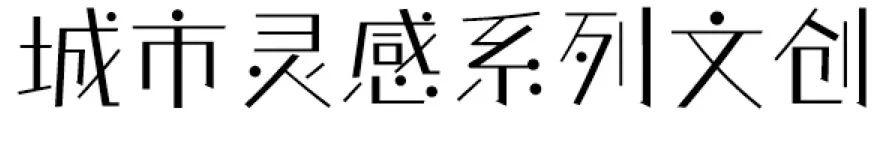

进入微店订购文创
秋季文创线上首批限量100份
报纸订阅线上渠道
中国邮政平台
→
本报为周报,周四出刊,通过邮局寄送,邮发代号3-22,全年订价61.8元
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