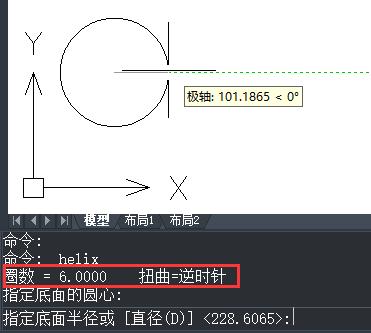不会数理化(整不明白数理化只能做个)
这是第二个原创者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个有故事的创作者
可以联系我们!
晏向阳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英语教师,同时还是一名文学翻译。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得来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偏文科,数理化不是他强项,这也让他成为一个学不明白数理化只能做个“翻译家”的人。在晏老师眼中,翻译承载着开阔眼界,沟通思想,助力建造人类“通天塔”之使命。从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一个教师的儒雅随和,也可以看到一个翻译家砥砺前行的坚韧。

01
如果要从头说起的话,我对翻译的兴趣应当追溯到父母亲是老师这件事上。母亲是英语老师,父亲是语文老师。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自己语文和英语要学好一点,而我也确实天生就恐惧数学,连背个乘法表都费半天劲,所以就一直偏文科吧。
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我是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文科,其实相对来讲,那时候在我们县城中学里,周围的人一般都选择理科,因为(理科)教学质量会好一点,考上大学的人会多一些,选文科考上大学的人就很少,但是我还是坚定地选择文科,因为实在太怕数理化了。在文科班要想跟别人拉开分数的话,英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科目,所以我一直英语学的还可以。
后来上了大学,选的也是不用学数学的英语语言文学,我考上的是江西师范大学。既然是学了这个,那肯定是要做点翻译的,这个就是你的专业嘛!
我毕业的时候分在我们南昌的一个师范学院教书,当时有空的时候会稍微翻译一些文章,那时候还能投稿到期刊上。后来到了北京,就觉得这方面有必要发展一下。我读研时候的翻译老师还挺不错的,跟着那个老师学习之后,的确觉得自己有点长进嘛!就跃跃欲试地要翻译一点东西,发表了几篇文章之后,认识了一两个编辑,然后有的编辑就会邀请你去做翻译。我记得我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小童书,关于沙漠探险的。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一步一步开始正式走上翻译道路的。
其实一开始我对翻译也谈不上特别喜欢,但跟数理化比起来那我还是选翻译,确实是因为真的不喜欢数理化!在文科里面你总要选一个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吧,所以就这样走上了一个外语翻译的道路。
如果要继续说我为什么从事翻译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受文学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能读的书不多,那时候有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节目就是中午12点到12点半的评书和小说连播,一般播的是单田芳、袁阔成的评书,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东西。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有一天突然开始播王刚老师演播的《神秘岛》。那是第一次从广播上听到外国小说,当时就觉得很新奇,开始对外国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接触到了史蒂文森的海盗小说、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那时候我们县城里面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借点书,我当时是把那里面能借到的这些外国通俗小说差不多看了一遍,导致我对译制片感兴趣了,虽然译制片充满了跟当时社会环境反差很大“外国味儿”,但当时吸引我的正是那种异国情调,“哦,我的上帝呀!”什么的就会让你觉得跟我们中国的东西不一样!从这个方面慢慢的对外国的文学感兴趣了。
听评书我是跟着我哥哥学会的,而我姐姐当时已经开始发表作品了,她在《儿童文学》上自己写了一篇安徒生童话的读后感,发表后竟然还获奖了。获奖的奖品就是一堆的文学书籍,其中有一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法国作家图尼埃对鲁滨孙故事的改写,叫《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是以《鲁滨孙漂流记》里的礼拜五为主人公的故事。看过这本书我好像忽然开窍了,突然就觉得这个文学真的是一个前后勾连的世界!前面的一个人可以写鲁滨逊的故事,后面一个人他可以把鲁滨孙故事当中的其中一个人物拿出来再写一部故事。后来我才知道《礼拜五》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一部作品,在这本书里鲁滨孙并不是那么积极向上的有资本主义开拓精神的人,他是干累了感到绝望了就会躲到一个泥潭里,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的感觉,那当时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它是个完全不受所谓现代文明约束的灵魂,最终反而把鲁滨孙的刻板资本家性格给扳回成自然天性了——原来文学不仅要写所谓积极向上的东西,还可以写个人深层次的体验!文学不一定是非得用来宣传方向、主义之类的东西,还可以写个人体会。这些引导了我对文学感兴趣,所以后来自己学了外国文学。
既然我对文学感兴趣,又学了外语,自然而然地会想着去翻译一些作品,会思考如果把它转化成中文会不会同样吸引人。我本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写的是关于狄更斯的论文,他的《双城记》当时我好好地看了一遍,就写了一些文字。到了读硕士的时候开始对一些现代派的小说、反战小说、战争小说比较感兴趣。比如库尔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这类战争小说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反战阶段了,不再去描写英雄主义,全都是反英雄的东西,这就开拓了我的视野。在没接触过这些现代主义作品之前,我觉得人生是非常严肃的、要不断的上升的,就是所谓的达尔文进化主义,直到看了这些作品,就觉得人类的历史未必都是进步的、光明的,也有曲折倒退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需要思想来表达出来。

《如果这都不算好,什么算?》 库尔特·冯尼古特 著 晏向阳 译
02
刚开始做翻译,是有困难的,而且有些困难不仅是当初经历过,我到现在也一直在经历着。其实中英翻译最主要的还不是语言上的问题,毕竟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好了,你可以上网搜索各种各样的词典、网络信息,它们都可以帮助你。但是最麻烦的是文化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在原书里,人家都觉得不用讲的,他也不会有解释,你在网上搜可能也搜不到有人解释的这个东西,因为懂的人没觉得需要解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只有进入那个环境里面,去跟别人互动以后,才能慢慢体会到。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一直都存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可以自己想方设法地通过结交朋友、到国外参观、去留学,这些都能够帮助你把文化体验感提升一点,但是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你毕竟还是在国内。其实那些在国外的华人做翻译会比较有优势。当然了,现在随着网络发展,在网络上的交往肯定会越来越多的,可以克服困难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就反过来。刚才说的主要是英译中,如果中译英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有些文化方面的东西,你意识不到你这样翻译过去,人家可能会觉得不好,这个还是要靠你不断地去提升。所以我们翻译其实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职业。我是通过了翻译资格考试的,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每年要接受一定学时的培训。那这些培训不仅是说你要在专业上提高的培训,而是说你要保持一种跟业界的发展、其他同行们还有一些专家们的交流,才能保证你在这个文化方面越来越精深。所以说这也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方式!

《黑河钓事》 科伦·麦凯恩 著 晏向阳 译
03
翻译家基本上就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人,因为翻译不能背离原文去完全做自己。我觉得翻译家跟作家的区别,一个是在于翻译家有更多的培训,受更多的束缚,在原创性上没有作家那么强。因为作家要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翻译家都是为他人做嫁衣。但是事实上如果人能够在戴着脚镣的情况下跳好舞蹈的话,他去写一些作品,应该也完全没问题的,主要是看个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翻译家跟作家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出了一两部作品的作者当然他就是个作家,可一个出版了十来部作品的人却不敢称自己是翻译家,只敢称自己是翻译者。还有,这两者的全国性组织,一个叫作家协会,一个只能叫翻译者协会。所以就说明大家对翻译家的要求更高。我们文学院的班级取名字的时候,还纠结是叫做翻译者班还是翻译家班。老师们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敢称自己是翻译家?翻译要求高是因为译者们翻译的作品往往是已经经过了检验和挑选的作品,像我虽然自己没写过什么作品,但我翻译的都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就会觉得你的水平要配得上作家的名气,对你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在鲁迅文学院的翻译家班学习
04
在翻译界,信、达、雅是一直在讨论的东西(“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这个概括只有三个字,可见它的抽象度非常高了。一般来讲,我们去看一部作品,首先如果是作为一个完全不懂外语的人来讲,是他能不能看懂。然后作为懂外语的人来讲,会去追求能看懂的前提下,你是不是很好地表达了原来的意思。最有争论的其实是“雅”字,一定要把原先人家不好的语言都变得文雅华丽才好吗?还是说就是要准确地表达原先的情绪、身份、文化背景等等意思?随着语用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等等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雅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更多的争议了。我自己翻译过程中的个人特色和习惯是肯定有的,因为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自己的一些限制吧。这个可以说特质、特色也好,可以说限制也好,或者特长也好。当然,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特色给充分地融合到作品当中去。但是基本上来讲,一个翻译的职业道德还是你应该要尽量地去理解原文,按照原文的特色来翻译。但是你插入了自己的东西,那也是没办法的,翻译界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翻译即叛逆,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100%地把原文的意思情感都表达出来,所以你只要翻译了,你就有背叛。翻译得好不好,融合得好不好,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如果融合的好,那你就有可能会成为经典,比如说像傅雷的翻译作品,他个人的色彩也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他跟原文结合得好,所以就成为了经典。

《大自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托尼•朱尼珀 著 晏向阳 译
05
挑选翻译对象这个其实就跟一个演员挑选角色一样,都想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但是往往翻译市场不由你来决定。有的时候出版社没有提供给你特别喜欢的作品,你也只能自己挑选可以接受的作品。我付出最多心血的译作应该就是福克纳的传记《成为福克纳》。因为福克纳本人的作品就非常的难懂,写他传记的人要不断地穿插引用,再从逻辑上勾连、判断他的艺术跟他的生活中的情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所以是相当复杂的。为了翻译这本书,我还特意去了一趟美国,在东南密苏里大学的福克纳研究中心待了一个月,向那边的老师们请教、沟通。即便如此,它未必是我一个最好的作品。前两天做纪念福克纳的活动,在豆瓣上带着网友们共读这本书,我又重新把它看了一遍,确实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佶屈聱牙的地方,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改进一些。翻译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只要愿意花时间去钻研的话,你总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成为福克纳》 菲利普·韦恩斯坦 著 晏向阳 译
06
我认为翻译这项工作的社会责任基本上就是开阔人们的眼界。为什么七八十年代会有一个大的文学爆发呢,其实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进来了一大批作品,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翻译的一个高峰啊。在这次福克纳共读活动,网友们提到余华、莫言都说自己当年读到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后大开眼界,尤其是读了福克纳之后,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路就打开了。现在的互联网不一定是打开了你的眼界,它有可能是更进一步地禁锢了你的视野,因为他总是把你喜欢的东西都推给你看。作为一个翻译家要养成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看,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吧!像我们翻译界最最闻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通天塔:以前只有一种人类语言的时候,大家能够通力协作,想造一个通天塔企图登上天堂,后来上帝就把我们的语言打乱了,我们变得彼此无法沟通。所以说翻译的责任就是帮助重造一座通天塔。

《午夜北平》 保罗•法兰奇 著 晏向阳 译
07
翻译领域的抄袭比较难判断。在前些年纸媒时代的时候,就存在着大量的抄袭活动,但那种抄袭就是把人家好的译本对着人家的句子重新改一遍,这其实就是一种抄袭。但是确实很难鉴定,基本上除非非常的粗制滥造的那种作品,直到担心它要污染我们的语言、污染我们的文化的时候,才会被人注意到,否则的话很难被读者关注到。在那些烂书的滋养下,再进行网络创作的话,确实是会弄出一大堆很烂的作品。现在的网络语言会被人诟病,可能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08
我还在高校任教,其实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是做翻译最好的一个身份。因为我可以支配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多做翻译,可以帮助做研究、教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好的想法迸发出来。最近几年,我开始转做行政工作,外事翻译(主要是中译英)之类的,这也就可以锻炼我的英文。其实白天工作和晚上自己做翻译虽然都是英语相关的活儿,但中译英和英译中切换可以调节一下(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接到更好的本子,然后能够发挥得更好,真正地翻译出一些能够留下来的经典吧!但是翻译行业,包括整个纸媒行业还是挺难的。其实我有好几本译本,交稿好几年了,人家都还没给出,确实是整个行业不景气。刚才之所以说《成为福克纳》是花了我最大心血的,也是因为我在翻那本书的时候,我的右眼出现了视网膜脱落的情况。那时候我自己也被吓到了,不知道这份职业还能不能持续下去。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制定什么宏伟的规划,只能说慢慢来吧,我还是会坚持的。毕竟翻译可以一直做到老,技艺还会越来越纯熟。

(图片源自网络)
文章:整理于晏向阳采访
编辑:吕圣芳、小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