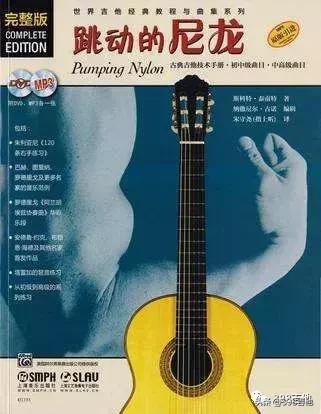观众向左毕赣(和毕赣一起洗头)

2018年度突破导演
毕赣
毕赣一直很排斥“艺术家”三个字。今年戛纳电影节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凯里,一个看着他长大的阿姨见到他,说了句,艺术家回来了。从那一刻,他开始认可“艺术家”这个头衔了。“什么奖项也好,鉴定也好,我都不认可。但像阿姨这样的人,说我是艺术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这个领域,却跨越了她的认知去理解,证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见的。”毕赣,1989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中国导演、编剧、摄影师,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2015年,他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作品《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银豹奖以及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2018年4月,他再次执导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定为2018台北金马影展的开幕影片。
❶
走出凯里,回到凯里
毕赣走进北京一条胡同里的老理发店,坐下了,他靠着椅背,从侧面看,黑色T恤绷着肚腩,勾勒出一个弧形。他29岁,有显著的“啤酒肚”,不过拒绝透露关于体重的秘密。
《智族GQ》的摄影师看见毕赣的头发有些长,和他开玩笑,趁这次拍摄把头发理了,毕赣回答,“是该剪了,实在太忙,有两三个月都没进过理发店。”
七八个人在毕赣周围布灯、打光、模拟拍摄,又拉来几个阿姨作为群演,狭小的理发店显得拥挤。毕赣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双手并列摆在双腿上,任由化妆师给他抓头发、抹粉底。摄影师让他对着镜头念对白,他的音调也毫无变化。
毕赣从小就在贵州凯里的一家理发店长大。父母很早离异,母亲独自一人开着理发店。他每次上下学途中都会到店里待一会儿,扫地,陪母亲聊天,有时直接上手帮顾客洗头,一直洗到他前往山西念大学。
毕业后,毕赣又回到凯里,家乡有湿气缠绕的山,“有山就有树,树会冒芽、开花,再到结果”。他在这里能感到时间流动,做梦,梦到在层层叠叠的时间里,人从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
现实却远没有这样梦幻,他首先被朋友介绍去了一个广告工作室,老板总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有天他和老板吵架,老板说滚,还说,“你有才华,但才华能当饭吃吗?”
这段挣扎与奋斗的经历被媒体反复渲染过。他接着去拍摄婚庆,考客运站公务员,靠说服母亲给了他两万块钱开始筹备电影,花完后又去考爆破证。毕赣的老师得知他要去当爆破员,咬牙掏出自己积蓄,他才能接着找来自己的亲戚朋友,20个人挤在两个群租房里,拍了两月,才有了《路边野餐》。
电影最后成了一个“惊喜”,也让无数聚光灯投射在这个小镇青年身上。《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拿下最佳新导演奖,之后又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也是毕赣的姑父,他回忆说,亲戚朋友一下都没法接受身边有个“天才导演”,《贵州都市报》报道“凯里导演毕赣书写传奇”,亲戚邻居只要看到,就买下报纸,送给毕赣的奶奶。
奶奶不懂电影,只知道是个好事。又有邻居亲戚托话来,下次毕赣要拍什么电影,你帮忙推荐我家孩子去当演员。等话传到毕赣那里,他没什么反应,只说再看看,有适合的可以。
T恤 Dior Homme
变化在毕赣身上悄悄地发生。毕赣以前每周都能去奶奶家,这两年一两月去一次。奶奶今年搬了家,在这之前,她住在一个封闭集中的老小区,里面有一座桥,每天都有互相认识的邻里在上边乘凉、唠嗑。毕赣现在得等到天黑,等到别人看不见他,他才去看奶奶。
当时,毕赣已经在上海开办荡麦影业,筹备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总是需要从贵州来返上海,家里写一段时间剧本,又跑去上海谈演员,确认资金,筹备前期。毕赣不得不走出凯里,现在,毕赣也要走出《路边野餐》了。
❷
从长镜头,到长镜头
在《路边野餐》那个令人瞩目的40分钟长镜头里,毕赣把时间缝合了起来。理发店是一个关键性场景,主角陈升在这遇见了自己的过去。长满黑色霉菌的墙上贴着过气女星的头像,陈升见到自己逝去的妻子张夕,他把小手电筒的光照进张夕的手掌心,皮肤泛着透明的精致的红光,陈升说,自己仿佛见到了海豚。
诗意的长镜头背后是糟糕的拍摄过程。剧组前后排练了20天,把剧本分成七八个局部,一个个排练。毕赣让摄影师和录音师分别坐在两辆摩托上,跟着设置好的路线。他们边拍边做处理,文本里不适合的马上就删掉。毕赣说,摄影师、录音师、演员之间要协调处理,工程庞大到不可想象,而且资金非常紧张。
毕赣觉得这段镜头遗憾太多了,他们一共拍摄三次,只有第一次的能用,但抖动得厉害。他最后一次找了一个废旧的上磁带的DV,想用一个“过时的”机器去拍这段影像,可DV太小,没法很好地操控。
这次,毕赣有了两千万的融资,决心要把《路边野餐》的技术瑕疵弥补回来。《地球最后的夜晚》仍然讲述一个在贵州凯里和虚构小镇荡麦发生的故事,罗纮武(黄觉饰)在离乡多年后,为处理父亲后事重新回到凯里,在挂钟内发现的一张旧照促使他开始寻找曾经爱过的女子万绮雯(汤唯饰)。
重头戏依旧是电影后半部分的一小时长镜头。黄觉摇着煤矿矿车,深入到十二年前的那个黑暗的夜晚,3D部分也由此展开。毕赣希望能像《路边野餐》一样通过持续的戏去获得时间,“前面一部分应该是断裂,像记忆,后面的那部分就应该是一个特别迷人的,出世的、不间断的画面,像罂粟,所以我用了60分钟的3D加长镜头。”
但这次拍摄,才刚开机就遇到了困难,毕赣对剧组宣布停机。主任来找他,一天开销几十万,不开机一天就亏几十万。毕赣说,那也不能开,你把导演费扣了。主任又回,导演费才多少钱,扣完了也不够。要知道《路边野餐》前期制作费也就20万,停机一天,就相当于浪费一部《路边野餐》。
毕赣不是不知道停机的后果。剧组一下变成两百人,每天从酒店到片场的油钱都不知要花多少。更别说比他经验丰富的职业演员都在现场,黄觉、汤唯、张艾嘉、李鸿其,停机十几天,怎么安置这些人?如果遣散了,还能把这些人召回来吗?
毕赣对我说,现场还没准备好,演员的档期却已经定下,他没法忍受场景还不完备就开拍,“每天都在解决问题,改建场景,你们可能真没法理解,所以永远补不回来,不停超支”。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并不专业,“我对国内的电影工业、电影制作完全不了解。”他延续了在《路边野餐》的习惯,经常在现场修改剧本。他觉得剧本的故事并没有很大意义,重要的是要抓住一种情感,有时是要抓拍摄场所的氛围和感觉,有时只是有了新的主意。
黄觉回忆说,开头原本定在一个废弃的火车,但开拍的时候,毕赣看到火车快被肢解了,他马上塞了两条烟给工人,说等我们一下,兴冲冲地跑回去改剧本,改成了一个围绕被肢解的火车进行的场景。
还有一场戏是黄觉从水池里冒出来,毕赣对剧组说,他想让汤唯走在水上面,美术部门没办法,就在水里垫东西,想着怎么才能不那么明显,当天晚上把水抽干,垫了台子,为了防滑,又在上面加了布,布在水里要缝起来,又拿钉枪钉。黄觉说,“他就必须有那股劲。”
有时大家一时没法消化毕赣的创作要求,他会“百分之百的坚持”,解决办法是,直接说,告诉他们最后要达到的美学效果。他认为拍电影不是为了呈现一个结果,“电影的时刻是存在于当下拍摄的时刻。比如看见火车一归来,诶,我要用个火车,然后就拍。那个时刻是我自己的电影时刻,一个人想做什么只有一次机会,一种面貌。”
等到了这次的长镜头,最难的还不是摄影,是灯光。长镜头在一个矿里,一层层跌落,一共长达三公里,毕赣说,“要方圆三公里都得打灯,灯光还得有变化,维持住我想要的美感,而且3D的光圈必须维持在4以上,得有很多打光的范围。”
黄志明之前是王家卫的御用灯光师,这次也加入了剧组。毕赣对黄志明说,他想要一个旋转的房间,得360度转起来,但是要把空间切割出来,不能用灯。“一般人估计就走了,而且还是个大师,结果志明老师说好,我去想一下,他想了一个星期,任务就完成了。”
但坚持也意味着代价。剧组更换三次制作班底,电影从2017年6月开拍,原本定在10月结束,拖延到12月,长镜头的最终方案还没能确定,但最初的资金早花完了。此时毕赣仍然对长镜头剧本最后的落点不满意,创作团队建议毕赣,趁演员都在,不如先拍,实在不行就当是一次演练。毕赣心想,我拍过长镜头,我知道要准备成什么样子才能拍,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做完准备工作,毕赣对黄觉说,觉哥,我们回办公室去聊一下剧本。逃回办公室,两人都没好的想法,不愿再聊。毕赣就问黄觉,你手机有《王者荣耀》吗,黄觉说春节前就删了,不打了。毕赣又问,要不再把它下回来,我们一起组个队。黄觉死活不打,毕赣也不好意思自己玩,两人尴尬地坐在房间里,没有说话。
毕赣觉得《王者荣耀》不值得玩,“但确实是心里有点压力,没办法”。黄觉事后才发觉,毕赣当时是在向他求助。
拍完长镜头,毕赣看到素材,觉得不能用,投资方说那回去再考虑。毕赣心想,完了,没机会拍了。如果到最后别人觉得这次还挺好,那怎么办?他心里没底,以前自己做决定就行,现在是拉着一大帮子人下水,都超支这么多钱了,其他人还像小孩一样陪着自己玩。
等投资方回应的那一两个月,毕赣每天待在家里,私底下,他一点点把这部电影里自己公司的股权稀释掉,以换取新投资。母亲旁敲侧击听说了一些情况,问毕赣,要不要我把凯里的房子给你卖了,你继续拍。毕赣回,你那套房才几十万,能顶几天啊?你千万别搞。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会慌张的人,这次压力没地消解,就往脑袋上排。他犯了毛囊炎,后脑勺长一个大包,灌脓,每天吃抗生素,擦药,都不管用。回到剧组,毕赣后脑勺不得不贴着一张餐巾纸,不然脓会让头发粘在一块。有次毕赣想要陈永忠再过一次他的戏,毕赣拍的时候,对陈永忠说,今天状态好一点,别出错,争取几条就过,别让我在这里受罪。
快过年的时候,投资方传来消息,可以再拍长镜头。年三十的前几天,毕赣记得,所有演员的时间就只剩这最后的档期。剧组排练两天,拍摄两天,第一天废了,第二天第一条废了,只有两次机会,第五条终于成功了。
毕赣说“够了”的那一刻,他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后来毕赣和陈永忠一起出去喝酒,毕赣还总是一聊聊回《路边野餐》。陈永忠说,《野餐》就像大家一块玩儿,《地球》承载的东西就太多了,得对得起投资方,还得考虑后续的上映,影展,太复杂。
❸
不妥协,还是不妥协
一个陌生人追随《路边野餐》,一直找到了毕赣母亲开的理发店。毕赣很久以前和母亲打过招呼,遇到这种情况,就说他不在,母亲照着回复,但还是邀请年轻人进来,一起吃饭,结果毕赣刚好就在理发店里。
毕赣一问,发现年轻人是学电影的,他心想,这人是想得到某种精神支持。《野餐》之后,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一次,毕赣还听说,有人因为《野餐》把工作辞了,转行去拍电影。“他们因为《野餐》改变了想法,得到一些力量,人生因此改变,那一部电影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私人的事情。”
“如果连我都变成差不多得了,或者说我使劲全力了都只能做成这样,那些在乎我电影的人会不会很难受?”他停顿了一下,“因为电影太容易妥协了。”
等到5月,戛纳电影节发来消息,《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一种关注单元”。
毕赣带着剧组主创还有投资方一起去戛纳。媒体首映后的第二天,团队得知《地球》“爆”了,多家媒体预测,这是“一种关注”大奖的头号种子选手。《好莱坞报道者》说,“毕赣用《地球最后的夜晚》带我们穿过记忆、悲伤、以及他独特的影视魔法。”《Desist Film》说,“在他的镜头下,电影就是造梦,而在梦里,哪怕再稀松平常的故事也必然都是梦幻多彩的。”隔天的第二场放映,一票难求。
5月19号,戛纳宣布获奖结果。当时陈永忠正和经纪人在街上乱逛,收到消息,《地球》一个奖也没拿。陈永忠问经纪人,这是开玩笑吧?经纪人回答,是真的。他们赶紧赶回公寓,看到大家都坐在那,不说话。毕赣还开着电脑,放邓丽君的歌。
我问毕赣对参加戛纳的看法,他说拿不拿奖不重要,但如果获奖,至少能有个交待。毕赣对《地球》的票房没什么信心,他说这部电影最后的成本高达四五千万,“我觉得就是少给大家亏一点。”
等戛纳结束,毕贛回到凯里,一个看着他长大的单身阿姨见到他,说了句,艺术家回来了。
“我一直都很排斥‘艺术家’这三个字。我也不是想做个艺术家,我是想拍好的电影对不对?”但毕赣说,从那一刻起,他就认可“艺术家”这个头衔了。
“什么奖项也好,鉴定也好,我都不认可。但像那个阿姨这样的人,说我是艺术家,那我就是。她不理解这个领域,却跨越了她的认知去理解,证明我现在做的事情,是能被她看见的。”
采访、撰文 / 李颖迪
编辑 / 靳锦
摄影 / 许闯
策划、执行:本刊编辑部
摄影:许闯
创意总监:Vicson Guevara 时装总监:Anson Chen
文字监制:何瑫、靳锦 编辑:李典 导语:康路凯
时装编辑:吴睿骐 、Jacky Tam
拍摄统筹:陈蔚、单连营 妆发:杨杰
时装助理 张霜晨、利霞、Steven、Jerry、Nico、冯逢
摄影助理:杨锦龙、珍响、绿仔、逸鳞、左舒同
视频策划:GQ实验室
创意:Max Li
制作:宝珂、许乔、曾晨(Chill Studio)
摄影:闫睿
灯光:张付海
执行:姒可欣、LJC
【本文由树木计划支持,在今日头条平台优先发布】
欢迎关注GQ报道(GQREPORT),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