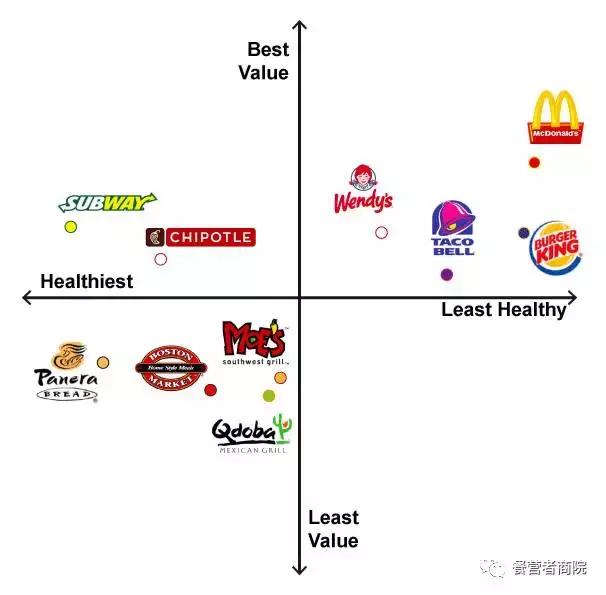林家人接林妹妹回去了(林妹妹去找她的)

1962年摄制的彩色越剧影片《红楼梦》
◎江平
8月6日零时25分,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我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王文娟老师生前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记得去年12月,她生日,我们通视频电话,文娟老师非常真诚地说:“旧社会我学了唱戏,唉,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难演处处演;到了新社会,人民政府把我们当宝贝,再也没有什么恶霸坏人欺负了……你看我现在,九十四五岁的人了,吃的用的样样不愁,生毛病了,公家出钞票住院。我晓得,这一切,都是老百姓给我的呀……”
周总理亲切地称王文娟“我的小同乡”
文娟老师告诉我,她清楚地记得,庆祝上海解放两周年时,陈毅市长问她:今都干啥子啦?她汇报道:上午在人民广场演出,下午在人民公园演出,忙煞了。陈毅同志哈哈大笑:“要得!要得!你们在人民的地盘上为人民演出,光荣,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啊!”
文娟老师后来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为人民服务”这个词语。
而后,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要增加越剧团、京剧团,负责到上海“招兵买马”的是剧作家黄宗江。王文娟和她的搭档徐玉兰大姐二话不说就报了名。那时候,王文娟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薪水也不低,母亲希望做大姐的能给乡下的弟弟妹妹多些贴补,同时也不放心女儿去北方当兵。黄宗江一身戎装,追到了浙江乡下,他拍了拍前胸的标牌,对老太太说:“阿孃!把你家姑娘交给这七个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放心!”
在一旁的王文娟印象极深,黄宗江念这七个字时,“人民”二字,念得特别响亮。多少年后,王文娟才知道,当年黄宗江也是用这样的办法,在王晓棠的母亲面前高声地念了这七个字,然后就把那杭州闺女带到北京总政京剧团,要不然,日后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还真是少了一位女将军女厂长。
来到北京,他们见到了祖籍绍兴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那是1951年的八一建军节。周总理亲切地称王文娟“我的小同乡”,并向大家介绍:“他们放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和高薪待遇,参加解放军,这以后,就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了!”
王文娟心头一热,她从此知道了“人民”二字的特殊意义。年底,王文娟和徐玉兰带着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自豪感,开赴中朝边界没日没夜地演出。有一天,防空警报刚刚解除,站在江堤上的王文娟望着对岸刚被美军飞机炸弹引起的滚滚浓烟,对徐玉兰说:“大姐,我们为什么不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呢?”
很快,她们全团写了血书,坚决要求上战场。1953年4月,他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这一去就是八个月。
去年,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出国参战70周年,王文娟老师也获得了一枚军功章。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祝贺,她看到了,给我来电话:“谢谢你记得我当过志愿军,但是,以后再介绍我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徐玉兰同志,而且要把玉兰大姐放在我前头。其实,比起真正的志愿军,我们算不了什么。你看,我今年身体不太好,住在华东医院,这里把我们当国宝一样,受之有愧啊!想想在朝鲜,我看到有许多小同志,受了伤来不及抢救,回后方的路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断了,就活活地等死,牺牲了……没有他们,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不是啊江平同志?”
这些年,我们那么熟,可她一直叫我“江平同志”。在她看来,“人民”“同志”“文艺工作者”……这些字眼,分量很重。
演到“化蝶”的那一场,一个志愿军战士站起来高喊:“梁山伯,你不要死,你跟祝英台一起逃啊!”
她们在朝鲜的那段经历,真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有一次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演出,里边很大,能容得下上千人。她们声情并茂地唱着“梁祝悲歌”,演到“化蝶”的那一场,一个志愿军战士站起来高喊:“梁山伯,你不要死,你跟祝英台一起逃啊!”一声唤,齐声和:“不要死,不要死!”那一刻,王文娟泪流满面。
还有一次,戏唱到一半,敌机轰炸,电缆断了,坑道里一片漆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一只电筒,呼啦啦,战士们都拿出了电筒,照向舞台,王文娟和她的战友们就在这特殊的追光下,完成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演出。卸妆时她发现身边堆满了战士们送来的慰问品:子弹壳、领袖像章、松树果、五角星……
最让她感动的还是那一沓信上附的一张纸条:徐玉兰、王文娟同志!谢谢你们带来祖国人民的问候,看了你们的演出,我们觉得和平真好,真想活着回去建设新中国,可是明天我们就要到新的战场去了,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为祖国和人民而死,没有遗憾!只是麻烦你们回国的时候,把这些信帮我们带走。没有邮票,我们放了八毛钱,一共十封信(八分钱一张邮票),请回国后贴上邮票寄出,给我们家里的父母大人……
快70年过去了,我们听文娟老师讲这段往事时,她仍然激动得难以自抑。
“您有没有想过也许会牺牲在朝鲜?”我问。
文娟老师回答得特别果断:“怎么会不想到呢?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牺牲了,也是一种了不起,因为我们也穿军装啊,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啊!”
文娟老师话不多,但很热情:
“没有什么小菜,随便吃点,讲讲话……”
“你是志愿军,我也当过志愿军”——当我和文娟老师聊抗美援朝时,她老伴孙道临老师偶尔会插那么一句:“兴许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曾经擦肩而过呢!”
文娟老师的爱人就是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大家从《渡江侦察记》《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革命家庭》《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电影中,都欣赏过他的非凡演技。
我认识孙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为拍摄电影《雷雨》到南通选景,看中了一座清末状元张謇建于1914年的英式三层洋楼,而那个别墅,恰恰是南通市话剧团——我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我们就这么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触。
十年后,我已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1993年,我跟随恩师吴贻弓导演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了开幕式既能有分量又有文化,我们决定请孙道临先生担任司仪。
第二天上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在上海市电影局大门口恭候老先生,九点半差两分的时候,孙先生来了,居然骑着一辆二八式的“老坦克”!我将他迎进会客室,一聊,他才想起来,十年前我们在南通见过,算是久别重逢吧。不用说了,后来他在电影节上的中英文双语主持,让中外嘉宾都叹为观止。
次年,我们一同出访开罗国际电影节,18天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约我去家里做客,就这样,我见到了心中的“林妹妹”——王文娟老师。
文娟老师话不多,但很热情:“没有什么小菜,随便吃点,讲讲话……”
那天,是王文娟老师的老母亲做的拿手菜:糟鸡腿和糟毛豆。饭桌上,95岁的老外婆精神矍铄,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讲话,王文娟老师不时用公筷给我夹菜,也不插言。晚上,孙先生拎出一盒精美的红宝石鲜奶蛋糕:“没有什么谢你,文娟特地买的,带回去给爱人孩子吃。”
文娟老师声音不高,甜甜糯糯的:“我这个人不会讲话的,这次出国,谢谢你对道临的关心和照顾……”
这以后,我们两家人的来往也就多了起来。他们的女儿女婿在德国工作,我就像他们的晚辈,孙先生回故乡嘉善搞电影回顾展,还特地带了我儿子去,一老一小开心地“疯”着,别人还真以为他们是祖孙俩呢!
黄宗江老爷子说:“孙道临、王文娟他们俩加一块,那就是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一首诗。”
两年后,王文娟老师想把《孟丽君》搬上电视荧屏。我立刻表态:不挂名,不拿钱,尽力帮着做一些琐事。文娟老师说:“这下我踏实多了,有你帮道临。”
孙先生当导演,那叫精益求精,文娟老师古稀之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为了贴云鬓、拉皱纹,乳胶把两腮的皮都给沤烂了,疼得钻心,但她却不叫苦,咬牙坚持。孙先生笑道:“看,臭美的吧!脸上将来要是留了疤,我可不要你哟。”
70岁的文娟老师忽然像17岁的少女那样,莞尔一笑:“道临,你不会不要我的。”
我在一旁,忽然想起黄宗江老爷子的那句话:“孙道临、王文娟他们俩加一块,那就是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一首诗。”
黄宗江是他俩的媒人,他最了解他们。
1958年初,黄宗江到上海完成剧本《海魂》。他和孙道临是燕京大学学友,妹妹黄宗英又是大明星赵丹的夫人。一日,约了在白天鹅西餐社小酌,同席的还有上影演员中有“政委”之美誉的张瑞芳,她在电影《家》中和孙道临扮演过夫妻,生活中更是挚友。酒逢知己,孙道临忽然惆怅落泪。赵丹诧异:“小阿弟,哪能啦?”
道临不语,抽泣着。瑞芳大姐快人快语:“哦,知道了,想找个媳妇了!”
大伙笑了。黄宗英指着黄宗江说:“大哥和道临同学、同乡、同龄,这事就交给你了。”
过了几天,黄宗江设了局,很正式地“保媒牵线”。饭后,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彼此不吱声,快到王文娟住的枕流公寓了,还是她先打破了尴尬的场面:“我看过你好许多电影,演得蛮好的!”
“是吗?真谢谢你的关注。我也看过你在舞台上演的林黛玉,很有感觉,不过……有些地方尚可推敲,比如,人物内心挖掘还不太够,一味程式化表演,会把内心的节奏和情感破坏殆尽。”孙道临文绉绉地接了话茬。
王文娟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崇拜有文化的人,孙道临一开口,她就觉得身旁多了位老师,有些小激动。
这以后,两人常在天黑之后出来悄悄地散步,因为都是名人,大白天不敢逛街。通常是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到了家门口,她又回送他,绕了一圈,再把王文娟送回家……就这样,梧桐树下,他们不知演绎了多少回“十八相送”。
接着,电影《红楼梦》开拍,剧中的才子佳人,最终都劳燕分飞,梦断天涯,而王文娟和孙道临却喜期将至。不料,导演岑范直摆手:“不行不行,拍完‘焚稿’再结婚。你们想想,新婚燕尔,甜蜜缠绵,这种喜悦,会冲淡林黛玉在那场重头戏中悲愤绝望的感情,对哇?”
王文娟听了,心服口服,孙道临自然赞同导演的建议,决定将婚期拖到1962年7月。那年,孙道临41岁,王文娟36岁,标准的大龄青年。
1964年10月,女儿出生,而孙道临正在外地拍片,王文娟叮嘱他以工作为重,绝对不要请假赶回来。那两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孙道临便给女儿起名“庆原”。孩子双满月那天,孙道临匆匆赶回,一进家门,见王文娟坐在沙发上,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不躺着休息?”王文娟笑了:“你以为是你们拍电影呢,头上搭块布,躺在床上。囡囡都60天了,你这个现成爸爸,当得倒蛮好咧!”
孙道临觉得愧疚,转身就要上街给妻子买些补品什么的,王文娟喊住了他:“道临,不要去瞎忙八忙的,坐下来讲讲话。过几天有一个慰问矿工的演出,团长还叫我发言,我普通话讲不拎清,你教教,我哪能念稿子,好哇?”
孙道临摇头,说你刚生完孩子,怎么就马上下煤矿?王文娟告诉丈夫,自己的母亲生完她三天就下田做事情了,不能娇滴滴的,要向工农兵学习。
“哟,‘妻’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看来,我娶的不是林黛玉,而是穆桂英。”孙道临幽上一默。
孙先生发现箱子里都是羽绒衫和厚风衣,给王文娟写了一封信:
“我忘了天下老虎一家亲了!‘王老虎’在帮‘秋老虎’发威啊,不然怎么不给我带些单衣呢?”
生活中,王文娟性格大大咧咧的,而孙先生却特别细致。每次王文娟出差,他都会帮她把行李收拾得妥妥帖帖,几十年如一日。有一回,我去他们家,文娟老师让我到客厅喝咖啡和孙道临聊天,自己招呼女儿一起帮孙先生收拾明天出差的箱子。第二天,道临老师到了广州。秋日的羊城骄阳似火,下榻之后,孙先生发现箱子里都是羽绒衫和厚风衣,没有衬衣衬裤和T恤。他上街临时去买了两件可以换洗的衣物,然后给王文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段:“我忘了天下老虎一家亲了!‘王老虎’在帮‘秋老虎’发威啊,不然怎么不给我带些单衣呢?”
文娟老师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道临是很调皮的,有时候还会捣蛋,一点都不死板。“我练声,唱得口干的咧,道临就为我削好梨子,剥好枇杷,让我润润喉咙,吃好之后嘛,我总忘记收拾。有一天晚上我撩开被子上床,吓了一大跳!原来,他恶作剧,把什么梨皮呀、枇杷核啊,装在一只塑料袋袋里,放进了被筒。他在一边哈哈大笑,说下次长记性了吧?他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收拾我这个马大哈的!呵呵……”
其实,文娟老师也有非常细腻的时候。那年拍完《孟丽君》,她跟孙先生说:“送点什么给江平同志吧,老麻烦伊,不好意思呢!”
孙先生沉吟片刻:“对了,家里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给小江做个纪念吧!”
文娟老师不同意:“哦哟,你押着我读书倒也算了,你还让人家也看你的这些老古董啊!江平同志是戏剧学堂出来的,这种书肯定有。我看,要实惠的。上趟你不是讲,出差时和他住一个房间,看到他睡衣睡裤都打补丁吗?说明他是蛮艰苦朴素的,我去给他买一套新的吧!”
那天,文娟老师来看我:“道临让我给你买了套睡衣,我特地挑了两套,可以替换着穿,不贵的,就是一屑屑心意啦!”20多年过去了,那两套布睡衣我已经穿烂了,但至今还留着,因为那是个念想。
文娟老师感慨万端:“我这一辈子,还是很幸福的,遇上了道临……”
文娟老师重情义。在她心中,观众永远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有一回,新版越剧《红楼梦》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主角都是她的学生。那天我也躬逢其盛,在大剧院的门口忽然看见文娟老师,似乎是在等人。一问才知道,是在恭迎老票友。她手上攥着十几张票,悄悄跟我咬耳朵:“现在戏票太贵,有些老戏迷看不起了,我就自己买了一些,约了大家聚聚,也是给我的学生捧场子。”
2007年12月初,我去华东医院看望道临老师,电梯里正好碰到王文娟老师。某层,上来一架轮椅,坐着一位老阿姨,一下子发现了王文娟,高兴得像小孩一样,嚷着恳请她给签个名,但大家身上谁都没带笔,文娟老师弯下腰,握着她的手:“阿姐,你不要着急,你住哪个房间?过一歇,我写好给你送过去。”
到了病房,文娟老师取出一张她和道临老师的合影,用圆珠笔在背面写下了一句话:祝你早日康复。她签上了自己的名,还风趣地对丈夫说:“你也签,你是电影明星,人家肯定更加欢喜你!”
孙先生乐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道临老师的笑容。
2007年12月28日上午,八时许,我刚进办公室,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是祝希娟老师打来的,摁下一听,却是文娟老师的声音:“江平同志,我想跟你说,五分钟之前,道临走了……我昨天离开去大连的辰光,他好好的……我现在心里乱,不晓得找谁,我就想用小祝同志的手机给你拨一个,麻烦你转告一下单位……”
她哭得说不下去了……
当天下午,她匆匆赶回上海。祝希娟老师告诉我,上午在广场上有一场慰问演出,文娟老师咬着牙,还是上了台,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她居然强忍着内心的悲伤,给大家唱了一段《孟丽君》。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段歌是电视连续剧《孟丽君》的开场曲。歌词,是孙道临先生写的。
几天之后,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孙先生。我看见王文娟老师穿着一件灰蓝的中式褂子,一直坚持站立在那里,和成百上千的观众一一握手,感谢大家来送别她的丈夫。
孙老师离开了,文娟老师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武康路的房子,是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一切都让她睹物思人。女儿和女婿特别孝顺,为母亲找了一个新的住地。逢年过节,我回上海也会去看她。文娟老师告诉我:“前几日中秋节,我买了月饼,去道临的墓地……从前他活着的时候,我不懂的事情就问他,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我习惯了,现在,我有时候还会问:道临,这个字怎么念?话说出来却没有人回答我了……”
2019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去香花桥路她家探望,带了些南通的茶食和扬州的包子,这也都是孙道临老师在世时爱吃的点心。我们又聊起了先生。
望着案头孙先生和自己的合影,文娟老师感慨万端:“我这一辈子,还是很幸福的,遇上了道临……唯一遗憾的是他走得早了些,要再能活个十年八年,看到现在日子过得更好了,他会大声地朗诵、唱歌的……”
如今,王文娟老师远行去了,不,准确地说,是“林妹妹”找“舒伯特”约会去了。在天上,他们还会演绎“十八相送”。
(本文作者为中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
来源: 北京青年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