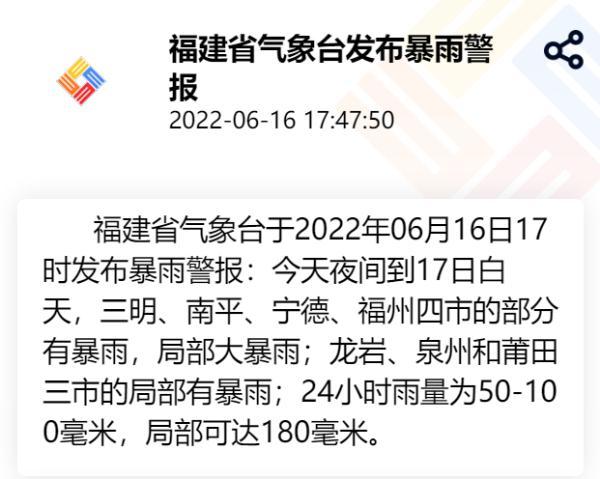物理学宿命论(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
撰文 吴骏(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基础课程讲师)
物理学中的确定性问题缘起于我正在教授的《与自然对话》[1]这门课。其中节选了詹姆士·华生 (James Watson) 在2003年写的一本畅销书《DNA:生命的秘密》。书中的第二章回顾了1953年他参与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2],在第二章的最后,他说道:“生命不过是物理与化学的事,尽管是极其精巧的物理与化学。(Life was just a matter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albeit exquisitely organized physics and chemistry.)”

(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句话向来引人争议。就算是在老师们之间,也常常意见各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讨论下来,其中一个落足点往往会归结到物理化学的确定性上面,也让我萌发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自牛顿力学开始现代科学的滥觞,仅仅凭借着手中一枝笔、一张纸,转念间便可以洞察行星运行的奥秘,甚至预测其轨道及周期[3]。科学的发展让世界的图景宛如一张精密的机械设计图,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此间,物理学往往以其精准确定的解释与预测收获了不少拥趸;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科学的刺针探入物理世界的复杂性里,让我们反省物理世界深藏的不确定性。
这个方程描述了布朗运动[4]的动态过程。布朗运动最早由爱因斯坦给出其统计意义[5],描述小颗粒在液体中受到液体分子随机碰撞而产生的运动。事实上,朗之万方程的物理意义非常简单,就是牛顿第二定律的直接运用:方程的左边是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其中 v 是小颗粒的速度,m 是其质量;方程的右边也就是受力情况,其中, γ 是粘滞系数,代表液体的性质,而 η(t) 就是代表液体粒子碰撞产生的随机力。之所以单独命名这个牛顿第二定律的方程,是因为在它的受力分析中出现了随机项 η(t),正是它,体现了整个运动的不确定性。
那么,什么是随机项呢?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随机项的出现,暴露了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让我们想象这个飘零在液体中的可怜小微粒,它被近乎无穷的液体分子包围着,忍受着来自它们的撞击。这些液体分子太多了,太小了,我们无法去跟踪每一粒分子的轨迹,只能用“随机行为”来描述这无法分辨与预测的冲击,这就是随机力产生的原因。简而言之,所谓随机,只是因为现象复杂到无法预测,所以不能给出确定的描述。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无法对小颗粒的运动行为精确预测,仅仅能给出一个统计上的概率分布。然而,这种随机还是易于处理的。毕竟,我们并不关心小颗粒受到的每一次撞击,只需要知道它在我们观测的宏观时空中的平均效应。观察成千上万的小颗粒的运动并非难事(例如:墨水的扩散现象),在我们关注的现象层面,这种随机性很容易就被平均掉了。我们仍然会惊叹于物理学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确掌控。
可是,这种随机性并不总能被平均掉。科学的成功助长了我们的线性思维,让我们常常忘记,这个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然而,世界又是狡诈的,它把非线性藏在无数细节里,冷不丁地跳出来嘲讽我们一下。在非线性效应地摇旗吶威之下,任何一点小小的随机性,都可能放大成为声势浩大的现象级后果。这,就是出名的“蝴蝶效应[6]”。对于地震预测的无可奈何,气象变换的难以琢磨;甚至对于生命运作的绞尽脑汁,乃至对于大脑意识的莫衷一是,无不标记了我们在世界复杂性面前的挫败感。
如果说物理学的不确定性仅仅来源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倒无损于科学家的信心。谁不知道世界是复杂的?科学的意义不就是洞穿错综复杂的现象,看到其本质吗?复杂与非线性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科学的精确预测能力罢了,而世界仍臣服于确定的物理规律之下。
吊诡的是,物理学似乎无意接受我们为之安放的确定性命运。量子力学再次颠覆我们的认知,从最基础的理论层面,再一次昭示了其隐藏的不确定性。
让我们还是从最熟悉的牛顿第二定律说起吧。 F =ma,这是牛顿为我们描述的机械图景,将运动现象纳入其间。对于受力分析已知的物体而言,只要知道它任何一个时刻的位置与速度,我们就可了解它的过去并预测它的未来。初始条件[7],仅仅是一个时刻的位置与速度,在确定的物理规律下,便可透露物体运动的全部讯息。这不正是物理学规律确定性的绝佳范本?正是牛顿,通过这一套运动定律的建立,奠定了现代科学分析世界的信心。只可惜,海森堡 ( Werner Heisenberg ) 的不确定性原理 ( Uncertainty Principle ) 当其面门奋力一击,这个经典巨人便倒地不起。根据不确定性原理:

位置和动量,也即是速度[8],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无法突破普朗克常数 ħ 的局限。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同时确定位置和速度,从根本上,也就无法确定一个物体(通常是量子级别)的初始条件。那么这个物体的历史和未来自然就逃脱了我们的掌握,即便它仍受制于确定的物理学规律。物理学的不确定性站在最基本的理论层面讥笑我们的自以为是。物理学家当然会予以反击。以玻尔 ( Niels Bohr )、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把一切秘密吸收进了波函数,赋予了量子力学一套统计意义,这便是著名的“哥本哈根诠释”。科学家了解统计力学,“哥本哈根诠释”也安顿了物理学家对于世界确定性的信心;然而,波函数终究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幽灵,我们自以为了解统计学,却往往忽略了正是波函数,把这种不确定性安放进了一个单独的粒子中。
或许我们可以从薛定谔方程 ( Schrödinger Equation ) 一窥究竟:

这个方程看上去很复杂,但物理意思很简单:就是总能量等于动能与势能之和 E = mv2 / 2 V 的算符写法而已。这里的 E 指粒子的总能量,而 V 则代表其势能。这也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另一种变换形式。就这个意义而言,薛定谔方程描述的是一个确定的物理过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方程,而在方程掌控的对象,也就是波函数。它告诉我们,粒子在给定时间 t 可以位于空间的任何一点 x,波函数 Φ(x,t) 本身正对应了粒子在此状态下的概率幅,而它的绝对值平方|Φ(x,t)|2就是粒子 t 时刻位于 x 的概率。有趣的是,和经典物理很不同,在大多数物理学家眼里,波函数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学工具,并不对应任何实在的可观测量。然而,由于包含了粒子运动的所有统计可能性,当观测发生时,波函数所代表的概率波会坍缩到其中一个可能的状态,从而给出一个物理意义清晰的观测结果[9]。这样的一套统计解释可以精确说明很多的量子力学实验(例如:著名的双缝实验[10]),物理学家似乎再一次把预测世界的话语权夺了回来。
可惜,并非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买账,薛定谔透过他那只有名的“薛定谔猫”捅破了那层薄薄的玻璃纸,暴露出这一套诠释的可疑之处。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倒霉的“薛定谔猫”被关进了一个由原子衰变控制开关的封闭毒气室,它的命运便由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与否决定:如果衰变发生,则毒气释放,猫毙命;反之,则猫存活。由于衰变本身是典型的量子行为,根据哥本哈根诠释,放射性原子的波函数是所有可能状态的线性叠加,当时间等于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时,放射元素有一半的机会发生衰变,相应地,与之命运相连的“薛定谔猫”的状态也就变成了:

其中 │live 〉表示猫存活的状态,│dead 〉则是猫毙命的状态。除非打开毒气室查看猫的生死,也即是观测发生,否则这只猫就永远处于一种不生不死,半生半死的荒谬状态。我们无法理解一只同时存在于生死边缘的猫,这严重违反了人们的一般直觉,也暴露出哥本哈根诠释面对量子世界时的无力与不确定。

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chrodingers_cat.svg
无疑,薛定谔的思想实验放大了这种无力,然而,正是在这稍带夸张的场景中,我们更容易把握埋藏在微观量子世界中的不确定性。正如之前所说,尽管薛定谔方程本身代表的是一个确定的物理过程,这个确定的物理过程描述的却不是一个粒子的运动过程,而是这个粒子运动的统计可能性。这才是真正吊诡的地方。如果说,统计物理的不确定性是源于参与者的众多以及过程的复杂,量子力学告诉你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存在于复杂系统中,甚至存在于一个单独粒子的描述里。物理学家用他们的天才把它藏在了统计方法的背后,让我们用技术上的成功去忘记其本质上的不确定性。
或许,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坦诚面对更好地反映在了费曼 ( Richard Feynman )的路径积分上。他不再用神秘莫测的波函数来吸收一切秘密,而是坦然标记了粒子可能走过的每一条路径,并赋予每条路径相应的统计意义。通过路径积分这样一个直接明确的统计手法,求和所有路径来给出单个粒子行为的描述。这,可能是物理学家面对量子世界时所能做出的最诚实的解说。

路径积分示意图:A, B是粒子运动的起点与终点,费曼的路径积分认为,粒子的行为由所有从A到B的可能路径通过统计平均共同决定。图片来自张天蓉在科学网介绍费曼积分的文章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7221-796611.html
诚实固然难得,但诚实却无助于消解物理学家的挫败感;经典物理所带来的那种对于客观实在的掌控与把握,那种分析世界、洞察自然的优越感毕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在很多人眼里,科学的发展是人类了解自然,甚至控制自然的过程。或者,他们忘了,这更是一个人类了解自己的过程。物理学作为现代科学的坐标性学科,它所暴露的不确定性也许不应该被看成是自然的狡诈,而是它的善意。让我们可以重新意识到自然的复杂、人类的局限,让我们可以保有对自然的敬畏,也包括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毫无疑问,生命当然是物理化学的事,是无可辩驳的精巧的物理和化学,但生命的内涵与外延又远不止如此……
注释
[1] 《与自然对话》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门通识课,面向所有本科生。通过经典阅读与讨论引发学生对科学相关议题的兴趣与探索。
[2] 因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华生与他的合作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及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DNA:生命的秘密》是为了纪念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而出版的。
[3]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哈雷 (Edmond Halley)利用牛顿力学计算了哈雷彗星的周期并预测其1758年的回归。
[4] 布朗运动最早由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 最早观察到,他发现悬浮于液体中的花粉颗粒会随机运动。
[5] 这是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的4篇革命性文章中的一篇,英文名为“On the movement of small particles suspended in a stationary liquid demanded by the molecular theory of heat,”Ann. Phys. 17 (1905).
[6] 蝴蝶效应是一个生动的暗喻,用以表示系统对于初始条件的极度依赖:一只蝴蝶几星期前的一次煽动翅膀就可能引起远方一场飓风的降临。很多非线性系统都会表现出这种对于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初始条件发生一丁点的改变就可以造成系统完全不同的演化方向。
[7] 因为加速度是位置对于时间的二次微分,为了求解这个微分方程,给出物体的运动曲线(其位置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必须知道其某一个时刻的位置与速度,始知为初始条件。
[8] 动量等于质量与速度的乘积。
[9] 这只是哥本哈根学派其中一种较广为接受的说法。事实上,即使是哥本哈根学派内部,不同的物理学家仍然有不同的看法,就不在此赘述。
[10] 双缝实验对量子力学至关重要。经典物理中的双缝实验又常被成为杨氏双缝实验,让相干光束通过两个狭缝,在后面的接收屏上会显示出干涉图样。这是反映光波动性的决定性实验;后来在量子力学中,对不同的微观物体,如电子等,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也得到了相应的干涉图样。哥本哈根学派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Watson James and Berry Andrew, DNA: The Secret of Life, DNA Show LLC, 2003.
[2] Cohen Bernard, The Birth of a New Physics: Revised and Updated,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5 by Cohen Bernard, 1960 by Educational Services Incorporated.
投稿、授权等请iscientists@126.com
赛先生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