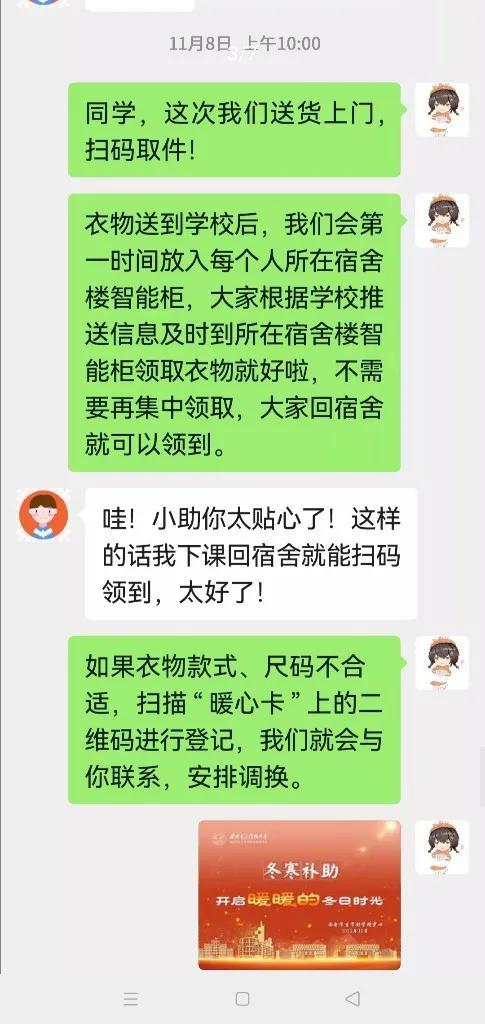儿子遗传基因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神奇的遗传性什么样的父母)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双性人”?
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颜值智商双高的后代?
如果未来通过基因改造提高智商成为可能,你可以容忍哪些副作用?
人类能否通过消除“不合适”的基因,来“治愈”犯罪、疾病和贫困?
有了基因工程改造,科幻电影中描述的混种生物世界是否将成为现实?

木村拓哉和他的女儿
如果你曾经好奇过这些问题,你或许可以在科普作家卡尔·季默(Carl Zimmer)的新书《她笑起来像妈妈》(She Has Her Mother’s Laugh)中找到答案。
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宣布了自己的退位计划,他28岁的儿子腓力二世在次年成为了西班牙国王。继承这个王位,是腓力二世天生——世袭/遗传——的权力。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所属的哈布斯堡家族,将战略联姻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他们通过或远或近的婚姻纽带,获得了欧洲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

腓力二世
然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哈布斯堡家族付出的代价就是,家族成员反复出现严重的精神和生理问题。查理五世的母亲是疯女胡安娜,他的儿子腓力二世据称是一个“体质虚弱、阴郁、严肃、顽固和迷信的人”。腓力二世的后代查尔斯二世直到4岁才开口说话,8岁才学会走路。1700年,查尔斯二世去世,死时还不到40岁,同时因为患有不育症,他没有留下子嗣。遗传学家计算得出,查尔斯二世的“近交系数”(指形成合子的两个配子来自同一共同祖先的概率)甚至超过了同胞兄妹乱伦诞下的后代。在他死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烟消云散,被一种在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遗传性”(heredity)压垮了。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不可能看不到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身上一再出现的这些不幸特征,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heredity”(遗传性/继承)这个词才拥有了“生物遗产”的现代内涵。由于“heredity”最初特指物质继承,通常是长子继承制,因此,我们倾向于用线性思维来考虑遗传性:世系、父系,乃至种系。英语中用来描述血统谱系图的词语——“pedigree”——可能来自法语“pé de grue”,意思是“鹤脚”,因为谱系图中的遗传线索正像是细长而分叉的鹤脚。
然而,线性思维并没有反映遗传性的本质,科普作家卡尔·季默(Carl Zimmer)在他的新书《她笑起来像妈妈》(She Has Her Mother’s Laugh)中说明了原因。该书对科学研究、历史和观点做了深入探查,揭示了对我们现有遗传学认知构成挑战的复杂性和异常现象,其结论颠覆了所有关于遗传性的单一性观点。
季默认为,遗传性是多重交叉的,它更像是蛛网,而不是鹤脚。
达尔文表弟的优生学:美貌聪慧的人要多生育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遗传性这个生物学概念出现得太晚了,但对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来说,却并非如此。当高尔顿在19世纪60年代研究一些引人注目的血统谱系时,他看到了优点的凝聚:高智商,高颜值,风骨卓然。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相信,才华和性格是可遗传的,因为它们反复出现在同一谱系的家族成员身上。先天和后天的概念也正是由高尔顿最先提出的。在弃用“viriculture”(优点培养)这个不太合适的术语之后,他把遗传改良这门学科命名为“eugenics”(优生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本义是“出生名门”。
高尔顿的优生计划是通过劝说和社会激励,来阻止那些他认为不合适的人生育后代,同时鼓励那些美貌聪慧的人多生育。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是“天才多如群星”。后期版本的优生学倒没有如此乐观。如果你采取高尔顿的“配方”,加入孟德尔的豌豆和摩根的果蝇,在进步时代(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的政治和文化中“煨煮”,并大力“搅拌”,你就能得到美国的优生学运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化,且具有强制性。如果把它跟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你得到的就是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对于优生学信条的残酷和天真,即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从基因库中消除那些“不合适”的基因来“治愈”犯罪、疾病和贫困,我们很难表示认同;而对于优生学家的谜之自信,即自认为已足够了解遗传性,可以去实施基因工程改造,我们也很难苟同。更难的是要记住,再过20年,很多在今天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也将被证伪。扮演上帝始终比看上去更难。
神奇的遗传性:既可“顺流而下”,亦可“逆流而上”想要深入了解遗传性,首先要找到玩弄各种把戏的染色体。
就拿“chimera”(奇美拉/嵌合体)来举例吧:对古希腊人来说,奇美拉是一个会喷火的混种怪物;对生物学家来说,嵌合体是包含了两组个体细胞的生物体。有一种类型的嵌合体,牧场主可能很熟悉,即“生殖器不全牝犊”,这是一头母牛怀上异性双胞胎时会出现的情况。小公牛和小母牛共享一个胎盘,它们会相互交换干细胞。小公牛差不多能正常发育,而小母牛——即生殖器不全牝犊——却会出现卵巢发育不全以及表现出雄性化特征。
季默描述了一个与“雄相雌牛”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奇异案例:一个女孩来到西雅图的一家遗传学诊所,她的两只眼睛颜色不同,而且有两套生殖器官。女孩的卵巢被证明只有XX染色体——这是典型的女性特征——但她的其他器官组织却混杂着XX和XY染色体。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她的母亲一开始怀的是异性双胞胎。但在发育初期,两个胚胎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与众不同的孩子。简单来说,这个女孩就是她自己的孪生兄弟。

不过,嵌合体不是怪人——知道么,你自己本人可能就是一个嵌合体!在孕妇身上,胎儿的干细胞可以穿过胎盘进入母亲的血液,并可能在那里停留多年时间。如果母亲再次怀孕,仍在其血液中循环的头生子女的干细胞可以反向穿过胎盘,与新生胎儿的干细胞发生混合。因此,遗传性可以“逆流而上”,从孩子传到父母身上——然后再“顺流而下”,传给未来的兄弟姐妹。
季默还告诉我们,基因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忘了这样一个概念吧,即基因组只是染色体中的DNA。我们的细胞线粒体(它们是为细胞供能的动力工厂)中拥有另一种基因组,虽然小,但却很重要。尽管线粒体中的基因数量很少,但如果它们受到伤害,可能导致大脑、肌肉、内脏和感觉系统出现病症。在受精时,胚胎会接受来自卵子的染色体和线粒体,但只会接受来自精子的染色体。因此,线粒体基因是严格通过母系遗传;就线粒体信息而言,每个男孩都是进化的死胡同。
后天获得的性状到底会不会遗传?在基因组之外,还有更多的意外。
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过,达尔文的前辈、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把遗传性搞错了。他认为生物通过后天经验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比如长颈鹿的脖子变得这么长是因为不断伸展去够到更高的位置,也许是为了吃到更嫩的树叶。这些被统称为“软性”遗传的理论,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进行过非常有名的驳斥。他说,如果拉马克是对的,那么把小鼠的尾巴切断,让它们进行交配,那么过了数代之后,小鼠应该生下没有尾巴的后代。但事实上并没有,也就是说,拉马克的理论行不通。
然而,最近的研究似乎正在为拉马克的学说背书。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微调系统能够在不改变DNA本身的情况下,关闭基因的表达。诸如热度、盐分、毒素和感染等环境压力可能引发所谓的表观遗传反应,开启或关闭基因表达以刺激或抑制生长,以及启动免疫反应等等。这些可逆的基因活性改变是可以传递给后代的,它们是染色体上的“搭车客”,可能会搭车走一段路,但能上车,也能下车。一些人推测,利用表观遗传,我们可以创造出拉马克式的遗传作物,这些作物可能在一两代中发展出对一种疾病的抵抗力,然后把这种获得性抵抗力传递给后代。但如果疾病离开了这片区域,那么作物的这种抵抗力也会消失。
所有这些遗传性——染色体遗传、线粒体遗传和表观遗传——仍然不能让你成为完整的你,差远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个独特的微生物群系,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基因组。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我们不会健康,也无法成为“我们”。这些微生物可以从父母传递给孩子,但也有可能是孩子传递给大人,孩子传递给孩子,以及陌生人传递给陌生人。
季默自己曾经充当了一回实验志愿者,他让研究人员对他肚脐眼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结果总共发现了53种细菌,而其中有一种细菌,科学家此前只在马里亚纳海沟找到过。“你,我的朋友,真是一处奇境。”那位研究人员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

如今,研究人员已经可以把取自脸颊拭子的成熟体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后者可以发育成任何类型的细胞,甚至是精子和卵子。新的技术,比如名为CRISPR的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基因工程的运用范围。
但道德困境也比比皆是。
尽管注射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以挽救严重贫血患者的生命,但对运动员来说却是非法的。
而通过基因疗法来提高一个人“天然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量,又会怎样呢?
是消除那些导致镰状细胞贫血和地中海贫血的基因变体更好一些,还是保留那些基因所具有的抗疟疾效果更好一些?
为了把孩子的智商提高些许,哪些副作用是可以容忍的?
与此同时,鉴于我们对遗传学逆流现象新获得的复杂理解,一些生殖技术的道德界限也变得更模糊了。
例如,代孕者很可能和她肚子里的胎儿交换干细胞,这让孩子和代孕者有遗传关系的说法能够成立。如果代孕者之后怀上自己的孩子,或者再为另一位女性代孕,那么这些孩子之间有遗传关系吗?
而有了所谓的线粒体替代疗法之后,亲子关系对我们来说变得更加陌生了。
如果一位患有线粒体疾病的女性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那么她可以把自己卵子的细胞核注入另一位健康女性去掉细胞核的卵子中,然后进行体外受精,最后得到的便是“三亲婴儿”。世界首例三亲婴儿已于2016年诞生。季默并未对这样的技术妄加道德判断,但他警告称,这类情形下的“知情同意”也许会出乎意料地棘手。
而且,为什么要止步于人呢?
研究人员可以在自然生物体身上,应用所谓的基因驱动技术,让生物体彼此之间进行基因工程改造,从而在数代时间之内,把一种特定的性状扩散到整个种群之中。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一过程制造防虫的作物和不会传播疟疾的蚊子,还可以在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实现不计其数的其他创新。相关试验正在进行当中。
对全球基因组进行基因工程改造,或可以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或产生电影《变种异煞》和《侏罗纪公园》里那种嵌合体混种生物。我们真的可以改变未来的基因库,在遗传性细密交织的世界中牵引和转动DNA的琴弦,扮演背后操纵者的角色吗?有一天,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拥有培育自然的智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深究。
本文作者纳撒尼尔·康福特(Nathaniel Comfort)系美国宇航局和国会图书馆联合设立的巴鲁克·布卢姆伯格天体生物学教席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教授。
翻译:何无鱼
校对:李莉
编辑:漫倩
来源:The Atlantic
造就:剧院式的线下演讲平台,发现最有创造力的思想点击蓝字“了解更多”,获取更多「造就」精彩内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