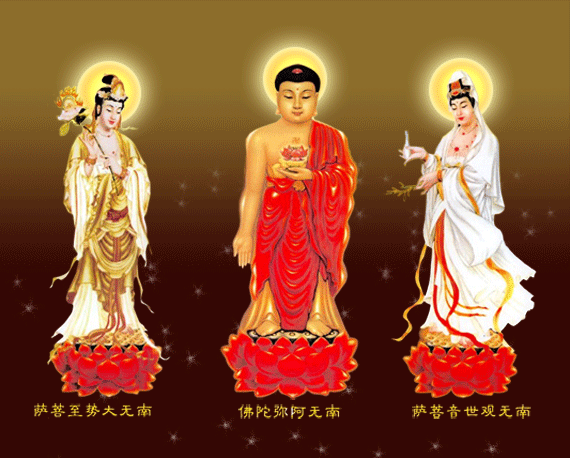律师的价值比大众更多(向往着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明天)
转眼间自己从律师业退休了,成了一位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师爷(因为不能再叫自己是律师了,又一直被人叫绍兴师爷,到了60岁就被直接叫成师爷了)离开律师业,回看律师业,自然有了一种旁观者清的视野和感觉在第三届新兴法律服务业论坛召开之际,就律师业和律师业相关的新型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说说自己的感想,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律师的价值比大众更多?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律师的价值比大众更多
转眼间自己从律师业退休了,成了一位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师爷(因为不能再叫自己是律师了,又一直被人叫绍兴师爷,到了60岁就被直接叫成师爷了)。离开律师业,回看律师业,自然有了一种旁观者清的视野和感觉。在第三届新兴法律服务业论坛召开之际,就律师业和律师业相关的新型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说说自己的感想。
壹
律师业自己比自己,成绩不得了
早些年曾经有过莫名的冲动,想拍一个律师业发展的20集纪录片,也写了一个20集的粗略提纲,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司,也就是现在律派巨匠的源头公司。为此也采访了律师界的一些前辈,对于律师业恢复后40年的发展历程,我的认知比晚辈的律师,乃至大部分同辈的律师可能都要充分一些。我也主持过一个内部的纪录片《君合20年》的拍摄,对于中国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脉络也有清晰的梳理。我也认认真真地读过《中伦的秘密》这本中国最大型律所之一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史,因此,对于中国律师业恢复后40年的发展史和中国最早期著名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史,我脑子里是有一个清晰脉络的。同时我作为一个北京律师,又长期派在海南和上海工作,对于北京、上海和南方律师业的发展也亲身经历。所以现在要回顾中国律师业恢复40年的发展历程,我肯定是可以讲些故事的人。
说到中国律师业恢复40年的发展,我们站在律师业自身的角度回头看,毫无疑问可以说,中国律师业40年的发展不得了,了不得。
中国律师业恢复的时候,是一批30后的律师,他们大部分是50年代受过冲击的”右派”律师,全国也就是2000人左右。像上海律协的老会长王文正,讲的都是怎么样一个一个苦口婆心地把30后的”右派”们劝回来做律师。30后的老律师傅玄杰讲的是最早的法律顾问处是多么的简陋,但是群众是如何地信任律师。那时候做律师虽然很苦很忙但是很自豪。
50后这拨中国律师业恢复后的律界新兵,谈的已经是创业和转型的艰苦。作为50后北京律师的代表武晓骥(原北京律协会长),肖微(第一届全国十佳律师)讲的是借了几万块钱开始创建君合搞合伙制不易,开业前两年君合合伙人都拿不到工资;作为上海50后律师的代表人物朱洪超(原上海律协会长)讲从法律顾问处转为合作制律所,合伙制律所的不易,律师事务所一点点资产算过来算过去,到底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也说不清楚;作为南方律师50后的代表性人物李淳(原深圳律协会长),从东北到深圳,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也深感律师创业不易。律师业恢复到现在,我们这批50后律师几乎全程参与其中,毫无疑问是中国律师业的建设功臣。想想全国的律师人数从2000人左右到现在36万多人;从律师事务所人数三、五个人开始,到现在事务所规模超千人,数千人;从律师创收几百块钱到人均几十万,高创收律师过千万;从案件只能做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到现在各种类型的法律事务都有律师参与;从事务所只有在一个城市执业,到现在大型律所在全国,在全球近百个城市的执业;从律所办公在平房和筒子楼一两间办公室开始到现在在最顶级的大楼中数千,近万平方米办公室;从律师办案的数量,到参政议政的人数等等,律师业的发展真是不得了,了不得。从我个人而言,多少次站在上海嘉里中心32楼,望着的上海展览馆当年看着高耸入云的红五星,怎么也想象不到,当年17岁第一次到上海,在上海展览馆地面仰望的这颗红五星,梦想着自己能够在上海有所发展,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能够在这颗红五星旁边,比这颗红五星还的高办公室办公10多年。思前想后,我们这批50后的律师,参与中国律师业恢复后近40年的发展,肯定是骄傲的。
贰
和其它行业比发展算一般
律师业总体发展进步很大,但就律师个体而言,客观地讲,幸福感,荣誉感并没有增加。我们50后当律师的那一代人,肯定人人都有当律师为民请命,匡扶正义的使命感。50后当律师的那代人应该都做过刑事案件,估计不少人面临过刑事案件的亲属在你面前扑通下跪的场景。就我自己而言,处理过一个一审被判死刑的案件。面对亲属下跪的场景,内心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心想着,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那颗脑袋保下来,最后二审确实被判了死缓,保住了脑袋。50后那代律师做经济案件,虽然挣钱不多,但是客户对你的尊敬是能够切身感受到的。还有,50后那代律师,曾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是非常受尊敬的,聚会吃饭间都会把你当做座上宾。但是,现在律师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程度明显不如当年。律师在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时候,已经处在被呼来唤去的境地,就是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不存在任何请你的感觉。而在处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时候,律师也常常被质疑、被诟病、甚至被殴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律师确实有点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感觉。
律师境况的变化,究其原因,律师业与其他行业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相比较,相对滞后。从知识层面而言,现在社会各界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大学生成为社会基本人群,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和理解已经不同于八、九十年代,法律和律师行业的神秘感消失,律师成了可以被随时揶揄嘲讽的人员;从律师作用角度而言,不时被披露的法律冤案和司法腐败案件,使得社会各界对律师的作用和公平正义感大大减弱;从收入角度而言,虽然律师界整体弥漫着以高创收为荣的倾向,但律师不论是事务所收入规模和律师个体收入而言和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老板收入大幅度扩大相比,心中很不是滋味;从行业人数规模和社会影响力而言,许多行业从无到有,从业人数过百万,行业领军人物社会和政治地位远超律界领军人物,很是酸楚感慨。以上对比说明,这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高速发展,律师业的发展最多就是个行业平均发展速度,但律师却要天天面对、服务、伺候那些高速发展的行业和人士,两相比较,现在的律师幸福感、荣誉感不如我们50后一代初为律师的时候。
叁
想的得不到,空间不够开
律师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在法学院学习法律的时候,同学们都已经被灌输为律师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是一个稳定的高收入群体。同时,又被灌输为律师是特别容易转化为政治人物的。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半以上的总统、议员都是律师出身。又由于法律专业本身的政治特性,法律人对政治问题的认知和参与的热情一定会比其他任何学科和专业的人士要强烈。学法律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公检法司等司法行政部门之后,由于进入到了体制之内又受到纪律的约束,就被约束训练成了体制内的人。但律师不一样,他们自谋职业,自找客户,在法律服务市场当中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但他们心中的政治参与热情却不会因此泯灭。因此,那么多年来,在重大社会热点问题上,律师是一类经常参与评论和表述的人。但是,由于多年来法学教育,国际环境影响,现实政治模式以及律师地位作用的不协调,造成了律师在参政议政方面方面的认知差异和失落感。如果法学教育模式和律师现实地位之间不能够形成教学与实践的平衡,诸多律师会长期处在政治参与感失衡的情绪之中。解决律师失衡感问题不是律师业自身能解决的,律师业本身也不必过多讨论。每个个体律师只能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调整好了就舒畅,调整不好就失衡。
但是从律师业定位为一个服务业而言,需要坚守也需要发展。坚守的是主要体现在律师的刑事辩护方面,这体现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和司法主权的设计,刑事辩护关乎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刑事辩护的资格必须授权给受过基本法学教育,通过法律考试并受过实务训练的律师。参与民事和经济诉讼和仲裁的权利,作为律师业本身应该去牢牢地守住,这也算是律师业的坚守阵地。但民事、经济诉讼、仲裁的权力和领域一定会有很多其它行业的人士觊觎和染指。这么多年来,律师业在行业坚守的问题上应该是不错的。然而,律师业作为一个法律服务行业,在非诉业务的拓展中实际空间和想象空间就很大了。现在从律师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律服务的面非常的开。但从服务的深度而言大部分是浅层的服务,这种浅层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对律师个体而言,不管是自我价值的体现还是服务价值的体现都感到有些不足。律师之所以在广大的非诉领域只能进行一些浅层的服务,这和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管理能力、行业约束有很大关系。从组织形式上来讲,律所的合伙制在执行力方面和企业的公司制差距太大。有的人会认为学法律的人特别的不好管,这是不准确的。学法律的人进到公检法司之后,在体制内、在半军事化的制度架构下,执行力依然是很强的。但是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制下面,执行力就大打折扣。同时在行业的约束方面,律师事务所的限制,和一般的咨询类、服务类公司相比,差距很大。光是律师事务所不能投资这件事儿,就约束了在非诉业务中律师服务的深入问题。律师业经常会因为行业的特殊性自我感觉崇高。但客观的讲,教育、医疗、媒体等行业自我感觉的崇高性都不会比律师业差。教育是灵魂工程师,医疗是白衣天使,媒体是无冕之王。我们从行业的角度对比,这几个行业的业态都比律师业要开放。讲个故事,作为老律师,我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学法律,但儿子就是不学法律,自己选择学了新闻传媒,我总对此有点不爽。有一次,电视在播全国记协召开大会,中央常委全部到场祝贺的新闻,儿子在边上问我,你们律协开会什么样的领导会去?我一时语塞。教师节、医师节、记者节都有了,律师节会有吗?律师行业地位低是因为人数少?因为学历低?因为市场化程度低?因为机构规模小?因为社会作用少?是因为律师太折腾?总之律师业行业地位相对较低,一定有行业自身的原因。
肆
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融合
现在几乎各行各业都受到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拥抱。在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推动下,许多行业的发展都超乎寻常地迅速,有的甚至无中生有,三、五年就形成一个行业。律师业是一个很保守的行业,律师业所受到的行业管控以及和公检法司等相关机构间的约束和依附,使得律师业成为科技、互联网和资本渗透影响最弱的行业之一。但是客观因素是一方面,主观上律师的自我、律师的不羁、律师的散漫、律师的无保障,也是律师不愿受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约束的一个内在因素。虽然律师业内的一些先知先觉,或者说敢于创新者,开始学习其他行业的经验利用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力量来搭建新的平台,但是三、五年的实践下来,一批先行者已经成为了行业发展的先烈。说到这里,一定要向这些行业的先烈们鞠躬致敬。如果说律师业相关的一些机构,在利用科技、互联网和资本来推动法律服务业发展中效果不好,失败案例太多,我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律师业对于如何利用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力量来推动行业的发展缺乏整体的考虑和战略,没有相应的激励政策和制度松动。
2
律师事务所合伙制的管理结构和长期松散的管理模式,无法适应科技、互联网和资本所要求的规范化、公司化等严格的管控模式。
3
具有创新精神的骨干律师,在行业和事务所体制的约束下,以及律师业个体化管理和公司管理之间能力的差异,使得勇敢地迈出创新实践的骨干律师们面临着发展的极大窘境。
4
来自于其他行业的科技、网络人才,在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又面临着律师业行业管理的壁垒和律师们对非专业人士涉足法律服务的内心抵触,再加上法律服务自身的专业化要求和服务流程的复杂性远超其他服务业,他们在法律服务相关领域的发展也是举步维艰。
然而,毕竟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力量是现代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在进行一次重新的洗牌,法律服务业也绝无可能成为潮流中的孤岛。在这几年法律与科技、互联网和资本的融合中,也有一些相关的机构找到了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方式。说到这里,一定要向这些行业的先辈们致敬。百事通是一家理工男创业的法律科技服务型公司,以冯子豪为代表的这批理工精英,创业12年,在科技加法律的领域中,痛苦摸索对接,终于编制成了司法部中国司法服务网和各省的12348热线,编织成了法律服务基层百姓的这张技术大网,受到了司法部的认可,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了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标杆企业。无讼在新兴法律服务业曾经像旋风一样刮过,红透整个律师界。我认真地对无讼的创始人蒋勇说,钦佩你用一己之力,一所之力想打通笼罩在法律服务业顶层的天花板,想让法律服务业照进智能的阳光,太了不起了。蒋勇回答,我也不知道能打通几层天花板,打通一层还有一层,一层又一层太难了,不管打通没打通,我一定会给后人留下标记,我曾经打到第几层。赢火虫以余畅池为代表的这批销售天才,用法律人的智慧拿起了资本的杠杆,撬动了沉淀在各行各业的死账和坏账的专项服务,为全国各地无数的律师创造了新的案源,为法律服务业如何驾驭资本趟出了一条道路。毫无疑问,这些代表性的机构,已经实现了法律和科技、互联网、资本的有效融合,他们的出现,让社会其它行业对法律人有了新的认知和新的尊重。
伍
新兴法律服务业大有前途
说句俗话,未来已来。法律和科技、网络、资本相结合的新业态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来到了我们身边。2016年9月,首届新兴法律服务业论坛在上海召开。这个论坛的命名确定了新兴法律服务业的行业成型。律新社作为论坛的主办方,王凤梅社长功不可没。律派巨匠作为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成员和论坛的协办方,也有推动作用。论坛期间,大家把酒言欢,我给大家算了个账,未来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市场空间会有5000个亿,是一个成长型的大行业,获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
对于与律师业有紧密关联的新兴法律服务业,从律师业的整体态度而言,以我曾经的老律师,现在新兴法律服务业的耕耘者而言,律师业上层对这个新兴关联行业的态度是保守和观望的,甚至在担心着啥时出点事情如何表态和切割;律师业个体而言,老律师相对漠然,年轻律师相对功利挑剔,能够拥抱理解和给予宽容支持的不多。这是律师特质所决定的,我作为老律师特别能理解这种特质。就是看风险多,提批评多,自以为是的多。因为律师做事长期只是抓住一点,给予钻透突破,全面考量和管控的机会少,这方面的能力培养缺乏,综合管理人才也少。但是,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机构业态是公司不是律所,业务是需要综合平衡的而不是做案件钻透突破就行的。这就对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很高的门槛。外边的人想进来,但法律专业的精深和律师个体的难控不敢进来。里边的人想干,但行业的管控,事务所的松散,个人管理能力缺乏,没干就想到一堆风险,也不敢干。所以,经过了三、四年前热热闹闹的互联网加法律的一波潮流后,现在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新增机构明显减少。但是互联加法律的热潮退掉之后,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依然是地火汹涌。科技领域的、智能领域的、互联网领域的、资本领域的、咨询领域的都在不断的涉足新兴法律服务领域。这些涉足过来的机构,大多都是他们的一个辅业而不是主业。比如科大讯飞法律智能领域的发展,比如阿里对法律服务业的惦记,比如一些投资机构对不良债权处置的创新模式,都和传统的律师业业务形成犬牙交错。面对一个具有5000亿到1万亿的发展市场空间,所有相关领域都是不会漠视的。就连现在有的企业聘有成百上千的法务队伍,根本的原因还是律师业不能适应他们的服务需求,稍作调整就可以来切律师业的蛋糕。但是如果,新兴法律服务业的机构能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形成服务外包的机会,则就给律师业创造了案源。可以想象的是,法律机器人、法律大数据、法律资本垫资、法律产品平台、法律专项培训、法律服务标准化产品、法律应用软件等等,都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到来。现在在新兴法律服务业领域,虽然谈不上有对律师业颠覆性的力量出现,但是,在当下科技互联网资本的相互作用之下,对一个行业产生颠覆的,往往是来自于非相关领域的人和机构。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对于传统律师业而言,如果采取保守和观望的态度,则未来在传统和新兴相加的整体的法律服务业中,规模和分享的蛋糕就会少。如果,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则有可能引导,融合新兴法律服务业,规模和分享的蛋糕就大。
最近一段时间律派巨匠内部员工在练习演讲。有位叫李悦歌的年轻人,她在演讲中畅想到,不久的将来,在律派巨匠的平台上,我们绍兴的会员机构,用他们的专业远程为新疆的客户服务,我会感到很骄傲。她的演讲,听的我心里热乎乎的。我也和律派巨匠的伙伴们畅想,我设计的关于公司控制权疑难杂症解决方案的万元标准服务包,在律派巨匠平台上,最终实现了全国一万个订单。也让大家一阵激动。律派巨匠这样的新兴法律服务平台,未来就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做为律派巨匠的带头大哥,源自于传统的律师服务业,我们的初心是服务于中小律所。现在律派巨匠走过艰难的生存期,成为新兴法律服务业的一个客观存在,我们依然要保持初心。我们依然要恪守保持不做律师业务,但要服务于律师的本源。律派巨匠要成为新兴法律服务业的开拓者、耕耘者、融合者,同时也要成为和律师业的联接者、瞭望者、分享者。只有这样,律派巨匠才能知道本源,知道去处,知道光明所在。
本文作者:律派巨匠董事长潘跃新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