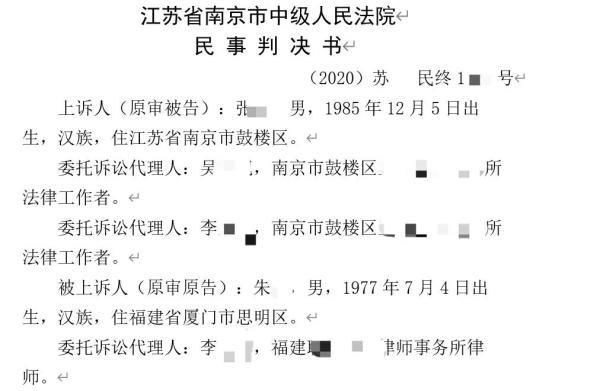来源:《人物》,文:曾诗雅,编辑:槐杨,封面图:YES24。
她揪住那个欺负的人,大声问:「为什么要欺负人家?」

2020年3月,赵主彬被捕,「N号房事件」曝光,震动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性犯罪仍是困扰韩国社会的顽疾之一。相对一般的性犯罪,「N号房」尤为可怕之处在于,涉案人数超过26万,相当于韩国出租车的数量,也就是说,在韩国街道上,你遇到N号房参与者的几率与遇到出租车的几率等同。窥视、威胁、以伤害女性获利,这些罪恶,就在每个人身边。N号房事件令数码性犯罪问题在韩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警方成立「数码性犯罪调查本部」,迄今处理了2800多起相关案件,相关律法得以改变。少有人知的是,最初发现N号房的,是两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女孩,两年中,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曾每天「潜伏」在N号房5个小时,身心俱疲,也因为被记者不断地追问目睹的细节,心理受到很大伤害,她们一度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但她们还是决定做点什么,让世界发生一些改变。《人物》作者曾诗雅在韩国采访了这两位女孩,年轻的火与丹。如今,她们是一个小组合,名字叫「火花」,她们试图像火花那样,点燃变化,点燃具体而微的光亮。笔记本里的地狱刚才看见的画面是真实发生的吗?两个女孩愣愣地看着对方。咖啡馆里吹出的冷气并不强,但两人的胳膊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开始,她们约在咖啡馆,是想寻找有关「非法拍摄」的新闻素材。她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关键词,仅10分钟,就找到了一个名为「AVSnoop」的博客,上面有一个引到匿名社交软件Telegram聊天室的链接。点击链接,在注册页输入电话、姓名(注册后电话可以隐匿,姓名可以更改),她们进入了N号房的第一道关口——一个名叫「高墙房」的聊天室,里面1000多个成员,正热烈地聊天。 「来Telegram里看正常东西的家伙没有吧。想看AV还不如去日本网站。」「当然,来Telegram就是为了看儿青物(有儿童、青少年的影像)呀。」高墙房的群公告显示,「存在能看性视频的8个N号房(1-8号)聊天室」。群主「Watchman」时不时地在群里发出N号房的「预告」——一些女生的照片、姓名、学校等信息。不断有群成员讨要N号房的链接,但Watchman给出的链接通向「衍生房」,这是进入N号房的第二道关卡。在「衍生房」内,需要上传偷拍视频或罕见色情片,才能得到进入N号房的链接;不上传相关视频或者不参加性骚扰对话则会被强制退群。这里已经开始出现大尺度视频,儿童被强奸,年轻女孩在卫生间或者独居房里被偷拍……女孩们惊呆了,看到这样的视频,原来只需要这么简单的操作。几小时后,通过一次「把头像换成日本动漫人物」的活动,女孩们得以进入N号房——一个与之前的聊天房全然不同的地狱。N号房的最初创始人名叫「GodGod」(真名文炯旭)。他在互联网上寻找上传了性感照片的未成年人女孩,给她们发带病毒的链接,再伪装警察,获得她们的个人信息,以此威胁她们按照他的意志拍视频。视频画面里,这些女孩有的像狗一样叫着,有的在男厕所全身裸露躺在地上,还有的紧紧盯着镜头自慰……每段视频都会露出性器官。他把这些女孩称为「奴隶」。两个女孩合上电脑,离开咖啡馆,回到其中一个人住的地方,继续守在N号房。此前,她们对「非法拍摄物」的理解还是偷拍,针孔摄像头被藏在公共卫生间、酒店或者随身物品里,受害者毫不知情。但眼前的这些「非法拍摄物」,女孩们有意识地对着镜头、按着「剧本」伤害自己。要报警吗?报警之后还能继续取材吗?报道出来的话,会妨碍警察潜伏搜查吗?问题一个连着一个地冒出来。2019年7月初的一天,发现N号房一周后,两名女孩走进警局的网络安全搜查科,向警方出示了高墙房、衍生房和N号房内的聊天记录和影像资料。警方表示,这是重大案件,他们会上报。一周后,根据两位女孩提供的资料,警方对N号房展开了正式搜查。调查至今还在进行,截至2020年9月,调查人数超过1000人。报警时正值韩国盛夏,热浪汹涌,早在两个月前,市民们就陆续收到了几次暴热预警。然而,2020年3月9日《国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在开头写道:去年夏天清凉又阴森。这篇报道最早讲述了两名女孩在N号房里潜伏6个月的经历。报道称,在N号房里,女性,包括未成年人,被当作性奴役的对象,被威胁拍摄下非法性视频,还有博士房、熟人凌辱房等不同程度的翻版「N号房」接连涌现,共26万男性参与其中。这篇报道获得了2020年韩国新闻奖大奖。在文末的作者栏写着「特别取材团」,后面的括号标注着共同作者「with火花追踪团」——火花,正是那两名女孩的代号。

火与丹。图源《韩民族》「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不舒服」2021年1月8日,我在首尔江南站附近的一家学习咖啡店见到了火与丹,她们在同一所大学的舆论学专业就读,丹年长一点,单眼皮,细眼睛,齐耳短发,说话语调轻快;火是丹的学妹,大圆眼睛双眼皮,头发留到了肩膀,说话温吞,但一听到不认同的地方,会迅速表达意见,「不」。在上大学前,她们都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丹是长发,总穿长裙,每次出门,一定要化精致的妆。对韩国女孩来说,保持精致妆容是一种基本礼仪。丹从初一开始学化妆,最先学会的是画眼线。这是个需要不断投入时间的过程:学习如何让底妆更无暇,如何让眼睛显得更深邃,如何让每一根头发朝最美的方向垂顺。这套严苛的标准几乎伴随着每一位韩国女性。在YouTube上用韩文搜索「10代的化妆」,会出现2.1万个视频,搜索「小学化妆」会出现1.4万个视频。韩国论坛Naver Cafe上,曾有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在家也化妆吗?」的讨论,20条回复中只有2条回复「不用」,12条回复「为了好看,每天起床后都要画完整的妆容」,剩下的6条说,「只要外出,就一定会化妆」。根据Mintel的数据,2017年韩国美容市场的销售额为130亿美元,是全球十大美容市场之一。2018年,韩国MBC女主持人林贤珠(音)因佩戴假睫毛和隐形眼镜感到不适,在新闻播报时戴上了圆框眼镜。一些观众向电视台投诉,认为「女主播戴眼镜是一种禁忌」。林贤珠问:「为什么男主播可以在节目中自由自在地戴眼镜,女主播却不行?」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对劲、不舒服。打工时,丹被男经理当众询问是不是要做另一名经理的office wife。她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和在场的其他男人一起笑,回到家上网一查,才知道这个单词意味着「办公室婚外情」。在报社实习第一天,男部长问她,这次就来了两名女生吗,为什么系里不派男生过来?据报道,男编辑让她放上女艺人穿比基尼的照片,说是更吸引眼球。休息时,男记者们讨论彼此的女友,有人提议,用怀孕威胁女生,逼她结婚……2018年,韩国社交平台上兴起「脱下紧身衣」运动,一群年轻女性毁掉化妆品,扔掉裙子和高跟鞋,剪短头发,不再化妆。想到自己每天化妆花一个半小时,而男友5分钟就能出门,丹决定加入这场运动。她走进理发店,要剪一个「超短发」。理发师问,中短发怎么样?之后想要留长也可以。她说,不,我要剪短发;剪到一半,理发师又劝,剪到这里就好了吧?中短发也很好打理。「不,我要剪超、短、发!」丹说。朋友们见到短发的她,「你疯了吗?」好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问,「是和男友分手了吗?」随便走进一家面馆,老板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只是剪了个短发。」丹笑了笑。

一些年轻的韩国女性毁掉化妆品参与「脱下紧身衣」运动2018年2月,韩国举办平昌冬季奥运会,火和丹都去做志愿者,住在同一间宿舍。那时,丹不再化妆,不再穿长裙,她变成了一个利落的细眼睛女孩,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对于性别问题的观点。有人问火,不觉得丹姐变女权后很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那样的啊。」火答。那时,火对性别议题还没什么概念,她只是单纯地不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火是个乖巧的、要求自己体恤他人的女孩。她只有一位姐姐,没有兄弟,爸爸说,「家里没有儿子,都没有人能和我一起泡澡」,妈妈不说话,脸上满是歉意。那时火还小,但她决定扮演一个缺失的「儿子」角色——像男孩一样,她和爸爸玩摔跤,在幼儿园把同学打到鼻子出血,大口地吞咽下整条五花肉。十几岁,她开始谈恋爱,在男朋友面前扮演「女友」,恋爱纪念日,她打扮了三小时,但男朋友不喜欢她穿裙子,让她回家换衣服,她什么也不说就照做了。在男友面前,她小口小口地吃饭,要去洗手间,就说「我要去接一下电话」。她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觉得那是社会的问题,并不存在于自己周围。她看到妈妈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包揽洗衣做饭等等一切家务,火觉得,妈妈很辛苦,但那只是她自己的选择。一次,班上讨论「2016年韩国江南站无差别杀人事件」,凶手因为厌女而残忍杀害了一名陌生女性,班里男生女生意见对立,轮到火发言,她说:「我不想站在任何一方,因为在我成长过程里似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性差别对待。」「这算得上我人生五大谎言之一」,火后来说。说那句话的瞬间,她忽然想起了过去的很多时刻,初二被男生问「能不能摸你的胸」的时刻,在照相馆里被店长夸奖长得像女明星还摸她的脸的时刻,在20岁成人夜被路人搂腰的时刻……「我一直用力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把那些时刻的不安、恐惧、羞耻慢慢地沉入水面以下。」但后来,因为和丹一起发现了N号房,这些情绪再次浮出水面,再也无法假装不存在。

韩国女性反抗偷拍行为的游行世界太安静了平昌冬奥会结束后,火与丹都成为《国民日报》的实习记者。她们关注女性话题,都想为此报道点什么,两人逐渐熟络起来。2019年春天,她们上了同一门新闻写作课,课程结束,教授建议她们一起写一篇关于非法拍摄的报道,参加「深度记实探查报道大赛」。教授说,如果能取得优胜,既能拿到最高500万韩元(相当于3万多元人民币)的奖金,也能让履历变得好看,对毕业后求职有帮助。火和丹同意了,那年7月,她们潜入了N号房。追踪一周后,她们报了警。警方告诉她们,可以继续潜伏在N号房取材。之后的几个月,白天,她们照常上课,晚上,她们潜伏在N号房,每天5个小时,经常到凌晨三四点才离开,保存聊天记录和影音素材,必要时整理后交给警方。在那里,她们看到很多难以想象的人。有人说,自己只想看儿童性视频,说自己「已经和04年生的孩子做过,想要尝试08年生的孩子」。这个人上传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视频。视频中,他走在路上,对一个越南小女孩问「多少钱一晚」。这段视频里出现了他的声音和手。火花将这段视频作为证据交给了警方。一个月后,2019年8月,这个N号房活跃分子Kelly被警方逮捕。同年11月,一审判决中,Kelly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火和丹觉得,这是「棉棒一样轻的惩罚」(Kelly案件目前正在重新审判)。在N号房潜伏两个月后,火花发表了一篇名为《贩卖未成年人淫乱物?...telegram非法活跃》的报道,获得了那一届「深度记实探查报道大赛」的优胜奖。4000多字的报道里,她们讲述自己如何一步步进入N号房,发现一重重犯罪现场。她们还采访了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科的李秀晶(音)教授。李秀晶说:「政府应当请求海外公司Telegram提供协助。即使这次请求没有答应,经过多次请求,也会成为改变的契机。」这也是火和丹想要达成的改变。报道的导语里,她们说,希望(N号房事件)能成为问责淫乱物非法拍摄、流通者的第一步。但是,世界太安静了。媒体报道的只有她们获得优胜奖的消息。与N号房有关的信息,只言片语地点缀在短短的新闻里。长达7个月,只有两家媒体联系火与丹,一家是《韩民族》,他们主要报道赵主彬;另一家是《国民日报》,火与丹曾经在那里实习,后来,《国民日报》的记者同火和丹一起在N号房潜伏6个月,发表了《N号房追踪记》。火觉得,是因为当时韩国政治风云变幻,前法务部长曹国正陷入丑闻,「比起数码性犯罪,人们还是更关心政坛」。丹觉得,是因为人们对数码性犯罪太轻视。2020年,韩国通信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数码性犯罪认知的调查,7458多名受访者中,29%的成人和5.7%的学生表示他们目睹过数码性犯罪。其中,认为「(数字性犯罪)完全不成问题」的成年人占9%,学生占16%。后来,在N号房事件已经进入公开讨论的4月,在讨论修订关于《性暴力处罚特例法修改案》的会议上,有国会议员提出:如果连写在日记本上的东西都要处罚,如果连想象都处罚,我们(男性)还能做什么?「这是体现国会议员凄惨认知水平的现场」,火和丹评价。

图源:电影《记得我》熟悉的加害者当世界对N号房回响平平时,火和丹发现,犯罪还在继续。2019年9月末,高墙房里,Watchman消失了,后来,火花得知,当时他已经被逮捕。N号房逐渐「过气」,「熟人凌辱房」成了Telegram上新的欲望载体。在这里,群成员上传熟人的裸体合成影像,以及她们的姓名、地址、职业等。火和丹发现,群成员们侮辱的是他们各自的朋友、妹妹、妻子……「这些人真的是平凡的丈夫、弟弟、儿子吗? 真的是笑着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吗? 」她们感到难以置信,那是一种自己所知的世界正在崩溃的感觉。在一间名为「女教师房」的熟人凌辱房内,群主发布了一名女教师的很多照片,火与丹看到了她所在的学校。要不要给学校打电话?万一消息传开,会给她带来影响吗?她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给对方打电话。那位教师沉默了一会儿,「确定吗?」她不敢相信。照片是她发在Instagram上的,只对特定的熟人公开。她一个一个地缩小范围,终于锁定了那个把她的照片合成、上传的人——她的高中同学。这个人的信息被火与丹交给警方,2020年1月,他被移交检察机关。有记者前辈提醒她们,做记者,不应该在事件中陷入太深,应该保有客观性。她们没说话,继续通过聊天室的信息联系受害者,努力和受害者一起锁定上传者。并非所有的犯人都能被锁定。火与丹曾在熟人凌辱房里发现了学妹的合成照片,她们猜测不出会是谁上传的,要告诉学妹吗?她们讨论过,觉得在不确定加害者的情况下,告诉学妹只会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她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次隐瞒带来的罪恶感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个凌晨,火收到了Telegram发送的平台提醒,「XX加入了Telegram」。这个人是火做志愿活动时认识的男生,她愿意相信他是因为工作注册的,但不一会儿,她就在N号房群成员名单里看到了这个人。她想给他打电话,想破口大骂,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做。那时,她们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真正的梦魇时刻:发现那些人并不遥远,甚至就在自己身边。丹每周至少做一次噩梦,梦里,她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熟人凌辱房,她哭着醒过来。火变得过分敏感。看到男生,她会忍不住想「是不是他也在N号房」;看见公共卫生间里的芳香剂盒子、垃圾桶里废弃的纸杯,她会怀疑里面是不是藏了偷拍摄像头。公交和地铁上,她每几秒就要抬头环顾一圈。直到今天,火仍然活得很小心,不愿意认识新的朋友。从2019年12月开始,毕业临近,火和丹不再每天守在N号房,而是一周进去两次。她们试图一点点拼凑回自己的个人生活。火想出国留学,报了首尔的英语补习班;丹想进入媒体,准备起了资格考试。N号房被大众关注、犯人被绳之以法的期待一直在,但灰心时不时涌来,火花觉得自己「好像一点点在熄灭」。

韩国媒体对「N号房事件」的报道为什么要欺负人家?2020年3月9日,《国民日报》刊载了「N号房追踪记」系列报道,提及了火与丹的追踪,两个女孩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一周后,3月17日,「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被逮捕。博士房中的视频更极端,且赵主彬通过欲望获利,需要通过网络虚拟货币支付150万韩元才能入场。突然,N号房和博士房一起成了新闻热点,被统称为「N号房事件」——比火和丹预想的迟了半年。火与丹作为事件的最初报道者,接受了很多采访。各自的生活计划停了下来,她们面对媒体,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最多的一天排了10场。有记者要求她们给出受害者的联系方式,还有节目要采访4个小时,让她们像演戏一样,把N号房的追踪过程表演下来。她们都拒绝了。她们以为记者会问现在受害者过得如何,政府的支援是否到位,相关的立法有没有更新,但是,大部分媒体更关注受害者的具体信息。她们被问得最多的就是「N号房里让她们最受冲击的场面」。「所有的场面都是冲击的」,她们答,但记者们总会请她们更详细地描述。两个女孩尽力回想,她们感到心脏在疼,呼吸困难。对着镜头,有一次,她们崩溃地哭了。火与丹开设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抨击舆论报道的方向,也接受各种各样的求助。每一个联系火花的受害者都说,自己的最大心愿并不是看到加害者被捕,也不是获得救助和补偿。她们只希望,那些影像被永久删除。2020年5月11日,N号房创始人GodGod被逮捕,火与丹觉得,「陈年的污垢终于被洗净」,但她们不敢高兴太久,她们怕别人觉得,抓到GodGod就结束了。事情并没有结束,类似的数码性犯罪还在发生。她们曾在一个聊天平台上伪装成初三女生,注册成功的同时就收到了五位男性的联系。在告诉对方自己未成年后,一个人说了抱歉,剩下四个人说「没关系,那也见一下吧」。五分钟后,唯一道歉的男性回过头问:「即使那样,你可以的话我们也能见面吗?」N号房消失了,新的N号房继续涌现。「我们的社会还需要专门针对数码犯罪的侦查组,避免报警后的不了了之;需要专门针对数码性犯罪的法律,让加害者、围观者都得到严惩;需要专门针对受害者的支援;需要做到永久性地删除非法影像……」火与丹说。早在2020年3月20日,青瓦台就出现了「公开所有N号房个人信息」的请愿,仅三天,146万人次表示了赞同。然而,N号房事件的参与者多达26万人,几乎相当于韩国庆州市的居民数。火与丹也承认,涉案人数太多,「那天」的到来几乎不可能。「但我们会一直等到所有法律制裁结束的那一天」, 她们说。试图让更多人了解N号房的罪恶,她们写了一本书,名叫《当我们称我们为我们时》(우리가 우리를 우리라고 부를 때),写下追踪N号房的经历,也写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各自的小环境中看到的女性困境,以及她们对女性议题的思考。写起来,有时很痛苦,会啪地合上电脑,有时很痛快,比如「原封不动地写下赵主彬(博士)和文亨旭(GodGod)的姓名」。2020年9月,书出版了,她们都给自己的家人看过。火的爸爸读完,生气地说,我哪有这样。但有一天,火看见从不做家务的爸爸正在洗衣服。丹则发现,当奶奶看着性犯罪新闻评论女性自己得小心时,往常沉默的爸爸会飞快地说,「那孩子有什么罪?」火也不再是那个言听计从的「标准女友」,她开始和男友协商,分担家务,或者一块看有关女权的电影。丹也向自己的男友普及什么是「厌女」。男友一开始不理解,男性的妈妈、姐妹、女友都是女性,怎么会厌恶女性?丹和他一起读女权书籍,讲起女性共同经历过的「特殊」时刻,「逐渐能感觉到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人」。

火与丹一起翻看她们写的书。图源《新东亚》还是有些东西被改变了。2020年4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内容包括「对持有、购买、储存、观看非法性摄影作品的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对利用性取向威胁、强迫他人的人分别处以1年以上徒刑和3年以上徒刑」,「未成年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从13岁提高到16岁」……2020年年末,N号房事件进入法律审判阶段。N号房创立者文炯旭(GodGod)被判无期徒刑,运营者之一Watchman被判有期徒刑7年,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在一审宣判中被判入狱40年,又因隐瞒犯罪收益1.0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2.5万元)再加刑5年,累计获刑45年,这是韩国迄今数码性犯罪量刑的最高记录。社会对数码性犯罪的敏感度正在上升。2021年,韩国政府有关数码性暴力的财政预算为37亿韩元,一年前,这项预算为9.8亿韩元。新的一年,火与丹还是很忙,她们去演讲,和政府部门负责人见面,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关注数码犯罪,回应受害者的求助。不过,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并不多,YouTube的订阅量刚超2万(2021年1月数据,后来数据被隐藏了),Instagram的的粉丝5000多,推特的关注数不到一万。丹说,她理想中的订阅量是30万,「可是也许人都不喜欢长久地沉溺在负面新闻里。」你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因为被反复地采访、追问,火在去年4月变得极其敏感。有一回,她从丹的住处回到家,打开玄关门的瞬间觉得哪儿有点不一样——每天开着的、用来通风的衣柜门,此刻却关着。有人闯进来了吗?柜子里是不是有人?她后退,关上玄关门,立刻给丹打电话。丹抓起防身棍就冲出去找火,两个人一起回到火的家,打开衣柜门,里面没有人。她们随时准备着帮助彼此,但很少聊起内心的脆弱,她们不希望自己再去加深对方的创伤,而是更多谈起怎么去治愈自己,或靠冥想,丹则静下来,去听钟表的声音。那些被她们帮助过的女孩也在给她们鼓励。有一个故事她们讲了很多遍:2020年夏天,一位受害者给她们发了一张照片,附上文字:因为太美了,所以想分享给你们。照片里,天空泛着粉紫色的光,一道绚烂的彩虹横跨而过。 「你们的勇气从哪里来?」我问。「啊,这不应该是我们的义务吗?这些事不是我们的话,还有谁来做呢?」火说,「我们两人都是那种忍不住的性格。」上高中时,她看见班里有同学欺负残疾同学,她一路追上去,揪着那个欺负的人,大声问:「为什么要欺负人家?」

图源:韩剧《就算敏感点也无妨》参考资料:<우리가우리를우리라고부를때><여성신문> 10명중 3명은일상에서디지털성범죄목격...‘지인능욕’ 가장흔해<한겨레21> 추적단불꽃의 n번방추적기<한겨레21> n번방을부순 ‘추적’의힘<국민일보> n번방추적기시리즈<The Guardian> 'Escape the corset': South Korean women rebel against strict beauty standards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