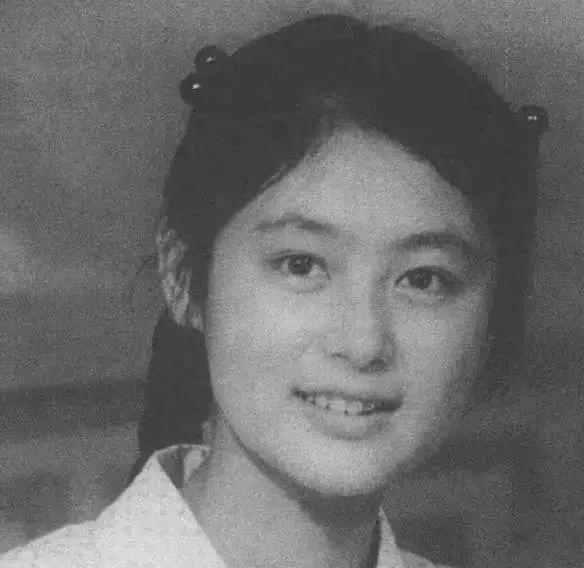潜江戏曲陈世美(村戏文陈玉龙)

外婆从乡下打来电话,说这个双休日村里演戏,要我带老婆孩子一起回乡看戏。小时候我是在乡下的外婆身边长大,村戏是乡里人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方式,许久没去看外婆了,我决定独自去外婆家看戏。
到达村庄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冬日里的太阳照射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们身上,让我的心头也感觉到一丝温热。奇怪的是外婆竟不在家,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一般在这个时候应该在屋中,听见我的声音,早该出屋迎着我。屋里只有二舅独自一人在桌旁吃饭,见了我,忙放下饭碗,接下我身上的背包,问我吃饭了没有。我并没有回答二舅的问话,而是急着问:外婆呢?二舅摇头一笑道:她呀,正在忙着呢,别管她,先吃饭吧。我这才放下心来,问外婆在忙什么呢,总不是忙着晚上演戏的事吧。没想二舅哈哈一笑道:正让你说着了,她正忙着那事哩。
剧团里有那么多的人,要她这个老太婆掺和什么呀?我接过二舅盛来的饭,不解地说。
二舅叹了口气道:剧团现在哪有什么人啊?年轻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还不是满生几个老角子在支撑着!女角更少了,小娥这两天感冒着,这不,你外婆她就亲自出马了。
外婆演戏?我几乎惊得把饭碗跌落了。外婆如今也有七十多岁了吧,她能演能唱能跳?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从没演过戏,她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到家就板着一张脸不大说话。外公非常怕她。只有村里或者外村演戏的时候,才见外婆开心地笑过。
村里有个祠堂,虽有些破旧,但是全村人最敬仰的地方。剧团的服装道具就放在祠堂的厢房里,演员的化装呀穿戴呀全在这里准备。戏台就在祠堂门口左侧,是个自建的土台,四旁有柱子,遇上雨天还可以在上面搭油篷布。戏台前面是一个大大的场子,可容纳千人。我径直走进去,厢房里果然有许多人在那儿忙乱着,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外婆的背影,她正在整理着一件艳丽的戏袍。外婆那聚精会神的劲儿,把我到嘴的喊声给噎住了。
外婆是什么时候学会演戏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笑着问外婆。外婆还没发话,旁边的满生抢先回答了:你外婆演戏还要学呀?你小子离出世还有老远的年头里她就是我们远近百里的名角儿了,她这叫重出江湖。
满生是剧团的团长,他的年纪和外婆差不多,满头白发,但精神挺旺,他说的话可不是戏言。我疑惑地看着外婆,外婆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她抬起头望着天空,仿佛在追忆那逝水流年。
小村的夜晚是伴着喜庆一起降临的,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话,我是不会相信如今还有那么多热心戏曲那么狂热的村人们。这种狂热与城里的年轻人不同,打一个比喻,城里人的狂热就像六月天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他们的狂热宛若冬日里的大雪,虽来势猛烈,但却慢慢融化,慢慢渗入到土地。场地上已挤进了许多人,戏台上早就亮起了两只大灯泡,我没有去找外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去打扰她的,隔断几十年的戏台,是否能让外婆找到以前的感觉呢?说实话,我非常为她担心。
戏台下还来了许多卖小吃食的摊贩,四邻八乡的村民们都早早赶来,很有一种热闹的气氛。来看戏的人中,大多都是中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占多。也真难为他们了, 他们早早吃晚饭,早早喂好猪,早早安顿好孩子,一步步从乡道上赶来,为的就是看一场村戏,或者说看一场我外婆和满生他们演出的戏。
戏还没有开演,我在场地上胡乱挤着,偌大的场地上竟然站满了人,这真有点出乎意料,也更让我为外婆担心了。既使外婆真如满生所说的那样曾经名噪一时,可时隔久远,外婆的演技不生疏吗?村人们还能接受她吗?
终于熬到了开场,只听得锣鼓密集地响起来,这是要把台下人们的精神和目光都集中到台上。果然,锣鼓一响,大家都抬头盯着台上,虽然目前还只是台右侧几个乐队的人在那儿打锣鼓,但他们生怕错过了一个情节,都不敢旁视。前边的人都是坐着的,后边的才站着,他们看上去很有秩序,连卖小吃食的小贩们也不敢吆喝,小小的土台上倏然显得神圣起来。
锣鼓一停,好戏开场。先上台的是一男一女,演了一个风趣幽默的小折子戏,台下笑得前仰后合,把场下的气氛搞浓了。接着才是正戏,叫作《平贵别窑》,说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
外婆一出场,确实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是外婆出演这个角儿,我也许根本就认不出来。台上哪有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踪影?完全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轻移莲步,与郎君依依惜别。待外婆一开腔,台下更发出热烈的掌声。
夫君此去西凉界,王宝钏我泪洒满胸怀……
小时候听过《平贵别窑》这场戏,可当我现在听到外婆的唱腔时,我还是被震住了。平常外婆总是不住地咳嗽,现在上了戏台,连那喘气声都没有了,戏曲真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文词戏是个地方戏,据说起源于当地的山歌小调,唱腔优美凄冷,伴以二胡,越发显出缠绵悱恻,以情感人。外婆的唱腔音色清纯委婉,凄苦时如泣如诉,欢欣时似山涧之流水,果有一种山歌小调的韵味在里面。唱到高潮处,我身旁的一位老头忘情地高举双手鼓起掌来,跟着大家都鼓起了掌。我注意到老头异常兴奋,有时还会跟着曲调轻声哼唱起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票友,我突然对这个老头来了兴趣,便跟他交谈起来,得知他是一个人从外村来的,而且他们那个村子离这里有十多里之遥。我不知道,一个老人孤身一人来这么个小村看戏,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拉到这儿来的呢?文词戏真有这么大的魅力?
然而,老头说出的一句话,差点让我笑出了声。

老头说:我是专门来看胡小燕唱戏的。
胡小燕就是我外婆,没想到外婆还有这么一个铁杆粉丝,真为她感到高兴,同时,也更相信满生所说的话,外婆曾经真正红火过。
一提到外婆的名字,老人眼前一亮,他说:几十年过去了,她的形象没有变。
我知道,老人是说舞台上的形象,现实中的外婆肯定是变化很大的了,十八岁的姑娘与七十岁的老人是有天大差别的,但我想外婆年轻时应该很漂亮,岁月的痕迹可以改变现实中的外婆,可舞台上的外婆却永葆了她的青春。
老头看样子很了解我外婆,我想与他拉呱拉呱,知道一些外婆过去的事情。因为外婆的那段光彩历史她从没在我面前提起过,或许是她那时认为我太小,不懂得这些事情;或许是她那时没有心情去谈论这些,她与外公总是在磕磕碰碰中过日子。等我长大了,就飞走了,逢年过节回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我太不了解外婆了,以前我还认为自己从小在外婆身边长大,对她最了解。现在看来,那完全是自己的表面看法,外婆的内心深处一定深不可测,要不她怎么能忍受这么多年不演文词戏?
老人把我打量了一会儿,说:现在年轻人对文词戏都不感兴趣了,你倒是个例外。
对于一个年轻人与他谈论文词戏和演戏的胡小燕,老头显得很激动,当他知道胡小燕就是我外婆时,老头仿佛遇到了知音,他说,为了使我更加了解文词戏,给我讲一个故事。
五十多年前,他们这儿的乡村曾活跃着很多文词戏团,都是各村自发组织起来的。而其中最有名的有两个,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村庄。而这两个戏团的名望是因为出了两个角儿,奇巧的是一个团出的是男角,而另一个团出的是女角。有一年县里要搞汇演,公社领导一合计,把他们两个团合并在一起组出了一个演出团,在县上演了三天三夜,尤其是男角和女角配合得非常好,声情并茂,珠联璧合,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县城。
那时,男角儿和女角儿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在那场演出中,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恋爱了。本来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的,因而也改变他们的人生。
有人要棒打鸳鸯,极力阻止他们的恋情,而这个人竟然是女角戏团的团长。团长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女角儿一旦嫁给男角儿,那么他们的戏团失去了台柱,就没有了竞争力,对方的戏团如虎添翼,他们的戏团将黯淡无光。当然,团长的反对不是公开的,而是暗地里行动,有时,暗地里的行动比公开更可怕也更具有杀伤力。
他们抗争过,甚至想到了私奔和殉情,可到底还是没有勇气走出那一步,终究难敌整个戏团或者说他们那个村庄全体村民的力量,他们的爱情就像他们戏台上演的许多苦情戏一样,所不同的是戏台上的男女最终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他们的爱情却夭折了。挥泪一别,肝肠寸断。
那个团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年后经多方撮合,百般做工作,在本村给女角找了一个老实憨厚的后生,让她嫁给了他,从此再也不怕别人抢走了他们的女角儿,他们村的戏团在方圆百里仍然可以响当当地走出去唱得响角儿亮。
然而,团长的苦心没有换来他们预期的回报,女角儿自从嫁给本村的后生后,再也不愿上台演戏,而这罢演一罢就是五十多年了。
老头一讲完,竟然泪流满面。不用猜我已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当年那个男角儿,也就是外婆的初恋情人呵。如果不是老头儿亲自讲给我听,我一定会认为这是个故事。我现在才理解了外婆为什么总是同外公磕磕碰碰地生活,为什么从不向我提起文词戏,为什么把她这段经历隐藏得那么深,为什么对满生说恨他一辈子的话。
戏台上的外婆坐在寒窑前思念着夫君,盼望着夫君早日的归来: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音信全无叫我好担忧,问一声我夫君莫非变了心……
外婆的演唱声情并茂,我看见台下有许多老太太在抹眼泪。我身边的老头对我说:年轻人,你外婆的声音真的没变,还是当年的胡小燕。
此时我已没有心情去看戏,我为外婆那逝去的青春忧伤不已。我突然烦躁起来,恨不得去把满生给揪出来痛打一顿,方解心头之怨恨。我悄悄地走出戏场,丝丝寒气袭来,我才感觉到夜已深了,头发上早沾满露水。回头一望不远处的戏场,那儿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演出,黑压压的人群根本没有理会到深夜的寒露,眼里只有那神圣的土台,以及心中虔诚的文词戏。
寒风一吹,我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一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我在黑暗中得意地一笑,走向戏场。
这时,戏已散场了,我去寻找那个老头,混乱的人群中是无法找到的。我想,他肯定去了后台,去见我外婆了。
外婆已回到祠堂里的厢房里卸妆,我首先给外婆鼓起了掌,祝贺她演出成功。外婆露出笑脸,外婆的扮相已不再是王宝钏,卸下妆的外婆恢复了本来面目,一笑就是几条皱纹,还轻咳了两声。我东瞧西看,满生问我找什么,我没好气地说:你不懂。外婆打了我一下道:这孩子,怎么能这样说话!满生他们几个也都停下卸妆,有些诧异地看着我。我问外婆,刚才有没有一个老头来过。外婆不明白地望着我问:哪有什么老头呀,老头来做什么?
我失望地坐在戏箱上,对满生说:刚才戏台下有个老头,他走了十多里山路来看我外婆演出,你说他还能是谁?满生还是满脸不解地望着我,在他的记忆中,外婆的初恋情人恐怕早就烟消云散了,胡小燕终归还是我外公的妻子,平凡地生活在小村里,生活在他们的身边,直至老去。
外婆这时夺口而出:刘清泉来过了?
我这才知道那个老头叫刘清泉,同时也证实了老头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不是他的自吹。满生这下把我紧紧抓住,问:真的有个高高个子的老头来过啦?我不理会满生,而是扶住外婆颤抖的身子,在她耳边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外婆,你好傻呀!外婆明亮起来的目光很快黯淡下去,外婆跌坐在戏箱上,喃喃自语:难得他来看我演戏了,那么远的路,他一个人……
搀扶着外婆回到家已是下半夜了,我一直睡不着,我在心中酝酿,我要做一件对外婆和刘清泉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夜太深了,要让外婆休息,我准备留到天明给外婆说。
吃过早饭,我把昨晚构想的方案向外婆公布了,我想外婆听了这个方案一定会高兴起来。没想外婆的反应却是沉默,接着是摇头否定。我问外婆为什么不答应呢,人家王宝钏苦等薛平贵也只有十八年,可你们却是五十多年了,难道就不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外婆还是摇头,说:你不懂的。没办法,我只好去找满生,本来,这个计划中也是需要得到满生的协助。
其实我的方案是十分可行的,并未有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只不过是要五十多年前的伙伴重新合作,让他们演一出当年没有演完的戏。这无论对外婆还是刘清泉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欣慰和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不仅把外婆的演戏生涯推进到一个辉煌的时刻,也给他们的美好初恋画上一个圆美的句号。这个方案的落实,首先必须要征得外婆的许可,然后得到满生的协助,一同去找刘清泉。刘清泉肯定是会同意的,从昨晚他走十多路山路来看外婆演出,就能看出他心中依然有外婆的位置。
满生听到我这个计划后,一拍大腿说:好,这事还真只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才可以想出来。你外婆的工作我去做。也许,这些年来,满生一直对我的外婆心有愧疚,如今顺水人情去做成这件事,也是对他们过去的一种补偿,他理所当然要去做好这件事。
我没进屋,满生在里面给外婆说了十多分钟,就把思想工作做通了,我猜想外婆以为我是在跟她开玩笑,看到满生来了才知我真的想办这事。外婆竟然像个害臊的小姑娘似的出来对我和满生说:人家要是不同意,切不可为难人家呵。我满不在乎地说:我保证人家会同意的,昨晚我跟他聊了那么久,可以看得出,他心里还是有外婆的。外婆嗔怪道:你瞎说什么哩!
事不宜迟,我在村里借了个摩托车,带着满生上路了。对于刘清泉的村庄,满生是熟悉的。一路上满生不住对我说着外婆过去的事情,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对外婆伤害得太深了,但从当时剧团命运的出发,满生说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半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满生也不知道刘清泉住哪里,好在村庄不大,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刘清泉的屋前。这是一幢二层楼房,有个小院,看样子日子过得不错。推开院门,屋里走出一个老太婆,她听说我们是找刘清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说:病了。
怎么会呢?昨晚不是好好地在看戏吗?老太婆肯定就是刘清泉的老婆,她又不知道我们的来意,不会骗我们吧?
倒是满生会说话,他说自己是刘清泉多年前认识的朋友,今天路过这里,想来看看。
老太婆的脸色还是阴沉沉的,她说:昨晚也不知是疯到哪儿去了,半夜回来摔坏了腿,还中了风寒,今天又是烧又是冷,正躺在床上哩。说着,她把我们带进房间。刘清泉一见我们,猛地想坐起来,可身子骨不管用,又躺下了。我真没想到,昨晚他还是那么起劲地为我外婆鼓掌,今天却躺在床上起不了身,人一到年纪,真是身不由己呵。趁着老太婆去给我们倒茶之机,我想了想,还是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虽然明知道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既然来了,我总要把事情说个明白,也好让他明白我的这番苦心,说不定下次还会有机会。床上的刘清泉这时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没有说出话来。从他的动作中,我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也看出了他对此深深的渴望,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刘清泉病得这么重,我们也不好多打扰,走时,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他,希望他病好后能践行我这个计划。
回来的路上,满生很是失望,我也有些心灰,回到外婆家,把情况给她一说,外婆表面好像并没有露出什么,可内心肯定是不平静了。从她的动作和言语来看,她竟然有些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我很少看到的。因而,我在心头暗忖,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把外婆平静的生活一下搅得浪花飞溅,对她的未来是好是坏?
更严重的后果是,今天晚上本来外婆还有一场演出,可她竟然不演了,满生满脸怨气地看着我,我也无言以对。如果不是刘清泉生病,今天晚上就是他们合演一台戏了,按照原计划,今天晚上外婆和满生同演一场《楼台会》,现在外婆罢演,满生只好又去求还在养病的小娥了。
那晚也不知小村演没演出,因为我下午就回了县城。坐在回城的车上,我还在想,难道是我的错搅乱了小村的一台戏么?
大概是一个月后吧,我正在单位开会,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那人说他叫刘小军,是刘清泉的孙子,他爷爷住在县医院的五号病房,他有话跟我说。
我请了个假,匆匆赶到病房。此时,我见到的老人与一个月前见到的刘清泉相差甚远,微弱的声音里隐隐约约可以听出一些意思。原来他还在想着我的策划,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想法,他想在病房里完成我这个策划,完成他最后的心愿。说实话,一开始我以为老人是在说胡话,可当我看到老人的目光时,我的心颤抖了,我看到他眼中那一丝亮光竟然全照在我的脸上,我点了点头,握住了他的手。
告别老人,我把刘小军约了出来,我们来到一个茶座,在那如水的音乐声中,我把外婆和他爷爷之间的故事复述了一遍。刘小军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故事,他爷爷给他讲过多少遍了。听医生说,他爷爷在世间的日子很少了,已快到弥留之际,对于我的这个策划,他觉得大胆而又新鲜,对他爷爷来说,没有什么比离开这个世界前与初恋情人同演一出戏更有意义了。我们两个年轻人商定,那边家人的工作由刘小军去做,外婆的这边肯定就交给我了。
第二天我专门找了一部车子,直奔乡下。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去做外婆的工作,是先骗她来县城,然后再作打算,还是先给她挑明?
出乎意料的是外婆听完我的话,默然无语了一阵,然后才说:什么唱不唱戏的,我去看他最后一眼吧。主动坐上了我的车。一路上外婆没有言语,看得出她其实还是在乎那个刘清泉的。车子一到家,外婆开口问了刘清泉的住院地方,就要赶过去。我把外婆接进屋,要她吃过饭后我和她同去。此时还只有十一点钟,妻子上班还没回家,儿子也在学校没放学,我先给刘小军打了电话,然后出门买菜,外婆许久没进城来我家了,得买几样外婆喜欢吃的东西,走时,我把电视里的戏曲频道打开给外婆看。
二十分钟后,我回到家一看,外婆不在了,四处一喊,哪有外婆的身影?莫非……我立即打的赶往医院。
赶到医院,还未进五号病房,我就听到了外婆那清脆婉约的唱腔,我不敢惊动他们,就站在门口观看着这场离奇而又珍贵的演出。刘小军同样站在房门外,他身边男男女女站着好几个,就连几个护士也都停在那儿出神地凝听。
胡小燕唱:王宝钏守寒窑一十八载,今日与夫君相会莫不是在梦中……
刘清泉唱:水流千里终要归大海,薛平贵千里征战心挂在寒窑……
刘清泉半躺在床上,脸色绯红,声音洪亮,根本不像个病人。
渐渐,刘清泉的脸色由红转白,声音也小了下去,咿咿呀呀谁也听不清在唱什么。
外婆凄婉的唱词戛然而止,忽大声哭出:我的夫君呀!
在场所有人的都听出,外婆哭喊出的仍然是一句文词戏腔。
(来源:2018年03月03西安晚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