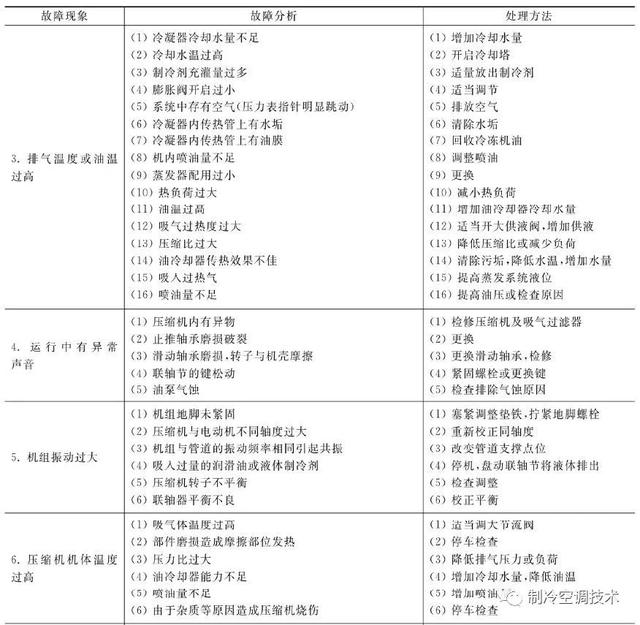岳麓书院是江南四大书院(岳麓有我师岳麓是我师)
湖南长沙岳麓山,天下名山,虽矮却巍巍。作者年青时居岳麓山从师读书工作,后来离开了多年……
1.驰过岳麓山
我下决心在过长沙岳麓山时不下车去看望老师,而是随车驰过去,于是岳麓山下老师住的那栋楼疾移到车窗后面去了,岳麓山也像一朵云飘向车后……
这是昨天那时之前虚拟的句子,没有写出来,因为根本不是这样过岳麓山的:乘高铁到长沙,高铁站出来即入长沙地铁,忽一站,又忽一站,站名很有我熟悉的站名,所有的站名都是一样地下地铁站的光景,“岳麓山”也一样,并且转眼就过去了,地铁隧道的灯拉成模糊的光带,眼耳都是忽忽忽。老师住的楼,岳麓山,城中的其他师友,故人,都忽过去了,在疾驰的节奏里人也没了情思悠悠,是木然的。“望城坡站到了”,到了,就出站,只望一望已越过了头长沙城一一其实还是望不见什么,被楼挡了。然后乘了高速汽车,疾驰回老家去,长沙只成了回老家要经过的、转车的地方。
因为,下高铁时再看了一眼弟弟发的信息:哥你今天一定要兑现回来,妈妈望你望得很!
又因为,怕路上自己沾上新冠病毒之类,中途去看望老师,怕……;而回老家,我可以到家先和住新房了的母亲和弟弟一家见个面,然后在空置了的老屋自我隔离几天……
这是昨日的事,昨日的心境,回老家后才写出。
2.“忽忽”中省度自己
昨天我写“驰过长沙岳麓山”的短文呈于微信朋友圈,有朋友留言:“……曾经构成你部分生活的一切,在'忽忽'的飞驰中消尽了,疫情让人和故交亲不起来,高铁使人和熟识的环境生分了。看来,故园是用来怀念的,回是难回去了。”
是的, 回不去了。你说出了我没有说出的话。
但古代人就有此叹。苏东坡乘一叶扁舟再遊赤壁就发出过:“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一一何况我们乘坐的已是子弹头一样的高铁呢?
所以不必由我感叹“我”之外的江山了,只对准我自己来感叹一下并问一下吧:我还是我吗?
时光的河匀速地拂身流过,除了牙齿痛那样的痛楚,自己难以感觉自身的变化,总以为我还是我。总以为自己还年轻。五年前,记得是5月份,张新奇从澳大利亚回国又要返澳,经停广州的间隙里打来电话约我相见一一我们大约三十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他就用我听惯的湖南长沙话惊呼:
“方能,你格样老哒呵!”
“格样”即“这样,“哒”即“了”一一“……你这样老了呵”,我心里重复这话,像闻重锤声。
我们中国人都有当面恭维别人的习性,文言词叫作“谀面”。张君虽也是中国人,但因在外国住久了吧,竟至不谀我面了。当然,他本来比我大,我私下里称他兄,当着第三方称他“老师“,何况他本是不谀人的,对我就更有打赤膊相见的自由和坦然。而我当年在他面前好像也全敢讲直话……。
一一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出了自己的变化:我会“面谀”了!
曾日月之几何一一我已不复那么真诚一一自我不可复识矣!
呜呜!呜呜!一一嘻嘻!
我独自在车的呜声中自己了呜了几秒钟,就笑了。这又是我的变化。隐隐记得,我年轻在长沙的时候,会沉郁着一人在岳麓山走很久很久的,然后走到岳麓之另一麓桐梓坡的张新奇家,也有几次是走到岳麓之另一麓银盆岭的韩少功家。那时候,他俩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
我知道他们早分了道,也早就都不住长沙城了。但在乘的车“忽“过长沙城的时候,恍然间我把他们仍当成长沙城的一部分,岳麓山的一部分。
哦,我的老师、同学,及文学的师友……
3.岳麓山的老师
思维还在“驰过岳麓山”,虽然驰过时并没有什么感觉,又驰过好几天了。
我对岳麓山是有感情的。二十几到三十几岁,我在岳麓山下读书和工作:读书两年,工作八年。读书和工作的处所都是在湖南教育学院,一所规模不大实际不小的大学。“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普世的专家们作的这种论断尤其适合此学院,因为院里有真正的大师。说到大师,我的同学们马上会想到陈蒲清教授,想到他等身的著作、渊博的学问、与人为善的胸怀及温和谦逊的笑容。但先生还有至大至刚的一面,只有近距离长相处的人才可能感知到,也只有国家民族处非常之秋、众人倒摇如风中草的时候才从先生身上显现出来,像顶梁石柱在地震波袭来时才溅火星:“这责任不在别人,我是系主任,找我!要处罚就只处罚我!” 并且仍然顶梁不倒。我的同学彭天翼在同一单位工作过更长时间,对此有真切回忆,不在这里引述。
还有刘上生老师。也是谦抑的笑,戴更深度的近视镜,学专一门,研究和讲授古代小说,尤其对准《红楼楼》。那是“新方法论”风行学坛的岁月,上生先生虽未置身于发明新方法论的上游,但实在成了运用新方法剖析古小说的先手和高手。学生听他讲《红》,就如第五回写的贾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听十二支曲子,迷了痴了,又获有高空视角。他边讲边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步态迥非平时,话音也曼妙非常,偶尔粉笔触黑板笃写一字,便像给弦乐打一节拍。一室陶醉,又恍然有悟。
后来,我不是学生而成这两位先生的同事了,仍想听他们的课。再后来,我调岭南,虽所居院子更小但毗邻南方几所著名大学,方便常到那些校园溜达,因运气不好之故吧,总没遇到过我的这样的大师或老师。北方呢?那最高的金字塔大学,也做过风一样拂过的访客,拂过也就拂过了,没生出景仰,以为不过如此,地势高而已,衬得上面的树成了显得更高的树。而岳麓山本是不算高的,教育学院又还在麓之脚。
其实岳麓书院也只在麓之脚,山的另一边的脚。
还有几个,回忆起来也是蛮有特色的:伍大希老师,名字出自“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却极爱显形和发声,似乎真秉承了他的闻一多先生的如火性格。唐泽定老师,写论文时署名唐牛,肚子庞得是有些像牛肚,却不是虚胖,走路昂首挺肚,雄赳赳赛健牛,讲朦胧诗也讲得出一股牛劲。还有一位刘城淮老师,北大中文系毕业,政治运动中打回湖南原籍,娶了个厉害的会种地会管理他的老婆,平反后他挈妇将雏来做教院教师,忙,家务做得少了,老婆却因无地可种成了专管他的干部,一不如意便抓起竹枝扫帚追着骂打:“刘城淮!你敢不做!你还敢跑,你还敢跑!……”
刘城淮老师后来送过我一本他著的《中国神话研究》,是他一生心血所铸。我几十年以后一一去年退休以后一一想写一部神话诗时才较认真地一读,我以为它是中国神话研究的经典,行文也颇精劲。而我过去没认真看,也就不曾当他面说过一声好。唉!
还有……
4.岳麓往迹
南岳衡山举世闻名,却非孤峰,而是以它为主峰的一条山脉。“湘江北去”,这条山脉从回雁峰起始也傍江北去,一起一伏亦涌如江浪,涌出七十二个峰头。北端最矮一峰,已不能称峰,只能叫麓。麓,山脚下的意思。南岳衡山的脚止于江心有个橘子洲的湘江边上。
江东面即长沙城。后来城区扩大,江东面仍是长城主城。城中扰嚷,早有读书人出城过江来搭寮读书,宋朝时终在山上建起一书院,命名“岳麓书院”,又请来张栻、朱熹这样的名师讲学。岳麓山开始出名了。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锺此……”
岁月移到清末民初,民初某年一个黄昏,少年毛泽东一身学生装,走出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门,站在湘江东岸脁望岳麓山,吟出这些诗句。他显然把岳麓山当成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代表,而且看出绵延的山川奇气都汇聚于此。他不是一个人,蔡和森、萧子升等十几名青年才俊相伴而出,走到湘江边。
郁结多日的阴云散了,太阳从西边岳麓山顶露出来,虽是夕阳,馀光仍当仁不让,照得江水跳玉翻金。蔡和森说:“过吗?” 毛润之说“过”,大家也喊“过”,于是纷纷脱衣,一群文雅书生成了赤身蛮子,都只著一条小短裤,干衣服等物件集中放在一个浮木架,噢嘿噢嘿下水游起泳来。他们要游到湘江对岸去。
去干什么呢?露宿,今夜到岳麓山爱晚亭去露宿。他们约好了的,要在风霜雨雪中锤炼自己,为将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做体格上的准备。今夜不是第一次。
中间有一位,叫罗章龙,要去日本了,自起了日人式的外号叫“纵宇一郎”,毛润之们也赞成,已为他饯过行了,但还是要一起在湘江水中和夜的岳麓上这么“纵宇”一回才肯行。所以在润之、和森近处游得很起劲。
毛润之喜欢仰泳,因为这种泳姿方便他仰望天空思考问题。他还继续做起没做完的诗,划水声中听他念,离得近的也听得见,知道是给纵宇一郎的送行诗:
“洞庭湘水涨连天,朣朦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又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这是五十年后我想像的画面。毛诗是真的,以游泳作和朋友的分别仪式却是想象的。这时的我,二十六七岁,刚调来长沙,住岳麓山下,有二三好友,约好一起夜登岳麓山。皓月当空,山林作银辉色,山虫吱唧如音乐,隐隐望见黄兴墓蔡锷墓也不怕,因为岳麓山葬的是国士。山那面下去,到了月光照亮也拖出影子的爱晚亭,那可是毛、蔡诸朋友们真正露宿过的亭子,有书为证的。我和朋友走着,议着……。
又三十多年以后,我过岳麓山一一倘若我能停下来游岳麓山,还敢不敢夜游?还有不有同游的朋友?问题是,还敢不敢“纵宇”?当年那位“纵宇郎”后来是落了伍的,几十年后靠出示毛润之的赠诗才挂名籍部……
但愿还有,还敢。独自也敢。
哦,岳麓山,永远唤人努力向上的山。2020年6月底

(岳麓山爱晚亭。图借自网上)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