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曾说过有关童年的句子(一群孩子的友谊)
埃米尔五岁时失去了爸爸,和妈妈相依为命,在德国乡下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这一天,住在柏林的姨妈写信来邀请埃米尔去度假,妈妈把辛苦攒下的140马克别在埃米尔的上衣内口袋里,让他捎给也住在柏林的外婆。没想到,在火车上,一个可恶的小偷趁他熟睡的时候偷走了这笔钱。埃米尔在追踪小偷的过程中结识了柏林的一大批男孩子,他们迅速地成为好朋友,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追捕大戏……

《埃米尔擒贼记》,[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华宗德、钱杰 译,明天出版社 2017年1月版。
《埃米尔擒贼记》由德国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年2月23日-1974年7月29日)于1929年出版,也是身为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的他所创作的第一本儿童读物,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埃米尔擒贼记》在出版后就一炮而红,也由此带领着凯斯特纳进行了多年高产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飞翔的教室》《两个小洛特》《小不点和安东》等多本著名作品。他在1960年获得国际安徒生作家奖,被誉为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还曾6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埃米尔擒贼记》于1931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如今已被翻译成至少59种语言。
本期“儿童文学通识课”,子葭要讨论的是《埃米尔擒贼记》的儿童文学经典叙事模式——“家-远方-家”,通过一群孩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擒贼”过程中结成的友谊,一个男孩完成了成长。
城市最可怕的一点,正是“匿名性”
《埃米尔擒贼记》的确是一本在儿童文学史上意义非凡的书。它是第一本创造了“儿童/少年侦探”这个概念儿童文学作品,是我们小时候曾流行的《冒险小虎队》等系列的大鼻祖了……同时,它也是第一个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所创作的儿童小说,并带领读者由小主人公的视角在城市里奔走。
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曼 (Perry Nodelman)在他的权威著作《儿童文学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书中提出,儿童文学中有一种经典的叙事模式,即 “家-远方-家”。在《埃米尔擒贼记》中,“远方”不再是一个永无岛类的幻想世界,而是真正存在于现实世界,有了具体的名字和样貌的现代城市——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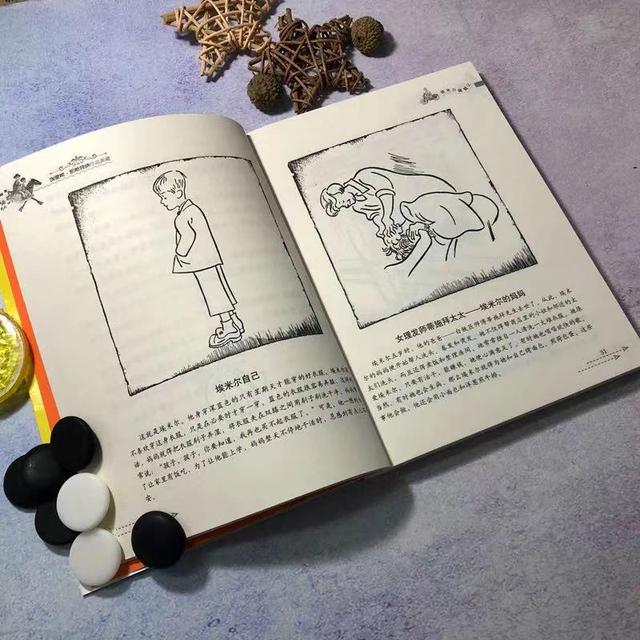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家-远方-家”的叙事模式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一个既定的、稳定的家庭空间,作为文本的起点和终点;二是在家庭空间之外有一个环境让主人公前往并探索。虽然《埃米尔擒贼记》基本符合这种离家又归家的叙事模式:埃米尔从在乡下的妈妈家离开,探索了柏林城,最后来到柏林的外婆家,并在这里与妈妈重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的“家-远方-家”的模式中,“家”和“远方”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的二元关系,然而,在《埃米尔擒贼记》的结尾,这种紧张关系被巧妙地消除了——在城市里,埃米尔招待了新朋友们,与家人团圆。在埃米尔的概念中,柏林从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城市转变为一个被朋友和家人围绕的熟悉的家。
这样的转变在随着故事的发生逐渐推进。在《埃米尔擒贼记》的第一部分中,“家”和“远方”的对立是极其明显的:凯斯特纳特意将埃米尔设定为一个生活在德国外省小镇的小男孩,独自前往大都市柏林,由此强调乡村和城市的冲突感。在故事中,这种对立被埋藏在埃米尔的潜意识中,并通过他到达柏林前的一个噩梦展现出来。
在梦中,埃米尔被敌人驾驶着由九头马拉的火车追赶,他先是试图躲进一栋高楼,然后爬上高楼的铁质防火梯,然而这两次尝试都没有甩掉火车。埃米尔一直奔跑,直到看到草地上和一座风车才感到安全——在梦中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妈妈在风车里,像往常一样给奥古斯丁夫人洗头,然后她毫不费力地通过操作风车把埃米尔从抓捕中救出来。卡斯特纳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埃米尔的疯狂噩梦,通过高楼和风车这两个地标形象地描述了埃米尔对城市的恐惧和乡村给他的安全感。
当然,对小小的埃米尔来说,乡村是熟悉的家,而柏林是一个危险和未知的地区,更别提他的母亲还一直紧张地提醒他要保证钱的安全并在正确的目的地下车。怕什么来什么,这个噩梦就是个坏兆头。当埃米尔醒来的时候,读者和埃米尔一起发现他的钱被偷了,他决定在终点站前下车去追赶小偷——完完全全把妈妈的叮嘱反着做了!
当埃米尔开始穿梭于柏林,努力尾随小偷时,大城市给他的不愉快脱离了想象,变得更加具体,乡村/城市和家乡/远方的对立得到进一步加强。起初,埃米尔对柏林这个城市拥有一种矛盾的看法,他对这里交通、商店和建筑既印象深刻,又不知所措,他感叹道:“原来这就是柏林!”然而,随着他在这个城市的冒险,埃米尔很快就感到,在这个繁忙的大城市里,自己是多么多么的渺小,并意识到“在一个城市里,没有人有时间处理其他人的麻烦。他们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一度,埃米尔沮丧得几乎放弃了行动,承认“感觉如此孤独真是太可怕了”,并恐惧于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冰冷的城市与书开头对埃米尔家乡的描写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友好的地方,埃米尔可以通过声音认出母亲的顾客,轻松地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并与他们进行真诚地交谈。正是在这种对比下,凯斯特纳展现出城市最可怕的一点,正是“匿名性(anonymity)”——每一个人都只是人海中的一张脸。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道,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时,“我们褪去朋友们熟悉的样子,成为了无名游荡者组成的大军中的一员”。当埃米尔在柏林街头游荡时,是珍贵的友谊将他从城市的“匿名性”给他带来的压迫感中拯救出来。当埃米尔遇到古斯塔夫和其他加入抓贼大冒险的男孩后,埃米尔的日常活动范围随着他对城市空间的熟悉而迅速扩大。在新建立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埃米尔开始通过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探索城市,建立起对城市的空间知识,也随之慢慢将家与远方(这座城市)的对立感消除。到故事的最后,埃米尔似乎完全熟悉了柏林。当他试图取回他的行李和送给外婆的花时,他甚至自信地给出租车司机指路。
更重要的是,埃米尔与城市儿童的友谊投射出了一个在城市环境中建立的和谐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孩子们追捕偷了埃米尔钱的小偷的过程中,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有适当领导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紧密组织。孩子们不仅在做决定、准备食物和钱、面对内部骚乱时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尽管在偶尔试图平息异议时,公开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完全遵守了好孩子和正义公民的行为准则:当他们需要在外面待到很晚的时候,他们会通知他们的父母;他们也拒绝从小偷那里偷回钱、坚持以合法的方式处理这件事。
故事的结尾,孩子们模范行为得到了社会和政府机构、警察和新闻界的奖励,也显示城市内的机构也相应地高效、理性和公正。埃米尔甚至与警察和记者都成为了朋友。记者凯斯特纳先生(是的,作者把自己安排进了故事)曾在一开始偶遇埃米尔,给落单又没钱的他付了车费,但并没有关心他的遭遇。而在埃米尔抓到小偷后,作为记者的凯斯特纳终于有机会听到了整个故事。他还主动给埃米尔买了奶油蛋糕,带他参观了编辑部,并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家。这一章以埃米尔和凯斯特纳先生持续互相挥手的友好姿态结束——“直到出租车转过一个弯,离开了视线”。通过这种方式,凯斯特纳赋予了城市和它的权力机关以人性。
在城市里认识的新朋友们的帮助下,柏林从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空间转变为一个理想的、运作良好的社会。埃米尔开始熟悉它,承认它,并了解到,即使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在可敬的公民的帮助下,冲突的解决和秩序的恢复似乎也总是有保障的。而凯斯特纳尝试在文中凸显的孩子们“友谊的力量”其实源自他自己的信念,寄托着他对青少年、对下一代人所能创造的更好的社会的期待。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埃米尔和侦探们》(1931)画面。
一个理想化的儿童榜样
城市的匿名性不仅让小男孩埃米尔感到恐惧,也是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的担忧。在埃里希·凯斯特纳生活的时代,德国民众正在体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生活带来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代,政府职能、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知识分子得出悲观的结论,认为人们终将无法从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权力体系中得到庇护。人们的人性和个性将屈服于功能性——在“社会系统不可阻挡的功能合理性”中,每个人都变得可被取代,无足轻重。
卡斯特纳希望对抗这种恐惧,并在儿童文学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斯普林曼(Springman)认为,卡斯特纳受到启蒙时代的代表作家和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重要影响。莱辛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善良和真理的社会表现。
在《埃米尔擒贼记》中,埃米尔的友谊促进了各类人群间交流和合法、有效的社会活动——这无疑反映了莱辛的观点,即这种人类关系包含了理性的讨论、宽容和道德上的卓越。此外,在埃米尔与新闻界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也在暗示,在公共领域中,友谊也可以与权力体系的冷漠相抗衡。故事的结尾处,在埃米尔外婆家,埃米尔的家人和新朋友们一起为埃米尔的友谊和这段友谊所成就的壮举庆祝,也代表着家和远方的对立完全被消除。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讲述乡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凯斯特纳的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另一部他在魏玛时代出版的小说,面向成人读者的《法比安》(Fabian),也同样有着类似的主题。在书中,当主人公在柏林漂泊时,他的种种经历向他表明,柏林是一个不道德的城市。
然而,当他回到家乡时,他发现他的外省家乡并没有能实现他的希望,让他过上能够保持自我的生活,他感受到了城市和乡村普遍存在的糟糕形势。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以为是对立面的两个地方,其实是平行的。虽然凯斯特纳对社会的悲观态度深深地印刻在了这部成人小说中,但显然他在《埃米尔擒贼记》中采取了更为乐观的观点。
这种对比表明,卡斯特纳对年轻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他们带来社会的变革,创造更好的未来。斯普林格曼进一步指出,不仅凯斯特纳认为“小孩拥有着成年人在这个糟糕的社会中被迫放弃的优秀人类品质”,而且“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开始将儿童视为正确社会行为和态度的最好老师”。(其实这种成人的放弃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也多少带着些绝望在里面,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德国社会正走向崩坏……)在《埃米尔擒贼记》中,卡斯特纳正是塑造了一个这样理想化的儿童榜样:一个优秀的男孩将成为一个有原则的公民,找到所有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并因此得到良好运作的社会的奖励。
然而,虽然他的成人读物在当时透露出他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忧虑(这也导致他的作品被纳粹列为禁书),但凯斯特纳在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中常常刻意回避社会现状对个人的影响,这令他的书自出版以来也收获了不少批评。
笔名为亚历克斯·韦丁(Alex Wedding)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曾在一本苏联流亡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凯斯特纳笔下对“好警察”的刻画,以及他认为社会冲突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解决的观点都应该被拒绝。另一批评家雷德曼(Redmann)则以书中埃米尔和他母亲遭受的贫困为切入点,阐述了类似的批评。
在故事的结尾,虽然他们物质上的困难被埃米尔因聪明地抓到小偷而获得的一千马克的奖励解决了,但“魏玛共和国这种贫困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提及,个人的成功掩盖了政府应践行的承诺和行动”。批评家们似乎在暗示,书中当代柏林的背景应该拥有现实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成为叙事手段,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可替代的符号。可以说,由于凯斯特纳坚持着在童书中构建把理性和正义作为基石的现代乌托邦,他模糊了魏玛时代动荡不安的底色,也将当时柏林的孩子真正的生活样貌隐藏了起来。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儿童读物是否必须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恐怕会一直进行下去。有趣的是,在亚历克斯·韦丁写的那篇旨在批评凯斯特纳的檄文中,也对他写出成功的儿童文学的能力给予了一些高度评价,认为“这种能力部分源于对儿童心理学的精确了解”。他避免了“爸爸最懂的(father-knows-best )态度,避免了伸长食指的说教,而代入了丰富的想象力、叙事艺术、双关语、情景喜剧的幽默、悬念——最重要的是采用了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虽然是来自批评者,但这也是一个对凯斯特纳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成就最真诚且全面的总结了。
回顾这本近一个世纪前出版的书,如今的学者也认为凯斯特纳是第一个“真正成功地在儿童文学中建立和普及了城市环境这一文学手法(literary device)的作家”。尽管如上文所述,凯斯特纳对儿童和社会改革的设想仍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埃米尔擒贼记》也的确对现实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都市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这本第一部刻画城市小孩的儿童读物,也走进了一代代新的城市小读者的家中。
——
参考资料:
1. Carroll, Jane Suzanne. Landscap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Routledge, 2012. ProQuest Ebook Central, ebookcentral.proquest/lib/oxford/detail.action?docID=995666.
2. Donahue, Neil H., and Doris Kirchner. Flight of Fantasy: New Perspectives on Inner Emigration in German Literature, 1933-1945. Berghahn Books, 2003.
3. Goga, Nina, and Bettina Kümmerling-Meibauer. Maps and Mapp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Landscapes, Seascapes and Cityscape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4. Kästner, Erich. Emil and the Detectives. Vintage Books, 2012.
5. Nodelman, Perry.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 ed., Longman, 1996.
6. Preece, Julian, and Osman Durrani. Cityscapes and Countryside in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PLang, 2004.
7. Redmann, Jennifer. “‘Läßt Sich Daraus Was Lernen?’ Children’s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Ideology in the Weimar Republic and Nazi Germany.” Die Unterrichtspraxis / Teaching German, vol. 31, no. 2, 1998, pp. 131–37. JSTOR, JSTOR, doi:10.2307/3531173.
8. Springman, Luke. “A ‘Better Reality’: The Enlightenment Legacy in Erich Kästner’s: Novels for Young People.”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4, 1991, pp. 518–30. JSTOR, JSTOR, doi:10.2307/406667.
撰文/子葭
编辑/申婵 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