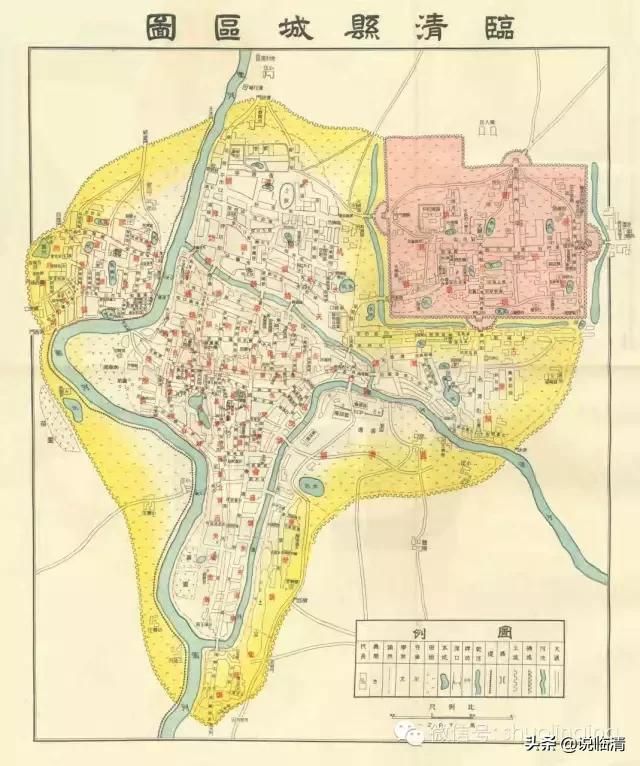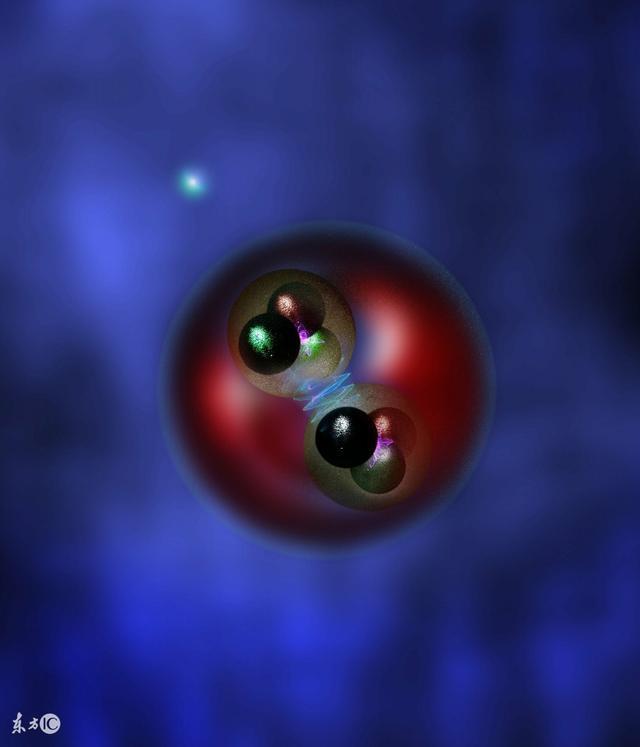看懂了神话已经明白了世界的真相(我们有可能在神话中再找到些许历史吗)

西塞罗与罗慕路斯
根据一则罗马传说,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11月8日申斥喀提林的场所——朱庇特神庙——是7个世纪前由罗马的缔造者罗慕路斯(Romulus)建造的。那时,罗慕路斯和他的小社群的新公民正在后来的罗马广场所在地(西塞罗时代罗马城的政治中心)与附近一个名为萨宾人的民族作战。形势对罗马人很不利,他们被迫撤退。作为最后一搏,罗慕路斯向朱庇特神祈祷——确切地说是“坚守者”朱庇特(Jupiter Stator),即“让人站稳脚跟的朱庇特”。罗慕路斯向神明承诺,如果罗马人能因此抵挡逃跑的诱惑并在敌人面前坚守阵地的话,他将修建神庙以示感谢。他们做到了,于是就在那个地点建起了“坚守者”朱庇特的神庙,这是城中为纪念神明帮助罗马取得军事胜利而建起的一大批圣祠和神庙中的第一座。
至少李维和其他几位罗马作家的故事是这么讲的。考古学家没能确定无疑地找到这座神庙的任何遗迹,它在西塞罗时代必然经历过大规模的翻修,特别是如果它的起源真能追溯到罗马的开端的话。但确定无疑的是,当西塞罗选择在那里召集元老院时,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想到了罗慕路斯的先例,想用这个地点来强调自己的态度。他希望让罗马人在新的敌人喀提林面前站稳脚跟。事实上,当西塞罗在演说最后向“坚守者”朱庇特请愿(无疑是面对着那位神明的塑像)并提醒听众回想起这座神庙奠基的情景时,他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
朱庇特,罗慕路斯在建城的同一年建起了你的神庙,我们正确地把你称作让这座城和帝国稳固的神明——你将不让此人和他的同伙染指你和其他神明的庙宇,不让他们踏入城墙和城中的房屋,以及夺走任何罗马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当时的罗马人没有忽视西塞罗把自己标榜为新罗慕路斯的暗示,这种联系可能产生了反作用:一些人将其变成了又一个嘲笑他小城出身的理由,称他为“阿尔皮农的罗慕路斯”。
这是罗马人对建城祖先,对早期罗马令人激动的故事和对该城诞生时刻的经典引述。即使到了现在,母狼哺乳婴儿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雷慕斯(Remus)的形象仍然是罗马起源的标志。这幅场景的著名青铜塑像是被复制次数最多和最能一眼认出的罗马艺术品,出现在数以千计的纪念明信片、茶巾、烟灰缸和冰箱贴上,还作为罗马足球俱乐部的队徽被张贴在现代罗马城各处。

图7 无论母狼塑像本身制作于什么年代,双胞胎婴儿无疑是为了刻画那个起源神话后来于15世纪添加的。世界各地都能找到该雕塑的复制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他将其作为罗马精神的象征四处分送。
由于这个形象如此常见,人们很容易对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按照罗马人的惯常顺序则是雷慕斯和罗慕路斯)的故事过于想当然,从而忘记了那是关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的任何建城活动中最奇特的“历史传说”之一。它无疑属于神话或传说,尽管罗马人认为它大体上是历史。母狼哺乳双胞胎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故事中的一个如此奇怪的情节,对于果不其然出现一只恰好处于哺乳期的动物来喂养这对弃婴这一点,甚至连古代作家们有时也提出了应有的怀疑。故事的其他部分混合了大量令人困惑的细节:不单单是这个不寻常的存在两位创建者(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想法,还有一系列完全不符合英雄形象的元素,包括谋杀、劫掠和绑架,而且罗马最早的公民大多是罪犯和逃亡者。
这些令人不适的方面让一些现代史学家认为,整个故事一定是罗马的敌人和受害者编造的某种反面宣传,后者受到了咄咄逼人的罗马扩张的威胁。这种试图解释故事之中的怪异之处的想法,即使不是罔顾事实也是过于异想天开的,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无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故事源自何时何地,罗马作家们对它从未停止过讲述、重述和热烈讨论。维系于这个故事之上的,并不仅仅是该城最初如何形成的问题。当元老们挤进罗慕路斯的旧神庙聆听这位新罗慕路斯——“阿尔皮农的罗慕路斯”——演讲时,他们应该很清楚那个奠基故事还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如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什...
我们若要了解古罗马人,弄清楚他们相信自己来自何方是必要的,还要仔细思考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故事的意义,以及其他奠基故事的主题、微妙和暧昧之处的意义。因为这对双胞胎并非最早那批罗马人的唯一候选者。在罗马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形象——他逃到意大利,建立了作为新特洛伊的罗马——同样引人瞩目。尝试看到可能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东西也一样重要。“罗马始于何方”这个问题对现代学者和他们的古代前辈来说几乎同样有趣和有吸引力。考古学家对最早期的罗马的描绘与罗马神话中的截然不同,它出人意料,常常造成困惑和争议。甚至著名的青铜母狼像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辩。它真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罗马艺术品之一吗?还是像近来的一项科学分析所暗示的,它实际上是中世纪的杰作?无论如何,过去差不多100年间,人们在向现代罗马城地下发掘时找到了一些痕迹,它们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00年那个台伯河畔的小村,这座小村最终成了西塞罗时代的罗马。
谋杀
关于罗慕路斯的故事不是只有一个。该故事有数十个不同的版本,有时还互相矛盾。在与喀提林发生冲突10年后,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给出了自己的版本。和此后的许多政治家一样,他在自己权力式微后选择政治理论(以及一些相当自负的高论)作为慰藉。书中,他在对好政府的本质进行长得多的哲学讨论背景下谈到了罗马“政制”自始以来的历史。但在开头简要讲述了那个故事后——他不太自然地回避了罗慕路斯是否真的是战神马尔斯之子的问题,同时对故事中的其他神话元素提出了疑问——他开始严肃地讨论罗慕路斯为其新定居点所选位置具有哪些地理优势。
西塞罗写道:“若不是把城建在永不停流和不断注入海中的宽阔河流边,罗慕路斯还能怎样更巧妙地利用靠海的优势但又避免其不足呢?”他解释说,台伯河让从外部进口物资和出口本地富余变得容易,而把城建在山上不仅为其提供了抵御来犯之敌的理想屏障,而且在“瘟疫流行的地区”营造了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仿佛罗慕路斯知道自己所建的城有朝一日将变成伟大帝国的中心。西塞罗在这里展现了某种良好的地理意识,后来又有许多人指出,该选址的战略地位使其对当地竞争者具有了优势。但他出于爱国情感而隐瞒了一个事实:在整个古典时代,那条“永不停流的河”也让罗马经常成为大洪水的受害者,而“瘟疫”(或疟疾)则是该城古代居民的头号杀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西塞罗的版本并非建城故事中最著名的一个。大部分现代叙述主要依据李维的版本。他的作品对我们了解早期罗马仍然极为重要,但我们对“李维其人”的了解却少得出奇:此人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帕塔韦乌姆(Patavium,今天的帕多瓦),他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开始编写罗马史。他与罗马皇室的关系足够密切,曾鼓励后来成为皇帝的克劳迪乌斯著史。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故事不可避免地在李维史著第一卷中占据重要地位,地理内容远比西塞罗的版本要少,但叙事要生动得多。李维从那对双胞胎写起,然后很快转向罗慕路斯一人后来作为罗马奠基者和第一位国王的成就。
李维表示,这两个小男孩是一位名叫瑞娅·西尔维娅(Rhea Silvia)的贞女祭司所生,她生活在意大利阿尔班山上的阿尔巴隆迦(Alba Longa),位于后来的罗马城址以南不远处。她是在一场手足相残的权力斗争后被迫成为贞女祭司的,而非出于自愿:她的叔叔阿穆利乌斯(Amulius)驱逐了兄长努米托耳(Numitor)——西尔维娅的父亲——夺取了阿尔巴隆迦的王位。然后,阿穆利乌斯以祭司身份(表面上是一种荣誉)为借口,阻止他兄长一脉出现令他难堪的继承者和对手。结果,预防措施失败,因为西尔维娅很快怀孕了。按照李维的说法,她自称被战神马尔斯强暴。李维似乎和西塞罗一样对此存有怀疑;他暗示说,战神可能只是用来掩盖纯粹人类情事的便利借口。但也有人自信地记录,西尔维娅照看的圣火中出现了离体的阳具。
她刚生下那对双胞胎,阿穆利乌斯就命令仆人把婴儿扔进附近的台伯河淹死。但他们幸免于难。因为就像许多文化中与此类似的故事经常发生的那样,接受这种令人不悦的任务的人没有(或不忍)完全遵照指示行动。相反,他们没有把盛有双胞胎的篮子直接扔进河里,而是放在了漫过河岸的水边(当时正在发洪水)。在婴儿们被冲走淹死前,那头著名的母狼前来营救了他们。李维是试图将故事中这个特别不可信的方面合理化的罗马怀疑者之一。拉丁语中的“母狼”(lupa)一词在口语中也被用来表示“妓女”(lupanare是“妓院”的标准称呼)。找到并照顾双胞胎的是否可能是一个当地的妓女,而非那里的一头野兽呢?
无论lupa指什么,一位善良的牧牛人或牧羊人很快发现了这两个男孩并收留了他们。他的妻子就是那个妓女吗?李维无法确定。罗慕路斯和雷慕斯作为那个乡下家庭的成员,不为人知地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两位青年有一天偶遇他们的外祖父——被黜的努米托耳国王。帮助后者重返阿尔巴隆迦王位后,他们开始准备建立自己的城市。但两人很快发生争执,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李维暗示,破坏了努米托耳和阿穆利乌斯关系的对立与野心现在被传给了罗慕路斯和雷慕斯这一代。
两兄弟在新城的选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在后来组成该城的几座山丘中(事实上不止那著名的7座)选择哪一个作为最早定居点的中心这个问题上。罗慕路斯选择了帕拉丁山(Palatine),那里后来矗立着皇帝的宏伟宫殿,英语中palace一词就来源于此。在随后的争执中,选择了阿文丁山(Aventine)的雷慕斯挑衅式地跳过罗慕路斯在中意地点周围修建的城界。关于随后发生的事有多种说法。但根据李维的记载,最常见的版本是罗慕路斯以杀死兄弟作为回应,从而成为以他名字命名的那个地方的唯一统治者。当他挥出杀害兄弟的那可怕一击时,他呼喊道(李维这么说):“其他任何跳过我的城界之人也会死去。”这对一座后来表现为好战之邦的城市是个合适的口号,但它的战争总是对他人入侵做出的回应,总是“正义的”。
劫掠
雷慕斯死了。他协助建立的城市里只有罗慕路斯的一小群朋友和同伴,需要更多的公民。于是,罗慕路斯宣布罗马是“避难所”,鼓励意大利其他地方的贱民和无依无靠者——逃亡奴隶、被宣判的罪犯、流亡者和难民——加入自己。此举带来了充足的男性人口。但李维接着说,为了获得女性人口,罗慕路斯采用了诡计和劫掠。他邀请来自罗马周围的拉丁姆地区的萨宾人和拉丁人全家前来参加宗教节日和娱乐活动。活动进行到一半,他指示手下绑架了来客中的年轻女性,把她们抢回家做妻子。
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以再现古罗马场景的画作闻名,他在17世纪时刻画了该场景:罗慕路斯站在高台上平静地注视着下方正在进行的暴力活动,背景中是一座还在建造的宏伟建筑。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应该会认得描绘早期该城的这一形象。虽然他们有时把罗慕路斯时期的罗马描绘成满是羊群、土屋和沼泽的样子,但也经常将其美化为尚在雏形之中的壮观古典城市。这幕场景在历史上还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媒介被重构。1954年的音乐剧《七兄弟的七个新娘》(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对它做了戏仿(剧中,妻子们是在建造美国式谷仓时被绑架的)。1962年,作为对古巴导弹危机所引发的恐惧做出的直接回应,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将普桑的画改编成一系列同主题的画作,更加突出了暴力的一面(见彩图3)。
罗马作家们一直在讨论故事里的这个情节。一位剧作家以此为题写了整整一部悲剧,遗憾的是除了一处引文其余部分都失传了。他们对该事件的细节感到困惑,比如他们想知道有多少年轻女性被劫。李维本人没有给出明确意见,但不同估计给出的数字从区区30人到683人不等——后者准确得令人生疑而且大得难以置信,据说这是非洲王子尤巴(Juba)的观点,此人被恺撒带到罗马,早年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从罗马史到拉丁语语法等各种学术课题。不过,他们最关心的是该事件中明显的犯罪行为和暴力。毕竟这是罗马历史上最早的婚姻,当罗马学者们想要解释传统婚礼上令人困惑的特征或表达时,他们首先会考虑到此事;比如,“啊,塔拉西乌斯”(O Talassio)这句欢呼据说来自一位参与此事的年轻罗马人的名字。①如果他们的婚姻制度源于劫掠,这产生了什么不可避免的影响?绑架和劫掠的分界线在哪里?更一般地,此事与罗马的好战有什么关系?


图8 这枚公元前89年的罗马银币描绘了两名最早的罗马公民抢走两名萨宾妇女。在画面下方,负责铸造钱币之人的名字基本能够辨识,为卢基乌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Lucius Titurius Sabinus),这很可能解释了他为何选择这个图案。钱币另一面是萨宾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的头像。
李维为早期罗马人做了辩护。他坚称他们只抓未婚女性,认为这是婚姻而非通奸的起源。通过强调罗马人不是“挑选”而是随机带走她们,他声称那是他们为了社群的未来采取的必要权宜之计,男人们随后会充满爱意地与新娘谈话,并做出感情承诺。他还把罗马人的行动说成是对邻邦不理智行为做出的回应。他解释说,罗马人最初正当地请求与周围民族订立条约,让他们有权迎娶对方的女儿。李维在这里指的显然是相互通婚的“通婚权”(conubium),不过他犯了严重的年代错误,这是很久之后罗马与其他国家结盟时的一项常规权利。只因这个请求被无理拒绝,罗马人才诉诸暴力。也就是说,这又是一场“正义之战”。
另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有的在该城的起源中看到了预示着后来罗马人好战的征兆。他们声称冲突完全是无来由的,而罗马人只抢走30名妇女(如果的确如此的话)的事实表明,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婚姻而是战争。撒鲁斯特暗示了这种观点。在他的《罗马史》(这是一部比《喀提林阴谋》内容范围更广的作品,只有零星引文保留在其他作家的作品里)中,他想象(只是想象)有一封据说是罗马的头号死敌所写的信。信中抱怨了罗马人在其整个历史中的劫掠行为:“从一开始,他们拥有的一切就都是偷来的: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帝国。”也许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神明。另一位罗马作家暗示,既然罗慕路斯之父是战神马尔斯,你还能指望什么?
诗人奥维德——他的罗马名字是普布利乌斯·奥维迪乌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的观点又不相同。奥维德大致是李维的同时代人,李维有多么因循守旧,此人就有多么离经叛道。他最终在公元8年遭到流放,获罪的部分原因是他言辞诙谐的诗作《爱的艺术》(主题是如何勾搭意中人)冒犯了当权者。在这首诗中,他颠覆了李维讲述的绑架故事,将此事描绘成一种原始模式的调情,使之变成情色韵事而非权宜之计。在奥维德笔下,罗马人一开始试图“盯上各人最中意的姑娘”,得到指令后则马上张开“充满情欲的双手”冲向姑娘。很快,他们在猎物的耳边低声说起了甜蜜的情话,姑娘们明显表现出来的恐惧反而增强了她们的性魅力。诗人坏坏地表示,从罗马最早的日子开始,节日庆典和娱乐场合就一直是找到姑娘的好地方。或者换句话说,看看罗慕路斯为犒赏忠诚士兵想了个多么巧妙的点子。奥维德开玩笑说:“如果你给我那种回报,我愿意参军。”
就像在故事的通常版本中所说的那样,姑娘的父母当然不会觉得绑架是好玩的事或属于调情。为了夺回女儿,他们与罗马人开战。罗马人轻松地打败了拉丁人,但与萨宾人的冲突陷入了持久战。西塞罗提醒他的听众回想起的正是这个时刻——罗慕路斯的部下在他们的新城中遭到猛烈攻击,他只好请求“坚守者”朱庇特阻止他们逃命。但西塞罗没有提醒他们,整个这场战争是由于罗马人抢了别人的女人而引发的。最终,多亏了女人们自己,敌对局面才得以结束,现在她们已经接受了做罗马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她们勇敢地走上战场,请求一边的丈夫和另一边的父亲停止战斗。她们解释说:“我们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失去你们任何一方,变成寡妇或孤儿。”
她们的干预奏效了。不仅和平降临了,而且罗马据说成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共同的城市,罗慕路斯和萨宾国王提图斯·塔提乌斯(Titus Tatius)一起统治着这个单一的社群。共治只持续了几年,然后塔提乌斯由于一定程度上由他本人引起的骚乱而死于邻城,②这种横死成了罗马权力政治的标志之一。罗慕路斯再次成为唯一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的第一代国王统治了30多年。
兄与弟,内与外
在这些故事表面之下不深的地方,隐藏着某些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以及某些处于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文化焦虑。关于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隐忧,或者至少是拥有时间、金钱和自由的罗马人的隐忧(文化焦虑经常是富人的特权),它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罗马婚姻的性质。鉴于其起源,它将注定有多么粗暴呢?另一个主题是内战,我们已经从试图让交战中的父亲和丈夫达成和解的萨宾妇女的话中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建城传说的重大疑团之一在于它声称有两名奠基者——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现代史学家给出了各种答案,试图解释明显多余的双胞胎设定。也许这指向了罗马文化中的某种基本的二元性,存在于不同的公民阶层或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或者这可能反映了后来罗马总是有两位执政官的事实。这也可能涉及更深层的神话结构,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是从德国到吠陀时代的印度等世界不同角落中发现的神圣双胞胎的某个版本,圣经故事中的该隐和亚伯也是其中一例。但无论我们选择何种答案(大部分现代猜想并不非常令人信服),一个甚至更大的疑团在于如下事实:双胞胎奠基者之一的确是多余的,因为在建城后的第一天,雷慕斯就被罗慕路斯所杀(在其他版本中则死于后者的亲随之手)。
对许多没有为了净化这个故事而给其贴上“神话”或“传说”标签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建城活动中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方面。它似乎让西塞罗非常不舒服,以至于他在《论共和国》中描述罗马的起源时并未提及此事:雷慕斯在开头与罗慕路斯一起出现,但随后就从故事中消失了。另一位作者——公元前1世纪的史学家哈利卡那苏斯的狄俄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此人是罗马居民,但通常用其位于现代土耳其沿海地区的家乡来称呼他——选择让笔下的罗慕路斯对雷慕斯之死感到痛不欲生(“他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还有一个我们只知道名叫埃格纳提乌斯(Egnatius)的人用更大胆的方式绕过了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埃格纳提乌斯的唯一记载是,他彻底推翻了谋杀故事,让雷慕斯得以寿终正寝,事实上比他的双胞胎兄弟活得还要久。
这种绝望尝试无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它想要摆脱故事中蕴含的冷酷信息:手足相残在罗马政治中根深蒂固,从公元前6世纪起(公元前44年恺撒的遇刺只是其中一例)反复折磨罗马历史的公民冲突一次次可怕地发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先注定的。有哪座建立在手足相残基础上的城市能摆脱公民的自相残杀呢?许多作家给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诗人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即贺拉斯)是其中之一。公元前30年左右,他在恺撒死后的十年纷争的余波中慨叹地写道:“不幸的命运追逐着罗马人,谋杀兄弟的罪行,自从雷慕斯无辜的鲜血流到地上,他的后裔就受到诅咒。”我们可以说,内战刻在罗马人的基因里。

图9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出现在罗马帝国最偏远的角落。这幅公元4世纪的镶嵌画发现于英格兰北部的奥尔德伯勒(Aldborough)。画面中的母狼显得欢快动人。双胞胎看上去危险地浮在半空中,他们似乎也是后来加上去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卡庇托山上那组塑像所做的。
罗慕路斯无疑可以被称颂为英雄式的建邦之父,而且经常的确如此。雷慕斯的命运引发的不安没有阻止西塞罗在与喀提林发生冲突时尝试接过罗慕路斯的衣钵。此外,尽管有了谋杀的阴影,但正在接受哺乳的那对双胞胎形象还是出现在古代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从首都——在罗马广场和卡庇托山上曾经分别立有他们的一组塑像——到帝国的偏远角落。事实上,当公元前2世纪时希腊希俄斯岛(Chios)的人们想要表现对罗马的效忠时,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竖立一座纪念碑,用他们的话来说,它描绘了“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和他兄弟的出生”。纪念碑没能留存下来,我们知道此事是因为希俄斯人将自己的决定记录在一块大理石板上,而后者留存了下来。不过,罗慕路斯这个人物无疑还是在道德和政治上让人不安。
在为新城寻找公民时,罗慕路斯把罗马变成庇护所,对所有投奔者都表示欢迎,无论是异邦人、罪犯还是逃亡者,这种想法引发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安。这种做法有积极的方面。特别是它反映了罗马政治文化在吸收外来者上不寻常的开放态度和心甘情愿,这与我们所知的其他任何古代西方社会都不相同。没有哪个古希腊城邦的包容程度与之相近,雅典对获得公民权的限制尤其严格。这并非因为罗马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开明”脾性。他们征服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片土地,有时展现出可怕的残暴;他们还敌视和蔑视他们所谓的“蛮族”。不过,经过一个在任何前工业时代帝国都不曾经历的过程,那些被征服地区(罗马人称之为“行省”)的居民逐渐获得了完整的罗马公民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权利和保护。该过程在公元212年(本书的结尾)达到顶峰,卡拉卡拉皇帝在那一年让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
甚至在那之前,外省精英就已经大批进入了首都的政治统治集团。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罗马元老院逐渐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机构,在罗马皇帝的完整名单中,有许多人不是意大利人:卡拉卡拉的父亲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是第一位来自罗马非洲领土的皇帝;半个世纪前的皇帝图拉真(Trajan)和哈德良(Hadrian)来自罗马的西班牙行省。公元48年,当克劳迪乌斯皇帝——此人的慈爱长辈形象更多来自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小说《我,克劳迪乌斯》(I, Claudius),而非来自其真实生活——就是否应该允许高卢公民成为元老的问题与不甚情愿的元老院展开争论时,他花了一些时间提醒与会者,罗马从一开始就对外邦人开放。他的讲话文本连同一些显然就连皇帝也不得不忍受的诘问被刻在青铜板上,放在行省某地(今天的里昂城)展示,并留存至今。看上去克劳迪乌斯没能像西塞罗那样有机会在发表前进行修改。
奴隶制也经历了类似过程。罗马的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与罗马的军事征服方法一样残暴。但对许多罗马奴隶——特别是那些在城市家庭中工作而非在地里和矿井中干苦活的——来说,它不一定是一种无期徒刑。他们经常被释,或者用自己攒下的钱赎身,获得自由;如果主人是罗马公民,那么他们也能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与生来自由者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在这点上,与古典时代的雅典的对比同样令人震惊:在雅典,很少有奴隶被释放,即使被释也肯定无法就此获得雅典公民权,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国籍的边缘状态。这种释奴做法(拉丁语术语为manumission)是罗马文化的鲜明特征,当时的外邦人对此做出了评价,将之视为罗马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像公元前3世纪一位马其顿国王所注意到的,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壮大了自己的国家”。释奴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公元2世纪时,罗马城中大部分自由公民都有祖先是奴隶。
罗慕路斯将罗马变成庇护所的故事清楚地指向这种开放性,这暗示了罗马的多样化构成是可以追溯到其起源的一个特点。某些罗马人赞同马其顿国王的看法,认为罗慕路斯的包容政策是该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为庇护所感到骄傲。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强调了这个故事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一面。觉得一个帝国将意大利的罪犯和贱民认作祖宗显得反讽的,不只是某些罗马的敌人,一些罗马人也这样认为。公元前1世纪末或2世纪初,喜欢嘲讽罗马人自命不凡的讽刺诗人尤维纳尔——德基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严厉批评了作为罗马生活一个方面的势利,并讥讽了那些自诩族谱可以上溯数个世纪的贵族。他在一首诗的结尾借机抨击了罗马的起源。所有这些自负有何根据?罗马从一开始就是奴隶和逃亡者组成的城市(“无论你的始祖是谁,他或者是牧羊人,或者是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起的人”)。当西塞罗在写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中拿罗慕路斯的“垃圾”和“渣滓”开玩笑时,他可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取笑一位同时代人,表示当此人在元老院发言时表现得仿佛自己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事实上他却生活在罗慕路斯的贱民(faex)中”。
简而言之,罗马人总是可以认为自己在追随罗慕路斯的足迹,无论结局是好是坏。当西塞罗在反喀提林演说中提到罗慕路斯时,他不仅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提及罗马的奠基之父(虽然这肯定是部分原因),也因为这个故事能在同时代人中就如下问题引起各种讨论和争辩:罗马人究竟是什么人、罗马代表什么和它的分歧产生于何处。
历史与神话
罗慕路斯的足迹被印刻在罗马的各处景观中。在西塞罗的时代,你不仅可以造访罗慕路斯修建的“坚守者”朱庇特神庙,而且能走进据说那头母狼哺育双胞胎婴儿的山洞,还能看到这两个孩子被冲上岸的地方生长的那棵树(已经被移栽到罗马广场上)。你甚至还能观赏罗慕路斯本人的居所,据说这位建城者曾住过帕拉丁山上的那座用木头和茅草搭建的小屋:在成为不断扩张的大都市后的罗马城,从这里可以一窥其原始样貌。正如公元前1世纪末一位游客所委婉暗示的,小屋当然是伪造的,他解释说:“为了让它更受崇敬,他们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但如果任何一个部分因为坏天气或年代久远而有所损坏,他们会把它修好,尽可能使其恢复原先的样子。”人们没有找到那座小屋的确切考古痕迹,鉴于其简陋的构造,这毫不奇怪。但作为对该城起源的纪念,它以某种形式至少一直留存到公元4世纪,当时的一份罗马著名地标名单提到了它。
上述实物“遗迹”——神庙、无花果树和精心修补过的小屋——是罗慕路斯作为历史人物的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罗马作家不是易骗的傻瓜,他们在重新讲述传统故事的同时也对许多细节提出了质疑(母狼的角色和神明祖先之类)。但他们并不怀疑罗慕路斯曾经存在过、做出过决定了罗马未来发展的关键选择(比如城市的选址),并基本凭借一己之力发明了某些最典型的制度。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元老院本身就是罗慕路斯创建的。“凯旋式”(triumph)同样如此,那是罗马人在取得最大(也是最血腥)的战争胜利后经常举办的胜利游行。公元前1世纪末,当所有举行过凯旋式的罗马将军的名字被镌刻在罗马广场的一排大理石板上加以纪念时,罗慕路斯的名字排在首位。第一条记录写着“罗慕路斯,国王,马尔斯之子,建城1年3月1日战胜卡伊尼纳(Caenina)人”,用来纪念他迅速打败了附近一座年轻妇女遭遇强夺的拉丁人城市,丝毫也不容许公众对其神子身份抱有任何怀疑。
罗马学者竭力试图界定罗慕路斯的功绩,并确定罗马最古老时代的准确编年。在西塞罗时代,最激烈的争议之一是罗马城究竟何时建立的问题。罗马到底有多古老?博学者巧妙地从他们知道的罗马年代回推到他们未知的更早年代,并试图将罗马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编年对应起来。特别是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历史同奥林匹亚运动会规律的四年周期相匹配,后者显然提供了固定和真实的时间框架,虽然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后者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早先的巧妙猜测的结果。这是一场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争论。但不同的观点逐渐在我们所说的公元前8世纪中叶左右这个时间点上达成一致,学者们得出了希腊和罗马历史大致同时“开始”的结论。这个成为标准并在许多现代教材中仍被引用的年代部分可以上溯到一部名为《编年史》的学术著作,其作者正是西塞罗的友人和通信者阿提库斯。这部作品没能流传下来,但人们认为它将罗慕路斯建城的时间确定为第六个奥林匹亚运动会周期的第三年,即公元前753年。另一些人的计算将时间进一步确定为4月21日,现代罗马人在这一天仍会庆祝自己城市的生日,举办一些非常俗气的游行并模仿角斗士表演。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常常很模糊(比如亚瑟王或宝嘉康蒂③),我们将会看到,罗马是这种界限特别模糊的文明之一。不过,尽管罗马人在这个故事上展现了出色的历史洞察力,我们还是有各种理由把它或多或少地视作纯粹的神话。首先,几乎肯定不存在所谓的罗马城奠基时刻。很少有城镇是一下子由一个人单独建立的。它们通常是定居点、社会组织和身份感模式以及人口逐渐变化的产物。大部分“奠基”是回溯性建构,把晚期城市的微缩版本或想象中的原始版本投射到遥远的过去。“罗慕路斯”之名本身就泄露了玄机。虽然罗马人通常认为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新建立的城市,但我们现在可以相当自信地认为事实恰好相反:“罗慕路斯”是对“罗马”所做的想象性建构。“罗慕路斯”只是典型的“罗马先生”。
此外,对于罗马历史的最早阶段,那些把自己关于罗马起源的记述版本留给我们的公元前1世纪的作家和学者并不比现代作家拥有多得多的直接证据,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更少。没有属于那个阶段的记录或档案留存。少数几件早期石刻铭文虽然很珍贵,但并不像罗马学者常常想象地那么古老,而且就像我们在本章末将会发现的,他们有时完全误读了早期的拉丁文。诚然,他们能接触到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更早期的历史记述。但其中最早的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个日期与该城起源仍有很长的时间间隔,这条鸿沟只能借助形形色色的故事、歌曲、大众戏剧表演以及多变和有时自相矛盾的口头传统大杂烩(根据环境和听众的变化,在一遍遍讲述中不断改变调整)来弥补。有关罗慕路斯故事的零星证据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世纪,但线索就此中断,除非我们重新把青铜母狼像考虑进来。

图10 在埃特鲁里亚人的土地上发现的这面雕花镜(镜面位于另一侧)似乎描绘了罗慕路斯和雷慕斯被母狼哺乳的某个版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面被认定为公元前4世纪的镜子将是该故事的最早证据之一。但一些可能过于多疑的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里描绘的是埃特鲁里亚神话中的场景,或者是一对远为神秘和鲜为人知的罗马神明:“守护者”拉尔兄弟(Lares Praestites)。
当然,反过来说,正因为罗慕路斯的故事是神话而非狭义上的历史,它才能切中肯綮地反映了古罗马的一些核心文化问题,对了解更广义的罗马历史显得如此重要。罗马人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仅仅继承了奠基者优先考虑和关心的东西,恰恰相反,通过多个世纪以来重述和改写那个故事,他们自己建构和重构了奠基者罗慕路斯的形象,将其作为他们的偏好、争执、理念和焦虑的有力象征。换句话说,内战并非像贺拉斯表示的那样,是罗马与生俱来的诅咒和命运;相反,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即便故事已经拥有了相对固定的书面形式,修正或改编叙事的可能性也总是存在。比如,我们已经看到西塞罗如何掩饰雷慕斯的被害,而埃格纳提乌斯更是对其全盘否定。但李维对罗慕路斯之死的描述生动地展示了如何让罗马起源的故事直接与时事相呼应。他表示,统治了30年后,国王突然在一场暴风雨中被乌云覆盖并消失了。悲痛的罗马人很快认定,他被从他们身边夺走,成了神明——在罗马的多神教体系中,有时允许发生这种跨越人与神的界限的事(尽管这在我们看来稍嫌愚蠢)。但李维承认,当时的某些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国王遭遇刺杀,被元老砍死。李维笔下的这两种情节都并非完全出于他的臆造,比如西塞罗就曾在他之前提到过罗慕路斯成神(虽然抱有一定的怀疑),而在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一位野心过大的政客曾受到将会遭遇“罗慕路斯的命运”的威胁,这很可能并非指的是成神。李维写下这些话时距离恺撒遇害仅仅过去了几十年(后者同样被元老砍死,然后获得了神明的地位,最终在罗马广场拥有了自己的神庙),他的记述显得尤其意味深长和别有所指。在这里,忽视恺撒的影响将会不得要领。
埃涅阿斯和其他
罗慕路斯与雷慕斯的故事时而引人入胜,时而让人困惑,时而又深刻揭示了罗马人的重大隐忧,至少是精英阶层的隐忧。此外,从钱币图案或者大众艺术主题来看,这些故事广为人知,虽然饥饿的农民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虑劫掠萨宾妇女背后的微妙之处。但让罗马起源传说的复杂图景更加扑朔迷离的是,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故事并非该城唯一的奠基故事。同时还存在其他几个版本。它们之中有的是与标准主题区别不大的变体,有的在我们看来则完全自成一体。比如,某个希腊故事引入了著名的奥德修斯和荷马《奥德赛》中的情节,暗示罗马的真正奠基者是一个名叫罗慕斯(Romus)的人,此人是奥德修斯与女巫喀耳刻艳遇的产物,而人们有时设想那位女巫的魔岛就在意大利沿海附近。这则小故事虽不可信,但很巧妙地表达了文化帝国主义,给罗马安了一个希腊出身。
另一个同样牢牢扎根于罗马历史和文学中的传说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故事,他在神话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荷马《伊利亚特》的背景)结束后从特洛伊城出逃。在牵着儿子的手和背着老父亲离开燃烧的废墟后,他最终前往意大利,命运注定他将在意大利土地上重建自己出生的那座城。他带来了家乡的传统和一些城毁时抢救出来的珍贵护身符。

图11 这幅来自英格兰南部下哈姆(Low Ham)罗马别墅中浴室地面上的4世纪镶嵌画描绘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一系列场景:埃涅阿斯抵达迦太基,狄多与埃涅阿斯外出打猎,画面尽可能简洁地刻画了迦太基女王与特洛伊英雄的激情。
和罗慕路斯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中也有同样多的疑团、问题和含糊不清之处,关于它何时、何地和为何产生的问题也悬而未决。维吉尔于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创作的关于这个主题的12卷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但也使其内容变得极为丰富。这部史诗是最受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之一,成了埃涅阿斯故事的标准版本。它为西方世界留下了一些最富感染力的文学和艺术亮点,包括埃涅阿斯与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悲剧爱情故事——埃涅阿斯在从特洛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沿海地区)前往意大利的漫长旅途中被冲上了迦太基海岸。埃涅阿斯决定追随自己的命运,当他抛弃狄多前往意大利后,女王爬上柴堆自焚身亡。在17世纪亨利·普塞尔(Henry Purcell)的同主题歌剧版本中,她的咏叹调“记住我,记住我”令人难忘。问题在于,我们经常很难分辨故事中的哪些元素来自维吉尔(几乎肯定包括埃涅阿斯与狄多相会的大部分情节),哪些属于更传统的故事。
埃涅阿斯的罗马奠基者形象显然在远早于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就出现在罗马文学里了,并在景观中留下了印记。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作家们简单提到过他的这个角色;公元前2世纪,请求与罗马人结盟的希腊得洛斯(Delos)岛使者似乎特意提醒罗马人,埃涅阿斯在西行之旅中曾在得洛斯岛停留,这是他们给出的结盟理由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哈利卡那苏斯的狄俄尼修斯相信自己在离罗马不远的拉维尼乌姆城(Lavinium)见过埃涅阿斯的墓,或者那至少也是一处纪念他的古老场所。他表示那里“很值得一看”。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罗马广场上的维斯塔女神庙(庙中的圣火由罗慕路斯传说中的瑞娅·西尔维娅那样的贞女祭司侍奉着,人们要求圣火永远不能熄灭)保管的珍贵器物中有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那尊女神雅典娜像。至少某个罗马故事是这样说的。关于谁抢救了这尊著名的塑像众说纷纭,整个希腊世界的许多城市都宣称自己拥有真品。
显而易见,埃涅阿斯的故事和罗慕路斯的故事一样是神话。但罗马学者对这两个奠基传说的关系感到困惑,花了很多精力试图理顺它们的历史脉络。罗慕路斯是埃涅阿斯的儿子或孙子吗?如果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埃涅阿斯怎么可能做了同样的事呢?最大的困难在于,罗马人将自己城市的起源定在公元前8世纪,而他们公认特洛伊城陷落(同样被认为是历史事件)的时间为公元前12世纪,两个日期的差别非常扎眼。公元前1世纪,通过构建把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联系起来的复杂的家谱树、敲定“正确的”日期,不同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融贯起来:埃涅阿斯开始被视作拉维尼乌姆而非罗马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建立了阿尔巴隆迦,后来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就是在这座城市中被遗弃,再之后他们才建立罗马城;朦胧不清且即使按照罗马的标准也纯属公然虚构的阿尔巴王朝,成了连接阿斯卡尼乌斯和公元前753年这个神奇年份的桥梁。这是李维认同的版本。
埃涅阿斯故事的核心主张呼应了罗慕路斯故事中的庇护所这个根本主题,或者说实际上是放大了该主题。罗慕路斯欢迎所有来到他新城的人,而埃涅阿斯的故事更进一步,宣称“罗马人”实际上最初是“外邦人”。这对民族身份来说是一个悖论,与许多诸如雅典这样的古希腊城市的奠基神话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认为他们最初的全部居民是奇迹般地从本土的地里冒出来的。④罗马起源的其他故事版本也一再强调了这种外来性。事实上,在《埃涅阿斯纪》的一个情节中,主人公造访了未来罗马城的所在地,发现罗马人的原始祖先已经在那里定居。他们是谁?这是一群埃万德国王(King Evander)统治下的定居者,国王是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流亡来到此地的。该情节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无论上溯到什么时候,罗马的居民总是来自他处。
在狄俄尼修斯记录的一条奇怪词源中,上述信息得到了尤为清晰的概述。希腊和罗马的学者对词语的由来着迷,认为这不仅能展示词语的来历,而且能揭示它们的意义。他们的分析有时正确,有时则错得离谱。但就像在狄俄尼修斯这个例子中一样,他们的错误也常常发人深省。狄俄尼修斯在所著史书的开头考虑了一群罗马城址上甚至更早的原始居民:阿伯里金人(Aborigines)。这个词的由来本该一目了然:这些人是“自始”(ab origine)生活在那里的人。公平地说,狄俄尼修斯的确提到了这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就像其他人那样,他同等重视甚至更偏向另一种很不可信的解释,即这个词并非源于origo,而是来自拉丁语的errare(流浪),最初被拼作Aberrigines。他写道,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认为严肃的古代学者对摆在面前且明显正确的词源视而不见,却赞成了一个通过Aborigines 的有倾向性的拼写而推导出该词源自“流浪”的愚蠢想法,这并不表示我们觉得他们愚钝。这仅仅表明,关于“罗马”一直是个多变的民族概念和“罗马人”不断迁徙的想法是多么深入人心。
挖掘早期罗马
从罗慕路斯和其他奠基者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到很多有关罗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价值观和缺陷的信息。它们还展示了罗马学者如何对过去展开争论、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它们宣称将要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最早的罗马是什么样的,它经过了什么过程、在何时成为城市社区——却什么也没说,或者最多也只是言之甚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西塞罗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63年,罗马已经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了。但如果没有建城时期的作品留存下来,而我们又无法依靠传说,那么我们将如何获得关于罗马起源的信息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了解台伯河畔那个后来成长为世界帝国的小城的早期历史呢?
无论多么努力进行尝试,我们都不可能构建一个融贯的叙事来取代罗慕路斯或埃涅阿斯的传说。确定罗马历史最早阶段的确切年代同样非常困难,尽管有许多人自信地断言这很容易。但我们可以开始对该城发展的总体背景增加了解,并获得一些关于那个世界的出奇生动的印象,有的甚至令人难以捉摸,充满诱惑。
方法之一是离开建城故事,转而寻找隐藏在拉丁语或后来的罗马制度中可能指向最早期罗马的线索。这里的关键是经常被简单而错误地称为罗马文化中的“保守主义”的东西。罗马并不比19世纪的英国更保守。在这两个地方,在与各种表面上保守的传统和修辞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激进的创新茁壮地成长了起来。但罗马文化的特点是永远不愿完全抛弃自己过去的习惯,而是倾向于保留各种宗教仪式、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化石”,即便它们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一位现代作家说得好,罗马人很像那些获得了全套新厨房设备但不愿扔掉陈旧小厨具的人,而是继续让它们占地方,即便再也不用。古今学者经常猜测,其中某些化石或陈旧小厨具可能是罗马最古老状况的重要证据。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每年12月在城中举行的“七丘节”(Septimontium)仪式。我们完全不清楚在这个庆祝活动上会发生什么,但一位博学的罗马人指出,“七丘”是该城在成为“罗马”之前的名字;另一位学者列出了该节日中涉及的山丘(montes)的名字:帕拉提乌姆山(Palatium)、维利亚山(Velia)、法古塔尔山(Fagutal)、苏布拉山(Subura)、科尔马鲁斯山(Cermalus)、奥庇乌斯山(Oppius)、卡伊利乌斯山(Caelius)和基斯皮乌斯山(Cispius)(见地图2)。名单中共有8个山名,这意味着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名单中的古怪之处(帕拉提乌姆山和科尔马鲁斯山都是被通称为帕拉丁山的一部分)连同“七丘”是“罗马”旧称的想法,暗示这些名字可能反映了各处村镇在发展成熟的罗马城出现之前所处的位置。名单中缺少奎里纳尔山(Quirinal)和维米纳尔山(Viminal)这两座醒目的山丘,这促使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罗马作家们经常把这两座山称为colles,而非更常用的拉丁语词汇montes(两者的意思大致相同)。这种差异是否表示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的某个时候曾经存在过两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呢?进一步说,我们是否可能遇到了罗慕路斯故事中所反映的那两个群体——与colles联系在一起的萨宾人和与montes联系在一起的罗马人——的某个版本呢?
这是有可能的。几乎可以肯定,“七丘节”与罗马的遥远过去存在某种关系。但具体是什么关系、到底有多遥远,却很难知道。该观点并不比我提出的观点看起来更有根据,甚至很可能更不可靠。毕竟,为何我们要相信那位博学的罗马人关于“七丘”是罗马旧称的说法?这看上去只是孤注一掷做出的猜测,用来解释一种让他和我们几乎同样感到困惑的古老仪式。而坚称存在两个社群的做法看起来可疑,背后似乎受到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罗慕路斯传说的“历史”色彩的欲望的驱使。
考古学证据要实在得多。向罗马城地下深处挖掘,在可见的古代历史遗迹之下仍然存在着早得多的某个或某些原始定居点的遗迹。罗马广场下方有一处早期墓地的遗址,当该墓地遗址于20世纪初被首次发掘时曾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兴奋。一些死者是火葬的,他们的骨灰被盛在简陋的骨灰坛内,旁边是原先装有食物和饮料的瓶瓶罐罐(有一个人得到了少量鱼、羊肉和猪肉——可能还有些粥)。另一些死者是土葬的,有时被装在将橡木切开并挖空制成的简陋棺材里。一个大约两岁的女孩下葬时穿着珠饰衣服、戴着象牙手镯。古城的其他各处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比如,在帕拉丁山上一座大房子下方很深处埋着一个年轻男子的骨灰,陪葬品为一支袖珍长矛,这可能是他如何度过一生的象征。
在考古记录中,死者和被埋葬者经常比生者更显眼。但墓地暗示着一个社群的存在,而在罗马各处(包括帕拉丁山)地下发现的茅屋群的依稀轮廓也被认为是社群的痕迹。除了它们是用木头、黏土和茅草建造的,我们对它们的特点所知甚少,更不清楚它们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不过,如果把目光投向罗马城外不远处,我们可以填补一些空白。20世纪80年代在距离罗马以北几英里处的费德奈(Fidenae)发现的遗址是保存最完好和发掘最细致的此类早期建筑之一。这是一座长6米、宽5米的长方形建筑,用木头(橡木和榆木)与夯实的土建造——所谓的夯土结构,至今仍在使用——周围有悬挑屋顶形成的一个粗糙而简易的柱廊。屋内有中央火炉、一些硕大的储物陶罐(还有一只较小的,似乎用于盛放制作陶器的黏土),以及某些完全不出所料的食物(谷物和豆子)与家畜(绵羊、山羊、牛和猪)。废墟中最意外的发现是一只猫的骸骨,它死于一场最终摧毁了这座建筑的大火,可能是因为被绳子拴住了。现在,它作为意大利已知最早的家猫而闻名。

图12 来自早期罗马墓地和周围地区的典型骨灰坛。关于生者居所的外观,这些形状为一座简陋小屋的死者之屋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最佳指导。
这里有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动剪影,从那个身着她最好的衣服躺在墓中的小女孩,到那只着火时没人为其解开绳子的可怜“捕鼠者”。问题在于这些剪影合起来意味着什么。考古遗迹无疑证明了在我们看到的古罗马背后存在着漫长和丰富的史前史,但具体有多长是另一回事。
部分问题在于城中的发掘条件。罗马城在经历过多个世纪的建设后,我们只有在碰巧没有被碰过的地方才能找到此类早期居住生活的痕迹。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罗马人为罗马广场的巍峨大理石神庙挖掘地基时毁坏了地表下的许多东西;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修建豪华住宅的地窖时挖穿了该城其他地区甚至更多的地下遗迹。因此,我们只有小小的剪影,从未获得大幅画面。这是最艰难的考古工作,而且尽管不断有新的证据碎片出现,对它们的解读和重新解读几乎总是受到质疑,而且常常充满争议。比如,人们对20世纪中叶在罗马广场发掘出的荆笆墙碎片仍然争论不休,不清楚它们表明那里曾经也有一座早期的小屋,还是它们是几个世纪后为了垫高这里的地面而无意中混入的瓦砾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这里作为墓地还不错,但对村子来说这个地方非常潮湿和泥泞。
准确定年甚至更有争议;因此我在上面几页中有意模糊地使用“早期”一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来自最早期罗马或周边地区的任何考古材料都没有独立的确凿年代,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仍然充满争议。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通过轮制陶器(被认为晚于手制陶器)、墓中偶尔出现的希腊陶器(人们对它们的年代了解较多,虽然仍不够好)等判断标志和对不同遗址进行详细比较——制作了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前600年的大致年表。
以此为基础,罗马广场最古老的墓葬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帕拉丁山上的小屋属于公元前750—前700年(就像许多人注意到的,这个时间段令人兴奋地非常接近公元前753年)。但即使这些年代也远远谈不上确定。新近的科学方法——包括通过测量有机材料中残留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来计算其年代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表明上述结果都太“年轻了”,最多的晚了100年。比如,根据传统的考古标准,费德奈的小屋年代被认定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但放射性碳定年法将其上推至公元前9世纪末。目前,年代的变动甚至比以往更频繁;总而言之,罗马似乎在变老。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6世纪时的罗马已经是一个城市社区了,拥有城市中心和一些公共建筑。对于更早的最早期阶段,我们从所谓的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1700年和前1300年之间)获得的足够多的零星发现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而非仅仅“路过”。对于两者之间的时期,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认定已经发展出较大的村子,很可能(从墓中的物品来看)同时出现了日益富裕的精英家族群体;在某个时候,这些村子合并成单一的社群,其城市特征在公元前6世纪时已经清晰可见。我们无法确知各个定居点的居民何时开始认为自己属于同一座城市的。我们也完全无从知晓他们何时开始把这座城市视作罗马,并如此称呼它。
不过,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年代和起源的。城中和周围地区乃至更远处挖出的材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罗马早期定居点的特征。首先,它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接触。我已经简略提到了墓地中那个小姑娘的象牙手镯和从罗马发掘出的希腊陶器(科林斯或雅典制造的)。用进口琥珀制作的几件首饰和装饰品则是罗马与北方有联系的标志;我们没有能揭示它们如何来到意大利中部的线索,但它们无疑指向罗马与波罗的海地区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就我们所能追溯的几乎最早的情况来看,罗马与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一如西塞罗在强调其战略位置时所暗示的。
其次,罗马和邻邦间存在相似点和某些重要差异。公元前1000年到前600年左右的意大利半岛组成极其复杂。那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独立民族,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起源和语言。记录最翔实的是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比如自公元前8世纪起由来自一些希腊大城市的移民建立的库迈(Cumae)、塔兰托(Tarentum)和那不勒斯(Naples)⑤——它们通常被称为coloniae,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colonies)。从各方面来看,半岛南部的许多地区和西西里都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通过文字和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留存至今的一些很古老的(也许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字作品样本是在那里发现的,这绝非巧合。想要重建半岛上其他居民——从北方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到罗马以南不远处的拉丁人和萨宾人,再到庞贝的原住民奥斯坎人(Oscans)和附近的萨莫奈人(Samnites)——的历史就困难得多了。他们如果有书面作品,也都没能留存,我们关于存在这些民族的证据完全依赖考古学与刻在石头和青铜上的文本(有时可以理解,有时不能),以及很久以后罗马人的记述,其中经常带有罗马优越论的色彩;因此,萨莫奈人的标准形象是粗俗、野蛮、非城市化以及危险而原始的。
不过,考古学发现的确显示,早期的罗马的确非常普通。我们在罗马大致看到了从分散定居点向城市社区的发展,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的过程似乎也出现在罗马以南的全部邻近地区。墓地中的实物遗存、当地的陶器和青铜胸针,还有更具异域风情的进口物品在那里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在罗马发现的物品不如其他地方发现的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和能够暗示财富。比如,罗马城的发现中就没有什么能与附近的普莱内斯特(Praeneste)的一些非凡墓葬中的发现媲美。虽然这可能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像一些考古学家怀疑的那样,19世纪时从罗马发掘出的一部分最好的东西被盗走并直接流入了古物市场。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罗马于何时变得不再普通?
缺失的一环
不过,本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考古材料是否必然与我所描绘的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神话传统完全无关。是否可能把我们对罗马最早期历史的探究同罗马人自己讲述的故事,或者说与他们对城市起源的精心猜测联系起来呢?我们有可能在神话中再找到些许历史吗?
这种诱惑影响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早期罗马所做的许多现代研究。我们已经看到有人试图让“七丘节”的故事反映罗慕路斯神话所强调的罗马城的二元性质(罗马人和萨宾人)。近来在帕拉丁山脚下发现的一些早期土墙引发了各种疯狂猜想,认为它们就属于在罗马建城那天雷慕斯跳过并引来杀身之祸的那堵墙。这是考古学上的幻想。诚然,一些早期土墙被人们发现了,而且它们本身很重要,虽然并不清楚它们与帕拉丁山顶的早期茅屋定居点有何关系。但它们与并不存在的罗慕路斯与雷慕斯这两个人物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关系。试图把土墙和相关发现的年代测定“包装”成公元前753年4月21日(我这里只是稍做了些夸张)是“片面辩护”。
在整个罗马城中,只有一个地方的早期材料可能与文学传统存在直接联系。但经过比较,我们没能找到两者的一致与和谐,只看到了巨大而有趣的鸿沟。这个地方位于罗马广场的一头,靠近卡庇托山的山坡,距离西塞罗在“坚守者”朱庇特神庙中攻击喀提林的地点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就在演说家们向人民发言的主讲坛(rostra)旁。公元前1世纪末之前,人们在那里的广场路面上铺设了一排独特的黑石板,形成长宽分别约为4米和3.5米的长方形区域,周围砌有低矮的石围栏。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贾科莫·伯尼(Giacomo Boni)——此人当时与特洛伊的发现者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iemann)齐名,但并无欺诈的不良名声——在黑石下展开发掘,找到了一些古老得多的建筑遗迹。其中包括一座祭坛、一根巨大的独立柱子的残余部分和一根短石柱,后者表面布满了大多无法辨识的早期拉丁文,很可能是我们拥有的这种语言的最早文本之一。这个地方是被有意掩埋的,填充物中包括各种寻常和不寻常的发现,从袖珍杯子、珠子和羊跖骨到一些公元前6世纪的精美雅典彩绘陶器。从上述发现(其中似乎包括宗教供奉)来看,最明显的解释是这里是早期圣所,可能属于火神伏尔甘。当广场在公元前1世纪前的某个时候被重新铺设时,这里被掩埋了,但为了纪念下方的圣所,上面铺了独特的黑石。
后来的罗马作家们很熟悉这片黑石板,关于它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其中一人写道:“黑石表示不祥的地点。”他们知道石板下方埋着某些可以上溯多个世纪的东西,但并非考古学家们现在相当确信的宗教圣所,而是与罗慕路斯或者他的家庭相关的古迹。有几个人认为这是罗慕路斯之墓;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养父法乌斯图鲁斯(Faustulus)之墓,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罗慕路斯成了神,他不应该真有墓穴;还有些人认为这是罗慕路斯的同伴霍斯提里乌斯(Hostilius)的墓,此人的一个孙辈后来成了罗马国王。

图13 贾科莫·伯尼在罗马广场的黑石下发掘出的早期圣所遗迹的示意图。左侧是一座祭坛(直角U形结构,在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右侧矗立着一根巨柱的残余部分,其背后依稀可见刻有铭文的柱子。
他们还知道下面埋藏着铭文,无论是因为在其被掩埋前曾亲眼看到过抑或道听途说。狄俄尼修斯记录下了铭文内容的两个版本:一种是霍斯提里乌斯的墓志铭,“记录了他的英勇”,另一种是罗慕路斯在取得一次胜利后“记录他的战功”的铭文。但两者无疑都不正确。铭文也不像狄俄尼修斯所宣称的那样“用希腊文字写成”,而是如假包换的早期拉丁文。不过,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罗马史学家对被掩埋的过去知道得既很多又很少,以及他们多么喜欢想象在他们城市的表面或地下不深处仍然存留着罗慕路斯的痕迹。
铭文的真正内容——至少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将把我们带到罗马史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将看到一系列据说是在罗慕路斯之后几乎同样带有神话色彩的国王。
①可能是萨宾婚神的称号。瓦罗认为Talassius来自希腊语τάλαρος,指一种装羊毛的篮子,因为纺毛线是罗马女主人最典型的家务活。
②在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共治的第六年,塔提乌斯的一些朋友抢劫了拉维尼乌姆(Lavinium)人的财物,该城派使者到罗马抗议,但塔提乌斯拒绝交出肇事者。使者返回途中遭到萨宾人突袭,罗慕路斯将袭击者交给拉维尼乌姆人带回受审,塔提乌斯出于同情救下了他们。不久,塔提乌斯前往拉维尼乌姆献祭,在祭坛前被遇害使者的家属谋杀。(哈利卡那苏斯的狄俄尼修斯,《罗马古事记》,1.51-52)
③阿尔贡金印第安联盟的酋长波瓦坦之女,嫁给了在弗吉尼亚种植烟草的英国殖民者约翰·罗尔夫。她的故事成为许多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的主题。
④古希腊许多地方都有地生人(autochthones)的神话,将本地最早的居民描绘成从土壤、岩石或树木中诞生,如卡德摩斯播种龙牙得到武士,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了忒拜城。神话中的第二代雅典国王厄里克托尼俄斯同样从地中诞生。《伊利亚特》547-549表示:这位国王在丰产的土地生他的时候,由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养育,使他住在雅典。
⑤拉丁语拼作Neapolis,意为“新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