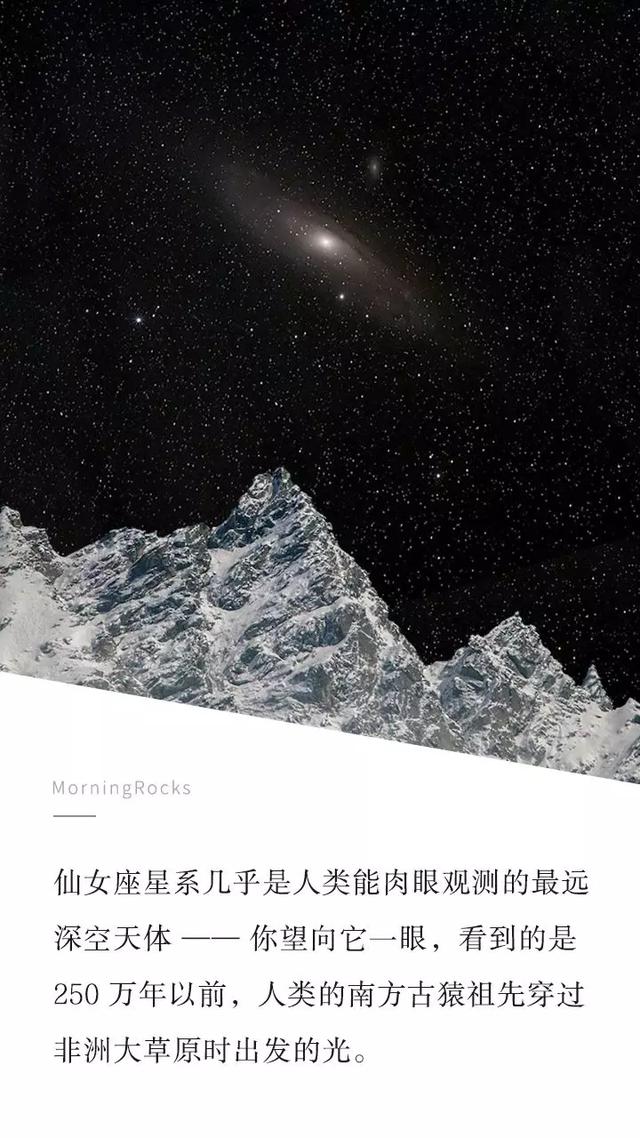民法总则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民法典公序良俗规定的宪法向度)

《民法典》关于公序良俗的规范构造,提升了概念的明确性程度,对于缓解概念泛化及其司法适用困境具有积极意义。不过,在高度多元和急剧转型的现代社会语境下,《民法典》注定无法给予公序良俗以自足性的整全理解。寄希望于《民法典》完全将公序良俗确定化,从而彻底消除泛化困境,是对《民法典》不切实际的奢望。对公序良俗的“精准赋值”,就必须从民法规范体系之外去寻求,而寻求的对象只能是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全部生活领域提供整体性与根本性规则的宪法。
公序良俗是宪法和民法的重要联结点。诉诸宪法,可将民法从对公序良俗进行主观界定的价值困扰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公序良俗以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和共识性的理解。遵循宪法和民法的诸种联结路径,基于宪法对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解释,方可有效激活其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制度功能,在相互尊重和保持自身法体系边界的基础上,实现民法体系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秩序衔接及协调。
一、准确定位关系。在体系结构上,民法基本原则可分为两类:一是“私的自治”的手段,包括平等原则与自愿原则;另一是“公的管制”的媒介,包括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及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在体系逻辑上,公序良俗是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行为人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中获益。从体系的层次性及其适用顺序而言,私法自治是民法核心原则,显著优位于公序良俗等公共性原则。唯有当私法自治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目标发生严重抵牾时,才可在具体个案情境中进行原则衡量,以确定究竟哪一原则具有更大的权重;而偏向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时,其理由应强于支持私法自治的理由。
二、确定适用情形。理由的强度较量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原则,在个案中仍难免陷入偏颇。在这一点上,《民法典》对公序良俗的规则具化,实则构造了公序良俗的两种适用情形及相应的控制模式:一是直接适用,一是经论证有必要方可适用。根据社会生活经验,《民法典》已将与公序良俗关联密切的社会领域明示出来,明文要求在这些领域要重点考察私法行为是否符合公序良俗。在这些领域,根据规则要求,必须明确地进行私法自治和公序良俗的情境权衡,以确定私法行为的效力。而在其他非明示领域,一般直接适用规则,且遵循“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限定,无须特意考量公序良俗;只有当私法行为以一种非常明显的程度影响到公序良俗时,即规则适用会产生明显的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有关公序良俗的考量方能进入行为效力判断过程。这是对私法自治原则优先性的贯彻,也是以“公”管“私”的管制逻辑体现。
三、解释及规则化。当在个案中有必要适用公序良俗时,对公序良俗的界定,就成为一个核心难题。学理上总结了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关于公序良俗的判断标准,但对于处在现实世界中的法律适用者来说,无论何种标准,均是对概念模糊性的相对降低,注定无法从内在的价值立场和外在的价值影响中超脱出来,从而真正在客观上消除其主观性。这就要回到上述基于宪法的解释路径,即依托宪法价值共识,在诸多方案中进行情境权衡,最终确定一个最符合宪法理解的价值判断。应当注意,即便对公序良俗进行基于宪法的解释,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其不确定性。但如上所述,相对于其他解释路径,这种解释更具有正当性、判断负担简省和相对确定性。
四、区分违反强度。当个案裁判中确须适用公序良俗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效力考量时,应当是必要、谨慎和适度的。根据私法行为违反公序良俗的程度,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有针对性地设定裁判策略:(1)最高强度是一边倒的道德不满,如在经典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如果依据规则判决里格斯可继承财产,其引发的不满必然是普遍而激烈的。此时对于公序良俗的适用,包括从反向逻辑折射出的公序良俗理解,自然不存在任何争议。(2)居中强度是各具理由的道德争议或价值“两难”,即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均会遭遇道德指责,如泸州遗赠案。此种情形尤其要注重裁判的可接受性。法官要在个体主义与社会公共利益、规则的稳定性和个案的社会效果、当事人诉求和大众理解之间进行复杂的权衡,在此基础上,通过合宪性解释在宪法价值、事实和规范间“往返穿梭”,最终选择一个契合宪法价值共识的方案。(3)轻微程度则是基于道德完美主义和主观化的道德联想将某种行为视为对公序良俗的挑战,如曾引发广泛关注的“MLGB”商标案。此种情形须从正面考量引发争议的该行为是否构成发展中的社会多元价值的一种,从反面考量该行为是否与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相抵触(社会可接受性)、是否与国家目标相抵牾,以此确定有无必要适用公序良俗。
经过基于宪法的解释原则与程序,公序良俗原则建立起民法规范体系与宪法价值秩序的衔接通道,使宪法在目前无法直接司法适用的背景下,仍然能够依托民法体系中的原则性条款,在价值争议中发挥对具体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控制功能。而在民法体系遭遇解释与适用困境却又无法自给自足时,宪法秩序又能够为其提供具有共识性的理解根基。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宪法与民法的联结,是法律体系内部功能分工和有序关联的适当安排,由此既可维持民法自主但又适度开放的结构,亦可促使宪法以必要和谨慎的姿态发挥根本法的作用。据此而论,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法,否则,势必陷入宪法泛化主义,反而遮蔽了宪法构造国家体制、确认核心价值的核心功能;民法也不宜替代宪法来发挥宪法功能,否则,势必引发法律体系的功能紊乱。质言之,民法体系虽具有自身独立的部门法属性,但又无法也不应脱离宪法秩序,宪法价值与秩序理念既需要也应当通过各种联结路径,在民法规范体系中获得彰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文章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1年4期,李树民摘;作者:秦小建、周瑞文,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图片源自网络)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