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光哪个出名(史学界的三司马)
学习中国历史的同学们都知道,那司马氏,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就像是“唐宋散文八大家”里面的“三苏”,他们司马氏的三司马,在中国的史学领域,那实在是傻傻地太占体积了啊。
前有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后有司马光创作的《资治通鉴》,中间,还有司马贞创作的《三皇本纪》。
如果中国的历史学领域,没有他们这司马家的这三大本书,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简直是大厦坍塌、黯然失色啊。
那么,有没有人专门比较一下,他们这司马家的三司马之间,各自又具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呢?

从职务上来说,司马迁,就是一个专门的史官,著史,就是他的本行。
所以,他的《史记》,也就是中国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
司马光,则是一个政治家,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著史,也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所以,他的《资治通鉴》,对中国政治,特别是宋朝政治的影响力,也是强大的。
相比之下,中间的司马贞,生在唐朝,官至散朝大夫。
他就只是做了个官而已,并不是什么政治家,也就没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
而在著史方面,这著史,也不是他的本行,就是一个爱好而已。
所以,他的《三皇本纪》,也就没有什么立场与感情色彩,也就没有设定什么特别的目标与目的。
这就使得他的作品的影响力,相对也是最小,甚至,就没有被现代学者列入正史。

不过,如果单就著史而言,他们这三司马之间,谁又是真正的史学匠人,是在专心著史呢?
谁又是在以史作笔、以史作枪,利用著史,来达到自己著史之外的其它目的呢?
司马迁,本是史官世家,著史,是他的本职工作,这是不假。
但是,他上有先祖与父亲,下有兄弟与子孙,都是在从事着这项工作。
却似乎,他的整个家世,都没有一个人,是有他这么用心,也没有一个人,是有他这么别具一格呢。
他的别具一格,在别人看来,就是打破了史学的传统样式。
他的《史记》,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历史上的第一本纪传体通史。
但是,在槐荫树下的老曹看来,他的别具一格,不单是在于他的纪传体史学,更是在于他的文学性史学。
他的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便于他这种文学性史学的表达。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他的《史记》,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那么,他这种史学著作文学性表达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当然就不是为了著史,而是为了抒情。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更是一个受冤曲者。
他作史,是为了吃饭;而他抒情,则是为了他这个小小史官的冤屈。
他为与他具有姻亲关系,却投降了匈奴的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狱,处以了宫刑。
这原本是由于他和汉武帝的身份不同、角度不同。
汉武帝,追求的是他们刘家大汉王朝之崛起;而司马迁,不过是追求一个他们小小官僚家庭的安宁与幸福。

所以,他和汉武帝对于李陵投降匈奴的态度,那就肯定是绝然不同的。
其实,如果汉武帝不问他,也许,他就不会说。
但是,既然汉武帝问到了他,那么,从一个只想过家庭小日子的小小官僚的立场出发,他当然是想极力地为自己的姻亲——李陵开脱和辩护。
结果,他就竟然遭遇了无妄之灾,一个小小官僚的家庭幸福,没有了。
所以,他的一腔冤屈,要向哪里去倾诉呢?
正好,他的职务就是著史,他就当然是要向这《史记》中去倾诉嘛。

同样是汉朝大将,司马迁对李凌的祖父李广,就是极尽颂扬,不仅借典属国公孙昆之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
而且,对其与敌作战,能够详写的,决不省略: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

可惜,这只是一场小战。
而遇到大战时,在司马迁笔下十分神勇的飞将军李广,就要么兵败被擒,要么迷路。
这时,正面作战,在司马迁笔下,就变成了略写,反倒是李广被俘后的逃脱过程,又变成了详写:
“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
总而言之,败也好,胜也好,飞将军李广——神勇。
但是,对于真正战功赫赫的卫青霍去病,司马迁的笔墨,就没有那么大方了。

不仅,卫青霍去病和其他大将,被共列为一传,即《卫将军骠骑列传》。
而且,有关卫青霍去病的作战过程,大部分都是“上曰”,从来都不肯像描写李广被俘、逃脱时的神勇那样,生动细致一回。
另外,对于两人的评价,由于卫青脾气好,情商高,司马迁的评价,就是“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而霍去病年轻气盛,司马迁的评价就又变成了“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
司马迁之所以对李广与卫青霍去病的态度不同,当然是因为,李广是李陵的爷爷,和司马迁有姻亲关系;而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宠臣,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和外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什么要打破常规,独创出一个纪传体的著史方式了。
因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他就可以把李广单独列为一传,而把卫青霍去病等人共列一传。
而如果按照编年史来写,或者是以事件为中心来写,那么,李广,就因为没有真正的战功,而没有什么可写的,就不可能青史留名;反倒是卫青霍去病,因为具有真正的战功,就必然会被占去很多的笔墨,而流传千古。
所以,司马迁所开创的著史的体裁,也是为他的创作目的服务的。
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确实是成就了“一家之言”。
我们再看创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并不是专业的史官,他之所以创作《资治通鉴》,是因为,王安石主张变法,他反对变法。

因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不得不靠边站。
所以,他才去写《资治通鉴》,以论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而正是因为他创作《资治通鉴》,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他的创作体裁,就与司马迁又有所不同。
司马迁的体裁是文学体,而司马光的体裁则是政论体。
司马光的每一次叙事完结之后,都要来一段“臣光曰”——“臣下司马光认为”。
也就是说,他要利用自己的历史叙事,来教皇帝——怎么做皇帝。

而由于他立场先行,所以,他对历史体裁的选取,当然也就是“独具匠心”的。
《资治通鉴》开篇,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
为什么,他要从这一年开始写起呢?
因为,这一年,周威烈王封韩虔﹑赵籍﹑魏斯三位卿大夫为诸侯。
司马光认为,周威烈王打破礼制规则,让韩﹑赵﹑魏三位卿大夫成为诸侯,是造成后来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存在感的公元前403年,在司马光的眼中,却成了极为重要的年份。

关于司马光的观点正确还是不正确,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还是先来通过司马光的两件施政举措,看一看他这个人的个性与为人吧。
先说说,他对于一件谋杀案的处理。
公元1068年,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刚开始的那一年,山东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少女阿云,对包办婚姻不满,却无法改变,她就趁着她的对象韦大宝睡觉的时候,剁了韦大宝十几刀,但是,并没有得逞,仅仅是剁掉了韦大宝的一根手指。
按照《宋律》,谋杀亲夫,要处以极刑。
可是,地方官许遵认为,阿云这时还没有嫁给韦大宝,所以,这件案子,就不能算是谋杀亲夫案,只能按一般的伤害罪处理。

但是,案子被上告到刑部,刑部又要按谋杀亲夫罪论处。
于是,这件事,就惊动了宋神宗。
宋神宗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讨论一下。
结果,当然是王安石支持许遵,而司马光则支持刑部。
由于王安石当时主政,所以,阿云当时就被从轻发落。
然而,17年之后,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主政。
司马光上任之后,立刻重审17年前的阿云案。
早已结婚生子的阿云,于是被重新定罪,斩立决。

再说第二件事,就是对于王安石主政时期从西夏夺取的河湟之地的处理。
因为要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所以,王安石当政时所做的一切,都要“拨乱反正”。
于是,王安石采取积极进攻策略而取得的土地,本为“夏国旧日之境”,必须全部归还!
但是,因为众怒难犯,河湟之地,就并没有退回给西夏,只是把米脂等四个地方,还给了西夏,使北宋西北方面的防御形势,又回到了从前。

了解了司马光的个性与为人,我们再看看,司马光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
同样是贰臣,对于韩非子,司马光的评价是:“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但是,对于魏征,他的评价则是:“文正(贞)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为什么韩非子的背叛,不能容忍;而魏征的背叛,就无伤大雅呢?
因为,韩非子是主张变法的;而魏征,则是一个礼制的“卫道士”。

最后,我们来看看司马贞和他的《三皇本纪》吧。
司马贞既不是史官,也不是政治家,他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受到什么冤屈,一个和平时期不大不小的,普普通通的官员而已。
所以,他的作史,就纯粹是像钓鱼爱好者钓鱼,为钓而钓,没有什么目的。
正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所以,他就对自己所叙述的历史,没有什么立场先行性的评论,也没有什么为了达到其创作目的的刻意剪裁。
他就是像钓鱼者钓鱼一样,耐心地从史籍中摘取他认为有用的信息,来补全历史。

他在《三皇本纪》的开篇就说:“三皇已还,载籍罕备。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论古史,不合全阙。近代皇甫谧作帝王代纪,徐整作三五历,皆论三皇以来事。斯亦近古之一证,今并采而集之,作三皇本纪。虽复浅近,聊补阙云。”
当然,他也并不仅仅是并采了皇甫谧的《帝王代纪》和徐整的《三五历》,他其实还是索隐了许多其它史籍的记载,而组成《三皇本纪》的。
不过,他虽然喜爱历史,他却并不一定读得懂那些先他之前的史籍著作。
他的《三皇本纪》,有一些内容,仅仅是因为他模糊地觉得那些信息有用,所以,就给懵懵懂懂地摘录了下来,拼凑在一起而已。

比如,他在《三皇本纪》关于女娲氏的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的原因,就是为了“以济冀州”。
那么,女娲氏为什么要“以济冀州”呢?
这段话中的“以济冀州”一句,实际上是司马贞从《淮南子》一书中摘录过来的。
而《淮南子》中的原句,是“杀黑龙以济冀州”。
也就是说,女娲氏“以济冀州”,是为了去冀州“杀黑龙”。

那么,司马贞为什么要篡改《淮南子》的原文、原意,去掉“杀黑龙”三个字呢?
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起码,司马贞搞不懂这个“黑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那么,“黑龙”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呢?
我们再看《三皇本纪》中另一部分的记载,就可以明白。
在《三皇本纪》中,关于庖犧氏的那部分里,司马贞记载:“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
联系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黑龙”其实是一个部落,是一个属于庖犧氏的部落,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其实,就是到冀州去帮助共工氏打击庖犧氏中的黑龙氏部落。

那么,共工氏与祝融氏打仗,女娲氏去冀州打击庖犧氏部族中的黑龙氏部落,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看《三皇本纪》中的庖犧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所以,庖犧氏其实就是祝融氏,而燧人氏就是共工氏。
庖犧氏原本是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入主中原,征服燧人氏,成为农耕民族,就改换名号,成为了祝融氏。
燧人氏被庖犧氏征服之后,就改换名号成为了共工氏。
并且,由于庖犧氏变成祝融氏,是“木德王”,所以,燧人氏变成共工氏,就是“以强霸而不王”。
又因为“水生木”,所以,共工氏因应祝融氏的“木德”,而自认是属于“水德”,他们就要“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
“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就是他们乘着洪水暴发,而去与祝融氏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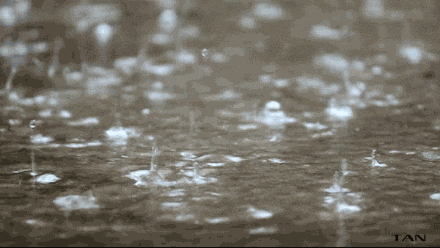
所以,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其中的“炼五色石以补天”和“聚芦灰以止滔水”,就是为了消除洪水,而举行的两种宗教仪式。
“炼五色石以补天”,就是利用“五行学说”中“石生水”“火克石”的原理,来通过“火克石”而达到阻止“石生水”的目的。
“聚芦灰以止滔水”,就是利用“五行学说”中“火生土”“土克水”的原理,来通过“火生土”而达到“土克水”的目的。
“断鳌足以立四极”,实际上就是一种类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因为,当时的天下,主要是有四大部族,所以,就有“立四极”的说法。
而鳌,即龟,就是当时共工氏部族的图腾。

我们现在的“五行学说”中,有金元素,但是,在女娲氏时代,是没有金元素,只有石元素的,所以,那时的“五行学说”,是“石生水”“火克石”。
由于这些历史知识,司马贞不一定懂得,他就不一定理解前人留下的史籍中,所记载的那些内容,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所能够懂的,而进行编写。
这样,虽然,司马贞很尊重历史,他却不一定能够,完美地传承历史。
所以,我们今天读史,就不但要用眼看,更要用脑想,还要通过比较多家之言,来判明他们各家著作的真伪与对错。
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司马之家啊。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