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潘光旦的评价(重温观察潘光旦对人与物的控制的思考)
原子弹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原子能的威力也逐渐引起了思想家的担忧。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潘光旦在《观察》周刊第二期上发文,论述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对自身的控制能力的思考。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
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
潘光旦
中国有句老话,说,童子操刀,其伤实多。这句话恰好形容了三百年来科学进步的一半的结果。刀是一种人所发明的工具,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是用途有好坏,用得适当就好,不适当就坏。刀自身不能发挥它的功用,发挥它功用的是人,而人却有好坏之分,有适当不适当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适当而健全的人来利用一种工具,其功用或结果大概也是适当、健全、而有益的;否则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后一种的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这眼光来看。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较具体的工具制作与比较抽象的典则制度在内,尤其是如此。说『尤其』,正因为它们是人造的,是人的聪明的产物,如果控制无方,运用失当,以至于贻祸人群,那责任自然更较严重;人的聪明能产生这些,而竟不能适当的控制运用这些,至于尾大不掉,自贻伊戚,也适足以证明那聪明毕竟是有限罢了。
我们也得用这种眼光来看科学,科学也正复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多。它本身也无所谓好坏,好坏系于人的如何控制运用。一部分人,见到科学昌明以后,人类的一部分获取了种种利用厚生的好处,于是就赞扬科学,歌颂科学,对科学五体投地,认为是人类的福星。我想除非一部分人中间,有人生就的是一副诗人性格,动不动要发抒他的感伤主义,这是大可以不必的。另一部分人,见到在同时期以内,科学表现了不少的摧杀败坏的力量,特别是在历次的大小战争里,于是就批评它,诅咒它,认为人类迟早不免因为它而归于寂灭。而自原子能的发明以后,这末日可能来临的很早;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感伤主义的表示,大可以不必的。

我们要认清楚,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关键在人。童子操刀,问题绝对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运用科学,问题也决不在科学,而在人的运用与运用的人。我们要问这运用科学的人是不是真能善于运用,真有运用的资格。换一种问法,就是他配不配运用。所谓善,所谓有资格,所谓配,指的是两层相连的意思:一是他在运用之际,能随再参考到人群的福利,始终以人群福利为依归;二是他,运用者自己,必须是一个身心比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个程度,足以教他实行这种参考,笃守这个依归。这两层意思,第一层指人的运用,重在运用;第二层指运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这两层意思的分别来,因为『人』与『运用』之间,比较基本的终究是人,人而健全,运用是没有不得当的,反过来就很难想像了。而近年以来,中外论者鉴于科学对人群的利害参半,对于有害的一半总说是『运用失当』,难得有人更进而提出如下的一类问题:失当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种失当是偶然的呢,是一时计虑的错误而可以避免的呢,还是有些基本的因素教他不得不发生而随时可以发生的呢?这基本的因素里可能不可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适当,因而他对于科学的运用也就无法适当?好比骑马,马是工具,人是马的驾驶者,骑马之人虽未尝不聪明灵活,未尝不略知驾驶之术,但也许年事太轻,或适逢酒后病后,神志不够清楚,终于把马赶进了一个绝境,造成了断头折足的惨剧。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则问题还不在一个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浅见而感情用事的人责备着刀。其次也只是在操字上做功夫,总说操得不得法,诚能操之得法,问题就解决了。一九三一年二月,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州工科学院对学生作公开演讲,说,『光辉灿烂的应用科学既算省了工作的时间,减轻了生活的负担,而对于人类幸福的促进,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们简单的答复是:我们还没有学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们的工作得以增加人类的福佑,只是了解应用科学是不够的。你们得同时关切到人。人的自身与人的命运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工的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们绘制图表与计算公式的时候,随时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番话是不错的。从爱氏的嘴里说出来,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够,单单就「操」字上找答复,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复,所以不够。爱氏在这话里,也似乎只见到『人的运用』,而没有见到『运用的人』。要见到了运用的人,问题才搔到了痒处。
三百年来,物的研究认识,物的控制运用,诚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能的发见与原子弹的实验成功,此种认识与控制更是将近登峰造极。但人自己如何?人认识自己么?人更进而控制自己么?我们的答复是,人既不认识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种物体,这物体是一个机械体也罢,是一个有机体也罢,它总是一个极复杂的力的系统。我们对于这力的系统,根据物有本末事有先后之理,我们原应先有一番清切的了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来,科学尽管发达,技术尽管昌明,却并没发达昌明到人的身上来,即虽或偶然涉猎及之,不是迂阔不切,便是破碎支离。结果是,我们窥见了宇宙的底蕴,却认不得自己;我们驾驭了原子中间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欲;我们夸着大口说『征服』了自然,却管理不了自己的行为,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这正合着好像是耶稣讲的一句话,我们吞并了全世界,却是抛撇了自己的灵魂。比起这句话来,上文童子操刀、醉汉骑马一类的话,还算是轻描淡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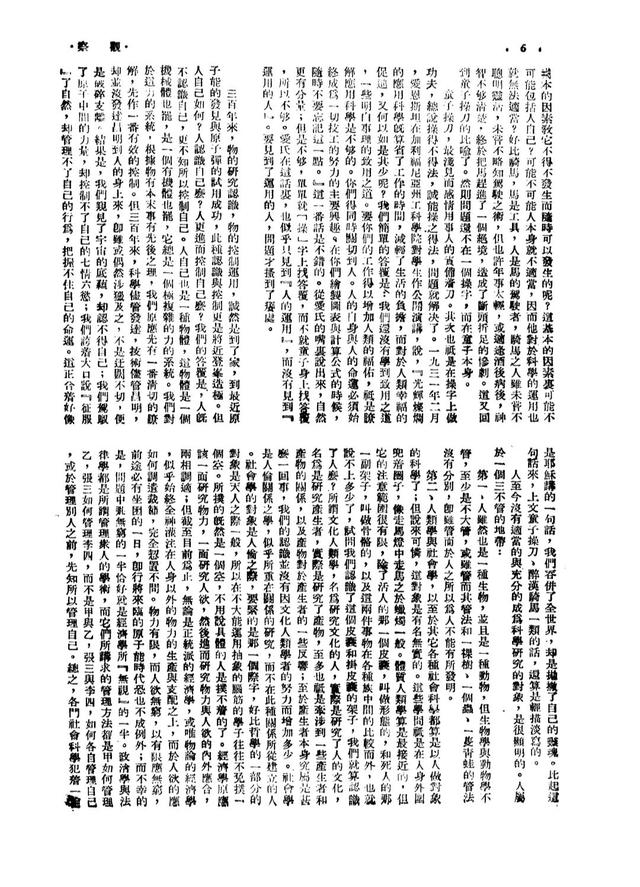
人至今没有适当的与充分的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很显明的。人属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第一、人虽然也是一种生物,并且是一种动物,但生物学与动物学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虽管而其管法和一棵树、一个虫、一只青蛙的管法没有分别,即虽管而于人之所以为人不能有所发明。
第二、人类学与社会学,以至于其他种类社会科学都算是以人做对象的科学了;但说来可怜,这对象是有名无实的。这些学问只是在人身外围兜着圈子,像走马灯中走马之于蜡烛一般。体质人类学算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范围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个皮囊,叫做形态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这两件事物在各种族中间的比较而外,也就说不上多少了,试问我们认识了这个皮囊和挂皮囊的架子,我们就算认识了人么?所谓文化人类学,名为研究文化的人,实际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为是研究产生者,实际是研究了产物,至多也只是牵涉到一些产生者和产物的关系,以及产物对于产生者的一些反响;至于产生者本身究属是甚么一回事,我们的认识并没有因文化人类学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会学是人伦关系之学,似乎所重在关系的研究,而不在此种关系所从建立的人。社会学的对象是人伦之际,要紧的是那一个际字,好比哲学的一部分的对象是天人之际一般,所以在不大能运用抽象的脑筋的学子往往不免扑一个空。所扑的既然是一个空,不用说具体的人是扑不着的了。经济学原应该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后进而研究物力与人欲的内外应合,两相调适;但截至目前为止,无论是正统派的经济学,或唯物论的经济学,似乎始终全神贯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产与支配之上,而于人欲的应如何调遣裁节,完全恝置不问。物力有限,而人欲无穷,以有限应无穷,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将来临的原子能时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问题中那无穷的一半恰好就是经济学所『无视』的一半。政治学与法律学都是所谓管理众人的学术,而它们所讲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张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与乙,张三与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于管理别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总之,各门社会科学犯着一个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远,趋虚避实,放弃了核心而专务外围。所谓本、近、实、与核心,指的当然是人物之际的人、和人我之际的每一个人的自己而言。这边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体生理学、心理学、医学、一类的科学在人的研究上我们承认是进了一步。它们进入了人身。上文所说的那种通病它们并没有犯,我们不能说它们『迂阔不切』。它们犯的是另一种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过的『支离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来一切研究具体事物的科学的不二法门。名为分析与综合并行,实际所做的几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结果是支离破碎,这在人以外的物经得起,人自己却经不起,死人经得起,活人却经不起。无论经得起经不起,支离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认识,等于未研究,不认识;因为人是囫囵的,整个的,并且是个别的囫囵的或整个的,而零星片段的拼凑总和并不等于整个。总之,截至最近几年为止,即在这些直接应付人的科学里,人也未尝不落空。我说截止至最近几年,因为一部分生理学家、病理学家,特别是精神病理学家,年来已经充分看到这一点,认为有机体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换他们的研究方法中;但时间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总上三不管的议论,可知人类自己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每一个人自己对于我之所以为我,至今依然在一个『无知』与『不学』的状态中。『不学』的下文是『无术』,就是,既不认识自己,便无从控制与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为管制必然是一种胡乱的管制;人对于自身系统中的力,不知善用,对于其意志、理智、情绪、兴趣、欲望、不知如何调度裁节,而但知支配运用身外的种种物质系统中的力,其为运用必然是一种滥用。滥用的结果是『伤人实多』,而这个『人』字最后不免包括滥用者自己。这在上文已经预先笼统说过,但至此我们更可以说得明细一些。

人对自身的认识与控制是一种尚待展开的努力。此种努力分两层。一是就整个属类言之的。人也是物类的一种,但究属与一般的物类不同,他有他的很显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与控制的技术势必和其他的物类不能一样。上文囫囵或整个之论便是属于研究一方面的。至于控制,即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们就不适用所谓『集中』『清算』或『液体化』一类的方式,这些都是把适用于一般物质的概念与方式强制的适用到人,此其为适用也显然的是一种不认识人的滥用。不过更重要的是第二层。人是比较唯一有个性而能自作主张的动物;也正唯如此,我们才产生了关系复杂的社会与制作丰富的文化。每一个人是一个有机体,每一个人是囫囵的,而其所以为有机,所以成为囫囵,每一个人又和每一个别的人不一样。这样,研究与控制的方式便又须另换一路;即事实上必须每一个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别人根本无法越俎代谋;别人有理由越俎代谋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绝少数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学术包括每一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阔不切的,支离破碎的,或是由别人越俎代谋而自外强制的。前人的经验,无论中外,其实早就看到这一层道理,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即是。不过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虽也有大致做到的贤哲,但总属少数,今后人的学术的任务,我以为就在更清楚的阐明此种方法,更切实更精细的讲求它的做法,而此种学术上的任务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务。目前的学术与教育是已经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学不为己而为别人,是错误,学不为人而为物,是错误之尤,目前该是纠正这大错的时机了。
有了明能自知与强能自胜的个人,我们才有希望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健全的社会意识由此产生,适当的团体控制由此树立;否则一切是虚设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识的产生必然的是由于宣传,而不由于教育,由于暗示力的被人渔猎,而不由于智、情、意的自我启发;而控制机构的树立也必然是一种利用权力而自外强制的东西。这又说着当代文明人类的一大危机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节,有恐怖而不知擅自镇慑,有忧虑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难而不知善自解决,于是有野心家出,就其应裁节处加以欺诳的满足,应镇摄与排遣处,一面加以实际的煽扬恫吓而一面加以空虚的慰藉护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传的暗示,一面依凭暴力的挟持,于是一国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为被控制者,成为奴隶;其间绝少数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终于因暴力的挟持而遭受禁锢、驱逐、以至于屠杀。独裁政治和集权政治不就是这样产生的么。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类的天罡星不就是这样应运而下凡的么?
什么是野心家?从本文的立场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聪明才干足以助纣为虐的人。野心家的野即应作如是解释,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别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种种欲望,其中最大的是爱权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运用意志的力量来控制这欲望,反而无穷尽的施展出来,一任这欲望成为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权柄便见得愈大,控制了德国不够,更进而控制东欧,全欧,以至于全世界。有一个笑话不是说希特勒拜访上帝,上帝不敢起来送行,深怕他一站起来,离开宝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气的取而代之么?这真十足描写了野心家爱权若狂而不知裁节的心理。不过从控制德国以至于全世界,但凭欲望是不够的,他必须运用物力,必须驾驭科学,规模之大,又必须和他的欲望相配合,于是他就从人的控制进入了物的控制,从人力的滥用进入了物力的滥用,而就当时德国与其邻邦的形势而论,因为大部分直接运用物力的人,例如科学家之类,向来没有讲求过自我控制,自作主张,也就服服帖帖的由他摆布,受他驱策,至于肝脑涂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缘不就是这样的么?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文明人类一大部分的祸患,我们可以武断的说,是由于人自己酿成的,而其所由酿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不讲求与缺乏。这种局势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缘故,则坐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既没有增加,甚或需有减削,而人对于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则因科学的发达而突飞猛进。两种力量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可以道里计的距离。社会学家称此种不能协力进行的现象为『拖宕』,拖宕一名词是何等的轻淡,而其所酿成的殃祸却真是再严重没有。不过这种严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战将近结束,原子弹发明以后,才进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发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视蒸汽的力量,电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数。惟其大,所以更难于驾驭控制,大底为了破坏的目的,在制敌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种控制比较容易,所以原子弹是成功了。但为了建设与人类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难得多了。浅见者流不断的以进入原子能新时代相夸耀,把原子能可能产生的种种福利,数说得天花乱。不过沉着的科学家却不如是其乐观,即如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科学顾问艾里斯教授说,我们可能用原子能来驾驶海洋上的巨轮,但为了保护乘客与船员,所必需一种防范机构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象,甚或根本不可能有此机构。又如生物学家赫胥黎说,原子分裂所发生的种种高度放射作用对于人的健康与遗传是极度的有害的。这又引起控制与防范的问题了。再如英国奥立芬脱指出制造原子能的厂房一带所遗留的灰渣会发出种种致命的电子性的『毒气』,而毒气所波及的地带,根本无法防卫,长期的成为无人烟与不毛之地。
也就是这一类的科学家如今正进一步的呼吁着物力的控制,觉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类便要濒于绝境。不错的,这是一个临崖勒马的时候了。不过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马,也不在那勒的动作,而在那作勒的动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问题,临时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会勒,总之,他对自己既作不得主,名义上对物做主,实际上等于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据说,当初英、美、加等国的科学家在新墨西哥试验场上,等待第一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大家就手捏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谓连锁的反应,一发而无所底止;后来幸而没有。可见即在谨严的科学家手里,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进希特勒一类的人的手里,殃祸所及,那真是不可想象了。
总之,我们不得不认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点,是一切控制的先决条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应付物力的时候,别人想谆谆的劝勉他作妥善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有如近顷许多作家所论,而在教育。童子在操刀以前,必须先受一番『明』『强』的教育。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