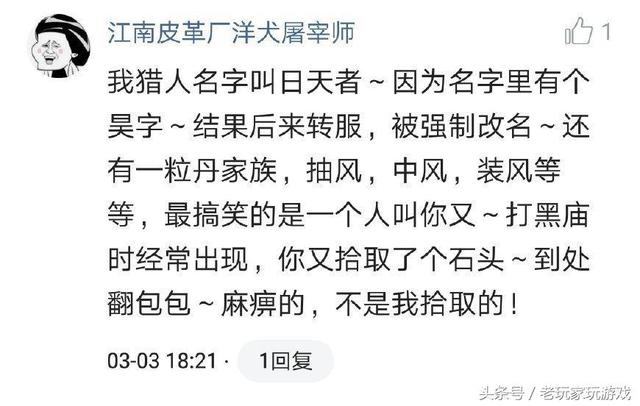父亲离世母女相依为命的故事(故事父亲去世继母打工赚出巨款)

本故事已由作者:一叶飞虹,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谈客”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丑姨来了,带着她的女儿翠妞,我高兴地不得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见翠妞了。
大半年前,我跟着金花去她家串亲戚,然后金花就再也不去她家。金花是我娘,利索又能干,长得也漂亮,但脾气暴躁,发起脾气来会骂我打我,还会把我撵出门去。我很怕她,心里总是喊她的大名金花。
金花说姨夫得了治不好的病,拖不了一年半载。她叹着气说,“丑可真够命苦的,找了个二婚,还是个短命鬼。”
“姨夫和他第一个老婆没登记,那就不能叫二婚。”我大声纠正她。我已经读四年级了,关于婚姻方面的事情我知道的可不少。
“你懂什么?都生孩子了,不叫二婚叫什么?还能叫头婚?”金花恶狠狠瞪了我一眼,我吓得不敢再辩驳。
丑姨是金花的堂妹,两人是一个亲爷爷。她从娘胎里带了一块青色的胎记,恰好长在脸上。父母给她起名丑,据说是想以毒攻毒,希望她以后能长得好看一些。但事与愿违,她脸上的胎记随着年轮,也风生水起地生长起来。
丑姨比金花小一岁,但我都五岁了,丑姨还没有婆家。人家都嫌弃她脸上的胎记,说那是不祥之物。最后,丑姨就找了姨夫。姨夫的第一个老婆跑了,没结婚登记,留下一个男孩。
丑姨结婚的时候,我跟着金花去给她送面,同去的还有丑姨的两个亲嫂子。我看到丑姨穿着一身新衣服,盘腿坐在炕上的角落里,微微低着头,一脸的幸福和羞涩,我觉得她一点也不丑。吃完撤席时,她大嫂对婆家人客套,“我家妹妹长得丑,手也不巧,您多担待。”
我一听很不高兴,在一旁大喊,“丑姨不丑,不丑。”
所有人都一怔,继而尴尬的笑了,我被金花拖过去,狠狠拧了一把,我眼泪汪汪的看向丑姨,她更深的埋下头,我望不见她的脸。那一刻,我坚信她心里一定是自卑和难过的。
丑姨进我家没多久,说起姨夫的病,眼圈就红了。她说姨夫疼得从床上爬下来,把身子横在院门的门槛上,大声呻吟。
“怕是这几天了。”丑姨哽咽,赶紧用手擦泪。
“他得了那种病,谁也没办法。”金花劝她,“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你不是还有翠妞吗?”
“还有建辉。”丑姨小声说。
建辉就是姨夫和第一个老婆生的儿子,以前时常跟着丑姨来我家。金花只是表面上对他热络,但心里一点不喜欢他,也不让我和他亲近。金花说他不是我的亲表哥,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又不是你的儿子。”金花哼了一声。
“姐。”丑姨叫了一声,眼神期期艾艾看着她。
“我这次来,是想和你家赊一袋化肥,地里的玉米不见长,没化肥不行啊!”
金花愣了一下,赶忙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要包饺子吃。”
剩下的时间,金花和丑姨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姨夫的病,我带着翠妞和弟弟小海在一旁画画。吃完饺子,丑姨说要回去了,金花把一碗饺子装进塑料袋,说给姨夫捎回去。然后,金花走到西屋,拎出一个瘪瘪的化肥袋,里面的化肥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家里的化肥都卖完了,这是田里剩下的,先带回去用吧。”
金花撒谎一点都不脸红,化肥明明还有很多,都锁在老房子里。看着丑姨失望的脸色,我很难过。
“你为啥不赊给丑姨化肥?别人赊账你怎么同意?”丑姨离开后,我问。
“一袋化肥五六十块,赊给她什么时候能还钱?你姨夫生病已经借咱三百块了。”
“可是丑姨很可怜。”我小声说。
金花瞪我一眼,“你爹娘天天干活,累得要命,不可怜吗?”
我不敢吱声了,但我心里为丑姨不平。自从我懂事,丑姨就是我家的常客。我爹是农村的能人,冬天倒腾卖炭,夏天倒腾卖化肥,都需要人手,丑姨嫁人晚,和金花又是好姊妹,便时常被金花叫来,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帮我家干活。金花说丑姨自小就是她的尾巴,听她的使唤。
丑姨结婚前的那个冬天,我爹进了好几车皮的煤炭,都卸在镇上。爹娘日夜在镇上卖炭,在家里陪着我的就是丑姨。每天早晨,她给我扎好小辫,再自己梳头发。她的头发又黑又长,绸缎一样。但她只对着墙壁梳头,从不照镜子。
“给你镜子。”我说,把镜子递给她。
“姨不照镜子,姨长得太丑了。”
她把镜子扣下,轻轻叹气,摸着我的脸蛋,“小雨长得真好看,姨如果和小雨一样好看多好啊!”
然后,她盯着问我,“小雨,你说实话,姨的脸是不是很难看?”
我认真地摇摇头,她笑了,把我搂在怀里,眼圈渐渐红了,“只有小雨认为我不难看。”
夜里,我一觉醒来,有时发现屋里亮着灯,看见丑姨坐在桌子前,偷偷照镜子,轻轻叹气。我这才明白,她也是照镜子的,不过是在夜里,自己一个人偷偷照镜子。
2
丑姨家来报丧,说姨夫去世了。我跟着金花去了她家。在灵棚后面,我看见了一身孝衣的建辉和翠妞,两个人都不哭,埋着头跪在铺着干草的地下。我听见几个妗子和舅舅骂建辉不懂人气,那么大了,他爹死了,也不哭。建辉比我大两个月,但个头不如我高,我向来是蔑视他的。
几个妗子舅舅姨妈围着丑姨,低声安慰她,丑姨低着头垂泪,一声不吭。
几个月后,丑姨和两个亲哥哥闹掰了。两个哥哥雇了一辆大卡车给她拉东西,让她先带着翠妞回娘家,毕竟还年轻,以后再找一个下家。可她竟然拒绝了安排,说她走了,建辉怎么办,她舍不得建辉,也舍不得这个家。两个哥哥很生气,一气之下不再管她的事,不准她再登娘家的门槛。
金花念着姊妹的情谊,决定去劝劝她。那天,金花骑着自行车,前面载着小海,后面载着我,车把上挂着两包点心,一路骑行十几里,压着地上沙沙响的落叶,来到丑姨家。
一家三口正在腌萝卜。建辉和翠妞在机井旁边把一个个萝卜洗得白白净净,放在大缸里。建辉好像知道金花来的目的,阴着脸叫了一声姨,就不再言语。
金花拉着丑姨进了屋,我想跟着她,金花瞪我一眼,用目光逼退了我的脚步。其实,不听我也知道金花怎么劝她。金花不时和爹唠叨,说丑姨真傻,建辉又不是亲儿子,守着他干什么?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还能过下去?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趁着年轻,带着翠妞再走一家,这才是有盼头的好光景。
建辉黑着脸不理我,我就忍不住刺激他一下,“你知道我娘来干什么吗?”
他用白眼珠看我,又低头洗萝卜。那边翠妞和小海玩得正欢,我百无聊赖,忍不住蹑手蹑脚走进屋,听到丑姨在里间小声呜咽。
“姐,别说了,我舍不得扔下建辉,我养了他七八年,我就是他的娘,我这辈子就守着建辉和翠妞过了。”
“可你才多大呀,才三十多岁,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
“我就是这么个命,我认了。”
我听见了她压抑的啜泣声。
刚放寒假,丑姨就带着建辉和翠妞来我家了。她来我家并不稀奇,但稀奇的是,她来我家住下,就不走了。
“姐,快过年了,要账的挤破门,我只好来这里躲躲,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娘家我又没脸回去。”丑姨低着头,一手拉着建辉,一手拉着翠妞。建辉低着头,翠妞怯生生望着我们。我们那儿有过年要账的习惯,也有过年还钱的习惯。
金花瞅瞅孤儿寡母三人,自然是不能拒之门外的。母子三人睡在我的西厢房,我搬到金花的炕上。以前,姨夫在世时,他们一家来我家串亲戚,偶然住一晚,都是这样安排的。
“冷,就点上炉子。”金花对丑姨说。我家卖炭,可不缺炭。
第二天,我发现丑姨那个屋子冷冰冰的,炉灰是凉的。
“你们怎么不生炉子,多冷啊!
“不冷,我们习惯了,在家也不生炉子。”丑姨笑笑。
“丑姨那边没有生炉子。”我偷偷对金花汇报。我本意是提醒她,晚上亲自去那屋生炉子。
金花的脸上却浮起一层笑意,“她倒懂点事,三口人白吃白喝,还能再烧咱的炭?”
我瞅瞅金花的笑脸,终于明白了什么。
丑姨在我家躲债的日子,正是我家最忙的时候。爹每天早出晚归,拉着一车煤炭去串乡,金花守在老房子里卖炭。于是,我家杂七杂八的活计都被丑姨包了。金花指使她干活也毫不含糊,让她把我家的棉被都拆洗一遍,还让她带着几个孩子进行大扫除,把房顶墙壁都清扫一遍。
她扎上头巾,穿上金花的破衣裳,举着系上长竹竿的笤帚,一会儿就成了土人。
金花就连厨房也不进了,做饭洗碗都是丑姨的。
冬天没什么菜,就是大白菜。丑姨隔一天蒸一次混合面的大包子,两层篦子,一顿饭就能吃光,因为建辉自己就能吃七八个。金花的目光在建辉那儿飘来荡去,但建辉只是闷头吃饭,根本不理会金花的眼神。
晚上,金花和爹偷偷抱怨,“他们娘仨再不走,就把我们家吃穷了,那个建辉,快赶上我们一家人吃了。”
“人家也给咱干活了。”爹是个善良的人,宽慰金花。
一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丑姨才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临走时,金花给她捎上炸丸子两棵白菜一斤肉,让他们初一包饺子吃。
3
大年初四,丑姨带着建辉和翠妞来拜年,天快黑了,还不说走。
“要不就住下吧!”金花客套一句。
丑姨马上答应下来,娘仨又住进了我的屋。
金花私下和爹唠叨,“这是赖上咱家了,又来白吃饭了。”
“吃就吃吧!怪可怜的,几顿饭咱还能管不起?”爹是个体面人,一向大度。
过年我家历来很热闹,人来人往的。爹有些小本事,像一盏小灯笼,总能吸引很多人来我家做客。爹和他的狐朋狗友天天在厅房喝大酒,而金花和五六个媳妇在里屋打牌,吆五喝六,鸡飞狗跳。
金花一边打牌,一边大声指使丑姨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那口气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丑姨像个陀螺,脚不沾地,满脸讨好谦卑的笑,一点也不嫌烦。我看着她,感觉有些心疼,为她不平。
“你们都在玩,为何让丑姨当保姆干活?不公平。”我对金花说。
金花用力戳我的脑门,“你个榆木疙瘩,你懂什么?她当保姆又咋的,我管她三口人白吃饭呢!她两个亲哥哥都不让她登门,除了我,谁还能这样好心对她?”
正月十五那天,爹忽然被村支书请去喝酒。半下午时,爹喝的满脸红光才回家,进门就拉着金花到里间叽叽咕咕。
一会儿,金花就把丑姨叫过去。
“你的福气来了。”金花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气。
“支书家托媒了,支书的弟弟看上你了,他虽然是只有一只眼,但不妨碍干活的,人家愿意帮你把外债都还了,也不嫌弃你的两个孩子,以后建辉娶媳妇他家包了,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你来了,咱姊妹就是一个村,啥事也方便,再说,你成了支书的弟媳妇,别人都会高看你一眼的!”
丑姨一脸蒙,良久才摇头,“姐,我不能答应,建辉大了,我不能再给建辉找个后爹,我怕孩子不适应。”
金花的脸色微微变了,她压根没想到丑姨会拒绝。她又劝了很长时间,丑姨只是摇头不松口,金花终于失去耐性,黑了半边脸。
“你可真是个死脑筋,嫁过去债也清了,有吃有喝的,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就不答应?”
丑姨低头不吭气,金花的目光凛冽的扫过去,“既然你不给我这个面子,就不要在我这里蹭吃蹭喝了。”
金花是真生气了,蹭吃蹭喝说的义正严词,冰冷刺骨。丑姨的身子瑟缩几下,像一片寒风中的叶子。
她带着建辉和翠妞走了,从此她再也不登我家的门槛。过了一阵,金花的气消了,也感觉自己有些过分,不该说那样伤人的话,但她好强气盛,绝不会服软的。
偶然听说丑姨被要债的人堵着门羞辱,金花咬着牙说,“她这是活该,她这个人就是死心眼,从小就这样。”
但我却从她的话语深处听出了心疼的意思。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丑姨了。
4
一年多以后,我成了一名初中生。开学不久,我发现建辉竟然在隔壁班。他竟然也考上初中,我始料未及。我和他假装不认识,遇见时,谁也不理谁。
想不到秋收以后,丑姨竟然又登门了,进门就跪下,把金花吓了一跳。
“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先起来说。”
金花好不容易才把丑姨从地上拽起来。
“姐,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多,家里的债一点都没还,听说上海的钱好挣,我想去上海。”
“上海?”金花有点愣。那可是个电视里的城市,遥远的就像天上的星星。
“你到上海能干什么?能找到工作?”
“我当保姆,听说上海人有钱,家家都雇保姆。”
“那,那就去呗!”
丑姨忽然又扑通一声跪在金花面前,“姐,我想让两个孩子先在你家住着,饿不死他们就行。”
金花惊的眼睛都直了,脸也白了,赶紧摆手摇头,“不行不行,我家有小雨小海,加上你的两个,四个孩子我可弄不了,再说,你那个建辉饭量那么大,我真养不起。”
“姐,我知道你的难处,等我到了上海,挣到钱我会寄钱给你,我说话算数。”
金花的呼吸慢慢平稳了,不摇头,也不摆手了。她把丑姨从地上拉起来,“你,你可得说话算数。”
我在一旁听了,心里不仅几分高兴,以后建辉在我家吃住,还好意思不理我吗?
爹给建辉在西屋搭了个木板床,翠妞和我睡一个炕。翠妞乖巧懂事,嘴巴很甜,可建辉对我依然像个陌生人,从不主动和我说话。他只对翠妞笑,使我的自尊心很受伤害。金花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
吃饭时,金花的眼睛不时盯他一眼,看他局促的模样,我就忍不住想笑,也很解恨。建辉吃饭很快,三下五除二,塞进嘴里一个混合面馒头,然后就匆匆离开饭桌。
金花瞅着他的背影嘟哝几句,“养着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还是个闷葫芦。”
转眼丑姨去上海两个月了,杳无音信,也没见到她寄来的一分钱。金花不时骂她是个骗子,有时当着建辉的面,也丝毫不避讳。
翠妞还小,看不出金花的眉眼高低,可建辉是明白的。建辉回家后,开始躲在小西屋,不愿出来了。瞅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忽然又有些同情他。
不知何时,建辉中午不回家吃午饭了。金花对此忽略不计,不闻不问。
那天课外活动,我们两个班在操场上一起做操,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有人晕倒了。我挤过去一看,倒在地上的人竟是建辉,脸色蜡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建辉是饿晕的。
从此,中午我便瞒着金花,偷偷在兜里藏一个馒头,然后让同学给建辉。也许是饥饿的原因,他没有拒绝。从那以后,建辉对我的眼神变得温润。有时我被数学题憋得头脑昏昏时,便屈下身段,请教他。他的数学特别好,每次考试几乎满分。
谁能想到丑姨竟真的寄钱回来了!那真是一个犹如节日般快乐的日子。金花举着手里的汇款单,好像举着一面光荣的旗帜,从支书家出来,她逢人就说,“我妹子从上海寄钱回来了,寄了一百五十元。”
二十多年前,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记得一个同学的父亲在乡里当干部,工资是一百五十元。
“你娘寄钱来了。”金花一把抱起翠妞,亲了亲。
“我看看汇款单。”我说。
我拿起桌子上的汇款单,署名是孙金菊。
“孙金菊是谁?”
“就是你丑姨,她大名叫孙金菊,小名丑。”
我这才知道丑姨原来还有一个名字孙金菊。
建辉回家了,金花乐颠颠报喜,“你娘寄钱来了,看来她是在上海挣大钱了。”
建辉的脸色明亮起来。
金花买了冬瓜,割了肉,包了烫面冬瓜包子。我们围着盖天吃包子,满嘴流油。
“快吃,敞开肚子吃。”金花看向建辉,特别对他说,她的眼神很温润,再也没有了原来的煞气。建辉一口气吃了十一个包子。
以后,丑姨每个月都寄回一百元。过年时,她没有回来,但她不仅寄了钱,还寄回了一大堆东西,譬如上海的围巾高粱饴绒线衣等。
里面夹着一封信,是丑姨写的。她说,她很幸运,东家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太,住着一栋小洋楼,她的任务就是照顾老太太,给老太太做饭,陪老太太遛弯。老太太的儿女也很有钱,时常给她买东西。寄回来的这些东西都是老太太的儿女给她买的。
从此,我们深信不疑,丑姨在上海混得很不错。丑姨也成为金花在村里的自豪,她时常炫耀,她的妹子在上海给富人当保姆,拿着高工资,吃着山珍海味,过着富人一样的生活。
有了丑姨寄回的一百元,我家的伙食上了几个档次。关键是,金花看建辉的目光温柔了,而我再也不需要给建辉偷馒头了,每天中午他都回家吃午饭。在金花温柔目光的沐浴下,建辉和翠妞茁壮成长起来。
5
丑姨一直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年夏天,我和建辉都考上了高中,她才回来了。
她提着两个大包,荣归故里,穿着很稀奇的衣服,连脸上的胎记也不那么显眼了。让金花特别羡慕的是,她的脖子上竟然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说这是东家给她的。东家的抽屉里有好几条,人家随便拿了一条就送给她了。
金花直楞楞瞅着她的项链,连连说好看。那时,村里还没有人戴项链,也很少见过戴项链的人。
丑姨把珍珠项链摘下来,“姐,你喜欢就送给你吧!这几年,多亏你照顾建辉和翠妞。”然后,她就把项链戴在金花的脖子上。
金花喜不自禁,摸着项链在镜子前端详了好久,欢喜的脸都红了。
第二天,丑姨就带着建辉和翠妞回他们的家了。她说,这几年她攒了一些钱,可以还清外债。一家人终于敢昂着头回去了。
丑姨回家没多久,两个哥哥嫂子便上门兴师问罪。自从她开始寄钱,哥哥嫂子就眼红,但碍于她没回来,不好发作。
“咱爹娘没了,你眼里就没有你的亲哥亲嫂子吗?去上海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言语一声,你倒是走了,可我们多担心,你知道吗?”大嫂先说话了。
“你的心可真狠,走了好几年,连个音信都没有,你不惦记我们,我们可惦记你。”二嫂也说话了。
“你这算咋回事?你有两个亲哥哥,却把孩子送到金花家里,你让我们的脸面往哪里放啊?我们可是孩子的亲舅舅,我们在村里没法做人了。”大哥说。
“我们商量好了,你再回上海,就让两个孩子跟着我们,我们两家轮着照顾孩子,我们是亲娘舅,是连着血脉的,金花又不是亲姨,毕竟隔着一层。”二哥说。
丑姨不辩驳,也不表态,只是把给他们带的礼物拿出来。
“哥,嫂子,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建辉大了,上了高中,自己能照顾自己,至于翠妞,她跟着金花姐习惯了。”
哥嫂们悻悻地回去了。
只是丑姨回上海不久,他们又去了我家,要接翠妞。金花可不是吃素的,自然不同意。两家不欢而散,从此关系也闹僵了。
丑姨一走又是两年。高二暑假,她回来了。她又风光了一回。她把家中的老房子翻盖了屋顶,盖了大门楼,那栋旧屋瞬间鹤立鸡群,高大上起来。
我们一家去给她温锅。那天,她家来了很多亲戚,摆了好几桌。我看见她的亲哥哥亲嫂嫂侄子侄女来了一大群。菜是专门从镇上饭店订的,她来来往往穿梭敬酒,满脸红光,接受着人们的祝贺,脸上的胎记也闪耀着光泽,好似一枚胜利的大奖章。
那场酒喝了半天才散场。
返回的时候,爹喝了酒,坐在金花的自行车上,我骑车载着弟弟小海。金花一路闷闷不乐,怅然若失,嘟哝,“她真是走了狗屎运,这日子眼看着都比咱家强了,要不我也去上海当保姆?”
爹在后面奚落她,“眼红了,是吧?你能舍得我和孩子,一走好几年?”
金花不吭声了,赌气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很快就把我落下一大段。
高三时,我参加了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拿了一等奖,寒假被选中去上海参加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金花说,“你丑姨在上海,你去找她呀!”
我嗯了一声,心想我到哪里去找丑姨?丑姨只说在上海干保姆,究竟在哪里干保姆,她从来也没告诉我们,我们并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我问建辉,能联系到他娘吗?他也摇摇头。
我随着海潮一般的人流走出火车站。上海的冬天竟然这么冷,潮湿的寒气像一件甩不脱的大衣裹着我,我向下拉拉帽子,遮住半边脸。
走一段就会有乞讨的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残疾人,也有健康人,都衣衫不整,蓬头垢面,有的面前还铺开一张纸,写着不幸的身世遭遇。这是一道奇异的景观,不时有善良的人驻足,放一些钱在他们面前。
那时的我,对这一切充满同情和好奇,对这些可怜人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别样情怀。我不时停下脚步,打量几眼每个乞讨的人,然后放下一块或两块钱。
我又停在了一个女乞丐面前,她蓬乱着头发,埋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的好像有几分熟悉。突然,她脸上的一块青色刺了我一下,我的心无端狂跳起来。她面前铺着一张纸,歪歪扭扭写着一些字,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孩子……
这时,她说话了,还给我磕了一个头,“好心人,行行好吧!”
这声音听起来熟悉又陌生,真实又飘忽,我的心慌乱的几乎要跳出胸膛,我扔下两元钱,逃也似的跑开了。
我一直跑,没有再停下,跑出去很远,我才敢回头,远远的遥望那个跪着的身影。
6
返回以后,我把这件事深深压在心底,对任何人都没有说。我心疼她,我也不想把天捅个大窟窿,因为这绝对是石破天惊的大新闻。
我和建辉都考上了大学。报志愿时,我避开了上海,建辉却一定要报上海的大学,说可以常和他娘见面。
丑姨回来了,依然是打扮光鲜,她塞给我一个二百元的红包。当时那绝对是一个超大的红包。我坚决不要,红包推来推去,丑姨最后都变了脸。
“是不是嫌少?是不是考上大学就不认我了?”
金花在一旁说,“你别给小雨了,我们也不给建辉了,两家兑了。”
“我一定得给小雨,小雨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亲。”她把红包硬放到我的书包里。
我心里很不安,眼前恍惚出现了上海火车站那个跪着的女乞丐,我的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难受。
我忍不住问,“你在上海哪里干保姆啊?我以后去上海,找你去啊!”
丑姨说出了一长串名字,我似是而非的点点头。
读大学以后,我更很少见到丑姨了。一次我在网上问建辉,是否和他妈常见面。他说经常见面,周末如果没事就去看他妈。
“她在哪里当保姆啊?”
“离我学校很远,那户人家挺好的,我去过几次,每次去都住在那里。”
我还想问问别的,譬如那户人家是不是住着一栋小洋楼?但最终什么也没问。建辉不可能对我撒谎,我忽然有点怀疑,或许那天在上海火车站我看错了人?更或许那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天下脸上长青色胎记的人不止她一个吧?
大四那年,偶然机会我到上海实习,便告诉了建辉。一路走出火车站,我特别留意路的两旁,奇怪,一个乞讨的人也没有!那道曾盛大的风景竟杳然无踪迹了。五年前,就是在这里,我看见了她,跪在那儿,还给我磕了一个头。
有人喊我的名字。是建辉,他来接我了。为了见他,我特地化了妆。见到他,我心里流淌着一种别样的感情。我心里明明是喜欢建辉的,但我却不漏痕迹的拒绝了他。只有我们两个人明白,我们之间曾悄悄开始,又悄悄结束了。
大学报道之前,金花很严肃地同我谈了一次。我和建辉之间的丝丝缕缕瞒不过她的火眼金睛。她说我可以在大学里谈男朋友了,但不许我和建辉有多余的瓜葛,因为我和他是表兄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她也不想让村里人讲闲话。
“小雨,你找谁都行,就不能找建辉,我可不想和你丑姨成亲家,姊妹本来好好的,成了亲家就成了仇家。”金花顿了顿了,放慢了语速,“再说,你丑姨那样的人家,怎么能配上我们家呢?”
这才是金花说的重点,她在心里,其实还是看不起丑姨的。她从小就压她一头,不屑与她做亲家。
我本来不是对金花言听计从的孩子,但这件事我却依从了她。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自从在上海火车站发现了那件惊天秘密,我对建辉竟生出了一种不明不白的怨恨,这种怨恨使我对他爱答不理,渐渐远离他。都是因为他,如果不是他,丑姨怎么可能吃这么多的苦?说到底,建辉又不是她的亲儿子!
7
建辉带我去见丑姨。是一座挺大的房子,里面收拾的光亮鉴人,一尘不染。我恍然,这虽不是她曾经信上说的小洋楼,条件也不错。
几年不见她了,她的气色很好,脸上的胎记看起来淡了许多。
丑姨欢喜的上下打量我,“小雨,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么漂亮了。”
主家是一位颤巍巍的半痴呆的老太太,见了我们,笑了笑,指着沙发让我们坐。
“我外甥女,小雨,在广州读大学,马上毕业了。”丑姨大声说,一脸自豪。
老太太又笑笑,呃呃两声,估计耳背,没有太听明白她的话。
丑姨拿出水果招待我,说这些水果都是老太太的女儿买来的,她女儿很孝顺,隔一天来一次。
我和丑姨说着闲话,门一响,一个打扮时尚化着妆的女人提着菜进来了。是老太太的女儿。丑姨又一脸自豪地介绍我。
女人笑笑,“菊姐,你外甥女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们说说话,晚饭我来做。”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菊姐是谁,有点发蒙,好一会儿才想起丑姨的大名叫孙金菊。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人们只知道她叫孙金菊,不知道她还有个小名叫丑。
丑姨赶忙站起来,“我的客人怎么能给你添麻烦呢?我是保姆,晚饭当然我来做。”她三下五除二就把老太太的女儿从厨房推出来。
女人对我和建辉无奈的笑笑,她走到老太太身旁,坐下来。我和她随意聊起来,她满口夸奖丑姨。
“我妈多亏了菊姐照顾,菊姐刚来时,我妈的腿几乎不能走路,现在,我妈都能走几步了,多亏了菊姐不嫌麻烦,时常牵着我妈练习走路。”
“我姨在你家几年了?”
“四年多了吧!”
我心里一震,不敢再问下去。
饭后,老太太的女儿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化妆盒。
“菊姐,我看上次送给你的那盒粉饼快用完了,这是我的化妆盒,我刚买了一套新的,这个就送给你吧。正好你外甥女在这儿,让她教教你。”
我这才明白,丑姨脸上的胎记为何看起来淡了,原来是涂了粉。
她瞅瞅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用那个?”
“你哪里年纪大了?比我才大两岁。”
老太太的女儿走了。临走时,她热情的让我们晚上住下,说人多热闹老太太更高兴。看得出,孙金菊和主家的关系处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我拿过化妆盒,对丑姨说,“来,我给你捯饬一下。”
她的脸忽然红了,说自己丑,何必费那个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按在椅子上。我着重在那块胎记上用工夫,好一会儿,终于完成了。老太太在一旁呵呵地笑,说好看,好看。
我把她推到镜子前,她忽然用手捂起脸,不敢看镜子。我心里陡然一颤,想起多年前她夜里一个人偷偷照镜子的情景。
“建辉,快过来看看,你娘漂亮了吗?”我冲在外面看电视的建辉喊。
建辉跑过来,嘻嘻哈哈搂着他娘笑,说好看好看。
第二天我和建辉回去时,走过一条小街,对面走过一个女人,穿
的很破旧,伸手向我们要钱。我拿出钱想给他,被建辉一下挡回去,“假的,别给,都是骗子。”
我随意问了一句,“怎么路上不见乞讨的人了呢?四五年前,我来上海时,火车站那儿一路都是跪着乞讨的人!”
建辉笑笑,“那都是些职业乞丐,这几年市政府整顿市容,听说都驱赶回原籍了。”
我呃呃两声,“那些人也有真可怜的,要不谁愿意蓬头乱发的干这个?”
建辉哼了一声,“傻瓜,你懂什么,乞丐那都是装的,人家比我们都有钱。”
我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娘在上海呆了十年,她一直干保姆吗?”
“我娘没文化,只能干保姆。”建辉点点头。
“难道你就没有想想,你娘在上海这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她都是为了你,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
建辉惊讶的看着我,我再也忍不住,便把几年前看到的那一幕告诉了他。
他直直盯着我,然后脸渐渐变了形,他愤怒地望着我,大喊,“你看错了,你一定是看错了,那个人不是我娘,那个人不可能是我娘。”
他丢下我,趔趄着向前跑去,但我听出来,他哭了。
父亲去世,继母打工赚出巨款,多年后知晓她钱来源我哭出声
8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城市,成了一名教师。
金花哭着闹着让我必须回来找工作。她说,离家近,她来去才方便,她才能沾上光。她还说,弟弟小海以后指望我,我可不能一翅子跑没影了。弟弟小海不是学习的料,没考上高中,上了职高。金花说让他在职高长长身体,再找工作。
建辉也回来了。当初,也是他娘让他一定回老家工作。他娘说,在外面风光了有啥用,只有在老家风光了才叫风光,十里八里的乡亲才知道。建辉很听他娘的话,但也坚决把他娘从上海带回老家,不许她再当保姆了,说她愿意当保姆,就给他当保姆,他给她发工资。
建辉混的不错,在市政府工作,很快就提了干,前途一片大好。翠妞也考上了大学,丑姨的日子舒心的很。村里很多人找建辉帮忙,丑姨很是光彩体面,她家的人来往不断。
金花有时来城里看我,口吻很酸地对我嘟哝,“你看看人家建辉,多风光,你丑姨的日子可比我好多了,想不到,她这么好命。”
“建辉再好,也不是亲的。”我说。
“她长那么丑,还化妆,我是你亲娘,你怎么不教我?”
“你长的那么漂亮,不需要化妆。”我怼金花。
我去看丑姨时,便教她化妆,慢慢的,丑姨在家也会简单化一下,金花妒忌的要命。以后,我只好给她买了一套化妆盒,但我从不教她。
有一天,金花忽然问我,“你丑姨说建辉还没有对象,他怎么还不找?”
我瞪了她一眼,“你关心人家干什么?人家又不是你的亲外甥。”
她又小心翼翼看我一眼,眼神闪烁,“建辉可真是好孩子,知根知底的,他和你可没血缘关系。”金花可能早忘记了几年前警告我的话了。
我不理她,但心里很高兴。其实,我和建辉又偷偷谈起了恋爱,不过瞒着金花和丑姨。
那一天,我和建辉陪着丑姨去公园玩。路旁,一个男人拄着拐杖站在路旁,一脸茫然,他的一条腿没了。丑姨看了几眼,指指那个人,问建辉有钱吗?
建辉明白了,拿出钱走过去,一会儿,他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哭笑不得,“娘,人家很生气,人家不是乞讨的。”
丑姨尴尬的笑了。我和建辉也对视一眼,笑了。那个秘密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原标题:《丑姨》)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