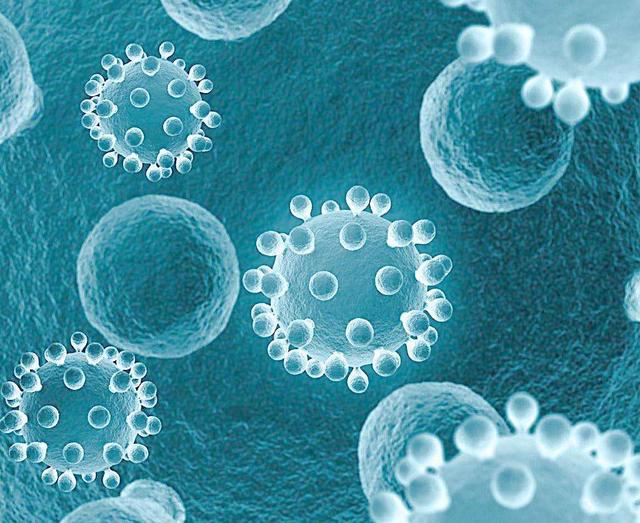京韵简介(京城京韵慢慢读)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一座极普通的四合院里。两扇红漆大门坐北朝南,门槛尺把高,每当黄昏,我常坐在上面边吃铁蚕豆,边看路上的人来人往,看算命瞎子吹着笛子幽幽地走过,看出殡的队伍去十字路口烧化纸人纸马。

进了大门是一个宽敞的门洞,两边摆放着六尺长的大门凳,娘说是柏木的。门洞是孩子们的游戏场。每当我们在屋里闹得太厉害时,大人就说:“去,门洞里玩儿去!”我们就一窝蜂地跑向门洞,那里是我们的自由世界,怎么闹大人也不管。门洞也是全院女人夏日午后纳凉的场所,她们坐在大门凳上聊天,纳鞋底儿,享受着像凉水儿一样的穿堂风。有大人在,我们玩耍的内容就变了,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叫卖声。五月的大樱桃,晶莹得像红玛瑙,碧绿的荷叶托着,那是必得让娘买来吃不可的。香喷喷的煮老玉米,清凉凉的甜瓜酥瓜,推车叫卖的扒糕凉粉……哪一样我们也不肯放过,只是娘有时不给买,说是怕吃了拉肚子。
穿过门洞,迎面是白色的影壁墙,左右两边各是四扇绿色的屏风门。拐进左边的屏风门,是长条形的外院,一溜五间南房,由南屋二姨一人住着。听娘说她是东北一位军阀的二小姐,所以叫她南屋二姨。
南屋二姨住的外院因是长条形的,所以总是阴凉凉的,我们很喜欢在那里跳房子。外院和里院之间有一道花墙隔着,所谓花墙即一道砌成十字镂空花样的灰砖墙。花墙中间是中门,穿过这道门,就是青砖墁地的里院了。
一进中门,满眼都是绿,都是花。南墙根一溜四丛玉簪花,爸爸说玉簪花喜欢阴凉,宜种于南墙下。但我却没见它开过几次,只是叶子总翠翠地绿着。中门两边是两个八角形的花池子,每年春天娘在里边种两架扁豆,吃一夏。有时也会爬出两棵丝瓜,嫩黄的花,正好掐来喂蝈蝈。丝瓜是没人吃的,秋天长得老长老长,瓤子用来刷碗。
爸爸爱养花,院子正中是爸爸的天地,五个巨大的水缸扣在当地,上面是五盆荷花,荷花缸里悠游着金鱼。周围是石榴、美人蕉、昙花、令箭,一片嫩黄浅红,灿烂夺目。爸爸的花,从不许我摘。我只与其中的一种果子有点缘分,就是莲蓬。夏天,下着小雨,爸爸常会折一只大大的莲蓬给我,我就会美美地坐在檐下的台阶上,细细地剥来吃。
院子东北角有个角门,穿过角门是后院,仅有一间小平房。这间小屋早先我家堆放旧家什用,后来房子粉刷一新,我和上中学的姐姐搬进去住,成了我们的卧室兼书房。屋前一棵桃树,据说是生我那年爸爸从白塔寺买的,买时说是水蜜桃,可到秋天结的果子却是小毛桃,根本不能吃。
桃树长到三尺高的地方分成了三岔,我喜欢爬上去坐在那里看书,遐想。每到春天,粉白的桃花落满一地,落满小屋的屋顶,我常常攀着树枝,跳到屋顶上,躺在柔软的桃花上面晒太阳。蜜蜂嗡嗡地飞着,太阳暖暖地照着,我闭上眼睛仍能感觉到周围都是美丽的桃花,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候。
有一年,哥哥从学校里带回来两只小黑兔,蓝蓝的眼睛,十分可爱。我把它们养在后院,不久,发现它们自己在地下打了洞,晚上不必再由我捉来放进木箱了。娘说它们的洞里东暖夏凉,比在木箱里睡要舒服多了。冬天时它们已经长得很大了,常常去啃桃树的树皮吃,我喜欢蹲在旁边看它们啃,惊异于它们牙齿的锋利。
第二年春天,是我盼望的桃花盛开的时候了。可是这一年,我家的桃花却没有开。我折下一根枝子来看,发现竟是干的。拿给娘看,娘说桃树死了。它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不久,它就被砍掉了,土也被抹平了,可是我却无法把桃树的死从心中抹去。多年之后,有一天在植物课上,我突然明白,肇事的凶手竟是那对小黑兔。是它们围着树根啃光了半尺宽的一周遭树皮,哪怕上下还有一处连通着,桃树也不至于死掉。许多年,我为桃树的死深深地悲哀着。

后院南墙上有一小门,通临街的跨院,院中有南房三间,住着修车的郑大伯一家。一进大门,拐进右面的绿色屏风门,就是这个跨院。所以我们藏猫猫或是逮着玩儿,常把大门洞当“家”,从左边的绿色屏风门跑进去,转一圈,从右边的屏风门跑出来,就到“家”了。
我家正院里有西房两间,住着西屋奶奶,东房两间,住着东屋大姨。北房五间我家自住着。“西屋奶奶”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称呼,一是因为她住西屋,二是因为她的年纪足以当我的奶奶,于是全院的街坊,不论男女老少,都随着我尊称她为“西屋奶奶”。
西屋奶奶一张四方脸,天庭饱满,地葛方圆,高身量,腰板挺直。一双小脚,干净利落,走起路来绝无忸怩之态。院里人都说她厉害。娘说:“西屋奶奶厉害是厉害,可厉害的是地方,不瞎厉害。”
西屋奶奶的独生儿子长得很高,很英俊,外号大个儿,是蹬三轮的,我顺理成章地称他西屋叔。据说他媳妇原来是窑子里的。他给一户有钱人家拉包月,恋上了这女人,没钱赎,正犯愁。主人知道了,笑着说:“今晚上的牌桌你好好伺候,包你连娶亲的花销都有了。”于是这女人就稳稳地坐在了他的炕头上,为他洗衣做饭,伺候老太太。
西屋奶奶很不待见这媳妇,听说她当年坚决不准这媳妇进门,跟儿子说:“你幼年丧父,我把你拉扯大不易,你现如今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了,咱们虽穷是清白人家,不能要这种烂货。”可儿子一门心思非娶不可,不让娶就不吃不喝,那么硬棒的汉子,愣是一病不起。老太太终是疼儿子,无奈,让儿子把那女人唤来,约法三章:一是永生不许和窑子里的人来往;二是戒烟戒酒;三是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老老实实操持家务。女人跪在地上流着眼泪发了重誓,才名正言顺地进了门。住到我家院里后,我们叫她西屋婶儿。每逢和娘谈起这媳妇,西屋奶奶依然是满脸的不屑。娘说:“看样子还老实,整日不出屋,只是做活。”西屋奶奶扇着鼻翅:“那是有我压着。没了我,你再看。”
西屋奶奶没有孙儿绕膝,这自然也是她对儿媳厌恶的一个重大原因,但她膝下并不寂寞,因有一花猫绕足。猫是黑白花,很胖,呆头呆脑,对谁都不理不睬,俨然一副衙内派头,唯对主人媚态十足。西屋奶奶盘腿往炕上一坐,拍拍腿,叫一声:“来,花子!”它便爬到腿上去,倒头便睡。西屋奶奶把它当成心肝宝贝,每天必去街口专为它买五百块钱(相当于现在五分钱)肺头,回来切碎,放在小锅里,与米饭一起煮了,晾凉,然后高一声,低一声,抑扬顿挫地喊着:“花子——花子——”于是胖猫或从台阶,或从墙头,懒洋洋地走来,吃它的美餐。那是真正的美餐,每当西屋奶奶在院子里为她的花子做饭,闻到那诱人的香味,我都要流口水,而我的黄猫是绝无此福气吃到如此奢侈的饭食的。
娘说黄猫和弟弟同岁,是只五岁的猫了,精瘦,从来没人专门喂它,我常奇怪它靠什么活着。它和我最要好,只要我一喊:“黄儿黄儿黄儿黄儿——”不管多远,不管在树上还是在房上,必是急颠颠地连声答应着跑来,抬头喵喵叫着,问我叫它来干什么。我常常只是因为半天没看见它了,并没什么好吃的给它,于是把它抱起来亲热一会儿。夜间它必是要和我同睡的,如果来晚了,我已睡着,黑暗中,它先是用头蹭我的脸,如果还不见我打开被,就用力拱进去;有时我想睡了,它还在玩儿,我把它捉来硬塞进被里,它也没意见,而且很快会打起呼噜。
自胖衙内来了以后,我很为我的黄猫感到不平,以至于对花猫多了几分鄙视。一次,胖衙内不知去哪里打架,腿上带伤,一瘸一拐地回来,把西屋奶奶心疼得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天,非说有人和她过不去,成心治她的猫。我却心中暗喜,知那必是吃了败仗的标记。西屋奶奶从娘那里讨来220红药水,给胖衙内染了半条红腿,捧在炕头,那样子委实滑稽。院里人无端被疑,皆迁怒于胖衙内,从此它在院中很没人缘。

西屋分里外两间,原是我家厨房,所以外间有自来水管子。西屋叔和西屋婶住里间,老太太住外间,迎门靠墙是她的床。左边靠着隔断是水龙头,龙头下是个大水缸,上盖半个缸盖。每天全院的人都要来此打水,桶快满时,水珠喷溅,常常会弄湿地面。西屋奶奶爱干净,每天都要用炉灰扫几回。我去打水时,娘常嘱我龙头要开得小些,把桶从缸盖上提下地时,要小心,别洒地上水。可是因为每天打水的人多,依然要把地面弄湿好几遍。修车的郑大伯想了个主意,剪了一段修车剩下的自行车内带,用铁丝捆在水龙头嘴上,车带垂入桶中,再也不溅出水来。喜得西屋奶奶见人就夸郑大伯心灵手巧。
郑大伯一家四口,在街口摆了个车摊,以修车为业。郑大伯修车时爱吹口哨,京剧、评剧、流行歌曲全会。吹得悠扬婉转,荡气回肠。郑大伯的手很大,粗糙得像钢锉,却无比灵巧,能用纸折出各种玩具,能用玻璃丝编出各种花朵。我上小学时,老师让用高粱秆做手工,我做不出,急得哭。郑大伯知道了,笑嘻嘻地说:“这还不好办?拿高粱秆来!”于是不过半点钟,一张漂亮的小方桌就摆在了我面前,桌面还是用编席子的花纹编出来的,拿到学校立刻被老师留下放进了展览窗。
西屋奶奶也爱养花,但她养的和爸爸养的花不同,她只种茉莉花和指甲草。在西屋窗前,围着扁豆架,种了满满一地。茉莉花摘下来,抽去花蕊,可以当小喇叭吹,结的花种,像小地雷,掰开来,里面有香喷喷的白色粉末,西屋奶奶说收了来可以当白粉擦脸。我往脸上抹过,白倒是白,但只能抹出一道白,于是就不再抹。娘说那不是真正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放在茶叶里的那种小白花,清香扑鼻。可西屋奶奶这样叫它,说这就是茉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它的花香有点像茉莉的香味,所以人们叫它草茉莉。

说心里话,比起爸爸的花来,我更喜欢西屋奶奶种的花。每当黄昏,红黄粉白,如云如霞,蔚然一片,开满半个院子,让人心里说不出的喜欢。爸爸的花是从不许我摘的,爸爸的花我也不敢摘,因为摘一朵就看得出来。西屋奶奶的花就不同了,每天晚上开几百朵,第二天早上就谢了,虽然西屋奶奶也不许我摘,但我摘多少她也看不出来。于是我常常采了拿到大门口去玩儿。
一天晚上,刚刚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西屋奶奶说这时采下的茉莉花放在注满清水的盘子里,摆在床头可以香一宿。我乘机说:“让我也试试好不好?”西屋奶奶竟然点点头说:“行。”我大喜过望,于是采了满满一大茶盘,放到床头。清香倒是没有闻见,因为黑甜一觉,醒来已然天亮。但是有花伴着睡觉,心头那份痒痒的喜悦,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
但我对西屋奶奶还是腹诽的时候居多。每天早上,西屋奶奶都把西边的半个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去后院把厕所也扫得干干净净。娘说自西屋奶奶搬来后,厕所就再没脏过。可是我若扔地下一张糖纸,她就会说:“莲,把糖纸捡起来,别弄脏了院子。”我心里说:“多管闲事!”却不敢不捡,因为娘不许顶撞奶奶。我家人口多,洗衣做饭里里外外全靠娘一人忙,她便时常帮娘干活。她帮娘择韭菜,见我玩儿,就说:“莲,过来,帮你娘择菜。”我心里自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也只好乖乖地去干活。
娘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像炸馓子,搂瓜子,蒸花糕等等,都会让我先给院里各家街坊送一盘去,然后再自家吃。干这种小跑我是最高兴不过的,总是能听到许多感谢的话,有时还能在口袋里装回糖果之类一人消受。街坊们做了好吃的,也常常给娘送来。别家送来,娘立刻给我吃了。可西屋奶奶送来的东西,就很难到我嘴里。
西屋奶奶做的拉面又长又细,配上腌胡萝卜切成的碎末和煮青豆做的菜码,红白之间杂着碧绿,又好吃,又好看。她每次做了都给娘端来一碗。起先她一出屋,娘就给我吃了。后来她再端来时,就坐着不走,一定要看着娘吃下去,尽管我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却只装没看见,坐着,慢悠悠地说:“三奶奶,你吃,别光顾孩子。”
娘看我那馋馋的样子,哪里吃得下?但又不愿负了西屋奶奶的一片心,只好慢慢吃着。西屋奶奶看娘吃到只剩两三口时,才瞥我一眼,像得胜的将军一样,挺着脊梁,走出去。真恨得我牙根疼。
我家的四合院在扁担胡同,这条胡同虽短,但并不窄,且铺着柏油,胡同两端是两个十字路口,像挑着一担东西的扁担,这大概就是扁担胡同的由来吧。胡同里常有汽车穿过,但很少有驻足的,因为胡同里住的全是平民百姓,没有贵人。那年突然有辆吉普车停在5号门前,立时就在胡同里传开了。大家纷纷从院中走出,围拢去看究竟,原来是5号的小七子偷东西犯了案。

我家住胡同里的3号,东边的隔壁2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原来住过一家日本人,再后来是鲍老太太一家住着,鲍老太太八十多岁,十分慈祥。那年十月,正是小阳春天气,忽然听说鲍老太太院中的一棵西府海棠开花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成了胡同里的奇闻。过了一会儿,又听说树上系了红绸子,大家争相去看。我也随着娘过去看,花开是开了,但并不旺,只是那大红绸子鲜亮无比。鲍老太太坐在廊檐下的太师椅上,高兴地看着大家来看花。看见我,连忙进屋,抓了一大把糖炒栗子出来,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回来后,我问院里的大人,为什么海棠冬天会开花,为什么树上系红绸子,院里人自然没有贾政的识见,说不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那样潇洒的话来,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还是西屋奶奶积年有识,说:“冬天开花,邪性。系块红绸子,辟邪呗!”不知红绸子是否真的辟了邪,反正那一年鲍老太太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若干年后,才在院中病逝,但那是属于寿终正寝。
鲍老太太院中的这棵西府海棠在我家北房后头,每年春天,数枝海棠出墙来,垂在我家北房的瓦垄上。爬上花墙,从西房绕到北房上,就能采到花枝。我常偷折数枝,插在水罐里,喜滋滋地看几天。西屋奶奶爱花,见我折了就来要,娘总是叫我挑好的给西屋奶奶送过去,我心里自是老大不乐意。娘说我不懂事,对奶奶不能那样。
那年春天,我正在爬花墙,二土哥来了,说:“你怎么这么淘,又上房。”我说:“你没见海棠开了吗?我去折几枝。”二土哥看了看墙头上探出的浅红深绿,说:“等着,我和你一块儿去。”
二土哥是东屋大姨的独生儿子,长得浓眉大眼,那年他二十,我九岁,但他和我很平等。他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了。他爸爸年轻时懂电,咱们的队伍上缺这种人,地方上一动员,他爸跟上队伍就走了。那年他14岁,听说后,一溜烟地追了去,成了队伍上货真价实的父子兵。一解放,就转业到地方当了话务员。他最爱回忆的“老革命”历史就是吃瓜。他说:
“夜里,去执行任务,渴了,看见西瓜地,爬进去,捡大个儿挑,吃个够。”
“那,有刀吗?”我想,我们家吃瓜,都是放在桌子上拿刀切成一牙一牙地吃的。
“嗨!要刀干什么?拳头,一拳头下去,啪!砸开,抱着吃。”
“给不给人家钱?”我想解放军是讲三大纪律的。
“给。带着钱呢,就拿块石头压在地边。没带钱的时候也有。那,吃了就走。”
“你们白吃人家东西?”我认为二土哥做得很不光彩。
“那有什么!老百姓才不在乎。过路人渴了,吃个瓜算什么?老乡还自动给你拣大个挑呢。只要你不偷走,吃了瓜把瓜子儿给留下,要吃瓜,管够!”
我最爱吃西瓜,可我家难得买一次。偶然买一次,切成十多牙,全家八九个人吃,还没尝出西瓜味儿来,就没了。我真羡慕二土哥的“老革命”经历,恨不得也早生几年,去当这样的吃瓜小兵。
每年春节,爸爸给我们压岁钱,也总有二土哥一份。其实压岁钱只有二角钱新票,但他很高兴。我问爸爸:“二土哥那么大了,还要压岁钱?”爸爸笑着说:“没娶媳妇,就是孩子,就有一份。”
二土哥和我很要好,从不拿大人架子。他说要和我一起去偷海棠,我自然高兴。我们爬上花墙,很快转到北房上,我先探头,看了看院里没人,就和二土哥翻过屋脊,采了满满一大把花,兴奋异常地从北房转到西房上,准备从花墙下去。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脚底下的西屋奶奶,懊丧地问二土哥:“她要怎么办?”二土哥问:“谁?”
“西屋奶奶呀!”
“你想不想给她?”
“不想。”
“那就别给。”
“她要要呢?”
二土哥想了想说:“别叫她看见,咱们一下去,你别把花往北屋放,马上拿到后院你房子里养起来,不就得了?”
我听了大喜,从花墙上下来后,抱着花,一溜烟地跑向后院,头也不敢回,生怕西屋奶奶看见。我和二土哥进了小屋,一边喘气,一边惊喜地看着桌子上的那一大把花。二土哥叫我找个花瓶养起来,我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么大的,他就回家找了个煮药的药罐,装了清水,把花插进去,倒也别有情趣。我突然担心地问:“西屋奶奶会不会看见咱们了?”二土哥说;“不会。西屋门关着呢,我特意看了。”
“每年我采了,她都要。”
“这老东西,什么好就想要什么……”
二土哥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窗外有响动。他立刻向我摆了摆手,叫我别说话。我俩尖起耳朵听着窗外,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二土哥小声说:“你出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
我小心地推开门,向外张望。小屋有扇南窗,糊着白色高丽纸,与女厕所之间有条一米宽的夹道,若从厕所出来人,定能听见我们屋里的谈话。可我看了,夹道里没人,厕所里也没人。回来对二土哥说:“没事,人影子也没一个!”我俩立刻放声大笑起来,以为自己吓自己,虚惊一场。
突然娘推门进来,说:“你们怎么为几枝花,把西屋奶奶气成那样!”
我们大吃一惊,说:“没有气她。她怎么了?”

娘说:“她哭呢。见你们采了花,她就跟过来,想要几枝。还没进门,就听你们在屋里骂她老东西。她找过我去,说:没想到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倒变成老东西了。你们怎么能这么骂奶奶呢?”二土哥听了只是搓着手嘿嘿地笑。
娘说:“还不把花给你西屋奶奶送过去!”
我拿起花,不敢去,怕挨西屋奶奶的骂。娘说:“有什么不敢的?认个错不就行了?”
我一步三挪地走进前院,心怦怦直跳,怯怯地推开西屋门,见西屋奶奶正盘腿坐在床上,腿上趴着胖猫。我说:“奶奶,给你花。”我正等着她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没想到她却温和地说:“插到胆瓶里吧。”
西屋奶奶的房间里,靠北墙一张大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擦得亮得照得见人。条案正中摆着一架座钟,二尺多高,罩着玻璃钟罩。两边是两个白瓷胆瓶,上有观音送子图样。西屋奶奶说这些东西都是她年轻时的陪嫁,说时颇有骄矜之色。这些东西她从来不让儿媳动,都是她亲自擦。我往胆瓶里插海棠花时,见里面早已注满了清水,原来她隔着窗子看见我抱着花往后院跑时,是准备好瓶子,诚心来向我讨几枝的。我心里立时惴惴地,觉得很对不起她,想说一句道歉的话,却说不出。
西屋奶奶见我插好了花,就下地从锅里拿出一个热腾腾的糖三角,给我,说:“玩儿去吧!”我如逢大赦,飞跑出屋。此后,对西屋奶奶很存了一段好感。
西屋奶奶的儿媳——西屋婶,个子矮小,皮肤黑黄,见人总是顺着眼,从不高声说话。她确实不好看,我总奇怪那么英俊的西屋叔,当初怎么会喜欢她。可西屋叔确实对她很好。她整天在屋里做活,绣衣服,为厂家绣的,按件得钱。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送活时才上趟街。
我喜欢看她绣花,她绣得并不好,大多是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之类,但我喜欢看。见我来,她很高兴,我让她给我讲故事,她就给我讲赵五娘寻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苏三起解。
我回家去喝水,娘在缝衣服,西屋奶奶正坐着和娘聊天。见我回来,西屋奶奶撇撇嘴,问:“又跟你瞎叨叨什么呢?”我说:“给我讲故事呢。”西屋奶奶扇着鼻翅:“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她能讲什么故事!”我理直气壮地说:“杜十娘,苏三,挺好听的!”
西屋奶奶转脸向娘,说:“三奶奶,你听听,给孩子讲这个!”娘说:“这倒也没什么,也难为她,整天在屋里干活,也没个人说话。有个孩子听她说,也解解闷儿。”
西屋奶奶说:“她那个拜把子姐妹从良嫁了个铁匠,前两天来看她,她又翻出那时候照的戏装,挂在墙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也不嫌寒碜。叫我骂了一顿,昨个才收起来。”
怪不得呢,前几天我见西屋婶墙上挂了张大照片,一个身穿古装的女子,手托花篮,十分好看。我连问西屋婶那是谁,西屋婶说是她。我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墙上那水灵灵的女孩儿和灰黄的西屋婶联系起来。我羡慕得不得了,我问她谁给她梳的头,谁给她的衣服,在哪里照的等等。西屋婶什么也不说,只问我好看不好看?我连说好看,她很高兴。但今天去看,墙上已没有了照片,我问她为什么不挂了?照片哪去了?她说收起来了,过些日子再挂。原来是西屋奶奶不让挂。
我家西边隔壁是4号。4号院子很大,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主人是孟大伯。孟大伯身材高大,脸总是阴沉沉的,我从没见他笑过。他和爸爸时有往来,谈养花。他家养有一只狼狗,常见孟大伯穿着蓝布长衫,倒背着手,直直地站在门口的高台阶上,狗必立其旁,一人一狗,一高一矮,能半天不动,像塑像。那狗看样子厉害,却从不伤人。常见它叼个篮子,里边放着钱,去买菜。菜店的伙计都认识它,见它闻闻什么菜,就收起篮子里的钱,把菜装进篮子里,它就叼着小水萝卜、小白菜之类的菜肴,颠儿颠儿地跑回家去。
孟大伯有三个儿子,他管孩子极严,三个儿子全怕他。最小的儿子连生和我年龄相仿,我们常在一块玩儿。一次,他约我去他家园子,他家园子比我家后院大多了,里面有两棵枣树,一棵大尖枣,一棵大圆枣。那时正是八月中秋枣落杆的时节,连生望着红了圈儿的大尖枣对我说:“这尖枣可甜了,你别看圆枣长得个大,个个是愣头青,木得很,也不甜。”

当时我家的枣树已经锯掉,听了连生的话,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打下来吃?”
连生说:“那不行,我爸爸不许随便打,谁要是不等熟了就摘着吃,准挨揍。得等熟了,我爸让打时,再一次打下来。”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回头看了看我,说;“你想吃吗?”
我说:“想。”
他说:“我上树给你摘点儿。”
我说:“你不怕你爸爸揍你?”
他想了想说:“我上树,你去园门口望着,一有人来,你就喊我下来。”
我兴奋异常地跑到园门口,正在守职地向外张望,忽听连生喊道:“过来,接着!”只见他像猴子一样站在枝头,不断地摘了大尖枣向下扔着。于是我又兴奋地跑回来,一个一个地拣着地下的大红枣,边拣边吃。连生在树上不停地喊着:
“又一个红的!又一个大的!接着!”
这时忽听一声断喝:“还不给我下来!”
我俩大吃一惊,全吓呆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孟大伯正铁青着脸站在我身后,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生吓得已听不懂他爸爸的话,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蹲在树上。
只听又一声断喝:“还不给我滚下来!”
连生这才苏醒过来,立刻像上足了发条的木偶,手忙脚乱地滚下树来。我胆战心惊地等着看连生挨揍,等了半天毫无声息,我壮起胆子回头一看,见孟大伯早已走了。
连生从地上爬起来,抹了抹脸上的汗,我忙过去帮他拍身上的土,以赎我失职造成的后果。
我问:“你爸爸怎么没打你?”
他说:“不知道。”又说:“也许是因为有你吧。”又壮着胆子大声说:“没事,咱们吃枣。”于是我们又高兴起来。
傍晚,娘在院里摆好小饭桌,正要吃芝麻酱凉面,只见连生兴冲冲地提着个鼓鼓的大书包跑进来,说:“我爸爸叫我送来的,给你们吃。”原来是满满一书包大尖枣,我乐得手舞足蹈。娘叫连生和我一起吃面,开始他还不肯,后来就不客气了,我俩比着吃,每人吃了三大碗。
我家有许多书,都是爸爸上大学时买的,我最喜欢乱翻着看,《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之类我是不看的,因为看不懂,但也时时能像发掘矿藏一样翻出我爱看的书来。有一段很迷陈端生的《再生缘》,一函二十册。那是看到第十二册的时候,我正坐在大门洞的长板凳上,边吃刚买来的云豆饼,边看书,忽然同学来找我去学校。我懒得把书送回屋,于是就踩着门背后的横木爬上门顶,把书放在了固定门轴的横板上。我经常这样爬上大门,因此发现了门顶上的这个秘密所在。心想这真是个藏东西的好去处,任谁也不会找到的。
那天傍晚,我从学校回来以后,急急地爬上大门去拿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书竟不翼而飞。我正看到孟丽君当了宰相,要约见皇甫少华的有趣之处,书却丢了,懊恼得饭都吃不下。我问遍了常和我一起玩儿的小孩儿,都说没见。三天过去了,我已完全失望,正坐在大门洞里发呆,街口膏药铺的小生子来了。这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儿,五岁,比我小四岁。我觉得他太小,不会拿我的书,所以没问过他。这天他跑进门洞来玩儿,我百无聊赖,无意问了一句,他竟然说:“见了。”
我陡然升起无限希望,忙问:“书呢?”
他说:“撕了。”
我大吃一惊:“你干嘛要撕?”
他说:“撕了纸包煮豌豆。”
我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但还怀着最后一点希望:“全撕完了?”
“还剩几张。”
“把剩下的给我拿来!快去!”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飞跑出大门。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大声说:“给你!”然后吮着手指头得意地望着我,好像为我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接过那仅剩了十几页的书,兴奋不已,摸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摸出两分钱,请小生子吃了牛筋豌豆。
有一阵子我迷唐诗,那天拿了《唐诗三百首》在大门洞里读,西屋叔恰在那里修他的三轮车,问我:“你咕咕哝哝的,念的什么书?”
“《唐诗三百首》。”我说。
他抬头看了看我,笑着说:“这么深的字书,念得下来?念一段我听听。”
我说:“行。”于是就翻到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说:“我能背给你听。”西屋叔说:“那你就背。”我就一字不差地背了下去:“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完了。”
西屋叔听了连说:“不错,不错,背得挺顺溜。可这诗说的是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出来呢?你会背,会讲么?”
我说:“这有什么难的?这说的是两个朋友……”刚讲了一句,就卡了壳,因为我不明白“动如参与商”的意思。心想,反正他也不知道,不懂我就跳过去,拣明白的给他讲,就接着说:“是说两个老朋友,二十年没见面了,这次一个来看另一个。分别时他还没结婚,现在儿女一大堆了。”
西屋叔停了手中的活:“诗里还说这个?”
“对,还说主人热情招待老朋友,半夜下着小雨,主人到园子里去剪了韭菜,做韭菜炒鸡蛋给他吃。”
西屋叔听得入了迷:“古时候的人也吃韭菜炒鸡蛋?”
我一下子红了脸,诗里只说了“夜雨剪春韭”,并没说怎么吃的,可我每读到这里,总好像闻到了春天韭菜炒鸡蛋的香味儿,恨不得钻进书里去和他们一块儿吃,因此给西屋叔讲时,不由得把自己的杜撰也讲了出来。我刚想解释,只听西屋叔大声说:
“好诗,真是好诗,还有韭菜炒鸡蛋!莲,你真行,不错!不错!”他惊喜地向我挑着大拇指。此后,逢人便夸我:“莲还懂唐诗呢,小小年纪,真不错!”西屋叔褒奖人的最高级词汇就是“不错”。
那阵儿图画课上老师正教我们画人头,方法是把图画本子上的人头用尺子打上方格,分成若干个小方块儿,再在白纸上打上同样多的小方格,用坐标的方法,照式描画。我认为这个方法很好,回到家里看到墙上的毛主席像,不戴帽子的,觉得很简单,于是爬上桌子,站在上面,把毛主席的脸上打了许多小方格,又拿一张白纸,也打上方格,趴在墙上照画。画好后,觉得不大像,只有毛主席嘴巴上的那颗痣,因为恰好落在方格的十字交叉点上,所以画得很得意。又找来墨,把毛主席的头发染得漆黑。脸呢?配不出那浅棕的颜色,我只剩了一点点黄色,全部认真地涂在了脸上,于是黑发黄面的主席像就完成了。正好西屋叔走来看见,拿起来仔细看了半天,大声说:
“不错,不错,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你看这颗痣,多是地方!”又笑着对我说:“等哪天我有空儿,你也给我画张像。”
我吓了一跳,连说:“不行!不行!”心想,我又不能在你脸上打格子,怎么画呢?可西屋叔说:“行,怎么不行?”

一天傍晚,我和连生正在花池子里挖蚯蚓,西屋叔过来说:“给我画像吧。”
我原以为画像的事说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他还认了真,我哪里会给人画像?立刻急红了脸,连连摇着两只泥手。可西屋叔认定了我能画,说:“你洗洗手,我去换件衣裳。”
过了一会儿,西屋叔来到北屋。呀,简直像换了个人:戴了一顶新的蓝帽子,一身新的中山装,还特意换了一双青布面白千层底儿布鞋。看了西屋叔的郑重其事,我更觉得这灭顶之灾无法逃脱,除了出汗,真是一筹莫展。西屋叔垂手并脚地站好,叫我画。我恨不得拿起尺子去他脸上画格子。而且我只画过脸,没有画过别的,就胆怯地问:“帽子也画?”
“也画。”
“身子呢?”
“也要。”
“脚呢?脚也画?”
西屋叔咧嘴笑了笑:“画,全画!”
天并不热,可我出了满头大汗。终于画完了,西屋叔在画纸上顶天立地,一双大脚紧踩纸边,差点儿就伸到纸外头去。帽子飘在头顶上,用橡皮擦了几次,也无法好好戴在西屋叔的头上。看着我的作品,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西屋叔接过画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我吓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忽见他咧开大嘴笑着说:“是我,大个儿!”然后从兜里摸出一包花生米来,算是奖赏。
我十二岁那年,西屋奶奶的花猫前腿摔掉了环儿,它又胖,连床也爬不上去,心疼得西屋奶奶瘦了三圈。不久,花猫死了,西屋奶奶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岁,再也打不起精神。
我对她说:“奶奶,再养一只猫吧。”
她凄惶地说:“不养了,养伤心了。”

第二年,西屋奶奶也死了。她病时,西屋叔和西屋婶极尽孝心,她生活不能自理,西屋婶天天为她擦身、洗涮。临死前,她拉着西屋婶的手说:“孩子,我委屈你了。别记恨我。”西屋婶哭成了个泪人。
西屋奶奶死后,院里再也没人种“茉莉花”,西屋婶只种指甲草。
(画:冯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