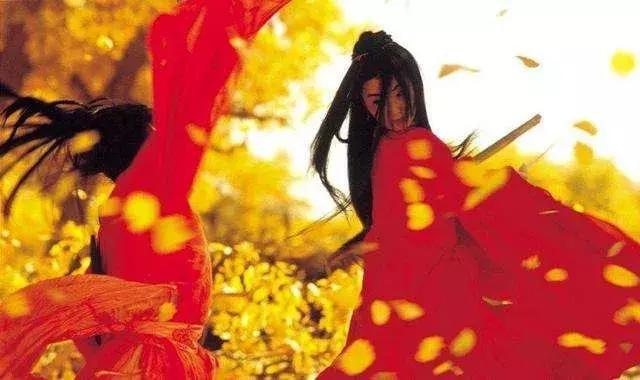著名晋剧鼓师陈晋元简介(谈谈晋剧著名鼓师冯煊)

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在我国戏曲艺术中,如司鼓者不善,则不能导诸器乐协调合作,完美地配合演员之“唱念做打”,完成全剧之演出任务,以感染广大观众。我省汾阳鼓锋剧团之冯煊同志,为晋剧艺术界善司鼓者之一。同行皆称之曰善,广大观众亦甚赞颂,是兼收并蓄,集思广益之名鼓师也。
一、投师与访友
冯煊同志,1925年生于汾阳城小南关,从小热爱戏曲音乐,14岁从师学艺(司鼓),15岁搭班学艺,随师在武场服务,先拜老鼓师张怀礼学艺,继承了该师为人忠厚功底扎实,善于打动弹戏之特长,当张老师上山参加革命后,又拜侯步高老前辈为师,侯原在孝义维风社学艺,曾唱过若干传统剧目,后改坐场面,与演员配台得特好;而后因就业于太原,又拜王德胜为师,继承其谦虚谨慎,与演员唱念做打配合默契之特长。在学艺期间,集张、侯、王三人之艺术与艺德,奠定了他司鼓一生之良好基础。之后在搭班司鼓之技艺,又向赵廷杰(润生师傅)、冯万福、李鹤山、田九云等老鼓师、琴师求教、获益非浅,以至和白晋山、贾炳正、陈晋元等名鼓师及王根寿等舞台老将,及文场名家秦亮、刘柱、杜步信等师傅,长时期地进行研究探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在投师访友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日增月异,渐入佳境。数十年来他在戏曲行业中以老者为师,能者为师,年龄相近者为友,相互学习,携手共进。在戏曲行业中,有“同行是冤家”之说,相互妒忌者有之,明争暗斗者有之,而冯煊同志却是尊重老师,侍之如父母,热爱同行,待之如兄弟,相互切磋技艺,互有所得。此为其突出的艺术与艺德,同行业者爱之敬之,为其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二、实践与真知
他从事戏曲行业数十年中,在太原学艺就业六七年,对司鼓艺术已达到一定深度。但从广度上要求,尚需开阔视野,博采众长。后来转至晋西临县等地搭班,因观众之爱好不同,演出剧目另为一路;如大城市中是在园馆中看戏,多欣赏折子戏,向精尖发展;当然也演些大本戏,艺术上相当讲究。而在山区广大农村,在露天广场演出,注重看大本戏,艺术上要求粗犷、明快、健壮、火爆。本来戏曲源于民间,普及于民间,以广大工农兵之爱好为依归;从进入城市园馆以来,艺术上迫切要求提高,对若干传统剧目,根据观众之欣赏要求面有所取舍,致使戏路偏窄。而广大农村则保留了若干传统大本戏,戏路偏宽。城市中多演《打金枝》或单独演“闹宫”、“劝官”,面农村仍演出《满床笏》;城市中选演“闯宫”、“芦花荡”,农村仍保留全本《回荆州》;城市中选演“藏舟”、“投县”、“洞房”,农村仍演出《蝴蝶杯》;城市中选演“二进官”、“三对面”,农村仍演出《忠保国》;城市中选演《卖画劈门》、农村仍演出《日月图》;城市里选演“探府”、“挂画”,农村仍演出《梵王宫》;以至《薛刚反朝》《三关排宴》、《下河东)、《游西湖》、《大报仇》、《武家坡》等大本戏,仍在保留演出。冯煊同志在临县等山区搭班时,如《战宛城》、《血诏带》、《出棠邑》、《雁塔寺》、《长坂坡》、《药酒记》、《火焰驹》、《血手印》、《明公断》、《金沙滩》、《天门阵》、《破洪州》、《八件衣》、《九件衣》、《北天门》、《忠义侠》、《假金牌》等剧目,仍在较普遍地演出。他深入到戏曲广阔的天地中去司鼓,自己过去未打过的戏,先得拉戏记戏,或向老一辈请教,记熟了戏,才能在演出中马蹄不乱。所以在这一时期,是他实践锻炼,继续丰富自己,艰苦奋斗,努力学习提高的时期。
他的后半生,落足于汾阳集星楼剧院,后改为鼓锋剧团,演员有来有去,司鼓冯煊却岿然不动,把鼓锋剧团的文武场,有侯步高(铙钹),宋立贵(马锣),王根孝(铙钹),秦亮(拉葫芦子)等人,形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文场乐队。即与晋中各晋剧团之文武场相比,公认为鼓锋剧团之场面,名列前矛;有一位戏曲音乐工作者写一篇学术论著,排列到第三辈之秦亮时,征求秦老师自己的意见。该配司鼓为谁?秦亮脱口而出曰:“秦亮的胡胡冯煊的板”。反问曰:“冯煊老师,应是你的晚辈”?秦曰:“除过冯煊,不能配他人。足见冯煊在司鼓艺术上的地位,可与上一辈琴师相配。冯煊在汾阳鼓锋剧团,约呆过20余年,其间曾随团演出,至介休、榆次、寿阳、阳泉、石家庄,以至内蒙呼市、包头、银川等地,进行演出活动,“十里乡谈不一般,一方水土一方人。”他谦虚谨慎,艺不厌精,亦不厌广,走到哪里,即与哪里的同行相互学习交流,以便适应当地观众的欣赏要求。因此他在本行业交游甚广,从实践中学到更多的剧目,戏路特宽,适应性特强,同行中无不为之称奇。更难者是晋剧与京剧“两下锅”演出,他来司鼓,亦能配合兄弟剧种之艺人,完成演出任务。即在汾阳剧院演出中充当鼓师,极不容易,有从陕北与晋西山区下来之艺人,亦有从东四处过来的演员,有从太原下来的朋友,亦有从石家庄转来兄弟剧种的流散艺人,为配合兄弟剧种艺人的演出,事先总得拉场子记戏,然后进行舞台实践。数十年来,自己打过的传统戏、现代戏、以及京剧的部分武戏,共有四百出左右,若和他促膝攀谈,虽非熟读如流、亦可谓有问必答。
三、艰苦中磨练
汾阳县原为汾州府所在地,实为秦晋交通枢纽,自古即为戏剧之乡,冯煊同志之后半生,即在此以司鼓为业。其艰苦生活,比同行业其他名家之遭遇,多而且难。如小三儿生郑雅楼所演之《伐子都》、《淮都关》,十三红郭云山所演之《上天台》、《高平关》;以及王银柱、刘芝兰、石金柱等名老艺人所演之戏,是较难配合的。他们的戏变化特快,演出非常认真,曾和他们合作多年,谁也离不开谁。在汾阳与其他山区县份演出过之《宁武关》、《连营庄》、《炮烙柱》、《白草山》、《溪皇庄》、《八蜡庙》、《塔子沟》、《铁公鸡》、《九龙杯》、《白水滩》、《四杰村》等武戏,纵然难打,都和有关名家合作过多次。至于在“两下锅”演出中,与京剧艺人合作,亦曾打过《挑滑车》、《艳阳楼》、《十八罗汉斗悟空》、《金钱豹》、《五花洞》等戏;与刘武花、张树桐、邱树山、赵月楼、赵玉祥、刘万春、任贵福、郭占福等艺人合作说难也难,只要求教于先,临场也能配合的较好。他将京剧的某某锣鼓经,等于晋剧某某锣鼓经列成表格,到用时备查应用。
一般说事业之发展,人材的造就,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他在学艺时期,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月,东逃西躲,朝不保夕,天时不佳,生活极其艰苦,从师三易其人,他却矢志不移,持之以恒,继承张、侯、王三师之特长,打下司鼓较好的基础,人定胜天,时奈其何?出师之后,离开大中城市,独自到老区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就业锻炼,工作生活虽较艰苦,鼓艺发展获得不少新知;后至汾阳鼓锋剧团落足,实践中技艺日新月异,此为其鼓艺发展之极好时期,能如或者,地利也、抑亦为“百花齐放”之天时也。冯煊同志谦虚谨黄,平易近人,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从未见其人称名鼓师而骄傲。在戏曲界多年共事之同人,未闻有非议者,人和也。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如他所逢之天时,他所处之地利,若无主客观之人和,焉能在司鼓艺术方面取得如此巨大之成就,既精巧而深厚、又广阔而贴戏,是其勤学苦练,深钻细研,日夜辛劳。奋斗一生,绝成晋剧界之名鼓师矣。
四、抢救与继承
至80年代汾阳县文化局为了继承本县老艺人所保留的戏曲艺术遗产,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成立了戏曲学校,由冯煊同志任校长,修业数年,培养了一批学生,抢救了部分戏曲遗产。但从其司鼓技艺来讲,自己所打的数百本剧目,是多少老前辈继承发展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某些剧目中有独特的艺术程式,相应的牌曲与锣鼓点,在相互接连处,亦有其发展创造;如《日月图》中之“辕门”,《战宛城)中之起兵等;某些剧目,有特殊唱腔,如《渭水河》中碰木头乱弹,《二娘写状》中的长短句乱弹等;某些剧目在锣鼓经中,有死鼓点活用,如《出棠邑》“拆命书”伍员在流水中下场,却又用“海沙帽子”“大流水头子”收尾;京剧锣鼓经中之xxx,等同于晋剧锣鼓经之xxx,冯煊同志列表备查;但保持等同,并非原样搬用,必有新的增删,在全国大排京剧样板戏中,汾阳剧团名列前矛,在器乐的移植运用上,有若干创造发展成功的经验。此外如本剧种之数种“花二通”,实为我省地方戏曲器乐之交响乐,形将失传,惟冯乃能全部传授下来;如上所述,在其所打四百出左右剧目中,其特殊的鼓点与独特的创造,难以枚举,有极其珍贵的成功经验,与形将失传的艺术遗产,他已与他的学生,和其子晋平传授过若干。
冯煊同志是晋剧界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且有若干发展创造的一位鼓师,腹内尚有若干艺术财富并未继承下来;作为一位戏界的名鼓师为戏曲事业奋斗一生,不慕名利,专心致志地为鼓艺钻研五六十年,亦可谓满腹经纶。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