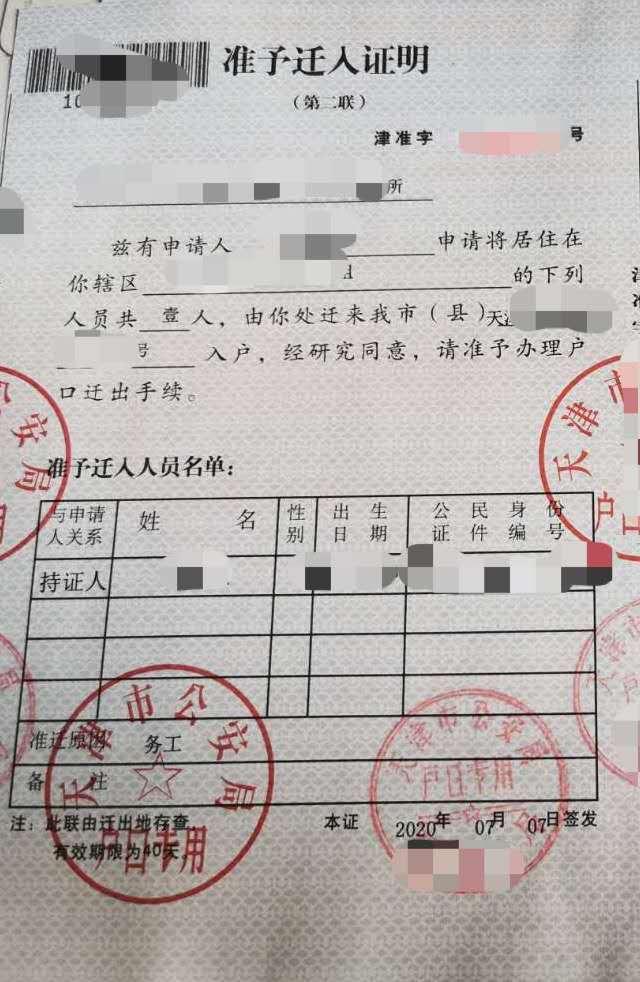胡适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捧(那年今日他就是胡适)


生平
胡适,原名胡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尝试派代表诗人之一。1891年12月17日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
幼时胡适就读于家塾,习四书五经。9岁起熟读多种中国古典小说。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1910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胡适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首倡“新文化运动”而一夜成名,很快就成为中国文学的领袖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他学识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传奇般的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他早年得志,一生显赫,人生相当的顺达;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倡导独立的精神,成为影响广泛的思想家。

年轻时的胡适
胡适26岁时来到了北京,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尤其是这里包容中西、博采众长的文化,更让胡适为之心折。闲暇时,他总是出入于琉璃厂,购买了大量的碑文拓片和古代器物,然后潜心进行研究,或者呼朋唤友,来广和居打牙祭。这一年多的时间,恐怕是胡博士入“围城”前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因为很快,一个外表柔弱的妻子就让这个名声显赫的学界领袖尝到了窝囊的滋味。
无情人成了眷属
胡适一生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件事,既不是他的实验主义,也不是他的哲学史、文学史,或小说考证,而是他的婚姻。他和江冬秀的结合,是个典型的“父母之命”。然而,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又是向“吃人的礼教”抗争的代言人。一个毕生为个人自由与尊严而奋斗的战士,自己的婚姻却是“吃人的礼教”下的一个祭品。正是因为这个有趣的矛盾,使胡适的婚姻,在新旧交替,东西合流的20世纪初年,成了一个思想史上的课题。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胡江二人的婚姻出于偶然。小时候,胡适随母亲到姑婆家看民间的社戏,适逢江母也来了。江母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聪敏伶俐,就有意招他为女婿。但胡母未曾答应。她考虑到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不合时俗。而且,江冬秀属虎,据民间说法,属虎的女人将是母老虎。但江母并不考虑这些,只一意招胡适为婿。江母托胡适的本家叔叔为媒。这位媒人说动了胡母。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旌德县江村江世贤之女江冬秀订婚。订婚后,胡适到上海读书,留学美国,一去十多年,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从未见过江冬秀一面。
胡适幼年丧父,是母亲一手将他抚育成人,慈母的影响在胡适一生中都不绝如缕,使他受益,更使他想冲破而无法冲破。所以,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婚后,胡适为使冬秀照顾母亲,就自个儿回了北京。直到1918年,江冬秀才离开乡村,到胡适身边。自此以后,天涯海角,江冬秀总是伴随着他。以至于唐德刚戏言:“胡适大名重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
一代人的偶像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大师的孤独
1949年,胡适偕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起初,他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去时胡适总是找唐德刚,因为唐德刚是馆内他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唐德刚替他借借书,查查书。从此唐德刚变成为胡适的朋友。

唐德刚说,胡适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侨报都看,而且有时“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这时,胡适在纽约连一个学生都找不到了,他空虚无比,难过无比,变成了“无人打影”的拳师。幸好唐德刚恰巧变成胡适唯一“可打”之人。他看到了一首好的白话诗,便向唐德刚解释半天。
胡适在纽约时,与唐德刚等人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蔡宝瑜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也就乐意变成这个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1956年6月,在“白马文艺社”做了《再论新文学新诗新文字》的报告。他说:“新诗和新文学的发生不但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的偶然。”他不知道这种偶然却是由于时势的变迁的必然而发生的。胡适终身不懂这个道理,以致固执己见而不悟。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留下“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话语,这清楚地勾勒了他的一生。
胡适去世后,世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来源:中国青年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等报道
本期编辑:石玲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