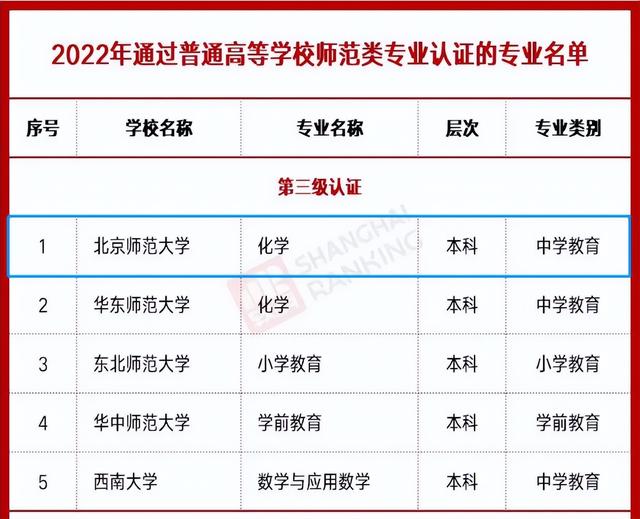逛草坪街的小学(小巷流学记)
文/李正明
初看本文标题,一定会使人疑惑:只见有到外国留学的,冇听说有什么小巷“流学”的,到底么子回事啰?诸位莫性急,且听我慢慢讲述民办小学的故事吧。


“两条腿走路”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生活渐趋安定,便出现了一个生育高潮。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高峰期出生的儿童都到了上学年龄,于是原有的学校就明显少了。
为应付蜂拥而至却难以全部接纳的学童,许多学校采取年龄一刀切的严格措施,规定9月1号以前年满7岁的方可报名,否则,差一天都不行。如此一来,就将众多8月31号以后才满7岁的报名者拒之门外。
本人1950年11月出生,也即因此而未能于1957年进入离樊西巷四中里旁,距家不到200米远的铜铺街小学。看着不少一起长大的“小二郎”,背起书包上学堂,我是既羨慕,又无奈!
政府有关部门也注意到儿童入学难这一社会问题,适时提出了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挖掘潜力,继续发展公办学校,另一方面提倡和鼓励兴建民办学校。
伴随着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运动的步伐,这一“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在1958年初便很快付诸实施。
1958年春节刚过,位于师敬湾的“学院街第一民办小学”,即应运而生了,老师们天天上门动员在家的适龄儿童报名入学,向持犹疑态度的家长们宣传公办民办一个样,并许诺小孩可先入学后交学费(实际上民办小学的学费始终比公办的贵,就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等方面来说,可谓“质次价高”了)。
左邻右舍许多像我父母一样的大人们,经不起老师们的连日宣传及求学心切的小孩缠扰,最终将小孩送到了“学院街第一民办小学”读书。

作者近期在现师敬湾巷留影

小庙改建成的学校
师敬湾北起成仁街,一条3、4米宽、弯弯曲曲的麻石路缓缓向南升高,延伸约300米后与上黎家坡相接。路两边分布着十几条窄而短的小巷。
在师敬湾中段东侧有一座小庙,青砖墙高约丈余,墙头堆砌几层小青瓦,花岗石门框双合木门,门上蒙有布满小泡钉的薄铁皮及两个铁门环,门楣上粉了白灰,应该是遮盖原庙名的。就是这座貌不惊人的袖珍小庙,被改建成了我们的学校,成了我的人生发蒙地,并由此结下了与其数十年来始终割舍不了的情缘!
跨过学校大门,左边是四间教室,右边西头是一座木结构厕所,东头是一间办公室及一间杂屋。杂屋及最东头的教室与围墙之间是一米多宽的走道,其北端墙角堆放着几具残破的泥菩萨,这是原小庙唯一的遗存,暗示着学校的前身。在教室、办公室及厕所之间是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空坪,如此弹丸之地,这就是我们全体师生学习和活动的全部空间。
我家住樊西巷老109号(后为103号)一楼,二楼住了彭家、潘家。我和同龄人彭双芳、潘云富3人一起进了“学一小”。我们在家是同屋邻居,在校又是同班学友,哪个在学校犯了错,到他(她)家告状也易得;哪个在家里有糗事,到班上他(她)扩散也不为难。

樊西巷老照片(约八九十年代拍摄)
有一天,彭的调皮弟弟闯入无人值守的校本部大门,径直爬到教室窗上,对着正在上课的师生大喊三遍:“毛毛伢子李正明!”顿时满室哗然!毛毛伢子是我的乳名,被他如此揭秘,叫我堂堂班干成了长不大的小“毛毛”,好没面子!此是题外话,打住。
当年一年级新生分为甲乙两班,我们甲班学生家住樊西巷的有12个,其余的来自四中里、同仁里、仁美园、劳动新村(旧称衙门坪)、西文庙坪,西湖路、上下黎家坡等处。
若以学校为中心,离校最东边的是东区化龙池的陈新民;最南边的是西湖桥的杨端群3人;最西边的是唐家湾的韩济群;最北边的是中和街的方孝诚。
来自东南西北小街小巷的数十名懵懂孩童,在此踏上了漫漫求学路。
刚开始一段时间,桌椅不全,我们自带小凳凑合。发的书是从公办小学学生手里收集来的残缺不全的旧书,上面画满了五颜六色的蜡笔印,邋遢死了!我的语文书最后两课“拔萝卜”与“给毛主席拜年”那几页,早就被撕掉了,学到这两课时,要和同学合作、借阅,才能“拔萝卜”“拜年”。
民办小学这条腿,就这样蹒跚起步了!我的六年半民小求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学无定所,打了6年半“游击”
从1958年年初入学到1964年年中毕业,我们学无定所,在数条小巷打了6年半“游击”。
随着1958年9月及以后每年9月招生,原有教室无法容纳得下,学校便设法设立分部,我们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打流——“流学”。先是搬到学院街西头南侧一户普通民宅中上课,这户人家有一座极其简陋的厕所,几块木板围成一间2、3平方的小屋,内设一小瓦缸,上面搭两块木板即为男女共用的方便之处。蛆虫翻涌,苍蝇乱飞,臭不可闻。一下课,几十人还要排队上缸轮蹲呢!

图中部为原学院街上学处(位于街南面,原系平房,左斜向前通黄兴路步行街)
后来,我们又先后迁到位于南墙湾与修文街交汇处,老师们叫做“培英”的一座民宅;到了泉嘶井;到了登仁桥“天妃宫”;到了上黎家坡大巷子等几处地方读书。

图中标红星处,除樊西巷一处为作者家,其余6处为当年上学处。
“培英”、泉嘶井两处都是带小院子的宅第,可能旧时是有钱人家的私宅,我们上体育课和课间还可幸运地在院子里活动。
泉嘶井巷系位于西文庙坪与上黎家巷之间的一条幽静小巷,有一水井,传说晚上井内常有泉水嘶鸣声,小巷便以此为名。我们细伢子对这其貌不扬的井,没有什么兴趣,我倒是对当年在那里读书的特殊学习环境,及师生融洽的温馨氛围,大半辈子以来长久怀念。
我们教室旁边住了老师一家,这是我呆过的6个校址中唯一的住教并存的状况。我们的班主任周笃孝老师夫妇就住在一排几间教室的最南边,我们课间或放学后,经常到他家串门喝茶拉家常、帮周师母择菜、看她搞饭。
有一次周师母问女同学徐晴峦成绩如何,徐说:大套子(一般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长沙土话及它的意思,记得特深。周家大儿子在长沙不知是上班还是上学,经常来。后来乡下小儿子也来城里读书,周老师特地要我平时多辅导他,把成绩提上来。

图中为原泉嘶井上学处。右侧泉嘶井91号为长沙市天心区不可移动文物
天妃宫原名玉泉寺,有几百年历史。湘籍作家唐浩明著《曾国藩》里,精彩重现了咸丰二年左宗棠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在天妃宫内外的一场激战。该宫毁于文夕大火,后重建,规模大不如前。解放后破除迷信,宫里僧尼还俗了。
我们迁去后是在正殿里上课的。记得当时进宫门左边一排房内及走廊上,有工人在开机子织玻璃布。往往是哗哗机杼声、朗朗读书声交织成一片,亦工亦读,相映成趣。

清代长沙地图中标记有天妃宫
大巷子分部没有院子,但房屋建筑质量好,档次高,系两层楼房,所有门窗、楼梯、地面都是精工油漆过的。楼内还有天井,采光通风良好,是大户人家气派,显然原房主非富即贵。我们下课后楼上楼下跑,有时还一个个坐在梯子扶手上,从楼上玩“唆唆板”一路溜下来,还蛮有味呢。
随着上学地点的变动,我的上学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出门右拐从樊西巷经成仁街到师敬湾或学院街、天妃宫、“培英“(也可穿过樊西巷土地庙经劳动新村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到上述各处);另一条是出门左拐经上黎家坡、狮石巷、公路局坪到泉嘶井或上黎家坡大巷子。
到最后,其他几处临时分部均陆续撤消,就只有师敬湾与大巷子两处校区,六年(半)上学,呆了六个地方,我们毕业前又回到校本部“定居”了。

天妃宫(资料翻拍)

一穷二白,但自尊、自强、自立
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人们还沒有像现代社会对于民营企业、民办教育有如此正确的认同和接受。在许多人看来民办学校是入另册的,是低人一等的,更何况,民办学校一穷二白,惨淡经营,确实难与公办学校相提并论。
学校被人瞧不起,学生自然也被公校学生看不来。我们常常遭到他们蛮押韵、蛮恼火的顺口溜嘲弄:“民办小学,打开脑壳”——至今我还冇搞清哪个的脑壳被打开了?
我们长期被他们编成歌唱而哑口无言,唯一能与他们融洽地一起忘形地大声吼唱的是,过苦日子的时候,一些发牢骚的人根据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改编的流行歌曲:看见老师端碗饭,口水流得丈把长,肚子里头闹革命,咕咙咕咙要呷饭……
我们没有机会像公校学生一样参与校际活动、社会活动;没有机会参加夏令营;没有机会担任校外交通安全监督员、文明卫生检查员……
但我们全体师生也不乏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上下课没有电铃提示,老师就敲铁块、摇手铃;没有大操坪,我们就操步伐、跳绳、跳“人马”……缺少办学经费,学校就从纺纱厂接来纱头布尾,安排我们上手工劳动课扯纱,再将扯得膨松的纱线送到厂里,收取加工费,以补贴学校开支的不足……
那时候全国正盛行打乒乓球,学校没有球台,我们放学后或星期天四处寻找地方打球。到西区少年之家,人太多很难轮得到,而且还经常受到外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

乒乓球比赛(仅供参考,非长沙老照片)
我们曾到过李坚同学妈妈单位东茅街市工商联打球;也曾结伴步行好远到龙全根同学表哥就读的南湖路省邮电学校打球(打到半路被赶出来了);到了最后,作为我们长期活动基地的是化龙池陈新民家和仁美园龙惟光、巢凱扬俩家。
我们课余自学小组轮流在他们三家做作业,作业完成后就拆下门板架球台,上面放两块砖,砖上搁根扁担当球网,五六个人便轮番上阵比起“六坨(分)制”的球赛来,水平高的常常“占老位”当“门板冠军”,大家苦中作乐,其乐融融。
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陶冶美好情操,学校还经常由刘仲道、李敬原老师举办课余作文知识讲座和女周老师主讲的绘画课。同学们求知欲强,参加者都十分踊跃。
我较喜欢写点东西自己欣赏,写作爱好也就是由此发端的,只不过一开始就将学到的写作技巧用错了地方。有天课间我和方孝诚合作,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你进园干什么——偷菜。
恶作剧的结果可想而知,同学哄笑!李敬原老师对顽皮的我俩的影射和不敬,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而李方二人则作为无理方,向李老师作了诚挚的认错和道歉!现已年过八旬的李老贵体安好?学生小李至今有愧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灭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有关部门分派给学校要按期完成一定数额的灭害指标。
我们学生主要是完成学校下达的灭蝇任务,能够灭掉老鼠当然是受欢迎并表扬的。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带着扑蝇拍上学,见蝇就拍,或在家设置纱笼诱蝇,并将苍蝇残骸交给班主席。也有消灭了老鼠切了鼠尾带了来的,由班主席验收点数登记,再将蝇骸鼠尾及登记表交给学校总务刘老师,用石灰拌好战利品防止腐臭生蛆。

除四害(仅供参考,非长沙老照片)
每周末,教导主任唐泽琼就派时任班主席兼少先队大队长的我,将包装好的全校一周战果送到福胜街“湘西自治州驻长办”。该办一楼有一个西区卫生防疫站专设窗口(很大可能该楼是防疫站,驻长办只是租了防疫站一部份,记不清了),负责收纳各单位交来的灭害战果。最终,政府爱卫部门对灭四害成绩显著的单位给予了隆重表彰。
我们“学一小“也获得了上述殊荣,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扩大了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校方也相应表彰了一些“灭害”积极份子。有个幕后旧闻今予以披露,当时有个别同学说某同学作弊,以豆豉混入蝇骸中滥竽充数而获奖,怪我“眼晴夹哒豆豉”,冇看出作假豆豉,他不该,我失职!这实在是猜测,今天忆及,犹觉好笑哟。
学校没有礼堂,学生又分散,很难得开一次全校大会,仅有的两三次都是借了樊西巷市工商联(后迁至东茅街)礼堂开的。每次开会,平时难得一聚的几百师生此时个个喜气洋洋。会上表彰五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和先进集体等,然后各班表演文艺节目,就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隆重、热闹欢腾,几天后,大家还沉浸在兴奋愉悦之中!

小学“本科”毕业,好吓人!
也许是当初太冲动、太跃进了,1958年春季招生学生将于1964年春季毕业,而中学要到秋季才招生,这中间有半年时间接不上,怎么办呢?
也许直到1962年年初,那些拍拍脑袋定下1958年春季招生的决策者们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荒唐!于是作出了让业已读完四年二期的我们那批学生,再复读一期,名曰“四复班”。幸亏除了我们这批,学校后来都是秋季招生,不然,害的人就更多了!
头脑发热,不按常规办事的决策者们,为他的工作失误不伤自身毫毛地交了一笔“学费”,而真正冤里冤枉地多交了一笔不菲学费的,倒是我们莘莘学子及其辛苦挣钱的家长啊!
四年二期的书已学过,复读课本又是怎样的呢?都是本市教育部门自已编印的简易教材,内容与原四年级的大同小异。语文、算术两门我唯一只记得一篇课文的大概,是描写乡村景色的,写了清晨雄鸡高唱,太阳露出笑脸,百花盛开,一只小狗在野外撒欢,汪汪叫了几声后在草地上打了几个恋滚……我也由此知道长沙土话“恋滚”的恋字是如此这般写。
就这样凑合混了一期,家长们说,关在教室里复读好歹比在外打流要强。
1964年6月底,读了6年半书的我们终于毕业.了,用某相声的说法叫:小学“本科”毕业,好吓人!

1964年在大巷子拍的毕业照
毕业同学中大部考进了普通中学,少数仍然进了民办学校,学生中的几个佼佼者,令人羡慕地考入了重点中学二中、附中,堪称民办小学“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几年前,我偶然得知多年老友原二中学生邹齐恕竟也是“民小本科生”。他家住南门口晏家塘,1958年春进入妙高峰(城市)人民公社上游分社小学,读了6年半,在天心阁、里仁坡、煕台岭等6个地方上过课;后又有中学同学张建均告诉我,他和我们班同学彭建祥、黄宁安等也系学校元老级学生,所谓“黄埔一期生”——1958年春进入南元宫小学读书。(为叙述简便,姑且把58年春天入学的叫春生,同年秋天入学的叫秋生吧。)邹和张等也是小巷“流学”,也是和我们一样62年秋春生与秋生混合编班一起毕业的。现在看来,当年的春生应是队伍庞大,遍布全城。
六年半小学经历给我最大的印象是师生流失量大。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有流动是正常的,但我们民小因各方面条件差,跳槽转校的比一般公小要多。很多能够有办法跳到好单位好学校的师生都陆续走了,这一点,老师最打眼。老师像走马灯一样变换,我们刚熟悉一个老师,很快又换来了一个新面孔,授业者不稳定,最终受到不利影响的是接受教育的我们学生。
至于学生流失,我一直有个概念,就是我校春生两个班、秋生两个班,1962年春秋生混合后,到1964年毕业时竟只有两个班。这其中除了少量留级生外,其余相当于一个多班的学生都是转校和个别辍学的了。
我想若是学校各方面条件较好,留得住人,老师安心教学,学生群体稳定,教学质量必然会保有一个较好的水平,1964年我们春生、秋生毕业小升初的录取率肯定高,上重点中学的“金凤凰”会飞得更多。

“花开花落何匆匆”
1966年文革兴起,全国学校瘫痪,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复课闹革命”。这时民办小学的道路已走到了尽头,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撤消所有民办小学,各校师生全部并入就近的小学。
仔细算来,民办小学仅维持了十年光景,而正式运行也仅有8年。当年我校号称“学一小”,看来巴掌大的地方似乎除了公办文庙坪小学、南墙湾小学外,至少还要办“学二小”,是不是有点盲目?
今天,我们曾经呆过的培英、泉嘶井、大巷子三个“流学”处均已建成几层高的商住楼,全无旧时痕迹。
文革后1988年又重燃香火的天妃宫,一度因周边拆迁而傲立于闹市,围墙上南无阿弥佗佛六个大字赫然入目。我们昔日的课堂又恢复成为庄严的大雄宝殿,每日里香火旺盛,诵经声、钟磬声不绝于耳,全然取代了曾经充盈于殿堂内的我们那稚嫩的朗朗书声。
不过,到了2004年登仁桥巷拓改,天妃宫迁至新开铺铁路桥边,恢复旧名为玉泉寺,现又早已正式迁建于金盆岭下。天妃宫原址已成为长郡中学(原二中)门前马路的一部分了。

现在的登仁桥巷
今年我重游学院街一带,在南墙湾巷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幸运地寻访到了两位长住此处的七旬老人,他(她)解开了我心中几十年的疑团:老师们提到的发音为“培英“的所在,原来就是培英小学,后来撤了,师生转入百米远的文庙坪小学,原校址现为航运局宿舍。

上为原培英小学上学处,现为省航运部门宿舍。右下角小路前行百多米处为西文庙坪小学;左下小路(斜上)20多米通修文街;左边200多米处原有南墙湾小学。几十年前这条300多米长、东西向的小巷里同时存在3所小学。
我真想不到当年长约300米的南墙湾巷竟同时拥有南墙湾、培英及文庙坪三所小学,与平行的修文街比肩,且文气更浓啊!同时我也明白了在培英上课时,感觉教室及桌椅较周正,原来它本来就是学校,教室非改建,桌椅非拼凑。我们入内上课,应该是我寻访的老者讲的师生转入文庙坪小学后,在校舍空置期内“学一小”见缝插针短暂进行的。
学院街分部原址现也成了烧烤店,融入了周边十几家门店之中。现在是师敬湾巷42号的原校本部,随着整个街道的升级改造,外墙已进行了粉刷修饰,但原轮廓仍未变,里面挤住了几户人家。目睹现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以前是如何装得下一个学校的?
几十年了,师敬湾基本没什么变化。早已有的变化是老麻石街已改成了平坦的沥青路,原来校门旁边的双眼井早已填了一一以前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学生伢子,在无任何安全警示的井边路过、逗留嬉戏,竟也无人掉入井内,令人惊异!
另外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原来的学院街办事处师敬湾居委会,现在改为坡子街街道樊西巷社区,若能穿越到过去,我的母校就会被称为坡子街第一民办小学了。
师敬湾58号旁有一段百米长古墙,系长郡中学西围墙,墙内有“汉忠臣韩玄之墓”为历史文物,古墙有一百多年了,历经风雨沧桑,见证了古城长沙的兴衰演变。
师敬湾原名司禁湾,清时臬司狱、府司狱均设于此,因而得名。又因此街与长郡中学相邻,后取谐音雅化为“师敬湾”。古墙与师敬湾有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令与师敬湾有缘的我心中又多了一份自豪与敬重!
至于师敬湾北口的市粮食局幼儿园,我们上学时就知道那里原是国民党陆军监狱。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上幼儿园的孩子,现在早已是送孙子入园的老人了。正是:
遥忆当年小二郎,
求知就读师敬湾。
六十四载光阴逝,
物是人非话沧桑。

1947年长沙地图中,师敬湾巷还是叫司禁湾

后记:“三无”的无奈
我有很深的母校情结,2017年7月的一天,我去天心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查询原西区学院街第一民办小学的档案资料,想借阅学校建校史、师生花名册及相关照片等。该科负责人说他1995年到西区(天心区)教育局,22年了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民办小学,局里更没有任何民办小学的档案。
我不太相信,更不甘心,又去楼上档案室问,结果同样失望碰壁。今年我又电询长沙市档案馆,最后一线希望依旧破灭!
我深感失望和遗憾并进而生怨,当年政府倡导兴办的众多民办小学,怎么会成为既无原有校舍、无名份、无档案的三无学校?校舍可以无,但名份和档案不可无!奈何昔日莘莘学子的艰辛求学痕迹、无数教书育人的老师,付出的宝贵岁月年华及满腔心血,被抹去了……这是我们命运多舛的50后的宿命?
我今天写的这篇短文,在再无其他历史资料可供引用佐证的情况下,恐有些许历史细节的不准确。但聊可自慰的是它是我极其看重的人生记录的一页,是我余生回顾少年求学史的唯一依据。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编辑 | 明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