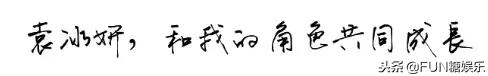吕蒙正是宋朝哪个皇帝的宰相(宋代赠谥资格再探)

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由于特殊原因获得谥号。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赠官制度萌芽于两汉时期,至唐宋已经成为一项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尤以宋代为完备。赠官作为中高级官员与殁于王事等获赠者官阶与官品一次重要的提升,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获赠者的官阶与官品,甚至实现质的突破。赠官作为官员卒后朝廷所加荣典,也成为丧葬礼制不可缺少的一环。赠官施予去世官员,无论对其生平贡献抑或政治地位,都是一种肯定。赠官很大程度上反映官员生前的社会地位,并且能够影响到官员卒后的赠赙、赠谥等事宜。宋代赠官的意义之中,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格外值得关注。官员通过赠官提升官品等级从而获得谥号,本无资格获得谥号者通过赠官可以达到赠谥资格,此种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将赠官与赠谥紧密联系起来。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目前,学界对宋代赠官意义的考察鲜有涉及[①],对宋代赠谥的探讨也相对较少[②],均未从赠官出发对赠谥展开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拟探讨宋代赠谥的资格、从宋代赠官出发对赠谥资格再探讨,以冀对宋代政治制度研究有所补益。
宋代赠官作为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评价之外,谥号也是对卒殁官员评价的重要内容。在很多情况下,官员赠官与赠谥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在《天圣令》的《丧葬令》中,体现出宋代赠官与赠谥的“诸谥,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录行状申省,考功勘校,下太常礼院拟讫,申省,议定奏闻。赠官亦准此。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锡谥曰‘先生’。”[③]初步来看,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可以申请谥号,这一标准高于赠官标准。王公之外的官员群体中,如果说赠官赠予对象为宋代较高级官员,那么赠谥对象则为宋代高级官员。宋代“赠官亦准此”,所指赠官至三品者也可以申请谥号,事实是否如此?据此,为了探讨官员最高官未至赠谥资格,通过赠官提升官品之后达到赠谥资格者是否即可请谥、获得谥号,需要考察出宋代赠谥的标准,继而探讨宋代卒殁官员获得赠官达到赠谥标准之后,是否能够据此得谥。
一、宋代赠谥资格探究
《天圣令》的《丧葬令》中载,卒殁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者可以请谥,也即达到赠谥标准。王公不难理解,即爵位达到公及公以上。职事官三品以上,则是需要着重考察的对象,这与宋代广大文武官员卒殁是否能够请谥、获谥密切相关。
宋人宋敏求对北宋前期赠谥资格制度规定即有所关注:“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④]“唐制,兼官三品得赠官,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终吏部侍郎,而赠礼部尚书是也。又观察使多赠两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谥。国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而史失其传。宝元中,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卒而辍朝,非故事也。”[⑤]宋敏求在其笔记小说中不厌其烦两次陈述了北宋前期赠谥资格问题[⑥],兹将其主要内容归纳如下。景德之前,文武官需官至三品可得谥、赠官至三品者不可得谥;大中祥符之后,文武官员官至尚书、节度使即可得谥,赠官至正三品者也可请谥。宋代文官官制在元丰改制前后变化很大,宋敏求所载赠谥标准当为元丰改制前,“尚书”当指文官阶,“三品”、“正三品”所指也当为文官阶的官品,那么元丰改制后如何?《丧葬令》中的“职事官三品以上”,又当如何理解?
宋人李焘也注意到了宋敏求关于赠谥的记载,在探讨宝元年间朝廷罢去诸司三品官员卒殁辍视朝问题时,指出:“宋敏求春明录云:国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官至正三品许请谥,而史失其传。当考。”[⑦]从李焘转载宋敏求关于赠谥记载来看,宝元年间朝廷罢去诸司三品官员卒殁辍视朝之礼,而宋敏求却指出宋真宗令陈彭年详定之后,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殁即有辍朝之礼,而这一时期尚书即为三品,也即三品卒殁者可有辍朝之礼,两者是有出入的。而关于官员赠谥资格问题,李焘并未质疑。其实,《宋会要辑稿》中也有关于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重定赠谥标准,并且表明宋代赠谥资格其实源自于唐典的规定: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朝廷诏:“文武官薨亡,准《唐六典》,诸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责历任勘校,送太常礼院拟谥讫,覆送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以闻。赠官同职事。
自今如本家请谥,更不先具闻奏,便依故事施行。”[⑧]《唐六典》中关于唐代赠谥的制度规定,从《宋会要辑稿》来看为唐代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官员卒殁之后,可以按照相关赠谥流程展开赠谥事宜。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关于赠谥资格的重定,即是依据《唐六典》将赠谥资格确定为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查阅《唐六典》在其考功郎中员外郎条中,有关于唐代赠谥的资格:“诸职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唐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锡谥曰‘先生’。”[⑨]由此来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所辑《宋会要辑稿》中关于宋代赠谥资格问题的记载,来源是一致的,都来源于唐代赠谥资格的制度规定。
较之于唐代赠谥资格规定中的“赠官同职事”,至宋代赠谥资格规定则改变为“赠官亦准此”,并且将散官二品可赠谥取消,职事三品以上则成为关键。《唐六典》中所谓的职事官,指的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官员,即六部尚书、侍郎、寺监等官员。进入北宋前期以后,这些职事官固然依旧存在,不过几乎均已成为文官阶。北宋前期的差遣,官品只能视本官阶而定,散官又不能作为赠谥标准,宋代赠谥资格规定中的职事官只能为文官阶。而赠谥资格中数次提到的节度使,在宋代也为武官阶。
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上述内容,可以得出宋代赠谥资格为: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可得谥,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均可得谥,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却获得谥号的特殊情况。绍兴三年(1133)中书舍人陈兴义等人向宋高宗奏言道:“旧来百官谥不命词,至政和、宣和以后,有不经太常、考功议定,百官集议而特赐谥者,始命词。近来乃一概命词,乞改正。今后特恩赐谥命词给告外,余给敕。”[⑩]可见,特赐谥作为一种特殊的赠谥形式,与达到赠谥资格得谥相对应,一些中、低级官员由于特殊原因可通过此种方式获得谥号。南宋以来长期同金人作战,宋廷规定“守臣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之人,若限以官品赐谥,即节义之人其名不显,无以激劝。应守臣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不以官爵上下,取旨特赐谥”,[11]使得许多未至赠谥资格的死节之士获得谥号。不过,特赐谥只能是赠谥中的特例、特恩现象,并不能称之为赠谥资格。但是,特赐谥也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达到赠谥资格者卒后得谥,共同构成了宋代的赠谥体系。关于宋代赠谥资格是否确实如此,下文将结合宋代赠官继续进行再探。
二、从赠官出发再探宋代赠谥资格
宋代赠谥依据为官员的官阶,通过对宋代赠谥制度规定的考察可以得出这一论断。从赠官来看,官阶作为是否给赠、如何赠官也成为赠官体系中较好的选择。文官的官阶在元丰改制前为是否赠官的重要判断标准,在元丰改制后也依然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标准;武官阶在政和厘定前后,也都是判断是否赠官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涉及到赠官恩数的问题时,官阶就成为赠官的起点。既然在赠官之中,官阶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又便于操作和管理,那么在赠谥当中,官阶应当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赠谥来看,与赠官不同的是不涉及恩数的问题,只涉及用何字样作为谥号的问题。相同的地方在于是否赠谥的依据,同样也应为官阶。宋代的差遣、职事官、军职虽然也有相应的升迁标准,但总的来看并不算严格,而且官品、转资很难确定。而官阶作为是否赠谥的依据,则清晰、可行、便于操作。
宋代赠谥资格中,有“赠官亦准此”的规定。那么,官员卒殁之后赠官达到相应官品,是否可以获得赠谥的资格?下面从不同时期赠官达到相应官品、获得赠谥的实例,来进行考察。宋代达到赠谥资格的获谥官员中,文官数量最多,其次为武将和宦官。宗室中与当朝皇帝关系亲近者几乎均可赠谥,故不再讨论。
(一)从文官赠官出发再探宋代赠谥资格
对宋代文官赠至正三品者是否可以赠谥进行考察,以此对宋代赠谥资格进行探究。由于元丰改制前后官制变化巨大,兹分为元丰改制前后分别考察,从而根据赠官探究赠谥资格。
1.元丰改制前从文官赠官出发再探赠谥资格
根据对宋代卒后获得赠官者是否获赠谥号的考察,宋太祖、宋太宗朝文官阶未至正三品而赠官赠至正三品者均无赠谥。宋真宗朝共有五人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之后赠官达到正三品或以上且获得谥号者,分别是杨徽之、宋湜、钱若水、赵安仁、陈彭年。杨徽之于咸平三年(1000)以兵部侍郎卒,赠兵部尚书;[12]宋湜于咸平三年(1000)以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后宋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赠刑部尚书”;[13]钱若水于咸平六年(1003)以邓州观察使卒,文官阶至工部侍郎,赠户部尚书;[14]赵安仁于天禧二年(1018)以尚书右丞卒,赠吏部尚书;[15]陈彭年于天禧二年(1018)以兵部侍郎卒,赠右仆射。[16]宋真宗朝大中祥符年间令陈彭年重新详定赠谥资格,将赠官至正三品者纳入到赠谥的范围。据此,杨徽之、宋湜、钱若水三人的赠谥时间具有特别的意义。杨徽之获得谥号在景祐二年(1035)十二月,谥文庄;[17]宋湜、钱若水获得谥号在皇祐四年(1052)七月,“赠刑部尚书宋湜谥曰恭质”,“赠户部尚书钱若水谥曰宣靖”。[18]关于宋真宗朝上述五人的赠官、赠谥,有以下内容需要说明。杨徽之在咸平三年(1000)卒殁获赠兵部尚书,景祐二年(1035)由于其外孙参知政事宋绶为之申请,朝廷加赠杨徽之为太子太师、同时赠谥。[19]尽管杨徽之是在赠太子太师之后获赠谥号,但不变的是杨徽之仕履最高文官阶——兵部侍郎,兵部侍郎官阶为正四品下,杨徽之获谥原因在于所赠之官太子太师达到了正三品。宋湜,咸平三年(1000)以正五品上的给事中卒殁,获赠正四品下的吏部侍郎赠官,但仍未赠至正三品。
而不久之后宋真宗对其追悼,又赠之为正三品的刑部尚书,皇祐四年(1052)宋湜正是依靠其刑部尚书的赠官获得了谥号。钱若水于咸平六年(1003)以邓州观察使卒,参考其仕履最高文官阶为正四品下的工部侍郎,获赠正三品的户部尚书,并据此于皇祐四年(1052)获得谥号。赵安仁与陈彭年均卒殁于天禧二年(1018),赵安仁以正四品上的尚书右丞卒殁获赠正三品的吏部尚书、陈彭年以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卒殁获赠从二品的右仆射,两人获得赠官之后即获谥号,并未如同杨徽之、宋湜、钱若水三人赠谥如此滞后。根据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宋初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文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无获谥者。而从宋真宗天禧年间开始,文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官阶者可获谥号,在此之前未获谥号的此类官员也可由其家人或其他官员为其请谥从而获得谥号。
从宋仁宗朝至宋神宗元丰改制前,文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官阶者,几乎在获得赠官之后即又获得谥号,此类官员的官阶、赠官、谥号等内容详见表1。
表1 宋代元丰改制前文官阶未至正三品、赠官至正三品方获谥号一览表
|
姓名 |
最高阶 |
赠官 |
谥号 |
出处 |
|
赵昌言 |
吏部侍郎 |
吏部尚书 |
景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267《赵昌言传》,第9198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8,第2068页。 |
|
鲁宗道 |
礼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肃简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6《鲁宗道传》,第9628—9629页。 |
|
薛奎 |
户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简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6《薛逵传》,第9631页。 |
|
王曙 |
吏部侍郎 |
太保、中书令 |
文康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6《王曙传》,第9633页。 |
|
蔡齐 |
户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文忠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6《蔡齐传》,第9637—9638页。 |
|
周起 |
礼部侍郎 |
礼部尚书 |
安惠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8《周起传》,第9673页。 |
|
高若讷 |
尚书左丞 |
右仆射 |
文庄 |
(元)脱脱等:《宋史》卷288《高若讷传》,第9686页。 |
|
吴育 |
尚书左丞 |
吏部尚书 |
正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1《吴育传》,第9732页。 |
|
王鬷 |
工部侍郎 |
户部尚书 |
忠穆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1《王鬷传》,第9750—9751页。 |
|
李谘 |
户部侍郎 |
右仆射 |
宪成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2《李谘传》,第9754页。 |
|
丁度 |
尚书右丞 |
吏部尚书 |
文简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2《丁度传》,第9764页。 |
|
张观 |
尚书左丞 |
吏部尚书 |
文孝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2《张观传》,第9766页。 |
|
王尧臣 |
吏部侍郎 |
左仆射 |
文安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2《王尧臣传》,第9776页。 |
|
冯元 |
户部侍郎 |
户部尚书 |
章靖 |
(元)脱脱等:《宋史》294《冯元传》,第9822页。 |
|
杨察 |
户部侍郎 |
礼部尚书 |
宣懿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5《杨察传》,第9856页。 |
|
李及 |
工部侍郎 |
礼部尚书 |
恭惠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8《李及传》,第9909页。 |
|
晁宗悫 |
给事中 |
工部尚书 |
文庄 |
(元)脱脱等:《宋史》卷305《晁宗悫传》,第10087页。 |
|
范仲淹 |
户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文正 |
(元)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第10275页。 |
|
包拯 |
礼部侍郎 |
礼部尚书 |
孝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316《包拯传》,第10318页。 |
|
明镐 |
给事中 |
礼部尚书 |
文烈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2《明镐传》,第9770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六月癸巳,第3954页。 |
|
孙沔 |
礼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威敏 |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70《孙沔传》,第64页。 |
|
王畴 |
礼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忠简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1《王畴传》,第9749页。 |
|
吴奎 |
户部侍郎 |
兵部尚书 |
文肃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4,第2529页;(元)脱脱等:《宋史》卷316《吴奎传》,第10321页。 |
|
唐介 |
给事中 |
礼部尚书 |
质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316《唐介传》,第10330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9之97,第2067页。 |
|
邵亢 |
礼部侍郎 |
吏部尚书 |
安简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4,第2529页;(元)脱脱等:《宋史》卷317《邵亢传》,第10337页。 |
|
钱明逸 |
尚书左丞 |
礼部尚书 |
修懿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7,第2532页;(元)脱脱等:《宋史》卷317《钱明逸传》,第10347—10348页。 |
|
蔡挺 |
右谏议大夫 |
工部尚书 |
敏肃 |
(元)脱脱等:《宋史》卷328《蔡挺传》,第10577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五月戊辰,第7240页。 |
上述文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官阶且获得谥号者,仕履最高文官阶最低者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最高者为正四品上的尚书左丞,均未至正三品。获得赠官大多为正三品的六部尚书之一,也有获赠从二品的左仆射。因此,从赠官的角度来看赠谥,宋真宗天禧年间至宋神宗元丰改制前,文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官阶者可获谥号。
2.元丰改制后从文官赠官出发再探赠谥资格
宋神宗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寄禄官阶且获得谥号者人数众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拟从三个方面对元丰改制后宋代赠谥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元丰改制后文官赠谥标准由寄禄官阶承担。元丰改制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官复其职,改制前的文官阶成为新的职事官。根据“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这个标准,似乎很可能指元丰改制后职事官官品达到正三品者。从元丰改制后职事官的官品来看,达到正三品的职事官主要有六部尚书、执政、宰相。可是,仅以吏部尚书为例,就有吏部尚书、权吏部尚书、行吏部尚书、守吏部尚书、试吏部尚书等类别,而吏部尚书为从二品、权吏部尚书为正三品有明文规定,那么行吏部尚书、守吏部尚书、试吏部尚书的官品又是如何?[20]此外,元丰改制后还出现不少低于正三品的职事官兼任吏部尚书、兼权吏部尚书的现象,该官员的职事官官品会按照所兼或兼权吏部尚书的官品来确定吗?特别是部分寄禄官阶很低、由于皇帝的特旨,被任命为重要的职事官,然而其寄禄官阶并会不会随之大幅度提升。作为确定官员是否应当获谥的机构,梳理官员无比复杂的职事官仕履,也定然要因此耽搁许多时间,甚至影响谥号的赠予。正是如此,南宋绍兴五年(1135)朝廷下诏:“文臣光禄大夫、武臣节度使以上身亡,依条取索本家行状,方许定谥。”[21]因此,元丰改制后至南宋绍兴五年之间,虽然没有史籍专门记载宋代赠谥资格依据为寄禄官阶,然根据以上考察与分析,可知元丰改制后赠谥标准应由寄禄官阶来承担。
二是官员所任职名与获赠职名达到正三品不能作为赠谥的资格。乾道五年(1169)礼部、太常寺上言道:“故礼部侍郎、赠延康殿学士谭世绩孙昭祖乞与祖世绩请谥。世绩在靖康时,虏立伪楚,坚不称臣。及令直学士院,力拒不受,痛愤至死。然所赠官序不该定谥,又不应守臣守御赐谥指挥,若朝廷特旨赐谥,旌褒守节,即无定法。”[22]谭世绩官至礼部侍郎,卒后于南宋初年获赠延康殿学士、左太中大夫。左太中大夫从四品、延康殿学士正三品。按照“赠官同职事”的规定,谭世绩既然获赠延康殿学士,即可以根据其职赠至延康殿学士,也即正三品。但是,“然所赠官序不该定谥”表明,其获赠延康殿学士虽至正三品,然在赠谥中不能作为资格依据,赠谥资格考察的是其寄禄官阶,从四品的左太中大夫未至正三品,因此最后以特恩的方式获得谥号。
三是寄禄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寄禄官阶者可获谥号。元丰改制后寄禄官阶未至正三品、卒殁获赠正三品或以上寄禄官阶者人数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仅以宰执官员为例予以探讨。从宋代迁转、俸禄、致仕、荫补、赠官等诸方面来看,在官员群体中宋廷对宰执最为优厚无疑。这种优厚在赠官方面即有很好的体现,元丰改制后宰相卒殁可赠七官、枢密使赠六官、执政赠五官,相当优渥。在赠谥方面,宋廷也是尽可能地将相关制度规定向宰执官员偏移。相对于宰相、枢密使,担任执政的官员寄禄官阶一般低于前两者,通过对宋代执政官员在任时寄禄官阶的考察可见,中大夫是他们最为常见的寄禄官阶。表2为元丰改制后官至执政、仕履寄禄官阶至中大夫、获得赠官赠谥者。
表2 宋代元丰改制后官至执政或寄禄官阶至中大夫获得赠官赠谥一览表
|
姓名 |
最高阶 |
职事官 |
赠官 |
谥号 |
时间 |
出处 |
|
朱谔 |
中大夫 |
尚书右丞 |
光禄大夫 |
忠靖 |
大观元年(1107) |
(元)脱脱等:《宋史》卷212《宰辅表三》,卷351《朱谔传》,第5517页、第11108—11109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政和元年五月丁亥,第740页。 |
|
苏辙 |
太中大夫 |
门下侍郎 |
宣奉大夫 |
文定 |
政和二年(1112)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5,第2530页;(元)脱脱等:《宋史》卷339《苏辙传》,第10832、10835页。 |
|
许景衡 |
中大夫 |
尚书右丞 |
正奉大夫 |
忠简 |
建炎二年(1128) |
(宋)胡寅:《崇正辨 斐然集》卷26《资政殿学士许公墓志铭》,第564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5,第2530页。 |
|
席益 |
左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左正奉大夫 |
忠清 |
绍兴九年(1139)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5,第2530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三年二月辛亥,第986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5,第2066页。 |
|
刘大中 |
左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左正奉大夫 |
忠肃 |
绍兴十年(1140)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八月戊辰,第 2591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八年三月庚寅,第1028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3,第2072页。 |
|
翟汝文 |
左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左正奉大夫 |
忠惠 |
绍兴十一年(1141)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6,第2530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绍兴二年四月庚午,第978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3,第2072页。 |
|
李邴 |
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正奉大夫 |
文肃 |
绍兴十六年(1146) |
(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70《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参知政事赠太师李文敏公邴神道碑》,第668—670页;(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绍兴十六年五月甲午,第2935页。 |
|
程克俊 |
左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左正奉大夫 |
章靖 |
绍兴二十七年(1157)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6,第2531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丁丑,第1122页;(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庚戌,第3395页。 |
|
杨椿 |
左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左正奉大夫 |
文安 |
乾道三年(1167)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6,第2531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壬午,第1137页。 |
|
陈诚之 |
左中大夫 |
知枢密院事 |
左正奉大夫 |
文恭 |
乾道五年(1169) |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丁酉,第1128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6,第2531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1,第2070页。 |
|
周葵 |
中大夫 |
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 |
正奉大夫 |
惠简 |
淳熙元年(1174)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9,第2076页;(元)脱脱等:《宋史》卷385《周葵传》,第11835—11836页。 |
|
郑闻 |
中大夫 |
参知政事 |
光禄大夫 |
正献 |
淳熙元年(1174)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6,第2074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淳熙元年七月丁亥,第1222页。 |
|
谢廓然 |
中大夫 |
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
光禄大夫 |
荣敏 |
淳熙九年(1182) |
(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淳熙七年五月戊辰、淳熙九年六月丁巳,第1243页、第1247页;(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1,第2063页。 |
|
许应龙 |
中大夫 |
签书枢密院事 |
银青光禄大夫 |
文简 |
淳祐八年(1248) |
(宋)赵汝腾:《庸斋集》卷6《资政许枢密神道碑》,第295页;(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2,淳祐九年正月丁卯,第4699页。 |
以上官员抑或以中大夫卒殁、抑或以中大夫致仕卒殁,仕履寄禄官阶均达到中大夫。宋人马端临指出,中大夫为执政所带阶官,太中大夫以上为宰相所带阶官。[23]中大夫官品为正五品,参照龚延明先生《文臣京朝官寄禄官沿革表》[24],可知不同时期赠五官后分别为:元丰寄禄格至元祐三年(1088),中大夫赠五官为银青光禄大夫;元祐三年(1088)至元祐四年(1089),中大夫赠五官为右光禄大夫;元祐四年(1089)至绍圣二年(1095),中大夫赠五官为右光禄大夫;绍圣二年(1095)至大观二年(1108),中大夫赠五官为右光禄大夫;大观二年(1108)至绍兴元年(1127),中大夫赠五官为正奉大夫;绍兴元年(1127)至淳熙元年(1174),中大夫赠五官为正奉大夫(左、右中大夫赠五官分别为左、右正奉大夫);淳熙元年(1174)之后,中大夫赠五官为正奉大夫。元丰寄禄格至元祐三年期间,中大夫赠五官之后的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二品之外,元祐三年至南宋后期,中大夫赠五官之后均右光禄大夫或正奉大夫,而右光禄大夫或正奉大夫又均为各自时期正三品寄禄官阶中的最低阶。而从上述统计官员也可以看出,许多执政官员以中大夫或中大夫致仕卒殁,寄禄官阶仅为正五品;而通过宋代赠官制度中执政可赠五官的规定,寄禄官阶达到正三品——赠谥资格的最低标准。寄禄官阶至中大夫的执政卒后获得五官以上恩典,则寄禄官阶一定提升至正三品甚至是二品、一品。
这意味着,宋代官员出任执政之后,朝廷极有可能授予其中大夫的寄禄官阶;而卒殁之时,即使其寄禄官阶仍然停留在中大夫,也依然能够通过五官恩数赠官达到正三品的赠谥标准。出任宰相者,寄禄官阶即可达到太中大夫及以上,卒后可赠七官,则寄禄官阶官品一定能够超过正三品,也即达到赠谥资格。不得不说,从宰执特别是执政官员的赠官与赠谥来看,宋廷为执政官员卒殁之后赠官规定的“五官之恩”,其实正是为其能够获得谥号而服务的。尽管不少执政即使达到赠谥标准者最终也未获谥号,多与政治因素相关,但是宋廷通过赠官手段为广大官至执政的官员提升至赠谥的最低要求是切实存在的。宰执之外,宋代一些侍从官也通过赠官提升官阶达到赠谥标准,获得了谥号。当然,侍从官通过赠官提升官阶达到赠谥标准的难度,是大于执政者的。
(二)从宋代武将赠官出发再探赠谥资格
宋代武将也以赠官至正三品作为能否赠谥的契机。宋代武将官阶较之文官阶简单了许多,更为重要的是正三品之上最低官阶即为节度使。即言,宋代武将只有官至节度使或赠至节度使者,方具赠谥资格。武将之中未至赠谥资格、殁于王事、事迹昭著者也可获谥,不过属于特赐谥类别,此处主要探讨武将达到赠谥资格的赠谥情况。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命陈彭年详定赠谥资格时,就涉及到了武将的赠谥资格:“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25]至南宋绍兴五年(1135),朝廷再次规定了武将的赠谥标准:“武臣节度使以上身亡,依条取索本家行状,方许定谥。”[26]武将之中,通过赠官官阶提高至正三品,可以据此获得谥号,表3统计了此类武将。
表3 宋代武将官阶未至正三品、赠官至正三品方获赠谥一览表
|
姓名 |
赠官 |
谥号 |
出处 |
|
王凯 |
彰武军节度使 |
庄恪 |
(元)脱脱等:《宋史》卷255《王凯传》,第8926页。 |
|
曹琮 |
安化军节度使兼侍中 |
忠恪 |
(元)脱脱等:《宋史》卷258《曹琮传》,第8990页。 |
|
夏随 |
昭信军节度使 |
庄恪 |
(元)脱脱等:《宋史》卷290《夏随传》,第9717页。 |
|
周美 |
忠武军节度使 |
忠毅 |
(元)脱脱等:《宋史》卷323《周美传》,第10459页。 |
|
王厚 |
宁远军节度使 |
庄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328《王厚传》,第10584页;(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8《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厚可赠节度使制》,第399页。 |
|
宋守约 |
安武军节度使 |
勤毅 |
(元)脱脱等:《宋史》卷349《宋守约传》,第11064页。 |
|
张蕴 |
感德军节度使 |
荣毅 |
(元)脱脱等:《宋史》卷350《张蕴传》,第11088页。 |
|
杨应询 |
昭化军节度使 |
康理 |
(元)脱脱等:《宋史》卷350《杨应询传》,第11090页。 |
|
张宗颜 |
保静军节度使 |
庄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369《张宗颜传》,第11478页。 |
|
闾勍 |
检校少保、昭化军节度使 |
庄节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8,第2075页。 |
|
关师古 |
昭化军节度使 |
毅勇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7,第2075页。 |
|
梁邦彦 |
保宁军节度使 |
清节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十月丁未,第3612页。 |
|
张潜 |
武安军节度使 |
恭壮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2,第2064页。 |
|
曹传 |
保顺军节度使 |
恭怀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3,第2064页。 |
|
陈广 |
威武军节度使 |
勇节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7,第2067页。 |
|
李端 |
威武军节度使 |
良定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6,第2074页。 |
|
郭钧 |
定江军节度使 |
壮平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8,第2075页。 |
|
王资之 |
奉国军节度使 |
温恭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8,第2076页。 |
|
王胜 |
庆远军节度使 |
毅武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8,第2076页。 |
|
刘从广 |
昭庆军节度使 |
良惠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3《刘从广传》,第13551页。 |
|
刘永年 |
崇信军节度使 |
庄恪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3《刘永年传》,第13552页。 |
|
杨景宗 |
安武军节度使兼太尉 |
庄定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3《杨景宗传》,第13554页。 |
|
李端悫 |
昭德军节度使 |
恭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4《李端悫传》,第13571页。 |
|
高公纪 |
感德军节度使 |
怀僖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4《高公纪传》,第13578页。 |
|
向传范 |
昭德军节度使 |
惠节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4《向传范传》,第13579页。 |
|
韩嘉彦 |
庆远军节度使 |
端节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90,第2062页。 |
|
钱惟济 |
平江军节度使 |
宣惠 |
(元)脱脱等:《宋史》卷480《钱惟济传》,第13914页。 |
王凯、曹琮、夏随等人仕履武官阶最高者为正四品的节度观察留后、承宣使,卒殁之后获得从二品的节度使,从而达到赠谥资格获得谥号。
武将殁于王事、事迹昭著者以及部分外戚通过皇帝特恩形式也能够获得谥号,但是宋代还出现了一些殁于王事、事迹昭著、武官阶较低者以及个别外戚,朝廷通过赠官甚至是数次赠官不断提升其武官阶,直至赠其为节度使后,再赠予谥号。庆历五年(1045)正月,四方馆使、荣州刺史曹傅卒,朝廷诏特辍朝两日,赠其保信节度使,赠谥恭怀。曹傅武官阶较低,因此特予说明“故事,官非三品无谥及辍朝,傅特以皇后兄故也”。[27]任泽为“仙游夫人母弟也。英宗入继大统,召至延和殿,授西头供奉官,赐第一区,宠赉甚厚。神宗时,累迁皇城使,领昌州刺史。护仙游柩迁祔于濮园,真拜嘉州刺史”。卒殁之后,朝廷赠其崇信军节度使,赠谥恭僖。[28]赵士跂在靖康末年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金人驱宗室北行,士跂得间道遁去。居邢州,结土豪将举事。有告者,金人执而杀之”。事闻于宋廷,特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果。[29]宋孝宗时期,魏胜在隆兴二年(1164)“以议和撤海州戍”,金军再次由清河口入侵,魏胜“拒于淮阳”,孤立无援、中矢坠马而亡。魏胜武官阶仅为忠州刺史,宋孝宗特赠其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30]咸淳九年(1273)四月,朝廷下诏褒奖襄城死节者,右武大夫、马司统制牛富赠金州观察使。同年六月,刑部尚书兼给事中陈宜中上言,“樊城之溃,牛富死节尤著,以职卑赠恤下范天顺一阶,未惬舆情”。于是朝廷诏加赠富宁远军承宣使,乃赐土田、金币恤其家。其后,朝廷又赠牛富静江军节度使,并赠谥忠烈,赐庙建康。[31]赵士跂、魏胜、牛富三人均殁于王事,朝廷均赠节度使后赠谥。赵士跂打算集结势力进行抗金,被告发而被金人所杀,宋廷特赠其为从二品的节度使;魏胜抵抗金军、不屈而死,朝廷将其从五品的武官阶赠至从二品的节度使;牛富由于死节昭著,影响力极大,而此时的宋廷又迫切需要能够为王朝舍生取义、誓死保卫之士,在较短时间内对牛富三次赠官,赠官从正五品的观察使、又赠至正四品的承宣使、再赠至从二品的节度使。宋廷对三人的赠官,使他们的武官阶官品都达到从二品,也即具有了赠谥资格,从而再赠予谥号。任泽与曹傅两人均为武官阶较低的外戚,朝廷赠官提升二人官品后方赠予谥号。任泽为濮王妃仙游夫人之弟,也即宋英宗之舅父。因此,武官阶虽仅至从五品的嘉州刺史,朝廷在其卒殁之后特赠为从二品的节度使。曹傅为宋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之兄,武官阶仅至正六品的四方馆使,朝廷在其卒殁之后特赠为从二品的节度使。任泽与曹傅两人均通过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卒殁之后以特赠方式获得从二品节度使的赠官,从而具有了赠谥的资格,最终获得谥号。
(三)从宋代宦官赠官出发再探赠谥资格
宋代宦官也可以通过赠官至正三品获得赠谥资格。宋代对宦官限制较多:宋代对宦官的额数有定额限制,宋徽宗朝之外人数并不多;宦官的升迁往往受到限制,“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若干办御药院,不许寄资,当迁官则转归吏部”[32];宦官不得与外官交结,丁谓由于“乃与宦官交通”由宰相被贬降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33],执政卢益也因与宦官潘永思“颇与之交结”,被宋高宗评价为“卢益观望,阴结永思,非端人也”[34];宦官一般不得领外局职事,李纲指出童贯领外局破坏祖宗法制,“自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始坏祖宗之法”[35],靖康元年(1126)六月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出“内侍领外局职事……非祖宗制,乞赐罢废,”得到宋钦宗批准。[36]
宋代对宦官的限制诸多,因此宦官建节是一件无比困难之事,宦官多通过赠官至正三品获得赠谥资格。宋仁宗十分宠爱宦官王守忠,一度欲为其建节,最终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王守忠自恃为东宫旧臣,数次请求节度使之命。“先是,高若讷为枢密使,持不可,故止”。而后王守忠患疾,再次请求为节度使。宰相粱适曰:“宦官无除真刺史者,况真节度使乎!”宋仁宗曰:“朕盖尝许守忠矣。”粱适曰:“臣今日备位宰相,明日除一内臣为节度使,臣虽死有余责。”御史中丞孙抃闻之,也奏疏极力争谏,王守忠最终没有获得节度使,但“犹得真为留后”。对王守忠拜为正任节度观察留后之命,“言者方奏疏论列”,翼日王守忠卒殁,于是不再议论。[37]整个宋代,宦官建节主要集中在宋徽宗时期,“真庙以来,宦者官虽尊,止于遥郡承宣使而已。宣、政间,始除童贯、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瑴、梁方平等十许人。靖康初政,皆贬夺之。渡江以来,间有为正任承宣使者”。[38]可见,宦官仕履中若想官拜节度使,难度极大;即使皇帝有意打算为某位宦官建节,也会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难以实施。从得谥资格的角度来看,官至节度使或以上方可请谥、得谥,这是宋朝在谥号方面的制度规定,也是与文臣正三品之上标准相对应的,宦官基本上与谥号无缘。
但是,宋代皇帝对于特别宠爱的宦官,仍欲给予他们赠谥之恩。由此出发,赠官就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解决途径,表4即为赠官至正三品方获赠谥的宦官概况。
表4 宋代宦官官阶未至正三品、赠官至正三品方获赠谥一览表
|
姓名 |
赠官 |
谥号 |
出处 |
|
王守忠 |
武康节度使 |
僖安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辛丑,第3145页。 |
|
蓝继宗 |
安德军节度使 |
僖靖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蓝继宗传》,第13634页。 |
|
张惟吉 |
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逾月又赠保顺军节度使 |
忠安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张惟吉传》,第13635页。 |
|
石全彬 |
太尉、定武军节度使 |
恭僖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6《石全彬传》,第13627页。 |
|
卢守勤 |
保顺军节度使 |
安恪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卢守勤传》,第13637页。 |
|
李舜举 |
昭信军节度使 |
忠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李舜举传》,第13645页。 |
|
苏利涉 |
奉国节度使 |
勤懿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0,元丰五年十月丙辰,第7949页。 |
|
石全育 |
太尉、彰德军节度使 |
勤僖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一月甲辰,第5545页。 |
|
李宪 |
武泰军节度使 |
忠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李宪传》,第13640页。 |
|
梁从吉 |
感德军节度使 |
敏恪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9,元祐五年十月乙巳,第10793页。 |
|
冯宗道 |
安德军节度使 |
良恪 |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9,元符元年六月丙戌,第11876页。 |
|
宋用臣 |
安化军节度使 |
僖敏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7《宋用臣传》,第13642页。 |
|
冯世宁 |
开府仪同三司 |
恭节 |
(元)脱脱等:《宋史》卷468《冯世宁传》,第13651页。 |
|
蓝安石 |
保大军节度使 |
良恪 |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58之107,第2074页。 |
|
康谞 |
保信军节度使 |
忠定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乙亥,第3268页。 |
|
黄冕 |
赠保宁军节度使 |
僖靖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五月庚子,第3098页。 |
|
宋唐卿 |
清远军节度使 |
恭靖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1,绍兴二十六年二月己卯,第3269页。 |
|
陈永锡 |
安德军节度使 |
温恭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五月甲寅,第3493页。 |
在此之外,还有一批卒殁时间不详的宦官通过获赠节度使得谥,不再列举。上述宦官中,张惟吉和李舜举需要特别予以说明。张惟吉卒后赠官为正四品的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未至赠谥资格,仅逾月朝廷又赠予保顺军节度使,张惟吉在获得第二次获得赠官之后,拥有了赠谥资格;李舜举虽为宦官,但在永乐城中阵亡,可谓殁于王事,朝廷先特赠其节度使,继而又赠之谥号。因此,从宋代宦官赠官与赠谥来看,由于王朝对宦官的种种限制,宋徽宗朝之外的在世宦官几乎没有建节者,也即生平仕履官阶没有达到正三品以上者。而不少宦官又深受皇帝宠爱,皇帝希望能够在其身殁之后,为其开展赠官、赠谥、辍朝等恩典。而赠官可以说是实现皇帝恩宠宦官身后之事的绝佳途径,无论是按照赠官资序迁转赠至节度使,还是以特恩形式赠以节度使,甚至是通过类似于阵亡武将二、三次赠官的形式赠至节度使,都使得被赠宦官获得了请谥、获谥的资格,从而相关机构可以“名正言顺”地为皇帝宠爱之宦官展开赠谥事宜。
结语
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之外,宋代赠官还具有若干重要意义。宋代赠官对逝者、逝者家属、王朝统治者、在世官员与百姓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赠官对逝者而言,关乎官品、资序、绘像等;对逝者家属而言,关乎赠赙、荫补等事宜;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而言,通过赠官的赠予可以笼络人心、稳定统治;对于在世官员而言,赠官成为其追求之一,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对于广大百姓而言,赠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无论恩荫入仕还是通过科举为官,这种荣宠都吸引着他们为王朝效力。赠官与赠谥对官员强大的吸引力,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站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高度上可以看出,赠官与赠谥不仅是宋代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皇权对官员生死两极的全面覆盖。赠官与赠谥制度经历萌芽、初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等阶段,至宋代日臻完备。宋代赠官与赠谥备受臣僚、百姓的关注与向往,正是其时代价值观的充分体现。官员在世之时,释褐、升迁、贬谪、致仕等都与皇权息息相关;官员去世之后,能否赠官赠谥、赠予何官和谥等仍然与皇权紧密相连。正是由于赠官与赠谥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通过赠官与赠谥朝廷最大程度地将已故官员和百姓全部纳入到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
赠官与赠谥成为时代价值观的体现、实现皇权对宋人的全面覆盖,与宋代的尚官思想也是分不开的。尚官思想诞生很早,宋代官制系统已经相当完善,宋人对入仕为官的渴望程度远迈前朝,又宋代科举取士为中国古代之最,通过科举即可能入仕为官,这种较强的政治流动性大大强化了宋人的尚官心理。为官既可实现政治抱负,又可实现家族夙愿。正是尚官思想的勃兴,宋人在世之时渴望出仕为官,去世之后也希望获得朝廷的赠官与赠谥从而实现“仕途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为其仕途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写作得到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程民生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注释
[①]郭文佳先生考察了宋代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指出宋代军队官员去世后,朝廷往往会赠予官职,以示优抚,并举数例加以阐述。郭文佳:《论宋代军人的优抚保障政策及影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6—21页。吴丽娱先生对《天圣令》中所涉及赠官的赠赙及其与赠谥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高级官员的赠官与谥号常常不可分。吴丽娱先生以《天圣令》的相关内容为切入点,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深入探讨分析了唐代以及宋初赠官与赠谥之间的关系,相当清晰地展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赠官在唐宋时期的重要历史意义。吴丽娱:《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3—438页。
[②]主要参见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杨果、赵治乐:《宋人谥号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丁建军、徐麓枫:《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③]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丧葬令卷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5页。
[④]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页。
[⑤]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页。
[⑥]汪受宽先生对中国古代的谥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探讨臣谥资格时,指出“宋朝必须是曾任三品官者乃谥,赐三品者不得谥。”然仅此而已,并未做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见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杨果、赵治乐两位先生探讨了宋代的谥号,引用了宋敏求之语指出宋代得谥条件十分明确,“‘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方可得谥”,又指出“宋代谥法还有其他一些变化”,再次引用了宋敏求之语“国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赠至正三品,许请谥”。在此之外,并未再对宋代的赠谥资格进行探讨。见杨果、赵治乐:《宋代谥号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第27页。丁建军、徐麓枫两位先生对宋朝官员的给谥资格进行了考察,然仅见“唐朝规定散官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即可得谥。宋朝对于官员的得谥资格亦作出明确的规定:‘惟正三品方得谥,兼官三品不得之’”,将宋敏求之语直接置于文中,再无对赠谥资格进行下一步的考察。见丁建军、徐麓枫:《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50—151页。因此,本文有必要对宋代赠谥的资格问题,再进行探讨。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宝元二年十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4—2935页。
[⑧]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9之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72页。
[⑨]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4页;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正:《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附唐令复原研究·唐丧葬令复原内容及分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91、711页。
[⑩]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8之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16页。
[1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8之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16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90页。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正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9页。
[14]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仪制》11之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29页。
[15]脱脱等:《宋史》卷287《赵安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58—9659页。
[16]脱脱等:《宋史》卷287《陈彭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65页。
[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景祐二年十二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67页。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七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165页。
[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景祐二年十二月乙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67页。
[20]惠鹏飞:《宋代吏部尚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25页。
[21]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8之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16页。
[22]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8之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17页。
[2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4《职官考十八·光禄大夫以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27页。
[24]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4页。
[25]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 29 页。
[26]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礼》58之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16页。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正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735页。
[28]脱脱等:《宋史》卷464《任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83页。
[29]脱脱等:《宋史》卷452《赵士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93页。
[30]脱脱等:《宋史》卷368《魏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60—11461页。
[31]脱脱等:《宋史》卷46《宋度宗纪》,咸淳九年正月乙丑、咸淳九年四月、咸淳九年六月,卷450《牛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1、912、914、13250页。
[32]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四笔》卷16《寄资官》,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2页。
[33]脱脱等:《宋史》卷283《丁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568—9570页。
[34]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辛卯,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20页。
[35]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靖康元年二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33页。
[36]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00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正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251—4252页。
[38]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宦官节度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0页。
作者简介:惠鹏飞,男,河南平顶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本文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