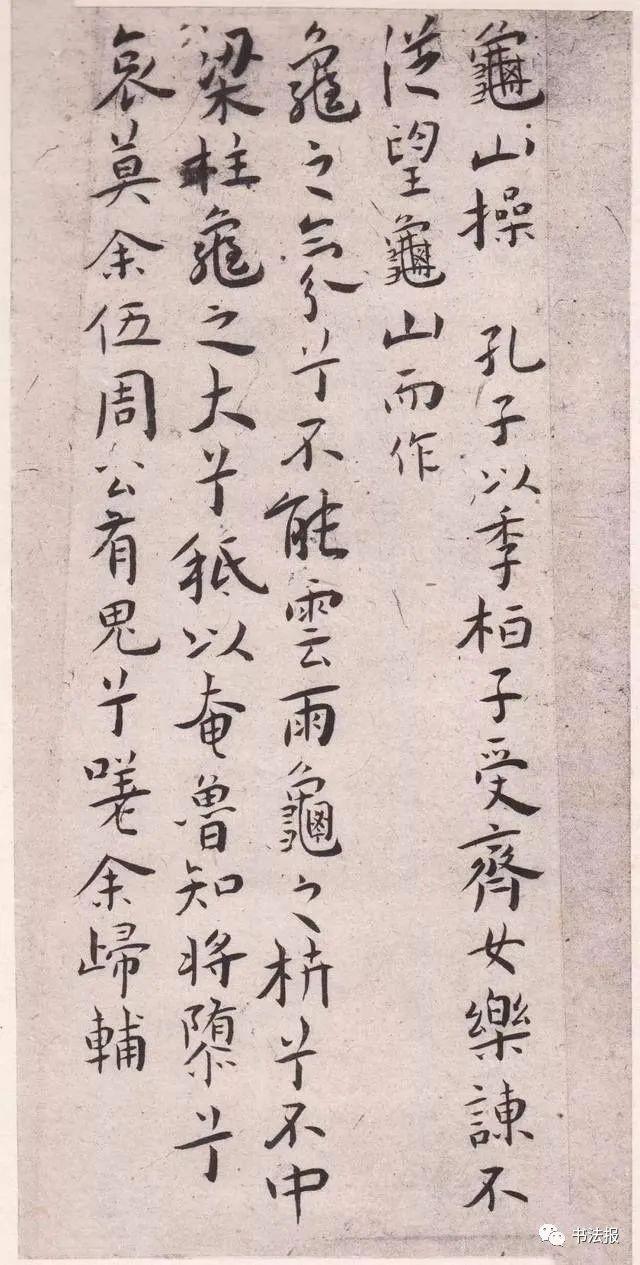无穷小亮的科普地球村讲解员日常(朱晓理解地球村)
理解“地球村”朱 晓,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无穷小亮的科普地球村讲解员日常?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无穷小亮的科普地球村讲解员日常
理解“地球村”
朱 晓
“地球村”,现在是地球人的口头禅了。这个词的发明人是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他1964年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地球村”(global village)。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众口一词说“地球村”,这当然是发明者麦克卢汉的荣耀,不过,众口也有难调的一面——人们从来没有就“地球村”的含义达成过共识。麦氏自己对此也不能前后一致。
就在1964年,麦氏为他所崇拜的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作序,序题为“媒介与文化变迁”,序中有这么一句:
电子技术不是有利于碎片的而是有利于整体的,不是有利于机械的而是有利于有机的。英尼斯没有想到,电在结果方面是整个神经系统的延伸,延伸成一种全球膜。
“全球膜”应该是“地球村”构词的备选方案,这也提示了在麦氏的头脑里“地球村”是有机的、整体的。在这里,“膜”也值得留意,后来在与《花花公子》的访谈中,麦氏就说“整个人类大家庭被用一张单一完整的膜状物密封起来了”;在1961年1月4日致比塞尔的信中还提到过“新的全球感官圈”,“膜”就是地球的一个新圈层。
1961年6月《加拿大建筑师》杂志发表了麦氏的《五官感觉中枢之内》一文,文中说到了地球村的起点:
卫星广播的迫在眉睫,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百多年前世界因为电报就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这有两层意识,一是地球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二是地球村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电报开始了地球村的雏形。
麦氏不是到1964年才在思考“地球村”的。此前四年,1960年12月23日他在写给提尔惠特的信中,既提到了“地球村”,也提到了“地球城”:
今天,有了电子器件,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任务是要创建一个地球城,作为具乡村特点的边缘之中心。这项任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决不是位置。有了电子器件,任何边缘地区都会变成中心,而且在任何中心都可以得到边缘体验。也许,必须以大机场协调多个航班的那种方法,用电脑来建设地球城,去协调策划我们地球村里散乱的感官活动。
这时候,在麦氏的构思当中,“地球村”是“具有乡村特点的边缘”,散乱,特指感官活动散乱;而“地球城”是这乡村边缘的中心,但是感官活动有序是一种什么状态?在这城乡类比的不伦不类中,麦氏的关键词是电子,电子信息使得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这才是“地球村”的基本特征之一。
在同一封信中,麦氏提到了“地球村”的另一个特征:
今日城市规划核心领域的问题就是,地球村越来越多地呈现语言本身的特征,其中包括每一个语词总是包含所有感官,不过是以变动不居的比例,这比例总是容许新的状态以体现它们。
“地球村”呈现语言本身的特征,即人的每一个感知、每一个表达包含他所有的感官,各种感官的比例随时随地变动不居,感官比例本身暗示了瞬间的感知暂留。
1960年10月28、29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举行的人文学术会议上,麦氏是中心人物,在会议第一天他的讲演《技术、媒介与文化》中,他提到:
我们的新科学和数学不仅消解了欧几里得空间,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创造了部落生活的模式。 我们必须理解,信息移动的电子速度和模式为整颗星球创造了口语村的条件。
……
今天,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学习的社区。而大学,不再是一个加工年轻人头脑的地方,而是成为人类交往的标准。校园里发生的人类对话具有一种全球国家和全球社区生活方式的特征。
……
如果对无尽知识的练习和交流提高了人的素质,那么在电子时代,他将有他第一次融入整体的机会去做完人。这样涵盖了所有人和各种知识的人类对话的扩展,在某些人看来,绝对有可能会把地球本身变成一一无二的计算机。
全球范围的部落生活、整颗星球的口语村、全球社区、地球变成一台计算机,这些都可以作为“地球村”的注脚。
从1959年到1960年,麦氏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公休学术假,担任了华盛顿特区全国教育广播协会理解媒介的项目指导。不久之后,他在《理解新媒介项目报告书·总论》中写道:
今天,不言自明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空间里,这空间由同时来自整颗星球上每一个点的信息维持。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一位媒介研究者,一个观点将会有什么可能的实用性呢?他必须采取马赛克的方法。他必须在所有媒介每天都有的相互作用中同时应对它们,否则就要付出离题和不切实际的代价。他应对媒介必须随着每一种媒介对我们所有感官的影响而不是当它给一种感官留下印象的时候。
“全球空间”是“地球村”的又一别称,这是靠同时来自全球每一个点的信息来维持的。
1959年,麦氏在《印刷术与社会变化》一文将近结尾的地方说到:
空间和时间被压缩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报纸上看到的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由关系构成的同时场。
这里的报纸指的是依靠电报的电讯报。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同时关系场,这是地球村很好的注脚了。附带提一下,麦氏所说的“同时性”就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的“共时性”。
地球村的部落色彩,麦氏在1959年5月16日写给摩尔根的信中,就提到过:
部落是一个单元,通过扩展家庭的界限以至于包括整个社会,等到它以一种地球村的模式存在的时候,就成了组织社会的惟一途径。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地球村模式是被信息的即时移动造成的,在同一时刻来自每一处到达每一点的信息。
地球村是“组织社会的惟一途径”,更重要的是,即时信息流造成了“地球村”……模式。
从信息流来俯瞰地球,是麦氏在1953年就有的视角,在《没有读写的文化》一文中,他写道:
今天,整个地球在共同的交互意识方面有了一种整体性,其速度超过了先前一个小城市——比方说伊丽莎白时代有八九万居民的伦敦——的信息流。当现存的社会被新闻业、图片新闻报道、新闻短片和喷气推进技术带入如此亲密的接触时,会发生什么?
信息流和信息速度是理解去来今的钥匙。整个地球的信息流速度超过书面-机械时代的伦敦城,这是理解麦氏“地球村”的关键之一。
在《女王季刊》第60期(1953年)上,麦氏发表了《晚年英尼斯》,文中提到:
随着19世纪通信线路在空间上的延伸,人们开始怀念人类的过去。诗歌和绘画回荡着对古老时代的轰鸣记忆,以力量和金钱的名义对时间所作的侦探游戏产生了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时代所没有的对人类大家庭团结的历史意识。通过将受空间条件限制的传播推向极限,我们今天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和文化大熔炉,这只有到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城市才会结束。
人类大家庭、世界性的民族和文化大熔炉、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城市,都可以作为“地球村”的注脚。
有人说,麦氏“地球村”的灵感,来自于1948年温德汉姆·刘易斯《美国和宇宙人》一书,这书提到了“地球成了一个大村落,电话横跨东西南北”。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就算是草蛇灰线,也不能排除更远的灵感来源。麦氏在1953年的另一篇文章《乔伊斯、马拉梅和报刊》中,引用了法国诗人兼政治家拉马丁1831年的一段话:
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报章杂志将成为整个新闻业本身——整个人类思想本身。自从艺术赋予言论以惊人的增殖能力——增殖能力还将成千倍地增长——人类将日复一日、时复一时、页复一页地写他们的书。思想将以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瞬时构思、瞬时书写、瞬时理解,在地球的尽头——它将从一极传播到另一极。
思想以光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就是130年后麦氏所说的“地球村”了。在第一种电子媒介电报发明之前六年就见及此,马拉丁可谓先知。
“地球村”问世之前,麦氏的思路变化,大致堆栈如前;问世之后,麦氏并不墨守术语。他1957年在《16世纪机印书对语言的影响》一文中说,中世纪“有个性的作者们都认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思想的发展而自由地定义和制订任何特定的术语”,这也可以看作是麦氏自况。他在“地球村”这个概念上与时俱进地切换思考方向,我们不妨顺着时间轴来扫描一番。
《理解媒介》出版之后第二年,麦氏以长文《我们的地球村》为人演说“地球村”:
地球村的电子文化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全部的小群落通过一种“肉眼可见的示意动作”相互交流,这根本不是惯常的语言。
“地球村”是电子文化的概念,地球村里的交流是图像交流,也不全是语音交流,根本不是惯常的文字交流。
地球村里所有的落后国家都像美国黑人或西方世界十几岁人一样,被电子环境所激发。读写社会里年龄较大的人们很不容易受到激发,因为他们的感受性在一套视觉模子里已经硬化。我们自己社会中尚未使用文字的、识字但不会书写的和无读写能力的人不仅“受毒品刺激而兴奋”,他们还跟过时的读写-机械文化作对。
这一段里重要的是,地球村是电子环境激发而成的。其他的怪力乱虽无神就暂不纠缠了吧,徒增口水。
在离开地球村这个主题开始讨论这些新主题之前,让我们沉思一下约翰逊总统是新的麦哲伦这个报章大标题,在我们这个同时性的小世界,美国的管理作业允许最高级别的政务在复活节岛的歌唱舞台旁或者北极浮冰上进行。
地球村是同时性的小世界。
1967年秋,麦氏离开多伦多大学一年,到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担任阿尔伯特·施韦策人文教授。9月18日,麦氏给选修了他的课程的200多名学生讲了第一堂课。课中提到:
詹姆斯·乔伊斯这样说这一点:“城市,它成球状。”城市在范围上变成了地球的象征,而地球反过来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地球被通讯的速度缩小了。空间被缩小到几乎为零。
地球村的另一面还是地球城。这时,麦氏从乔伊斯那里找到了“地球城”的新依据。六年之后,1973年,麦氏与工程师合写《论证:电子世界中的因果性》一文,说乔伊斯用“urb”(城市)、“orb”(球)两个字营造出共鸣意义的宇宙:“球形城”和“城市球”。这也提示人们应该从共鸣意义来理解地球村。
1967年同一年的文章《一种媒介竟会占用并开拓另一种媒介,这是自然的吗?》又回“村”了:
电子时代的媒介用一时所有事取代了一次一件事。信息以近乎光的速度流动,已经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产业。相应地,对这样的信息的消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整颗星球一方面成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同时,就其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言,整颗星球已经成为一个小村庄。
相互关系日益紧密,地球就村了。
当年年底在给汉弗莱的信中,麦氏复述了《我们的地球村》中的一个意思:
今天,在我们这个由即时传播创建的地球村里,所有落后国家都成了对发达国家的“威胁”。就像我们国内的黑人和十几岁人,他们受新电子时代的刺激而“兴奋”,他们从未经历过工业时代或19世纪,他们是从最新的电子信息着手的。
地球村是由即时传播创建的。更重要的是,地球村里的人“是从最新的电子信息着手的”,不背历史包袱,也不背历史财富的包袱。所谓“威胁”,也只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968年4月,《时尚芭莎》上发表《麦克卢汉看时尚》,在其中第一节“整个世界就是一场偶发艺术”中,麦氏这么看地球村:
■电子媒介创造了一个地球村,在这里,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被分享,人人同时分享;在这里,人们之间、艺术之间、思想之间的所有的壁垒都被推倒。在这个极其混乱的环境里,待解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数据选择和数据处理的问题。
地球村的第一推动力是电子媒介,而非政府;地球村里无隔阂,当然也没有防火墙;混乱是地球村的常态,极其混乱;地球村问题的解决方案藏在信息选择和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地球村就是一场引观众参与的偶发艺术,这可以作为麦氏后来的口头禅“环球剧场”的注脚。
1968年12月,麦氏在《花花公子》发表了一篇关于媒介的文章“过热意象的逆转”,示范了很独特的思维拓展。随后,《花花公子》派人登门采访,麦氏尽情发挥了一番。关于地球村,他说:
一定要记住电子媒介的基本要点是:它们不可阻挡地改变每一组感官比例、重建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和制度习俗。我们传统政治体系的彻底革新,仅仅是因电子媒介而形成的重新部落化过程——这正在把这颗星球转变成一个地球村——的一个表现。
地球村就是因电子媒介而起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因为电子技术而正在形成中的地球村环境比昔日标准化的机械社会,激发了更多的间断、多样性和分歧;确切地说,地球村使得极大数量的争论和启发想象力的对话不可避免。同质和稳定都不是地球村的特征;更多的可能是,矛盾冲突与友爱和谐的程度一样——这是任何部落民族惯常的生活方式。
地球村与机械社会形成对比,包含更多的间断、多样性和分歧;在地球村里,对话是必须的;在地球村里,“矛盾冲突与友爱和谐的程度一样”。
世界部落基本上会是保守的,这是真的,就像每一个传统风格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一样;有一种神话般的自然环境超脱时空,几乎不产生极端的社会变化。每一种技术都成了共有规矩的一部分,部落用规矩来极力保持稳定和长久;就其本质而言,一个口头-听觉的部落社会是被人根据听觉空间仿造成的一个同步的整体场,其中的关系、叙事与视觉世界格格不入,在视觉世界里,观点和目标把社会的变化当成了一种必然的、一再重复的附带结果。一个因电子而内爆的部落社会,抛弃了线性向前的运动“进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随着我们开始对地球村的挑战作出深入反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家是如何变成反动派的。
“世界部落”,与“地球村”同构。调换一下字眼的位置,概念仍旧成立:世界村,地球部落。在电子时代,随着深度卷入或者被卷入地球村,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书面文化的反动派,或者说书面文化因电子文化的深入,必然成为不合时宜的反动文化。
电子媒介将创造一个属于退出者——他们从旧的碎片化社会及其受到整齐划分的分析功能中退出——的世界,同时促使人参与进到新的浑然一体的地球村社区。
浑然一体的地球村。
1969年7月30日,麦氏在给洛伊维尔的信中就把“地球村”改成了“环球剧场”:
电视世代中的部落化风俗习惯和更多东方化的道德观念,根植于一种响应,既是对瞬时形象式电视图像的响应也是对地球新的人造卫星环境的响应。后者把整个地球改造成一个环球剧场,在其中,职责和制服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事物,而且每个人都探索“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探索穿着独特的服装去完成独特的角色。
环球剧场对应于角色的话题,地球村对应的是社群。
1969年,麦氏与斯特恩交谈过多次,斯特恩根据录音编成《斯特恩问答录》。在其中,麦氏两次提到地球村:
任何一个家庭在一个屋檐下,比起同一城市成千上万的家庭来,多样性较多、相似点较少。你创造越多的村庄环境,不连续性、分歧和多样性就越多。地球村绝对保证了在每一点上的最大分歧。我一刻也没有想到,统一和安宁是地球村的特征。它有更多的恶意和嫉妒。空间和时间被从人群中抽出来。一个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深度接触的世界。
麦氏一刻也没有畅想过地球村的统一安宁。地球越是村就越多不连续性、分歧和的多样性。地球村在每一点上都保有最大的分歧,地球人们在分歧中不断地深度接触。
部落-地球村比过去任何民族主义都制造更多的分裂——充满了搏斗。村庄是深度裂变,而非融合。人们离开小镇是为了避免陷入其中。大城市以其统一的、非个人化的环境衬托着他们。他们追求礼仪,在城市里,钱是靠规则和可重复性赚来的。在你有巧匠一般的多样性的地方,你创造的是艺术品,不是金钱。村庄不是寻找理想的和平与和谐的地方。完全相反。民族主义从印刷品中来,为地球村环境准备了一场令人惊奇的消解。我并不赞成地球村,我是说我们住在里面。
“地球村”是部落-地球村的简称。值得深思的是:“地球村”一词的发明人“并不赞成地球村”,可是“地球村”的使用者却有太多的畅想。
在1970年与巴林顿·内维特合写《来听者》评价彼得·德鲁克,麦氏在“组织结构大师”一节中捎带了一句:
美国的西进现在已经以越南告终(走出始于东方的西方),这以后又在向月球进军中以庞大的军事预算反弹!新的边疆是一个旧的陨星垃圾堆——月球,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乡村,一个在疆界以外的边疆。
在向月球进军的时代,月球这一新的边疆被麦氏视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乡村、疆界以外的边疆,联想一下月地关系,这可以作为“地球村”的一个很特别的注脚:地球村不必是连续的。
在1971年2月17日致华生的信中,麦氏把地球村改称为“电磁城”:
凭借着电——无论在电话上或者广播上或者电视——被传送的人正是传送者本人。我们在想象中亲身被电带入特定的时空。因此,电磁城的人都是天使,毫不夸张。
这两句话里,重要的是“天使”二字。电子人的天使化,是麦氏的重要思想之一。
两个月之后,麦氏又换了一种说法,致戴维斯信:
作为一个了解70年代的人,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环境中。另一方面,你的很多同事还被困在19世纪的旧硬件环境中。作为一个对70年代的教育和对话有梦想的人,你会看到它被“硬件”迷们阻挠。作为一个能够满足连线星球的本地政治要求的人,你打交道的那些人,他们的关于70年代的当下需求和机会的眼界依然被旧式专家的道德“目标”所掩盖。
越明年,麦氏在为英尼斯《帝国与传播》的重版作序时,进一步把地球说成“为过载信息所累的连线星球”。连线星球,算是强调了地球村的底层硬件吧。别忘了,连线也是为了接触。
大约在1972年,麦氏与人合著的《把握今天》中的“宣言”,解说了地球城或者地球村的一个细节:
同时性是处理地球城的过程中的新闻形式。同时性是侦探故事和象征主义诗歌的写作套路。
地球村的同时性,不宜作计时器之想,要想到侦探小说的由果及因,要想到象征主义艺术里的蒙太奇、马赛克等等碎片-整体的效果。
麦氏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顾问,给他写过不少信,1974年3月26日的那封为地球村另安了两个别称:
用发明了“第三世界”一词的巴兰迪耶的术语来说,有19世纪工业主义的第一世界和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第二世界,还有被排除在这些恩典之外的第三世界。他肯定忘了第四世界,即时的全球村,自有人造卫星(1957年10月)以来,它创建了地球号宇宙飞船,一个没有乘客只有船员的生态实体。
第四世界,即时的全球村。地球村是第四世界,只是说地球村不同于第一、二、三世界。麦氏从来没有承诺过前后一致,他在1979年以录音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人与媒介》中说“第四世界是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混在一起的电子世界”。也许可以调和一下两处的提法:混而不同,说明地球村是整个世界的平行空间。
地球号宇宙飞船,是地球村很好的注脚。对于麦氏一时兴起说出的种种别称,列位看官也不要轻忽,因为在当下的语境里,这别称也许能够引发思维的穿透力。1974年7月24日,麦氏写给《多伦多星报》编辑部的信,又冒出一个别称:
在昔日——在电报出现之前——信息慢速度的情况下,人们有着超脱和客观的习惯,这些习惯不足以阻碍全面卷入和沉浸到那世界池中。
世界池,地球村,是同义词。世界池有助于流体想象——信息流、事件流——这让人更好地理解麦氏津津乐道的卷入和沉浸。
1977年12月28日,麦氏作客安大略省电视台公共事务节目《迈克·麦克马纳斯的启迪》,两次提到地球村:
我认为如今我们正在倒带播放地球村,我们将回到二分心智,这是部落的、集体的,不带任何个人意识。
倒带播放是麦氏的理想实验,就像爱因斯坦有他的理想实验一样。不过,麦氏在这里思维跳跃太大,不是倒带播放地球村,而是倒带播放口语-部落文化转变为书面-机械文化的崩解过程以联想地球村的整体化过程。
地球村是一个由非常艰难的边缘区域和非常粗暴的环境构成的场所。
这句话表达的不是地球村既边缘又粗暴,而是麦氏垂老的沮丧。这是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了。
仅仅三年之后,1980年12月31日,媒介研究的开创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睡梦中弃世,他不在他发明的“地球村”活了,享年69岁,古来稀的先知。
麦克卢汉走了,地球村向何处去?麦氏留给地球人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一个答案集,或者说一团语义云。这云,就像笼罩蚁群的信息素,任何一只蚂蚁都不知道蚁群向何处去,蚁后也指明不了任何方向,蚂蚁在即时信息的环境里交流合作,协同走向未来。当然,其中也许有那么几只蚂蚁或者一小撮蚂蚁,社会化程度不高,在反常的低信息水平里自欺欺人,不交流,不合作,既边缘又粗暴,它们很快就会被已经发生的未来湮没的。
向马歇尔·麦克卢汉致敬!
本文中的引文摘自《读麦·讲演》《读麦·访谈》《读麦·书信》《读麦·文萃》,朱晓译按,博登书屋·纽约,2021年7月至2022年4月出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