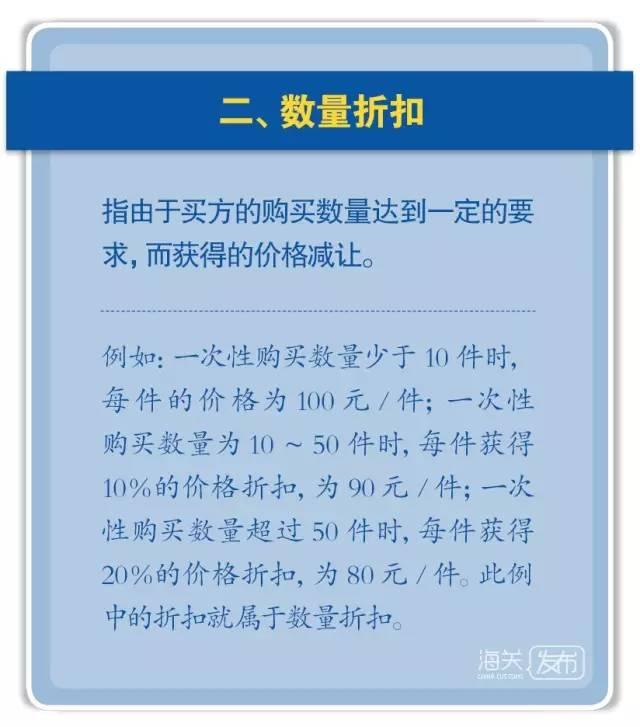杨卓成妹妹叫什么(杨卓成阅读母亲)
原标题:阅读母亲作者:杨卓成(中国作协会员,现居云南),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杨卓成妹妹叫什么?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杨卓成妹妹叫什么
原标题:阅读母亲
作者:杨卓成(中国作协会员,现居云南)
半个多世纪前,我十岁那年,追随母亲到了她任教的学校。
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一座寺庙改建的小学校里,母亲待了好多年头。
她教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地理、自然。从小学一年级到高年级的课她都教过,有女教师请产假,有班主任借调出去,便由母亲顶替上课,她教的课多且杂乱,似乎是学校里的全能教师。
我当时已上小学四年级,算是外校转来的插班生。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殊的班上,这个班大半是女生,经常有人迟到和旷课,退学也时常发生。当时,在我们那地方,女孩子能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找猪草、洗衣服、担烧柴这些活计,才是她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样的班上,学习风气能好到哪里去?我心里有些窝火。我从老家来投奔母亲,为的就是借母亲的光,受个优质的教育,将来谋求个好的出路。母亲在本校任教,就是凭着薄面,也不至于安排到这样的班上。在我上学的事情上,母亲肯定没有尽到责任。
那天上午,我见母亲拿着课本走进教室,心跳立刻加速。这个出了名的问题班,四年换了五任班主任,最近一任仅仅来了一个月,就说身体差,不适宜做班主任的工作。难道就该母亲来吗?母亲真是窝囊到了极点!
母亲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窗外白云浮动,微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搅得我心烦意乱。下课后,我飞快地奔出教室,故意与母亲拉开距离。母亲抄近路追上了我,她喘着粗气,轻轻帮我拍掉身上的灰尘,递给我一个布袋说:今晚有事儿不回去吃饭了,对付一顿,你来跟妈妈做个伴儿。
布袋里放了五个煮熟的洋芋,几根大葱,半小碟老酱。我身子一缩坐在了草地上,伸手就去抓洋芋。母亲拍了下我的手:洗洗手去,讲究卫生。我没说话,也没起身,心里还堵着没发泄出来的无名火气。此时此刻,我恨透了母亲,我对母亲的情感,仿佛突然消失了。
母亲望着我,没作声,用喝水的口缸从山梁下的水沟里取了水来,一点点淋在我手上。水很凉,滑在手上,如母亲的指尖掠过。我不好再任性,顺从地洗好了手,消灭了五个大洋芋。
母亲替我擦去嘴角的残渣,带着我朝山路走去。走啊走,直到太阳西下,我们才来到一个村口。一条小河,缓缓从村中穿过,映着太阳的余晖,缥缈而神秘。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正挽起裤腿站在水里忙碌,有的浣衣,有的淘猪草。母亲和她们闲聊了一会儿,又向她们打听了个地址。母亲要去的地方不好找,又问了好多人,终于找到了。
此时我才知道,母亲是为了让一个叫美唤的女孩子复学。在母亲的一再劝说下,美唤的父母终于松口了,说他们家离学校远,得给孩子置办套住校的铺盖,家里一时凑不出钱,只能等等了。
那天很晚了,美唤才回来,背上是一大篮猪草,见了母亲,连忙放下背篮给母亲行礼。那一晚,母亲跟美唤说了很多话,直到月上树梢,我已经困得两眼朦胧,母亲才起身要走。
美唤站在门口目送我们出村。前方卧着一条黑狗,美唤远远地说:这狗仔乖巧,不咬人的。我心里踏实了,放心地紧跟着母亲往前走。一轮明月挂在天上,如一面刷净了的铜锣。母亲回过头来,正要跟我说几首明月的古诗,见一条黑影已蹿到了我身后,我的大腿被狠狠地撕了一下。母亲声嘶力竭地呵斥狗仔,美唤一家也赶来帮忙,黑狗才夹着尾巴跑了。
母亲仔细查看了我的伤口。原来不是说好不咬人的,怎么就真下口了?母亲自言自语,边说边往我的伤口上吹风。母亲用嘴贴在伤口上,吮吸着血污,一口,两口,吸一会,就往地上吐几口污水,像树上捉虫的啄木鸟。我没感觉到一丝疼痛,只有柔柔的暖流滑过。
母亲吸了一会,累了,抬起头来,月光下,我看到母亲眼中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我劝母亲,这么一点伤口,根本不痛。话音刚落,一滴湿热的液体掉落在我脸上。
我从没见过母亲流泪。那晚滴落在我脸上的液体,也许根本就不是泪水。借着月光,我偷偷看了看母亲的眼睛,依然是那么平静,没有恐惧,没有忧怨,也看不到一丝后悔。母亲平时话不多,那晚就更无语了,默默地一直走到学校。
母亲见校长宿舍的灯还亮着,就让我在门外等着,她进去跟校长说事。暗夜里,我听到母亲的声音越来越高,提到了美唤、铺盖,校长只是慢条斯理地打着哈哈。哈哈打得多了,气氛明显有些紧张,我在门外都感觉到了校长压抑着的愤怒。可母亲没感觉到,依然不停地讲。在后来的教职工大会上,母亲仍旧紧追不舍,提出学校应该为困难学生解决些实际问题。校长非常难堪,连哈哈都打得不那么顺畅了。
没过多久,母亲接到了一纸调令,那是一所更偏远的山区小学。
新学校也是由寺庙改建而成,但寺庙更小些,办学规模也小得多,两个教室,十多名学生,却有四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此起彼伏,如同变魔术。到新学校的那天下午,我们来得急,没备下当晚的口粮,村里又没有买东西的地方,只能顺其自然了。
母亲点火烧了一锅水,让我先喝些水,她出去看看能否找点吃的。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我有些伤感,母亲的肩上,不但担着事业,还担着我们一家人的生计。我突然想到了母亲的几个朋友,据说有一位还在省里当官。我得提醒母亲一下。
母亲回来,掏出两枚鸡蛋。她将鸡蛋煮熟,吩咐我,今晚一枚,留下一枚明日做早餐。她明天放学后下山,晚上回来才能有米下锅。我剥着鸡蛋,眼光却一直没离开她的眼睛。窗外,一只暮归的老鸦正伏在柏树上嚎叫,冷风从门缝中挤进屋来,此情此景,又冷又饿,我估计她鼻子一酸,泪水马上就会涌出来,乘着这机会,我要向她提提那几位老朋友的事。有的时候,一个念头也许真能改变命运。
但母亲似乎丝毫没有感伤。她找出本厚厚的线装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仿佛她已经吃得五饱六足,正在消遣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真弄不懂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被狗咬伤的时候,她伤心得落泪,此时却又若无其事,她难道不冷不饿吗?
吃完鸡蛋,我喊了声母亲。我实在忍不住了,跟母亲说起了她那几位老朋友。母亲头也没抬,低声对我说,自己的事,自己办,找什么麻烦。早点洗洗睡吧,新到一个地方,总得适应几天。见母亲无心谈她那几位老友,我的心都凉了。由于我的存在,这个学校冒出了个五年级的学生,母亲得从一年级的课程备起,一直到五年级,她这么辛苦,我不忍再添乱了。
我学习很努力,效果却不好。五年级只有我一个学生,母亲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也就格外地吝惜,不可能给予我过多的辅导。母亲劝我转回老家去读,可村里的学校只设了初小,上高小得跑十几里路。但即使这样,我也想回去了。
母亲嘴上说让我回去,却始终没送我走。后来母亲的工作调动了,虽然条件越来越好,却都是在学校里打转,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堂。直到退休。
我后悔去参加母亲的光荣退休座谈会,在会上,我亲耳听到领导说,组织上曾多次安排母亲转行,公安、法院、体育等部门任由她选,都被母亲谢绝了。听到这话,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看着母亲满脸放光,好享受地听着组织上给她的各种荣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她的儿子。
母亲退休了,本应静养的人反而忙碌起来,除了来看望她的学生、朋友外,不时还有人来拜访她,找她要资料,看她的纪念章,让她口述回忆录。我有些好奇,多方打听,才了解到母亲是位资历很深的老革命,还在念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工作。
熟悉母亲的人都说,母亲是当地的一部活字典。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紧随母亲多年,并没真正读懂母亲。但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加,我一定能更多地读懂母亲。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0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