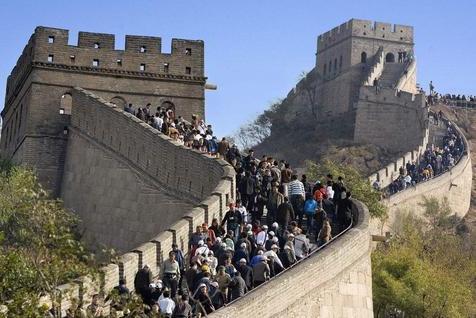粟品孝答辩(粟品孝苏学盛于北)
本文原刊于《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感谢粟品孝老师赐稿!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 要: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关键词:“苏学盛于北”;金朝;理学;经学

作者简介
粟品孝,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和巴蜀历史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金朝在灭掉辽国和北宋后,占有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与南宋形成长期对峙之势。这一新的政治格局,对于北宋中期以来兴起的宋学各派在区域空间上的发展传播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认为以三苏父子特别是以苏轼为代表的苏氏之学,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以致明清学者有“苏学行于北”“苏学盛于北”的概括。当代一些著述也对此力加论证,[1]其中魏崇武一文虽然主要是从“苏学盛于北”说的来龙去脉的角度讨论,但最后仍是强调苏轼曾对金元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讨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这里的“苏学”限定在苏氏的文学以及书画艺术的范围,这也是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也就是说,不仅苏氏的文学、书画,其经学著作和思想也对金朝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笔者所见,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大约是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篇主要讨论金朝朱子学的论文中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苏学盛于北”之说,但有这样的表述:“苏轼在北方不仅仅作为一个‘文学之神’而存在,同时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其著作如《东坡易传》《书传》,还有今日已经失传的《论语解》,乃至其弟苏辙的《诗集传》,都在北方盛极一时。”[2]不过在深入研究金朝儒学的美国学者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和包弼德(Peter K. Bol)看来,此论未必成立。田浩指出:“金代学者显然是欣赏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不一定是他的文化哲学。”[3]观其全文,这里的“文化哲学”是指超越苏轼之“文”的儒家之“道”。包弼德的语气更加肯定:“苏轼在金朝一般被当作‘文学性’人物来对待,并且‘文学性’而不是‘哲学性’才是这场知识复兴运动的中心。”[4]二人对吉川观点的修正似乎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和肯定,相反,一些学者还加以反驳。如刘辉在《金代儒学研究》中就说:“田浩先生所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亦不尽然。观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对苏氏之学的议论,足见他们已经把握住了苏氏哲学的精髓,他们对苏学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学术旨趣上的趋同所致。”[5]杨珩在最近出版的关于金代儒学的专著中没有提到上述观点,但她在引用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说后指出:“苏学对金地域内文人士大夫的影响颇深”,接着又写道:“从儒学方面来看,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著述主要有《苏氏易传》《论语说》《书传》,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蜀学的经学注疏等”,[6]显然杨珩对翁氏“苏学”的理解,是包括了苏氏的经学著述和思想的。另外,由于晚清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在其《经学历史》中也有“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表述,以致当代学者周良宵等在《元代史》中谈“金代的儒学概况”时就说:“三苏之学盛行于金,清人翁方纲、皮锡瑞都早便指出。”[7]韩钟文在《中国儒学史·宋元卷》中论及宋金时期儒学在北方的传播与演变时也说:“三苏之学盛行于北方,皮锡瑞在《经学历史》早已有评述。”[8]
现在的问题是,清人翁方纲、皮锡瑞所谓的“苏学盛于北”是否可以理解为苏氏(尤其是苏轼)的经学著作和思想在金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呢?或者说,“苏学盛于北”的“学”是否有更宽泛的指称,不仅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经学、哲学思想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先来回溯一下“苏学盛于北”说法的由来及其具体内涵。
二、“苏学盛于北”说的由来及其具体内涵
关于“苏学盛于北”,学界一般喜欢引用清儒翁方纲(1738—1818)的表述。翁氏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有宋南渡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金朝)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9]并有“程学盛南苏学北”的诗句。[10]这些说法概括力强,为学界津津乐道。但实际上,翁方纲的说法远有端绪。前述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一文已有很好的论述,下面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梳理。
(一)明朝初年宋濂所谓“洛学在南,川学在北”及其表述渊源
魏崇武指出,后世流行的“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说法,“肇始”于元末明初的大儒宋濂(1310—1381)。[11]宋氏在《跋东坡所书眉山石砚歌后》中写道:
自海内分裂,洛学在南,川学在北。金之慕苏,亦犹宋之宗程,又不止宝爱其书而已。呜呼!士异习则国异俗,后之论者,犹可即是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寘品评于字画工拙之间也。[12]
这里的“川学”,即是“苏学”。诚如魏先生所揭示的,宋濂的说法与元末明初程朱理学地位不断强化的思想环境和宋氏自身的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因此他继承了朱熹扬程抑苏的立场,从学术偏正的角度批评了苏学的不正。[13]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了这种学术环境之外,单从这一学术概括来说,宋濂的说法是否还可以追溯呢?
应该说,在宋金分裂时期,以二程洛学为奠基的理学主要流行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当时北南双方学者、宋金以来的学者对此都是公认的;但苏氏之学并不限于北方,在南方同样流行,这一点宋末元初学者就有观察和总结。如四明(今浙江宁波)人袁桷(1266—1327)就说:“方南北分裂,两帝所尚,唯眉山苏氏学”,“宋金分裂,群然师眉山公,气盛意新,于科举为尤宜”。[14]事实也正是如此,三苏尤其是苏轼在金朝和南宋都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曾枣庄等著的《苏轼研究史》对此有集中的论述。[15]南北双方均推崇的“眉山苏氏学”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宋濂的“川学在北”这一局限于北方区域的说法呢?
这一问题或许与元代学者认为北方文学胜过南方文学这一较普遍的看法有关。元儒这一看法,邱轶皓在《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一文中已有初步揭示,[16]兹不赘述。这里要补充的是元儒虞集(1272—1348)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的分析。这是一篇讨论宋金元时期文学演进的长篇序文,大意是说北宋欧阳修、苏轼文道合一,达到了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到南宋,理学太盛,“说理者鄙薄文词之丧志,而经学、文艺判为专门”,文学、文风衰败不堪;而在北方地区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承袭此风,元朝文学也有“雄浑之气”,并出现了理辞兼胜、文道合一的刘桂隐。[17]大约正是由于虞集等人认为“多有得于苏氏之遗”的金朝文学胜于南宋文学,后人遂有“川学在北”的进一步概括和提炼。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上引袁桷、虞集和宋濂的话,都是在讨论文艺、文风时说的,似乎没有涉及苏氏的经学和哲学思想。
(二)明朝前期张弼提出“苏学行于北”说,后成为流行说法
比宋濂晚数十年的张弼(1425—1487),在谈到金朝蔡松年等人的书法有苏轼笔意时指出:“当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金之尊苏与孔子并,故习其余风,皆有类耳。”[18]不难看出,张弼说法脱胎于宋濂,他把宋氏的“洛学在南,川学在北”改为“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把宋氏的“金之慕苏,亦犹宋之宗程”改为“金之尊苏与孔子并”。不过在价值观上已大变,张弼是尊苏的,同时又是理学家,因此没有学术偏正的价值判断立场。
尽管宋濂和张弼的价值立场完全不同,但他们均是从书法艺术这一角度入手,以对称性的手法来表示程学和苏学在南北两大区域的流行情况,而且都特别强调金人对苏轼的尊崇和仰慕。尽管他们没有界定“川学”或“苏学”的内涵,但从他们行文入手情况来看,说这里的“学”更多还是文学艺术、风格气质的层面,而非儒家经学,当更接近事实。
较张弼更有名望的丘濬(1418—1495)则在弘治年间(1488年后)为宋儒杨时争取孔庙从祀的奏疏中写道:“在宋金分裂之时,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虽伊洛之间不复知有程氏之学。”[19]丘濬这里重点是说二程之学之所以盛行于南宋,杨时是很有贡献的,北方没有杨时,以至理学中断,甚而二程长期讲学的“伊洛之间”也没有程学的传播,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无疑,丘氏言说的核心是在褒崇杨时,为杨时争取孔庙从祀。因此这里虽然提到了与“程学”相对的“苏学”,但通篇文字再无有关苏学的情况。可以说,丘濬只是对当时流行说法“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的引述而已,从中看不出他对“苏学行于北”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也没有明确说苏氏的经学盛行于北方。后来章潢(1527—1608)编纂类书《图书编》,也只是将丘濬的奏疏摘编入内,没有任何阐释。[20]
晚于张弼、丘濬一百多年,也比章潢晚数十年的冯从吾(1556—1627),生活在明朝理学大盛之时,他用心编撰《元儒考略》,旨在表彰元朝理学。他在为北传理学的赵复作传时写道:“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洛闽之学惟行于南,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苏氏之学。”[21]这里前一句的“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出自《元史·赵复传》,后一句“洛闽之学惟行于南,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苏氏之学”,应该是对前贤“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的另一种表述。他这里特别使用了“惟”字,显然不符合事实,意在夸大北方理学的荒芜情况,以此来突出赵复北传理学之功。应该说,冯从吾这里所谓“北方之士惟崇眉山苏氏之学”也只是对前贤“苏学行于北”的变通性表述,并没做特别的诠释,也不能说他的意思就是苏氏的经学盛行于北方。
(三)清朝初年王士祯改提“苏学盛于北”,后来翁方纲反复宣扬
到清朝初年,学者王士祯(1634—1711)在一段诗歌评论中,把“苏学行于北”改为“苏学盛于北”,“(宋室)南渡以后,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金元之间,元裕之其职志也,七言妙处,或追东坡而轶放翁”。[22]王士祯虽仅一字之改,但程度明显加深。他这里虽然还是将程学与苏学对举,但着重强调的是苏学在北方金朝的盛传情况,并正面肯定苏轼对元好问(字裕之)文学成就的重要影响。其“苏学”之“学”,明显是指文学。王说为学者少见,以致有学者说“苏学盛于北”是从翁方纲开始的,[23]从而把“苏学盛于北”之说缩短了一百多年,这是应予纠正的。
当然,后来翁方纲所说的“苏学盛于北”最有影响。从目前的梳理情况来看,翁氏只有一处沿用了明朝诸儒“苏学行于北”的说法,前已引述。他更多的还是说“苏学盛于北”,如在《石洲诗话》中就说:
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按指元好问)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
尔时苏学盛于北,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所以士大夫无不沾丐一得,然大约于气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蕴。[24]
“金人之尊苏,不独文也”,是说不仅苏氏的诗文得到推崇,还包括苏氏的豪放风格或忠义之气,即所谓“气概用事”,前引元朝虞集说金朝文人“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也是此意,绝不是指苏氏的经学或哲学思想。
除了诗话以外,翁氏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也多次使用“苏学盛于北”的说法,如在《斋中与友论诗五首》之一中就写道:
苏学盛于北,景行遗山仰。谁于苏黄后,却作陶韦想。[25]
在一首题为《再题》的长诗中也有这样几句:
当时苏学盛于北,明昌未出遗山翁。
谁言党禁所泐毁,尚与墨本追沈雄。
苏门果有忠臣在,藏锋百态谁与穷?[26]
我们知道,翁氏的诗学出于黄叔琳,而叔琳得自王士祯,翁、王二人之间是有学术上的“血缘关系”的,[27]因此可以肯定翁氏“苏学盛于北”说有着王士祯的影响。他在《复初斋外集》诗卷第十七的《代杨钝夫作》一诗中所谓的“古云‘苏学盛于北’”的“古”,至少就包含已经作古的王士祯。
从翁氏多次使用的情况来看,他所说的“苏学”,主要是指苏氏的文学方面,包括文风(所谓“气概”),绝没有扩大到苏氏的经学层面。大约正因为如此,所以清末光绪七年(1881)方戊昌在为遗山先生元好问文集作序时,明确写道:
尝论宋自南渡后,疆宇分裂,文章学术,亦判为两途。程氏之学行于南,苏氏之学行于北。行于南者,朱子集其大成;行于北者,遗山先生衍其统绪。[28]
这里就把程氏之学和苏氏之学的“学”分得很清楚,分别是指“学术”和“文章”,对应的主要就是经学与文学。
但是,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的“经学积衰时代”一节中有一段总论汉学、宋学流行区域的话: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29]
由于这是在讨论“经学”历史,所以这段“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话,很容易让人觉得皮锡瑞所谓的“苏学”是指苏氏的经学,并加以沿用。前述周良宵等的《元代史》、韩钟文的《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就是这样。不过在明白了“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说的由来后,我们只能说这是不恰当的,皮锡瑞未必有此意,他只是沿用前贤说法而已,重点是谈朱学如何由南而北,最后完成全国的统一,对“苏学”没有任何展开性的论述。
综合上述情况,“苏学行于北”说起自明代,宋濂是肇始者,张弼则是最早明确说出“苏学行于北”五字的儒者,之后丘濬、冯从吾等明儒和翁方纲等清儒都使用过。而清初的王士祯则最早提出“苏学盛于北”说,经一百多年后的翁方纲反复宣扬,形成巨大影响,甚至清末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加以沿用,近些年学界还连续出现好几篇专门论文。从这些论说的语境来看,有两方面:一是在儒学史、经学史著作中谈,给人以苏学的学是与程学相对应的儒学、经学的印象,但实际很难说就是如此;二是在诗文书画和文学史研究中的讨论,显然主要是指苏氏的文学、艺术和风格层面。从这些梳理来看,传统的“苏学盛于北”的“学”实际限于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文风、气象,很难说有经学、哲学思想的意涵。
虽然明清学者在说“苏学行于北”或“苏学盛于北”时,其“学”都没有儒学、经学的内容,但在今天使用时,是否可以扩大到经学和哲学思想层面呢?这就要看当时苏氏的经学和哲学思想是否真正盛行于北方金朝地区。下面我们再就此展开讨论。
三、苏氏经学在北方金朝地区的传播概况
关于苏氏经学在北方金朝地区的传播情况,过去一直缺乏梳理。这里打算从以下两方面来观察。
(一)从苏氏经学著作的版本和宋金之间书籍交流上看
苏氏的著作在金朝初期就受到特别重视,金朝灭亡北宋时还专门加以搜罗。史载:宋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金军攻下开封后,即在城内搜取“苏、黄文”。[30]这里的“苏、黄文”是否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便有,应该也不多。因为受元祐党禁的影响,北宋当时只刻印有苏氏的《易传》《书传》,其他经学著作都没有单独出版。[31]而且,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金朝初期还未见学者重视苏氏《易传》《书传》等经学著作的研读。
那么金朝人自己是否刻印过苏氏的经学著作呢?从我们已见资料来看,金朝确实刻印过苏轼的一些著作,如《东坡奏议》,史载:金世宗曾问丞相耶律履(字履道):宋名臣中谁最优秀?履道答道:苏轼最优。并说:“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才。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世宗遂诏国子监刊印《东坡奏议》。[32]同时金朝也刻印过苏轼的文集,《金史》载:章宗明昌二年(1191)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33]另外,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还说题为王十朋辑撰的《集注东坡先生诗》也有金刻本。[34]这些都属于苏轼的诗文部分。我们目前并没有见到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所撰的任何一部经学著作在金朝得到了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又名《道德真经注》)一书虽然被金朝后期大儒赵秉文的《道德真经集注》全文引用,[35]且放在每一卷的开头,地位重要,但他所依据的究竟是什么版本,我们并不清楚。
不但金朝方面未见刻印,南宋刻印的苏氏经学著作,目前我们也未见明确的材料说有流传至金地的,或金朝方面有求购苏氏经学著作的情况。关于南宋著述流入金朝地区的情况,孔凡礼、刘浦江等已有一些梳理,可以否定清儒赵翼所谓“南宋人著述罕有入中原者”一说,实际情况是已有很多南宋刻印的著作流传到了北方。[36]但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南宋刻印的苏氏经学著作(包括《老子解》)传播到了金朝地区。
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但目前未见苏氏经学著作在金朝刻印或从南宋流入金朝的任何一条材料,那至少说明即便金朝有刻印,南宋有传入,数量和传播也是极为有限的,与吉川先生所谓苏轼经学著作“在北方盛极一时”的说法相去甚远。
(二)从金朝科举考试科目和金朝本身儒家经学的发展来看
众所周知,词赋科而非经义科长期是金朝主流进士科目,[37]以至有“金以词赋举进士”之说,[38]这自然是“苏学盛于北”中苏氏文学部分的内容大行于金朝的制度因素。[39]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又是造成苏氏经学内容不能在金朝地区广泛传播的制度障碍。
事实上,由于基础薄弱,加之科举制度重词赋轻经义的影响,金朝儒学发展长期不理想。关于金朝儒学发展的简略情况,学者喜引《金史·文艺传》开头的一段话: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40]
这里将金朝文明的演进分阶段进行了描述,虽然可见其由低到高的序列,但金朝儒者一直缺乏“专门名家之学”的倾向则是明确的。相对于北宋和南宋来说,这也应是事实。
虽然没有两宋那样一批又一批的“专门名家”,但儒学在金朝仍有其地位,“金以儒亡”可能言过其实,[41]但本身就说明儒学在金朝有相当的势力。这方面近二三十年陆续有一些重要的通贯性研究成果,[42]其中邱轶皓立足儒释道三教背景的讨论尤为精彩,而最新的成果则是刘辉的《金代儒学研究》一书。刘书虽然是没有儒释道三教背景的视野,但其对金朝儒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则令人信服。所谓三个阶段,一是“借才异代”阶段,即金太祖、太宗时期。所谓“借才异代”,是说金朝初期儒学人才匮乏,主要对辽宋人才的借用;二是制度的儒家化阶段,即熙宗至章宗统治前期,包括礼仪制度、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三方面的儒家化;三是学术繁荣阶段,即章宗统治前期到金朝灭亡,出现了一批以儒名家的代表人物,如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等。前两个阶段金朝儒学本身发展有限,没有出现以儒名家的代表人物,我们也没有见到哪位学者重视和研读苏氏的经学著作。那么第三阶段出现的这些以儒名家的代表人物又是如何对待苏氏经学著作的呢?
赵秉文(1159—1232)“主盟吾道将四十年”,[43]在金朝后期具有长期的影响力。他著述甚多,但保存有限,不过其文集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流传至今。可惜的是,我们从中很难看到他对苏氏经学著作的研读情况。其文集卷首的《大学》部分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论著之一,有几处引用到苏氏的论说,但经学著作只提及苏辙的《老子解》,而且还是持批评的态度,苏氏其他经学著作或文章并没有被述及。
李纯甫(1177—1223)对苏氏之学要更为推崇一些,以至清儒编的《宋元学案》将李氏视为“苏氏支流余裔”。比较而言,李氏确实在很多方面与苏氏相类,如在公开嗜佛、倡言三教合一方面即是。李氏曾明确将孔子、老子和佛祖列为三圣人,指出:“三圣人者,同出于周,如日月星辰之合于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汉之汇于尾闾之渊,非偶然也。其心则同,其迹则异;其道则一,其教则三。”[44]这种公开宣扬佛道长处、公开宣扬三教合一的立场,在北宋新儒学各派中,最突出的就是王安石父子和苏氏兄弟;理学诸儒思想的形成虽然也受到佛道很大的影响,但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甚而还要极力排斥佛道。正由于此,李氏在论述历代学术思想发展特别是宋代新儒学的发展轨迹时这样写道:
四圣人(按指老子、孔子、庄子、孟子)没……一千五百年矣……诸儒阴取其说(按指佛学)以证吾书(按指儒、道两家之书),自李翱始。至于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于前,苏子瞻兄弟和之于后,《大易》《诗》《书》《论》《孟》《老》《庄》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横渠、伊川之学踵而兴焉,上蔡、元城、龟山、横浦之徒又从而翼之,东莱、南轩、晦庵之书蔓衍四出,其言遂大。[45]
显然,由于王氏父子和苏氏兄弟在三教关系立场上更为接近李氏,所以他完全不顾实际的自然时间序列,而是从他自己设定的逻辑时间出发,把王氏父子和苏氏兄弟放在理学诸儒之前,认为正是王氏、苏氏的大力倡导,才掀起了大规模的援引佛教学说来发展新儒学的浪潮,才有后来“其言遂大”的理学诸儒的崛起和前赴后继的巨大发展。
李氏这里实际上在建立区别于理学诸儒尤其是朱熹一派的道统,认为接续孟子的不是周程诸儒,而是王氏父子和苏氏兄弟。基于此,他在反驳张载和谢良佐的反佛言论时又分别写道:
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谈大道,一千五百年矣,岂浮图氏之罪耶?至于近代,始以佛书训释《老》《庄》,浸及《语》《孟》《诗》《书》《大易》,岂非诸君子所悟之道,亦从此入乎?张子翻然为反噬之说,其亦弗仁甚矣!谓圣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学而知,夫子自道也欤?讠皮淫邪遁之辞,亦将有所归矣。所谓有大过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苏氏兄弟是也。[46]
中国学士大夫,不谈此事者,千五百年矣!今日颇有所见,岂非王氏父子、苏氏兄弟之力欤?[47]
这两段话进一步表明李纯甫独特的道统立场,认为王氏父子、苏氏兄弟在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史上有开创之功,理学诸儒实际是接续他们的思路来发展的。
尽管李氏有如此立场,但我们在李氏现存的著作中仍然很难见到他对苏氏经学著作特别重视和特别研读的情况,目前只在他的《鸣道集说》中见到了他引用苏辙的《老子解》,以及苏氏的一些单篇文章,至于苏氏的其他经学著作,目前仅知他有“(王氏、苏氏对)《大易》《诗》《书》《论》《孟》《老》《庄》皆有所解”的说法,究竟是否真有所见、所读,不得而知。
相比于上面两位,王若虚(1174—1243)似乎对苏氏的经学著作更为重视,有更多的讨论,在其文集中涉及苏氏《论语说》《论语拾遗》《书传》的论评甚多,有褒有贬,但苏氏的《易传》《诗集解》《春秋集解》则完全没被提到。[48]
由上观之,我们从金朝儒学发展情况的梳理中,实在看不出苏氏经学著作在北方有多流行。可以说,苏氏的经学在北方地区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晚金时期,才见有以儒名家的代表人物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研读苏氏的经学著作,但重视程度有限。这样的状况,自然不能体现出苏氏的经学“盛行”于北方地区。
这里提出一个疑问,有著作说金朝孔庙配祀有苏轼、苏辙兄弟,[49]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史料依据,我们在《金史》和《大金集礼》等文献中也没有见到。因此此说是否可信,还需要进一步考究。
四、金朝晚期北方地区的理学与苏学势力的比较
由上一节论述可知,金朝中前期苏氏的经学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晚期才有学者对其有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金朝晚期也是理学在北方地区“复兴”的重要时段。[50]现在的问题是:理学和苏氏的经学都在金朝晚期得到儒者的重视,比较而言,究竟是理学更盛还是苏学更盛呢?从我们目前的梳理来看,似乎理学的发展势头在苏学之上。下面继续以金末三大儒为例来说明。
赵秉文对苏氏的文学才华固然十分欣赏,也认为苏学在儒家之道上是有成就的,反对南宋朱熹等人把苏氏列为“不知道”的类别。[51]但是,从整体的学术倾向上看,赵氏偏向理学而不是苏学。从他的一系列论文来看,他在道统上、学理上都认同儒家理学。如在《性道教说》一文中,认为周、程接续孔孟绝学;其系列论文也展示出他在哲学思想上的理学面相,声言要“存天理,灭人欲”。正因为他对理学更为倾服,所以在将理学与欧苏之学比较时,明确指出:“欧、苏长于经济之变,如其常,自当归周、程。”[52]即欧阳修、苏氏只是长于经邦济世之术,若论儒道的思想深度,则理学更为高迈,所以赵秉文宣称归依“周程”发展起来的理学。
不仅如此,赵氏还像南宋正统理学家那样,对苏氏“杂佛”的一面加以批评。他在《中说》的引言中开头就引苏辙《跋老子道德经》的话:“苏黄门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即六祖所谓不思善恶之谓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六度万行是也。’”之后则详细区分了儒、佛、道三家的中论,明确指出佛老所谓“中”,“非吾圣人所谓大中之道也”;儒家圣人所谓“中道”,乃是“天道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是“位天地、育万物,非外化育、离人伦之谓也”。基于此,赵氏对苏辙儒佛混溶的中论非常不满,直斥“苏黄门言不思善不思恶,与夫李习之(翱)灭情以归性,近乎寒灰槁木,杂佛而言也”。[53]
至于李纯甫,他固然嗜佛,且在三教合一上与苏氏相同,并在儒家道统上认为苏氏兄弟和王安石父子一起具有开创之功,还专门针对南宋传来的理学丛书《诸儒鸣道集》中理学诸儒的反佛言论进行批评,著成《鸣道集说》。这些都显示出他与理学家很不相同甚至相反的立场。但不应该把李纯甫完全视为理学的对立面,在宋代新儒各派中,李氏认为只有理学才达到了最高成就。上节所引那段文字,李氏认为直到出现理学诸儒,才形成“其言甚大”的局面,就是明证。而且,即便是批评理学诸儒言论的《鸣道集说》,其重点也只是批驳他们反对佛老的言论,而不是彻底否定理学。所以他在《鸣道集说》卷五最后的综述中提醒读者:他与理学家的全部分歧都已表现在这部著作中了,而《诸儒鸣道集》中的其他内容以及理学家们的各经解著作,“嗣千古之绝学,立一家之成说”,自非汉唐诸儒可及,也是非理学家的宋代诸儒(当然包括王安石父子、苏氏兄弟)可以比肩的。[54]这里也明显把理学看得比苏学、王学更高。
而且,在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上,李纯甫是赞同孟子性善论的,对包括苏学在内的其他人性论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吾自读书,知孟子为圣人也。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杨子曰善恶混,韩子曰有性有情,苏子曰有性有才,欧阳子曰性非学者所急也。吾从孟子,不得不与诸子辨。”[55]苏氏不从孟子,还专门有八篇与孟子辨的情况,而理学诸儒都认同孟子,认同孟子的性善论,成为他们主敬立诚、克己复礼修养论的重要基础。因此李氏宣称“从孟子”,实际是认同理学人性论的表现。
与李纯甫生年相若而更为长寿的王若虚,对苏氏的文学固然佩服,但在对待苏氏的儒家思想上,几乎就是南宋正统理学家态度的翻版。比如在三教关系上,王若虚以儒为本,坚决排斥佛老二教,明确指出:“苏氏溺于佛老,每以闻大道自矜,而时持害教之说,不为无罪于吾门也。”[56]这与赵秉文一般性地批评苏氏学说“溺于佛老”不同,而是认为它危及儒家的地位,苏氏实际是儒家的罪人。另外他批评苏辙所记“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之论,认为不仅仅是“屈法容奸”,而且“有害正理”,[57]也显示出他维护儒家正统的鲜明立场。
基于维护儒家正统地位的思路,王氏对苏学所包含的纵横之学内容进行指责,甚至像一些宋儒如朱熹那样斥责苏氏“不知道”。[58]他写道:“老苏《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予谓挟仪、秦之术者,必无逢、干之心,存逢、干之心者,固无事乎仪、秦之术也。苏氏喜纵横而不知道,故所见如此。”[59]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王若虚也是站在儒家卫道士立场。他从儒家道德史观出发,对臣事二主的荀彧、冯道等人深致不满,认为“人臣至于荀彧、冯道,其邪正、逆顺不待辨矣”,[60]二人是不容争辩的“邪”“逆”之徒。但苏轼兄弟却不这样认为,苏轼以为荀彧是“圣人之徒”,苏辙对冯道也奖饰有加。[61]对二苏的看法,王若虚认为简直是奇谈怪论,他特别指出:“冯道忘君事仇,万世罪人,无复可论者。”而苏辙反“曲为辨说,以为合于管、晏之不死,虽无管仲之功,而附于晏子,庶几无愧”。对苏辙此论,王若虚视为“有害于名教”的“谬戾之见”,无法容忍,是“不知道”的表现:“吾尝论之,士大夫诵先王之书、食人主之禄,而敢昌言以冯道为是者,皆当伏不道之诛也。”[62]所谓“有害于名教”“当伏不道之诛”,均显示出王若虚维护儒家道德史观的强硬立场。
同样从儒家道德史观出发,王若虚还批评那种只计成败得失不顾道德伦理的行为,进而对肯定这种行为的苏氏予以谴责:“李希烈攻宁陵,刘昌令守陴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居西北,未尝内顾,而捽下斩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围。杜牧之所记如此。呜呼,无罪而杀其所亲,以之警众,虽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为好事者傅会。此盖有功于昌,而东坡讥笑之。信苏氏之学驳而不醇也。”[63]所谓“驳而不醇”,与朱熹斥责苏学为“杂学”,[64]实际是一样的。
上述几方面的批评均显示出理学与苏学“道不同”的原则分歧。另外对孟子的思想,苏轼有多方面的指责,而王若虚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明确指出:“苏氏解《论语》,与孟子辨者八,其论差胜,自以去圣人不远。及细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并具体对苏轼的四条论辨进行了驳斥,或言“其说近于释氏之无善恶,辨则辨矣,而非孟子之意也”,或言“苏氏几于不解事”。[65]虽然不能说王若虚的论辩完全是从理学立场出发的,但理学家在道统上号称继承孟子学说,在思想上也多是宗仰和维护孟子,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王若虚在孟子问题上对苏轼的反驳,实际上是带有理学背景的。
通过对金末三大儒思想倾向的以上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北方的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66]
结 语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苏学盛于北”的“学”自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明清时期的言说者那里,主要还是指文学艺术,以及相关的文风、气象层面。虽然一些儒学史著作如明之《元儒考略》、清之《经学历史》也加以使用,但它们基本上是对传统流行说法的套用,并没有加以专门的阐发,不好说它们就把“苏学”理解为苏氏的儒家经学。现代研究者在讨论金朝儒学发展情况时,或继续加以套用,或则有具体的论述。但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金朝时期苏氏经学的传播实况。我们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来看,发现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得不到重视,晚期虽然受到一些代表性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二者“道不同”,在一些学者那里明显形成了张力,比较而言,理学势力远在苏氏经学之上。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认为应当重视田浩和包弼德的观点,“苏学盛于北”必须有限制地使用,它只适用于文学艺术方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向上滑动阅览参考文献及注释
[1]参见胡传志:《“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曾枣庄:《“苏学行于北”:论苏轼对金代文学的影响》,《阴山学刊》,2000年第4期;刘明今:《“程学盛南苏学北”解》,王水照主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391页;张惠民:《从金源文论看“苏学行于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胡梅仙:《苏学盛于北与金词的发展历程》,《长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徐传法:《“苏学盛于北”与金代初期书风之关系》,《书法研究》,2017年第4期。
[2]吉川幸次郎:「朱子學北傳前史——金朝と朱子學」、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會編:『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記念東洋學論叢』、東京: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記念會、1974年、1247頁。
[3] [美]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此文现已收入[德]苏费翔、[美]田浩著,肖永明译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19页)一书中,但观点和表述一仍其旧。
[4] Peter K. Bol,“Seeking Common Ground: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7,No.2,(Dec.1987),p.468.按:包弼德此文的发表时间虽较田浩一文早,但写作则稍晚,他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田浩一文的英文版(名为“Confucianism Under the Chin Dynasty:The Introduction of Sung Confucian Taohsueh”)。又,包弼德此处所谓的“知识复兴(intellectual revival)”,是指1190年代以来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金儒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推动建立起来的“可以自立的知识文化(selfsustaining literati intellectual culture)”,其核心是复归北宋那种重文崇儒的传统。
[5]刘辉:《金代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6]杨珩:《女真统治下的儒学传承——金代儒学及儒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6页。
[7]周良宵、顾菊英:《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页。
[8]韩钟文:《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7页。
[9] (清)翁方纲著,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则,第153页;第四十五则,第162页。
[10] (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四《药洲集三·雷州道中读道园学古录忆甲申冬曾读于此用录中韵作诗寄萚石蕴山未窥其旨也爰为改作时丁亥七月廿四日》、卷六七《石画轩草十·又书遗山集后三诗》,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11]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2] (明)宋濂著,黄灵庚辑校:《宋濂全集》卷四二《跋东坡所书眉山石砚歌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册第926页。
[13]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4]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二一《乐侍郎诗集序》、卷二二《曹伯明文集序》,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册第1117、1157页。
[15]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176页。
[16]邱轶皓:《吾道——三教背景下的金代儒学》,(台北)《新史学》,2009年第4期。
[17]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页。
[18] (明)张弼:《张东海诗文集》卷四《跋东坡书太白逸诗卷》,明正德十三年周文仪福建刻本。
[19]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六六《治国平天下之要·秩祭祀·释奠先师之礼下》“正统中以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元吴澄从祀”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712册第758页。关于丘濬的上疏时间,清初高世泰在《道南列传叙》中有“直至弘治年间丘文庄特疏补入”语。参见(清)高廷珍编:《东林书院志》卷一六,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20] (明)章潢辑的类书《图书编》卷一○四将“程学行于南”表述为“程学分于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2册第257页),或是误刻一字。
[21] (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3册第764页。
[22]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四,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23]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24]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则,第153页;第二十三则,第156页。
[25] (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六二《斋中与友论诗五首》之一,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26] (清)翁方纲:《复初斋外集》诗卷二二《再题》,《嘉丛堂丛书》本,民国九年(1920)版。
[27]陈迩冬校点:《谈龙录 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28] 《光绪本方戊昌序》,(金)元好问著,周烈孙、王斌校注:《元遗山文集校补》下册附录一,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1378页。
[29]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1页。
[30] (宋)丁特起:《靖康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三《靖康中帙四十八》,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48页。
[31]参见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校》,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4页。
[32] (金)元好问著,萧和陶点校:《中州集》壬集第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9页。
[33] 《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8页。
[34]转引自孔凡礼:《南宋著述入金述略》,《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
[35] 《老子解》一书是明儒焦竑编《两苏经解》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也以其为经学著作。
[36]孔凡礼:《南宋著述入金述略》,《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张希清、田浩、黄宽重、于建设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5页。
[37]详见薛瑞兆:《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1页。
[38]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二九《滕县尉徐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册第1374页。
[39]参见刘辉:《金代儒学研究》,第96页;赵宇:《金元时期北方汉地理学接受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8年,第48页。
[40] 《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第2713页。
[41] “金以儒亡”说最早见于《元史·张德辉传》,学界对其认识还存在很大分歧。或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如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袁行霖主编:《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现收入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64-271页);或认为不可信,如宋德金《大金覆亡辨》(《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42]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7-224页;魏崇武:《金代儒学发展略谈》,《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宋德金:《金代儒学述略》,徐振清主编:《金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晏选军:《金代儒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以及前引田浩、包弼德、邱轶皓文、刘辉和杨珩书。
[43]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卷一七《闲闲公墓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44] (金)李纯甫:《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辨》,(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李文标题依据清人张金吾辑《金文最》卷三○(清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45] (金)李纯甫:《鸣道集说序》,《鸣道集说》卷首,《频伽大藏经》编委会编:《频伽大藏经续编》第195册,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582页。
[46] (金)李纯甫:《鸣道集说》卷一,《频伽大藏经》编委会编:《频伽大藏经续编》第195册,第598页。
[47] (金)李纯甫:《鸣道集说》卷四,《频伽大藏经》编委会编:《频伽大藏经续编》第195册,第632页。
[48]参见(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集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9]此说在前引吉川幸次郎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金朝孔庙的从祀者当中,恐怕也包括有苏轼苏辙兄弟,甚至在南宋被逐除从祀行列的王安石王雱父子,或许在金朝也还占有一席之地”(吉川幸次郎:「朱子學北傳前史——金朝と朱子學」、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紀念會編:『宇野哲人先生白壽祝賀記念東洋學論叢』、1245頁),语气并不肯定。但前引田浩一文则据此表述为:“金朝的孔庙还配祀苏轼、苏辙和王安石(在南宋则不如此,因为南宋道学风行,对于这些道学的对头是排斥的)”(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十四辑,第112页),语气已转为肯定。方旭东在为《中国儒学史》的“宋元卷”部分撰写《金代儒学述略》一章中也说:“终金一代,朱熹所建构的道统谱系都未能得到响应,被朱熹排除于道统谱系之外的那些人物(如王安石、苏轼父子)在金的孔庙里却享受配祀的殊荣”(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页),方先生没有说明他的依据,很可能源于田浩一文。
[50]详见[美]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十四辑,第107-141页;魏崇武:《金代理学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1] (金)赵秉文著,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二○《书东坡〈寄无尽公书〉后》:“近世尚有以温公为奸党,以欧、苏为不知道,此皆处己太过、责人太深之弊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页)
[52] (金)赵秉文著,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一《性道教说》,第2-3页。
[53] (金)赵秉文著,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一《中说(并引)》,第4-5页。
[54] (金)李纯甫:《鸣道集说》卷五,《频伽大藏经》编委会编:《频伽大藏经续编》第195册,第656-657页。方旭东对此亦有揭示,参见方旭东:《金代儒学述略》,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524页。
[55] (金)李纯甫:《鸣道集说》卷末《杂说》,《频伽大藏经》编委会编:《频伽大藏经续编》第195册,第659页。
[56]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二八《臣事实辨中》,第320-323页。
[57]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三○《议论辨惑》,第339页。
[58]关于朱熹的斥苏情况,可参见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8页。
[59]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三○《议论辨惑》,第337页。
[60]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二七《臣事实辨上》,第312页。
[61]参见(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论武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38页;(宋)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栾城集·后集》卷一一《历代论五·冯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5-1277页。
[62]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二九《臣事实辨下》、卷三○《议论辨惑》,第333-334、338页。
[63]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二九《臣事实辨下》,第327页。
[64]朱熹斥苏学为“杂学”的情况,详见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第51-67页。
[65]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八《孟子辨惑》,第96-101页。
[66]田浩甚至认为金末三大儒的“思想发展总方向,是从苏氏之学转向道学”,参见[美]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十四辑,第140页。
粟品孝:历代周敦颐文集的版本源流与文献价值 | 202003-33(总第1244期)
粟品孝:宋末泸州抗元义士先坤朋家世考略 | 201903-52(总第889期)
【编辑】鲁畅
宋史研究资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