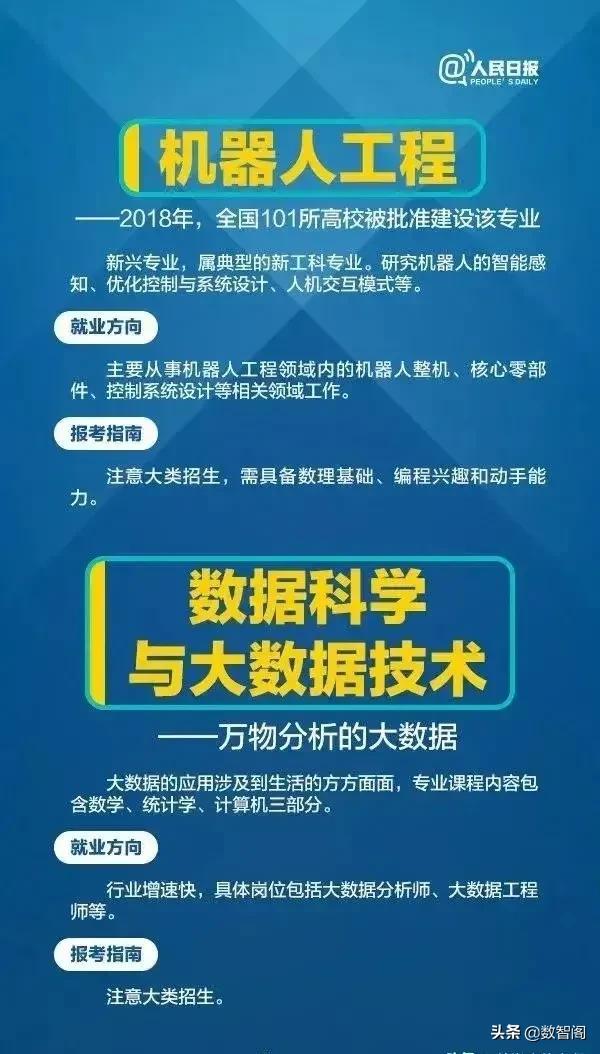异客当红歌手(异客悬浮中的农村大学生)
作者:少年闰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如是写道。处在异乡的游子,在张灯结彩的佳节里,往往更能体会到亲情的存在。每到春节,我们更能体会到“家”对于中国人根植于心的含义。“家”的含义之于中国人与西方人是不同的。于是乎,产生了只有中国才会有的人类奇观——“春运”。人群伴随着车水马龙以及汽笛声回到家的方向,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土壤。然而,有一群人是很难再回去的。他们通过努力在千军万马的高考中成功走出独木桥,却在回头时发现桥已坍塌。他们回不去家乡,却也融不进城市。就这样,成为了悬浮中的异客。
——题记

高考——鲤鱼跃龙门
前些日子,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严飞出了一本叫做《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的作品。作品以城市的边缘人群,诸如快递小哥、打工人群为对象,不可谓不新颖。他用一个极其形象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城市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悬浮。这让我不由得思考起来悬浮着的另一个群体——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凭借努力从传统的农村文化场域来到极其现代化的城市文化场域之中。并随着城市生活的经历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感受到处在两种文化场域的剥离感。对于这一点的关注越多,让我越产生众多疑问。是哪一群人在承受着这种剥离感?为什么是他们成为“异客”?何以重构“异客”心态?
(一)“异客”者,何人是所有的农村大学生都成为了“异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定义“异客”。这里的“异客”概念是与传统的“异乡人”概念不相同的。传统的“异”往往强调的是地域上面的不同。指的是某人由于某种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产生了流动,从而到底了空间地域上的不同。我们在这里的“异客”则着重强调由于流动产生的一种社会普遍心态。一种剥离与抽离感,一种既不属于这里又不属于那里的丢失感。
因此,从定义出发来回答“‘异客’者谁人也?”便会较为容易了。首先,“异客”产生于社会流动这一社会层面的运动。显然,几乎所有的农村大学生无不需要离开故土去城市上大学。所以从社会流动这一“异客”产生的客观基础上我们还是难以辨别谁是“异客”。所以,我们通过尝试回答谁更容易产生此种“剥离感、丢失感”来寻找“异客”群体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在经过对一定量来自农村大学生的观察与访谈,我们惊讶的发现。在高校层次上,来自双一流及以上的农村学生比来自普通一本、二本的学生拥有更为强烈的剥离感、丢失感;在对该群体的家庭学历状况进行进一步跟进的同时,我们有了另外的发现,即属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大学生群体丢失感、剥离感更为明显。他们更加明确的表达了自己对于城市与家乡的无所适从。因此,本文暂且将“异客”概念侠义地定义为农村第一代双一流高校大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言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之所以是他们表现得最为强烈大抵上与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值更高有关。双一流大学生由于拥有更好的平台,往往增加了他们接触更多开放思想的就会,拥有更高远的眼界。这时候就会滋生出强烈而又自然的想法“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在思想层面的这一追求激发了这一群体深刻的感叹,其威力不亚于林则徐、严复等人的“睁眼看世界”。在思想层面这一想法是进步的,但是在面对现实一次次的打击时他们便感受到了无尽的痛苦。正如余华在小说《活着》中写到的“谁让你读了这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个大世界。如果从小你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是的,之所以他们成为“异客”是因为他们在同龄人中思考的更多,有了远大的目标和对自身处境清醒的认识,然而不幸的是却又一次次陷入了现实的骨干之中。想要挣脱桎梏摆脱贫穷实现华丽的阶级跃迁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想要摆脱相对落后的文化却陷入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夹缝之中难以融入。这便是这一代人的异样感所在。

毕业的本科生
(二)“异客”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异客”之所以产生“异物感”,与场域的转换极为相关。他们生长于传统的农村文化场域,而借助高考这一流通渠道获得了流向城市文化场域的通行证。显然,城市与乡村的转换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差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可以通过刨析城乡间差异来找到此种剥离感的渊源。第一点也是最直观的一点便是空间上的差异。传统的农村相比较之城市,其空间结构相对要更加扁平化。无论是坐落于山间的存在,亦或是地势开阔的平原小村落,它都是匍匐于此的存在。而发达的城市,由于土地利用的需要,更加突出了“高效”二字。于是乎,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条条地铁从湖底、楼下、山脚穿过。城市给予人更加的立体感,而农村更给人以扁平感。这是初到城市的农村孩子所感受到的。于是乎,他们产生了源自内心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第一次乘坐地铁时慌乱而不知出口,是一路手持导航而不知入口,是驾驶自行车时误打误撞跑入机动车道的惊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表达,此种现象不是农村人笨的缘故,而是他们不知道城市生活是该如此。正如常年居住于城市的人来到农村认不得庄稼是一个道理。是的,来自农村的这些年轻大学生们面对着逛过陆离的空间是充满惶恐的,但与此同时是好奇的。这与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第一次来到乡村旅游大概是同一个心境。第一次望见这绿油油的麦田、低头喝水的牛犊,他们便面露欣喜地掏出手机拍着这农村人司空见惯地一幕,生怕漏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这帮农村孩子面对车水马龙、高楼大山地城市,同样迫不及待的掏出手机,努力的调整好摄像头与它合了一张影。由于空间上的不适,造成了心里的复杂激荡——好奇、欣喜、惶恐、热爱、慌张。
第二点是社交变迁,初次来到大学的农村孩子眼里是有光的,他们渴望与城里的孩子交朋友。但是,他们此刻的欣喜很快就会被浇上一盆冷水。他们并不清楚自身所具有的“土气”。所以,希望能与宿舍以及班级几乎所有人都建立联系。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朴实的告诉他们“多个朋友,多一条路”。然而,只有在逐步的相处之中,大家才会明白一个道理。因为每个人的地域环境不同、家庭环境不同所产生的习惯不同。更为宏观的可以用布迪厄发明的“惯习”来概括。因为天然的不可抗拒的便是我们身处于不同的场域,被不同的文化所包裹。而此种包裹培养了我们的“惯习”,我们自身的“贴标签”行为恰恰又加强了我们的“惯习”。并将之以“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刻,农村大学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原来,当他们安静下来时才发现,你与我,他与我是不同的。此外,普遍的胆怯也来自于不经意的对比。比如,在一次英语口语课堂上,突然发现昔日熟悉的同学用极其流利的伦敦腔与老师对话,谈论着自己年幼时去澳大利亚学习骑马的故事。另外一个同学在才艺表演时,拿出了自己的萨克斯。然而轮到自己时,只是迟钝的说了句“我为大家唱首歌吧”。这时便体会到,原来我们真的是不同的。第一知道原来口语还可以听出是伦敦调还是爱尔兰调。原来,童年不只有弹珠,还可以有小提琴、萨克斯、钢琴。于是乎,在下课后这些同学便暗下决心,一定要留在大城市,一定要努力学习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希望自己未来的孩子也能够从小接触到自己同学所接触到的这些。
第三点是归属感的缺失。归属感的缺失是“异客”最为重要的情感体验。他们归属感的缺失要从社会关系讲起。归属感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发自内心的“我属于这里”。而这批青年人恰恰陷入了“既不属于这里,又不属于哪里”的境地。他们归属感的背后是社会关系的变迁。
自传统乡村鲤鱼跃龙门般进入一流学府,随着生活地域的变迁,他们的社会关系也产生了激荡。在城市里他们进入了全新的话语体系。在这里他们谈论着星巴克、论文、PPT等等种种在农村或在以前从不谈论的名词。当然,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这源于他们由于地域上的优势更早的熟悉这套语言。而由于他们的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父母,所以与孩子间的共识成本较低。而农村第一代大学生们却很难生活在一套话语体系里面。当他们的父母询问他们最近做了什么时,是不能直接说“做PPT”的。需要切换到他们另外的一种话语体系转换为最容易理解的“做作业”。这种话语体系差异感觉最强烈的时候便是放寒暑假回家时期。这时他们会惊讶的发现自己与家人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与儿时玩伴(当初那些并未进入一流学府的人)也产生了一定思想的差异。从而再次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静谧的乡村

光怪陆离的城市
(三)丢失与重构:“异客”群体的自救在城市里没有建立一种强关系,在农村又处于关系的弱化阶段,从而导致他们失去了归属感。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和昔日熟悉的乡村是一样的。都会产生归属感的缺失。而很少有人专门将他们当作“异客”。从而从本群体内寻求慰藉便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共识。所以产生了诸如“985废柴”这样的社群。他们借助互联网平台聚集在一起,寻找着共鸣与理解。
除了借助社群的共同体力量之外,还需要从自身出发展开自我价值的重构。第一是客观认识“异客”身份以及不适感的来源;从场域转换等多维视角客观认识“异客”身份的来源于空间变换与心理嬗变的叠加。此种现象具有普遍性亦具有其特殊性。其显性表现于自组织形式的社群中,隐形的藏于无数此种叠变中的大学生群体。第二是突破他人价值的束缚,构建新的价值定位;处在此种不稳定的关系中的群体表现出“两不亲近”的特征,即不亲近传统农村关系又不亲近新的城市关系。加之年龄与经验的局限所以往往容易出现价值的扭曲与崩解。此时最容易发生的事件便有两种:一是未完全跳脱农村糟粕传统的保守束缚,从而沦为其价值取向的傀儡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跃迁;二是陷入城市高度资本化的异化价值取向中,价值观纯粹的被金钱与权力包裹而又难以自知。所以自我价值的重新定位显得尤其重要且迫切。此时的可取做法便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系统熵增的角度或许更好理解或者阐释这一观点的合理性。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比较禅意的词讲便是“遇”,用更口语化的语言来讲就是“不断折腾”。当然这里的折腾不是瞎折腾而是“无为”的折腾。“无为”意为不乱为、不枉为,此般折腾便是正确的做法。从而达到保持自身“开放性系统”的目的。在在深入思考与阅读中加之“走出去”,从而强化价值定位。第三是强化城市关系,减缓农村关系的弱化;乡村的衰落与城市的兴起已经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这一群体走入现代化的城市并建立城市里的新关系也成了必由之路。或者换句话说即使不生活在城市中,也必然与城市元素展开密切的互动。因此强化城市关系是这一群体需要做到的。城市关系的强化中需要掌握大量现代沟通的技巧,对于这一技巧的迫切渴望不光是这一群体的餐食还是现代人共同垂涎的盛宴。《人性的弱点》一书的出版奇迹正是这一点的印证。当然,一味的学习技巧所带来的效果并不会显著,了解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才能从根源上把握其脉络。而对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是极为丰富的。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索罗金提出的“亲密关系”、“契约关系”。贝克尔提出的“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这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现代城市社会提供了可行的观察方式。为我们强化城市关系提供了一个有本之源。此外,减缓农村关系的瓦解也是尤为重要的。之所以在加强城市关系的同时还要减缓农村关系的瓦解,是因为这一群体处在转角这一特殊的地带。虽然走向城市或者与城市接触是必然的,但这是一个处于过度的阶段。所以需要与乡村有短暂的缓和。那么如何减缓这一群体与农村关系的瓦解呢?其一是“求同存异”,在农村关系的相处上保持着空杯心态;其二便是做文化传播的桥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朴实的乡村口吻讲述出来;第四是做到降低期待,减少比较;“异客”群体处于嬗变之中所以往往容易产生两种极端,一是与同一“附近”的农村青年相比,了解到曾孩童期朝夕相处的玩伴在这一阶段或好或坏的境遇从而产生落差。二是和同一“附近”的城市青年做比较,在了解到其背后差异化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阶级“惯习”带来的心态差异与处境异质化。因为意识到了群体间的差异,所以企图利用有限的资源仅凭借学历优势跨越阶层是他们最佳的选择又是不得不要做的选择。故然产生了对未来社会地位、职业等的无限期待。一面望着光怪陆离的城市,一面看向已经回不去的农村。这群未被社会关注的“异客”应该何去何从?或许最好的方式便是降低期待、减少比较。第五是多参与异质性群体活动,突破圈层局限;所谓异质性群体,其“异”之维度并不限于一种。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年龄、性别、地域等常见或者便随着互联网衍生的新型社群。之所以需要与异质性群体接触,是基于同质性群体的弊端而言。异质性群体在思想、方法、理念、信仰、立场上表现出与该“异客”群体颇为迥异的观念。对于这些通常较为逆耳或不顺的言语的接受与聆听对于打破“信息茧房”将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既需要极大的勇气又需要极为强烈的自我革命、自我否定的意识。
总之,空间的变迁加之心态的嬗变构成了该群体强烈的“异物感”。“异客”群体的进阶之路任重而道远,远非一种结构一种理论一种解释所能穷极。实现阶层的跃迁,对于文化资本本就匮乏、信息资源严重不足的农村第一代大学生来说将是艰难而又孤独的道路。最后,引用费孝通老先生的一句名言,作为对这一试图改变命运的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期许“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