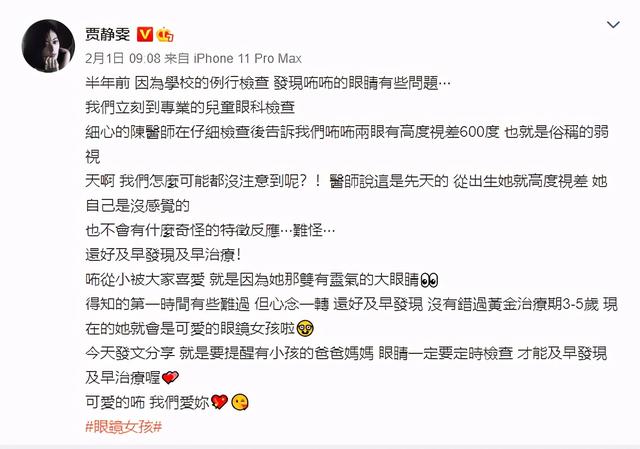大面积脑梗昏迷请专家有用吗(父亲脑梗昏迷不醒)
- 作者舒生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圣经·约翰福音》

急救室里的父亲
父亲昏迷不醒的第二天,弟弟和妹妹赶回家将他送到(贵州)习水县中医院急诊室抢救。我从北京赶到县中医院时,已经是昏迷的第三天晚上十一点。父亲在ICU病室,靠呼吸机维持着已经不见有任何意识的生命。弟弟、妹妹、母亲和三爷在ICU外的走廊上交际地等待着……
中医院的检查结果已经很清楚,父亲的问题是大面积脑梗死 肺部感染。医生告诉我们,由于错过了抢救脑梗死的最佳时期(昏迷六小时以内),父亲已经命悬一线,除非奇迹,苏醒过来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苏醒过来,也基本是无意识的木偶人。父亲的肺部感染也非常严重,中医院没办法治疗,所以医生最后给我们两个建议:要么放弃治疗,立马将父亲拉回家;要么送到更大的医院检查治疗。
就这样放弃治疗我们内心过意不去,于是商议半个多小时,决定当晚将父亲转送到遵义医学院。
午夜12:00过,我们在中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然后将父亲送上联系好的救护车。弟弟和妹妹提前开车去遵义医学院办理入院手续,我和三爷跟着救护车走,必要时配合护士护理。
救护车在安静漆黑的高速路上疾驰,天下着浓密细雨。时近2:00,我们到达遵义医学院急救室门前。将父亲的病床推进急诊室后,医生过来招呼我们。里面放满了需要急救的病人,负责照顾的亲人来来去去,很喧闹。都是重病在身,亲人们一脸焦虑,医生们则早已见怪不怪,保持着职业的冷静。
医院已经没有空余的住院病床,只能先在急救室检查。一番解释说明下来,医生给父亲供上呼吸机。输液断了一阵,但因为父亲血压高达130以上,便配了降压药一直输着。
昏迷中父亲血压最高时的状态
在医生要求下,我和弟弟推着父亲去照CT,半个小时后我去打印CT胶片交给医生,之后就等医生的诊断结果。
天亮后,一位女医生把我们叫到面前。父亲患的是肺结核脑膜炎,由于未及时抢救,治疗下去很可能是人财两空。最后女医生表示,父亲的病情也可以住院后进一步检查。
住院检查?——但我们已经对这种治疗不抱希望。早上9:00过,医生给父亲输晚上开的最后一瓶液。我们三兄妹坐在急救室门口边的一排靠椅上,一开始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但静坐一阵,妹妹终于低声说出放弃治疗的提议,接着弟弟默默点头。我也想放弃,但一听妹妹说放弃时,眼泪就一下夺眶而出了。
这样放弃,意味着接下来只得找辆救护车将父亲送回老家,然后拔掉呼吸机,眼睁睁看着他停止呼吸。我也明白治疗下去难免人财两空,也清楚父亲苏醒过来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也相信他活下来很可能像个植物人一样失去知觉,但他现在毕竟还有呼吸。只要呼吸机一直供养着,加上医院治疗,再活十天半月也不是不可能。可一旦拔掉呼吸机,他就只能等死了。这情形,我们岂不是见死不救吗?
对外人见死不救尚且心中有愧,对自己的至亲见死不救,这种滋味怎能好受?但是医治下去,一天一两万的花费,对总是捉襟见肘的我们,必将债台高筑。父亲虽说没昏迷几天,但也与他十多年的病史有关。我们一度以为他患了肺癌,将在短短几个月离开人世,但那之后他又活了十多年,直到现在。如果他听医生和家人的话,在得了肺结核之后就停止抽烟喝酒,完全按照治疗的要求康复,他的肺结核想来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发。如果他不能改掉他那些有害健康的行为,活下去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给我们带来更多负担。所以放弃治疗,也许是最明智的做法。再则,我们也看不出他有恢复意识的可能。
在家昏迷以后,谁也没见他醒来过。每次站在床前看着他毫无知觉的脸,我都在想,只要还能见他苏醒过来,我绝不会轻易放弃。如果他还会睁开眼,还会流泪,手还会微微颤抖,还会支吾一声,都能给我坚持治疗下去的信心。但是,这一切他都没有,整个昏迷期间,除了呼吸,他没有任何反应。
那就放弃吧!那就见死不救吧!
既然放弃治疗,那就得从急救室挪走,其他病人还在源源不断地推进急救室来。在急救室,父亲的病没有多特殊,他才49岁,但比他年轻的也有好几位。医院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他放弃治疗了就可以免费占用床位。
医生通知我们,过了中午13:00,病人得挪走。但是到了一点,联系的救护车还没到。一直拖到14:00过,才将父亲抬进救护车。那会儿只要看到父亲的床,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父亲曾多次提到他自己的死亡,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机会说“我要死了”。当死亡真正笼罩在他身上,他连害怕都来不及。父亲曾一次又一次津津乐道地谈及别人的死亡,好像死亡完全与己无关一样,最后沦到他自己死亡的时候,却不再吭一声。
坐救护车的那三四个小时,我夹在司机和三爷之间,一句话也不想说。一想到父亲,我就热泪滚滚。
七年前,也就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母亲不再忍受父亲的缺点,执意与父亲离婚了。离婚后,父亲先一个人在县城呆了三年,之后来北京工作了一年半,因为周身水肿,他决意回贵州康养。临走的下午我们一起吃饭,他说康复了再来北京,可我却悲伤地预感他再也不会来北京了。之后他又在习水呆了一年左右,期间我们三兄妹一直劝他回老家,偶尔我也劝他来北京,但他始终觉得留在县城更好。去年年初,他终于答应回老家。

在北京与父亲吃的最后一顿饭,之后直至临终,再未见面
爷爷奶奶毕竟都在,在家想来会减少他的孤独和寂寞,也有个照应。但是,他在家这一年多,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他独立生活,少给家人添麻烦,但还是总传出他和家人闹矛盾的事。这倒不意外,因为一家人都不好长期相处。父亲之前不想回老家,一个原因就是家人不和,这情形就像刺猬,彼此靠近了就会蛰伤对方。他们到底谁对谁错,大家各执一词,至今无定论。为了打发时间,父亲养了五只羊,自此以后,他像父母照顾子女一样喂养着几只羊。我们通的最后两个电话,他的话里满满的都是对那几只羊的怜爱,仿佛几只羊才是他在这个孤独人间的最后安慰。他去世后,我从爷爷和三爷口里得知,他会夜半三更将圈里的羊放出来玩耍。
谁也没想到他会走得如此突然。这个中秋国庆前一个月,我还特意嘱咐弟弟8天的假期回老家看望重病在床的爷爷。当时一心想着给爷爷买点能吃的营养品,完全没考虑给父亲带什么,毕竟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健健康康,无须任何担心。哪知道中秋节前一天,他晕倒后就再没有醒来。人生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与父亲最后一次通话,除了问好,我们没有别的交流。听他说“我还好不用担心”后,我就想挂电话了。几乎每次打电话给他,我都会提醒他不要抽烟喝酒。家人也以为他一直酗酒不断,但他过世后我才从亲友口中得知他生命的最后半年几乎戒了酒。而我却总爱在电话里呵斥他乱喝酒(因为家人邻居经常说他喝酒),有一次他罕见地怒怼我:“是是是,你就认为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喝酒造成的,你说的就对!”说完就挂了电话。跟母亲离婚后,我还是头一次见他这么气急败坏,以后批评他抽烟喝酒时我也顾忌了很多。
他去世后与家人闲谈才逐渐明白,他生命最后时期表现出的胡言呓语和谵妄行为,大多与他的病情有关,很少是酗酒所致。原来,我们都或多或少错怪了他。
父亲生前,我习惯于鼓励他坚强。我一次又一次让他相信,我们一定会苦尽甘来。我激励他,等我在市里首付买的房子最迟明年装修好了,我们的生活就能有很大改观。但遗憾的是,他两年前就知道我买了这个房子,却始终没能看一眼。弟弟和妹妹去市里看房的时候他也想去看,但我想到来日方长,等我回来再带他看也不迟,就没让他去。
我还想着房子装修好了,把他接过来,让他每天帮忙做一日三餐,这样对大家都好。我想着要教会他用微信发信息、会付款。我还要教他用电脑,让他帮我运营自媒体号,这样既可以让他赚点生活费,也能活跃他的大脑、充实他的生活,不亦乐乎?我还想着给他制定生活作息计划,从饮食、运动上一步步改进他……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救护车在幺爷家门前停下,已经有二三十人等在那里。他们中年龄大的基本是熟悉的面孔,部分年轻面孔则完全没有印象。我已经八九年没有回过老家,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幸亏了他们,病床上的父亲才被顺利抬进家里。抬回家的路程全是陡峭的上坡路,最后一段是接近垂直的水泥路,因为坡面崩塌,完好的水泥路不到原来的一半。大家伙抬着父亲,一度差点全部摔下陡坡。我当时被吓得有些晕眩,感觉脚下地动山摇,每前进一步都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去。一开始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老房子,它的瓦、墙壁、水缸、柱子、屋檐、牛棚猪圈、门前的坝子完全超乎我印象的陈旧、荒凉、破败和低矮。我万万没想到在精准脱贫、全面奔小康的今天,我们家却似乎比以前更糟了。
父亲平时住的那个房间太狭窄,因此将他安置在堂屋紧靠东墙的一面。爷爷的床也在堂屋里,父亲占了他原来的位置后,爷爷被暂时移到堂屋西边靠墙一侧。平时大家来都先看望肌肉萎缩得像干柴的爷爷,但现在我父亲才是焦点病人。
安置好父亲的床,接着医护人员当着大家的面告诉我父亲死后以后该如何拆掉他身上的吸管、尿管等医用设备。之后我补交给护士600元转运费,他就走了。屋里子人越来越多。我守在父亲床边,似懂非懂地摸着父亲的手臂。下车就拔掉了呼吸机,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铅色的脸面越来越平静,油腻腻的头发稀疏凌乱,他像是大热天大汗过后熟睡了。他的死亡还没有到来,但大家都在等待宣布他的死亡,这下,好像他不死都不行了。我原以为送回老家怎么也得一两天才停止呼吸,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咽气了。
我摸他的手臂,没感觉任何跳动;看他鼻孔,不见一丝翕动。我掀开被子摸他的胸腹,依然温热。我认为他已经死亡,但大姑婆用一小团棉絮放在他鼻孔前,显示有一点点微弱的气息。一位邻居大哥过来摸他手臂上的脉,也发现偶尔会轻轻跳动几下。
我守了半个多小时,弟弟妹妹到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母亲也到了。母亲还没进屋就失声痛哭。母亲来到我身边,我低声告诉父亲:“爸爸,妈来看你了。”我想母亲一来,父亲就可以放心走了。
父亲的头、手和脚逐渐冰凉,双眼微闭,右眼角始终噙着一点眼水。我用棉絮测试,鼻孔已不见有任何气息。我再摸他的胸腹,依然暖暖的。但是,知客官再次进来用手测呼吸,摸手脚后,就对我们说父亲这回确实死了,可以拆掉他身上的医用针线、管道设备。接着,知客官出去安排放鞭炮,宣布父亲的死亡。当时是晚上七点半左右。
宣布父亲死亡后,我们就开始为父亲的丧事而忙活。人声喧哗中,我暂时走出父亲死亡带来的伤感。整个丧事期间,我也没有再为父亲掉泪。哭丧的时候,姑姑、二娘和大姑婆呜号着哭得特别惨烈,我跪着,一点都不想哭,也挤不出眼泪,只觉得这回父亲是真的没了。

父亲的灵柩
根据道士先生推算,父亲得在死后第三天的凌晨2点下葬。我和弟弟端着灵牌送葬。到挖好的坟前就背对坟墓跪下。天飘着细雨,跪的泥巴土全被踩滑溜。墓地开棺前有经验的家人几次提醒我们,整理父亲的寿衣时要避免掉眼泪进棺材,完了要说“爸爸回家了”。下葬仪式结束,回家路上又要求我们三兄妹说“爸爸回家了”。我轻哼了两句,他们嫌声音小,让大声点,于是我鼓足勇气大喊起来。
“爸爸回家了!”
“爸爸回家了!”
“爸爸回家了!”
……
弟弟和妹妹见我开始高喊,也高喊起来,震得我耳朵轰隆隆响。这时,父亲的死亡不再让我悲伤,反而带给我一种直面死亡的洞彻感和和解感,仿佛死亡成了一个人所能体验的最神圣经历。
但是,葬礼过后,无论我怎样用理智说服自己不再为父亲的病亡悲伤,内心的悲哀依然会时不时地泉涌出来。真正让我难过的不是父亲的死亡本身,而是他这样悲剧性地离去。他昏迷前一天曾打电话给弟弟,据说那时他是希望弟弟立马送他去医院。但他已经口齿不清,支支吾吾一阵,弟弟没听懂几句,还以为他又喝醉了乱打电话,就没管他。如果我们三兄妹有人在他身边,这个悲剧就能够避免吧。
父亲穷了一辈子,苦了大半辈子,痛了十多年。最后几年,他的身体已经严重营养不良。他的食欲越来越差,有时一天就喝几口水就饱了。明明很饿,他却常常吃不下几口饭。去镇上买了一袋米和十来斤蔬菜回来,他似乎怎么也吃不完。我自己也常常厌食,我想厌食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对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既然吃不下东西,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变得瘦骨嶙峋、脸色如铅了。
医生说,父亲的病的根源是长期营养不良,致使免疫力下降造成的。我们都认可这一点。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长期独居的后果。
和母亲离婚后,父亲就开始了独居生活。无论在县城,在老家,还是来北京工作,他都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过。在北京时,他最多就是下班了来我住这里做顿饭吃就走,从不曾在我这儿过夜过。(我的房间小,和女友一起,根本不方便他住,他很清楚这点,即使我强留他也会走)在县城时,弟弟放寒暑假都跟母亲住,最多就是回去了顺带去看看他。在老家虽有爷爷、奶奶等家人在,但他跟他们关系极度不稳,平时很少交流沟通,还经常闹矛盾。所以无论住在哪里,他都是孤身一人。母亲说她曾在县城见父亲和一位老妈妈一起生活过,但我们从不曾听他说起过,想必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父亲从来不喜欢独居。他喜欢热热闹闹,喜欢有人在一起消遣。年轻时,他在家根本呆不住。回到家就变着法子出去找邻居和朋友耍,要么就想法子喊邻居朋友来我家玩。绝大多数时候他很享受跟家人以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因为他好交际的天性,他没生病前要好的朋友还比较多,至少许多亲友也乐于与他交往。但是断断续续生病十多年,他的交际圈越来越窄,身边朋友越来越少,说白了,已没几个人真的关心他。他倒是爱主动联系他的“朋友们”。他独自在老家生活的时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心交往,他甚至经常回避邻居和路人,这倒不是因为他真的厌倦了交际,而是受限于病弱之躯,情非得已。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他也常去邻居家聊天。
独居的生活,白天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夜晚就麻烦了。父亲虽然不是特别怕黑,但也不喜欢一个人的夜晚,特别是失眠夜,外面是死寂的群山,周围黝黑一片。老家又不像城里那样光亮和方便,一旦无聊起来,个人内在的时间就可能被无限拉长。住他隔壁的三爷说他经常听见爸爸大半夜给人打电话,说得很起劲,也不知道是真打还是假打。有时候他三更半夜把几只羊放出来,像个牧童与羊跑来跑去玩。这种作风,在外人看来很荒唐,却可能是他逃避失眠夜的好办法。也许正因为长夜难熬,他才无法彻底戒烟戒酒。他从没跟我们抱怨过长夜难熬,可能是因为羞于向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你总能感觉出来。有时他打电话给我,简短问好过后,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他又不挂电话,宁愿沉默着也不挂。我们父子间从来都羞于向对方表达感情,他一句话不说,尴尬几秒后,我只能没话找话说。我能体会他的不容易,我是真的为他的不幸心酸,但是像我这种寒门子弟,总是需要向前(钱)看的。
北漂这几年,我一事无成,也经常小病缠身。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我被上一家公司辞退了,没有任何赔偿,最后一个月还降薪一半。前年在遵义买的期房,首付的一大半是借的,除了房贷,至今欠着四五万的债。但是这套房子已经承载我很大的希望了。父亲始终没有摘掉“贫苦”的帽子,现在村里多数人既在城里买了房子,又在当地修了宽大的平顶房,我们家却依然没有一个完整的居住地,依然是村里典型的贫苦户。村里跟他同龄的人很多都有了孙子,开始享清福,要么活得健健康康,正要奔小康,他却不得不拖着病弱之躯独守着那间室内阴暗潮湿、正变得摇摇欲坠的老木瓦房。我是多么希望他有生之年能住进我买的房子,哪怕不为享受,至少也能求个心灵的圆满。如今这一切都晚了。
母亲总抱怨父亲不称职,我们三兄妹也经常被这位“问题”父亲惹恼,但他毕竟是生身父亲。最后这几年,他在尽可能地为我们三兄妹而活。每次他开口跟我们要生活费都会嗫嚅,仿佛他是在跟我们乞讨。我很讨厌他这种做法,但也明白他内心深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却又只能向我们求助。与母亲离婚后,他变得越来越弱势,越来越唯我们三兄妹是从。他脸上再也没有生病前那种一贯活泼泼的表情,代之而起的是忧郁和皱纹。
他来北京当保安一年多,很为自己能够给爷爷、奶奶、弟弟他们打钱而兴奋。担心爷爷病逝没钱办丧事,他提前恳求邻居为他准备三四千块。为了减轻自己死后带给子女的负担,他决定买一副极其廉价的棺材,在我的反对下,他才作罢。他知道我每个月得还房贷付房租,许多时候宁愿跟外人借也不愿跟我开口,而我得知他跟人借钱就会怒斥他一顿。生了病,凡是一千以上的花费他都会犹豫再三。如果他知道他的病得两三万才能治好,那他宁愿死掉也不愿医治。别说两三万,就是一万八千,他也很可能放弃治疗。他就是这样,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又有病在身,所以不能给我们什么时,就想着尽量少花我们的钱。可他这样做时,却让自己雪上加霜。
我为此感到无奈、羞愧和遗憾,作为家里罕有的大学生,我工作了七八年,为什么还让自己的父亲过得乞丐般潦倒?就算家乡人会理解和同情我们,但我尽到了子女应尽的责任吗?子欲养而亲不在,以后我还敢让类似的悲剧在至亲至爱的人身上发生吗?我总想着熬过这阵,以后就好了,要是没有“以后”呢?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结果却以至亲的猝然离去才醒悟,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
作家马尔克斯曾感慨,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等到父母过世了,你才会直面这些东西,不然你看到的死亡是很抽象的。父亲去世前两个月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躺在老家堂屋里的床板上,周围站满了家乡人,我无法动弹,我意识到死亡从心脏开始在我体内扩散,最后是大脑,犹如突然熄了灯,我眼前完全漆黑一片。我一生做过无数次梦,梦见自己死亡还是第一次。之后我不停地回味这么梦,它的许多细节越想越觉得意味深长。现在看来,它是在预示父亲的死亡。而以梦见自己死亡的方式预感父亲的死亡,也足以说明父子之间有着深层的纽带。一定程度上说,父亲的死亡确实是我自身死亡的一部分。父亲死前,我自诩对死亡许多认识,但那毕竟是一种隔岸观火的认识。父亲死后,我才意识到死亡是任何人或早或迟都必须直面、谁也无法逃避的课题。我一直推崇奋勇向前的激昂人生,但父亲离去后,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原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谢谢你,我的父亲,你不会白白长逝,你将带给我无限的哀思和反省!
愿你安息,愿我们受指引!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