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孔子论道的关系(孔子问道于老子是道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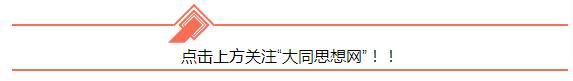


道家的自我抬举和儒家的基本态度
——东海客厅论儒道
余东海
一
《列子·黄帝》中记载了几个神通故事,其中一个是石壁中人。大意如下:
赵襄子在山中狩猎,见一人从石壁中出来,随烟烬而上下。赵问:“你怎么会处于石壁当中呢?你怎么能入于火中呢?”那个人反问:“什么叫石,什么叫火?”石壁中人为什么能穿石入火呢?子夏引孔子的话说:“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问子夏:“孔子为什么不游金石、蹈水火呢?”子夏回答说:“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
《列子·黄帝》是道家书籍,其中故事大多是寓言,具有非真实性。关于孔子师徒的对话就是伪造瞎编的。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孔子大圣人,当然有神通,但不是游金石、蹈水火的神通。认为孔子是“会而不用”,会游金石、蹈水火之类神通而不使用,那是道家混扯。孔子的神通,非彼辈所能知,更非彼辈所能。
礼文厅友言:“诸子百家都喜欢拿孔子说事,列子也不列外。这也是列子编的一则寓言。道家喜欢语怪语神甚至于以为造神,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不许可,说得越光怪陆离越是偏离儒家。”此言甚是。
以寓言的方式伪造故事、贬低儒家和自我抬举,是道家的习惯性动作。说孔子问道于老子,显然是道家的自我抬举。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典故,圣经不载。《史记》有载,是否事实,迷离恍惚,众说纷纭,颇难确定。
即使属实,也是问礼而非问道。一定要说是问道,也是问先王之治道,即古代之礼乐。老子作为周藏史,孔子向他请教周礼或古礼,就像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样。凭儒经中亲宣之圣言可知,孔子无论怎样尊重老子,不可能拜其为师,认同其道,
黄老一词,也是道家妄攀。吾《中国故事》一书“黄帝事迹”中评论如下:
黄老并称,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五帝政治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白虎通》明确指出黄帝所得所行就是中和之道:“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二
道家思想存在很多偏差。例如,宽容是好的,但宽容有度,不能过度,不能宽容罪恶、血海深仇和君父之仇。否则,所谓的宽容就变质了,恶化了。老子讲“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就很容易变成宽容无度。
对此,孔子有针锋相对的批评。《论语宪问篇》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坚持仁本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各种学说和观点,无可无不可,该反对则反对,该批判则批判,该认同则认同。例如对待恩仇,儒家坚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坚决反对以怨报德。但对道家的以德报怨,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至亲,可以以德报怨;外人小怨,也不妨以德报怨。但于君父之仇,则报复到底,死而后已,绝不允许以德报怨。
儒家无可无不可,但可不可,有标准在,五伦五常,书理易理,春秋大义,非常严肃而严格。可以随心所欲,不许越礼逾矩,外有礼法之矩,内有天理之矩。某些道家人物也好讲无可无不可,是缺乏基本原则和立场,或者立场可以变来变去。
例如君父之仇,道家无可无不可,就是可报可不报,不报也有很好的借口,以德报怨嘛,报什么仇。某些道家和杂家人物往往没个准,靠不住,不适合为政乃至不适合社会生活,根本因在此。
老子说,弱者道之用,柔弱胜刚强。这亦不为儒家所肯。道家局限于坤道,即地道臣道妻道,故主柔弱。儒家大乾元,主阳刚,在此基础上强调阴阳统一,刚柔相济,刚强柔弱,皆道之用。故该柔弱时柔弱,柔弱胜刚强;该刚强时刚强,刚强胜柔弱。《易经系辞下》说:“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道家最大的优点是有得乎道,尊道重德。缺德也不少,最大的缺点有三:轻蔑仁义,轻蔑知识,轻蔑语言文字。殊不知,仁义是人道之本,道德之源,而正知正见和语言文字都是道德之用,是上达天道之阶梯。故东海早就指出,道家将体用分裂,以致大道小用,乃至执性废修。属于偏激的智慧,非人间正道也。
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两句名言就是将道体与知识和语言割裂开来的妄言,不知误了多少学者,导致他们无知无识而狂妄自大。正确的说法是,有德者必有其言,五伦五典五常道仁义中庸之道,就是历代圣王圣人道出来的。
没有老庄,天下无所伤;没有仁义,万古如长夜。对于老庄和道家,儒生不妨有所尊重,但切忌儒道同重,孔老并尊,忌称《老子》《庄子》为经,更不必为道家各种显而易见的思想缺陷曲辞狡辩。否则,无异于对孔孟、圣经和儒学的贬低。
三
关于儒道两家,东海客厅有过讨论,摘录如下。
山海厅友言:“孔子开启平民教育。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把孔子的思想给分裂了,分成了儒门四科。其中文学科演化成了儒家,政事科演化成了道家、法家、兵家,言语科演化成了名家和纵横家。德行科是百家共同遵守的基本价值原则”云。
东海曰:都是外行话,纯属想当然。凡是儒家,必然四科并重;只有儒家,才能德行中正。道家、法家、兵家、名家和纵横家,有正有邪,皆发源于儒,但割裂大道,各成门户。吾儒颇重兵家,略尊道家,轻蔑纵横,憎恶法家,都是经典和历史之事实。
说吾儒略尊道家,主要指孔子。儒经中孔子对道家人物的言论态度,或尊其人,但不重其道,如对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甚至对其人都谈不上尊重,如对原壤。孟子就更无尊重之意了,如对陈仲子。欲洁其身而乱大伦;鸟兽不可与同群;老而不死是为贼;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诸如此类批评,显而易见都是针对道家之道的。
一介厅友言:“我理解儒家刚而能柔,道家柔而能刚。”
东海曰:此言不错。然复须知,儒家是以乾为主而能刚,道家是以坤为主而能刚。都能刚,但性质大不同,儒家是乾坤并重,刚柔相济;道家则不明乾道,唯知坤道。坤至柔而动也刚。这是坤动之刚,与乾之阳刚性质不同。
礼文厅友言:“儒家道家一体两面。一种是天道阳刚的一面,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不息,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种是取天道阴柔的一面,顺应天命,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云。
此言不无道理,又有失准确。盖儒家乾健,可以覆盖道家,代表太极;道家坤柔,不能覆盖儒家,代表天道。儒家文化,乾阳挂帅而阴阳刚柔合一,为君为臣,为父为子,无所不可,无不可以各尽其道。道家则是阴性文化,局限性性很大,只能尽臣道妻道。若欲凌驾儒家之上,试图主导家国天下,就是僭越,大不祥也,难免大误,误己误儒误家国乃至误天下。
李建春厅友说:“儒家恐怕只有中国人能理解,道家的解决思路却是世界性的,尽管明知是不可实现的,纯粹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或许问题在于圆融与偏至的区别。”
东海曰:儒学是普适性最高的人学,普适于全人类,儒家的解决思路也是最世界性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中,确实是中国人最能理解儒学,中国人与儒学最相应。其次,儒学太圆融了,对信奉者的德智要求较高。在德智达到一定高度之前,人类对偏至的学说更感兴趣。《中庸》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有道家人物将儒佛道三家要义概括为三个词:自强、自然、自证。这个概括没错,但认为道家最高就错了。于人道而言,自然有两种,一种是习性自然,从心所欲必逾矩,轻则非礼,重则非法;一种是本性自然,从心所欲不逾矩;欲获得本性自然,必须克己复礼,自强不息,自证本性。人之本性,即天命之性,天地之性。乾健是天性第一性征。君子之自强不息,正是天性彰明的表现。
四
儒家对道家说,你有的我也有,唯独没有你的缺点,你能的我全能,只是不能如你那样,或以德报怨,或与禽兽同群,或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或不尚贤,或以百姓为刍狗,或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弃利。你的这类说法我都不认同。但我知道你有你的好,故应该维护你的言论信仰自由并予你和佛教以特别的贵宾式尊重。待之以未来中华辅统,最是合乎天理人道,也合乎道家根本利益。
不仅于道家,儒家于佛道西学,都是超越。高于她们而超越之。西学蔽于人道而不知天,儒家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通天彻人,天人双彻,故能超越;佛道蔽于坤静而不知乾健,儒家允执乾元而乾坤并建,故能超越。儒家是真正的圆教,上下内外一体贯通,非佛道所能及也。
吾少时,先酷嗜道家,后耽恋佛学,差点出家。后来成为小诗人小商人,在出入儒佛道的同时,又恋上自由主义,为了民主自由,持续喝茶多年,未入马帮监狱,实属侥天之幸。最后皈儒,是因为对佛道两家和西学西制之优点和不足认识深刻,对儒家之中正坚信不疑,是历尽苦难艰险而作出的终极选择。于佛道西,知其优点故有尊亲,引以为辅;知其不足故有异议,不容混杂。
佛道两家有得乎道,故优于其它无道之学;然得之不全,远逊于儒学,于人道利弊双存。儒者对于佛道,有两大忌:一忌混同,只知三家之同,不知三家之异,一味强同横通,沦为杂家而不自知;二忌过严,只见其异,不见其同,视为仇寇,防如大敌。两种态度,皆非所宜。
2021-12-7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附《列子•黄帝》: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众谓鬼物。火过,徐行而出,若无所经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窃,人也;气息音声,人也。问:“奚道而处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闻之,问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闻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阂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虽然,试语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文侯大说。
订购杜钢建《文明源头与上古茶陵》《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黄守愚《儒学新编》、《稻生一》,请点击大同书城“阅读原文”。
关于大同思想网:大同思想网是由大陆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青年学者枕戈、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岳麓书院唐宏站博士发起,并有学界代表人物郑佳明、陈明、秋风、林安梧、黄玉顺、伍继延、杜文忠、韩星、何真临、曾亦、韩秉欣、黄守愚等一大批学者支持的文化学术网,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中,大同思想网已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学网站之一。
欢迎向大同思想网公众号投稿:
datongsixiangwang@163.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