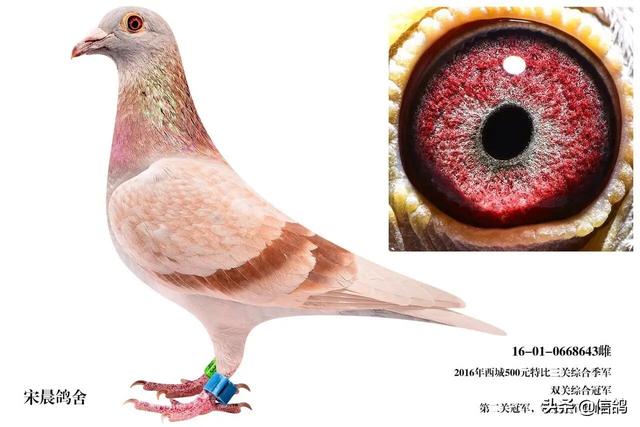人间世庄子名句(入世出世隐世)

更多精彩关注微信公众号哲学式生存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概括起来主要是以孔孟(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学和以老庄(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流派。
加上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由乔达摩·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教(释教),统称为儒释道三教。
这三种文化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支柱。
其中儒家主张“入世”,最典型的一句名言就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学好了有余力一定要去做官。受这句话影响,中国学子的职业规划,几千来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做官(做臣子或作奴才),所谓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诚不欺我。
也正是如此,官本位与奴性思想在中国才死而不僵,阴魂不散。追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百年之前的国民性甚至到如今也未曾改过。细数不过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皇权神授,俯首称臣(臣子);第二种是卖身为奴,被上位者驱使(奴才);第三种是一介草民(平民),安贫乐道。这三个层次的人生追求,都是儒家(孔孟)文化在影响,排在首位的就是做官官,次之乃为奴,最次是做民。
倘若以上三种“社会理想”都无法实现,就另辟蹊径。
有点血性的人会走造反的路线,像历史上的黄巢起义、农民起义,都是打着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旗号进行的。
其次就是走特立独行的且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式的自我救赎、自我疗愈路线。如以老庄(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学和以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学,皆是如此。
相比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的“入世”原则,道家和佛家别出一格的提出“出世”的原则。相比积极入世,遁入红尘求取功名的路线。“出世”也并不是消极无用的。
“入世”是心在朝廷,求仕问官,热衷功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出世”则是不屑(不得)仕途,所以淡泊功名,蔑视权贵,追求人格之独立和精神之自由。
两者虽无对错高低。但以上帝视角来看。无论是“出世”还是入世,都需要经历荡涤,如此入世出世的境界才能是全然真实的。
也只有经历了红尘沉浮和俗世荡涤,“入世”“出世”的维度才能更高。特别是出世后的再入世的智慧,则更接近开了天眼。
因为它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去接近人性,是一种更为本色和聪明的处世态度。
试想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冒着杀身之祸与株连九族之虞,积极入仕为官,这种勇气固然可圈可点。
但甘做草民,身处江湖,醉心山水,亦是一种洒脱的睿智。它绝不是避世,是在专制高压的强权之下的追求人性的解脱。
换言之若能带着入世的洒脱去积极入世,岂不更好?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
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社会主流游戏规则这张“皮”上。
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
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能、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于是无数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以此来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
就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于是乎,正如如今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
倒是顺遂了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指望文人标榜什么“精神自由”,侈谈什么“人格独立”。
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才暂且当稳了臣子和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主宰“他人生死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
所以说几千年的孔孟儒学到如今看来,无非是拿来诱惑莘莘学子飞蛾扑火的灯。
而老庄道学就像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般的文人“精神的避难所”。
之所以说它是文人的精神避难所,是因为俗人有俗人的生活目的,道人有道人的生命情调。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来讲,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不仅如此,老子还进一步说,随缘而遇还要“顽且鄙”,坚持个性,又不受任何限制。
意思是我们与其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不决。倒不如干脆跳脱桎梏。做个身做入世事,心在尘缘外的人。即该当入仕则入仕,该当隐退则隐退,无为之为,无可无不可,可谓是将出世入世的智慧拿捏得恰到好处。
但不是谁都能做到如老庄般洒脱,其行入世,其性出世。大多数平凡又普通的我们,做不到完全跳脱。就像老子、庄子早期也不完全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和庄子的走运在于他们与官场关系始终很浅薄。我觉得正是由于他们仕途上的坎坷,不受统治者重用,因而才避免了“失足”的尴尬,也摆脱了“沉沦”的危险。
所以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心灵的自由度和内心清澈自然的底色。
才可以大白天睡懒觉,做梦变蝴蝶,“ 鼓盆而歌”,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
像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曾一度比较热衷官帽,幻想着成为“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憧憬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
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拷问、折磨, 患得患失、自寻烦恼、甚至扭曲偏激。
至于官场得志如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之流,亦官亦学,则是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腔调。
由此我认为,处世态度绝不止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可以相对多元。无论是孔孟儒学提倡的那样积极入世、还是老庄哲学的跳脱出世。都可以为我所用,最终助我达到悠游于世(也就是游世)的目的。
一如庄子所言:
乘物以游心、游心无穷、游无极之野、游无何有之乡、游于世俗之间、上与造物者游、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吾游心于物之初,游于世,游于道。
换言之游世并不需要在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头衔或经历,更不需要身在名山大川、人间仙境,或是世外桃源。而是在最简单平凡的事物中也能遨游,在命运的夹缝中生活的践踏下,也能游走于入世出世之间,解放本真、悠游逍遥。
更多精彩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哲学式生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