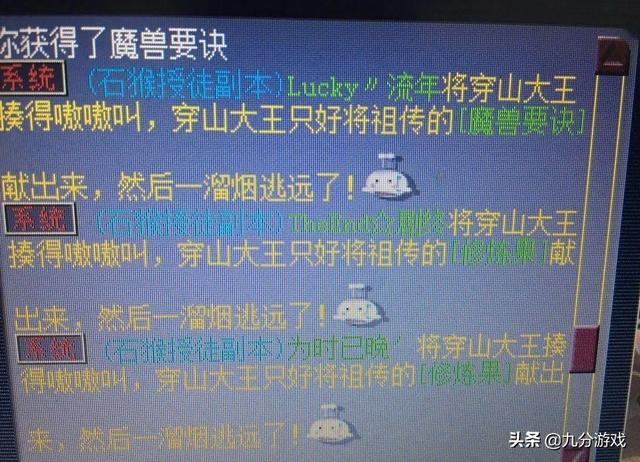孔子主张人性论(理响笔记安乐哲)
2021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文明对话与全球合作”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挖掘古老文明的深邃智慧,共同探讨多元文明的相融途径,呈现了一场人文荟萃的文明盛景、一场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
为了更好地展现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创新理论成果,《理响中国》特别推出《理响笔记——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专栏。今天,《理响笔记》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他分享的题目是《孔子其人所彰显的关系性身份和主体性》。

安乐哲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对以儒家角色伦理为基础的由关系构成的人的概念的常见关注之一围绕身份和主体这 两个问题展开,并且在与自由个人主义所假定的自主、自决式的人的概念相对比时变得更为明显。问题在于:焦点 - 场域的人观,能否对个人的身份、完整性、自主性提供足够清 晰的说明?回应上述关注的一种可能方式是去反思儒家文本是如何塑造个人身份和主体性 的,尤其是这两者又是如何在孔子本人身上反映出来的。若能这样做,我们或许可以找 到一种方法——一种诉诸腿与行走之间、身体与具身化生活(embodied living)之间重 要分别的方法,来替代那种早已陈旧却仍根深蒂固的“物”(thing)的思维模式。在这 里,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主体观:前者视人为离散的个体,并以每个人的意向为指引其 活动的内驱力;后者既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又推动着世界上分散却又非常集中的人之活动 (activities)或事件(events)出现。正如行走是双腿与世界之间的一项重大协作,我 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与情景离散或者分离的某物(thing);同样,人是作为事件(events) 存在于世界的,主体的概念必须具备反映这一事实的复杂性。
《论语》中间部分的一些篇章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与孔子生活相关联的真实画面,它们与孔子的饮食、行坐、衣着有关,也与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如何与人相处有关。这些不同段落 , 为读者提供了很多图像与轶事,将这位模范老师的生活呈现给他那个时代的追随者, 以及代代相传至今的学生。也正是在这些核心篇章内,孔子被描述为有四件他个人绝不能 容忍的事情——“四毋”,这深刻揭示了孔子的自我认识和他自己的价值观: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杜绝了四种毛病:不凭空臆测,不武断绝对, 不固执拘泥,不自以为是。) 这四个“毋”加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整体,其积极含义在于:对孔子而言,过一种道德 的生活,不仅仅指遵守某种道德教义、依从某些既定规则。依据这些严苛的要求,我们可 以推论孔子有他自己所期许的一套总体的、自觉性高而且诠释性强的个人行为习惯;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毕生所追求的是务实的参与(pragmatic engagement)而非抽象的假设 (abstract speculation);开放、包容的态度而非对终局(finality)的执着;灵活的意愿 而非固执己见;对他人之需求的敏锐与尊重而非对一己私利的过度关注。这种惯常的、高自觉性倾向即使不能使人们做到像整个文化传统之榜样的孔子那样圣贤,也足以激发对德 行的追求。
孔子的过程宇宙论 (process cosmology) 回避了一切强目的论或者唯心主义,它的焦 点是如何更好地活在“当下”(very now)。作为一种个人的处事方式,孔子的“四毋” 将行为与人类经验中最直接的东西——关系——联系起来,并且专注于塑造一种习惯性倾 向,而这种习惯性倾向在具体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时最为有效。虽然我们可以视“四毋” 为一个整体,认为四者相互蕴含,但我们仍可追问:当我们单独分析这四者时,我们又如何推知孔子自觉的道德主体?
从记载他生平的文本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他并不看重迂阔的 抽象原则所提供的表面明晰,而是务实地利用更直接、更显而易见的信息。孔子似乎专注 于思量我们生活中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事件中那些现成的杂乱无章而具体的可能性,并依此 行事。孔子之叙事的结构和节奏在他致力于克己复礼(即完善自己的各种角色和关系)的 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
在对人的理解方面,孔子不但抗拒臆测,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全自然主义视角 的主体观,不诉诸于自我的形而上学,也不诉诸任何统一的基础,如灵魂、心灵、自然或 性格。孔子把“人”定义为“仁”,标明了一个在活动中而非活动前,关系中而非关系外 的具有批判意识、自我意识的主体。在对经验世界的理解方面,孔子同样抗拒臆测,反而 引领我们朝着每一天都在发生的日常事件进发,从中寻找我们行为的依据和理由。孔子给 我们提供的这一个主体概念,远非诉诸于某种简单、孤立、高高在上的统一性,对其最恰 当的描述应为——通过一个个生活片段中与孔子相交的同仁、学生和朋友对孔子所表现出 的尊敬而聚焦的自觉的决心。在上述的这些关系中,“诚”在人们的选择方面似乎担当了重要角色:孔子并没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其他人身上,他的影响力似乎更多地通过他对 周围人需求的尊重和理解发挥作用,而这些人的行为也受到了他这一做法的影响。
理解个人自主性 (personal autonomy) 的传统方式是自我规范 (self-legislating):人们 在自己的行为中行使自由和控制权,只要他们受自己个人意志所支配。在更专业的康德哲学 的意义上,自主性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地服从普遍的道德法则,因为它由客观理性所决定。与 这些假设相反,对由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离散的人们而言,他们关系中强制力(coercion) 的缺乏可能成为我们思考关于自治的这种替代理解的另一种方式。对孔子而言,自主性似乎 被表达为人们对自己的角色和行为有自觉的决心,对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有充分的、创造性的 参与;他们通过协商的尊重模式(negotiated patterns of deference)行事,而在这一模 式下,他们能够在尊重他人利益的同时找到自己需求的满足,并在与同伴的关系中达至一种 融合的品质,使他们在所做的事情上不受强制。这样的一种自主性,表现为一个人在行动上 的复杂统一(complex coherence),正如《孟子》所描述的,这就是“配义与道” 。
这种在推测性假设上的阙如,立即就体现在以家庭而非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观念之中, 这是儒家传统的标志之一。当樊迟问及“智慧”时,孔子并没有尝试为它下一个我们从柏 拉图对话中熟知的那种通用、正式的定义。孔子仅就樊迟这个人自身,告诫他要分清事情 的本末轻重: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鉴于亚伯拉罕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的推测性假设,孔子这一与人建立务实有效的关系、 与鬼神保持距离的建议,使得许多评论家认为孔子对人为培育的宗教信仰的各种要求缺乏 兴趣——尽管他也未必厌恶它们。
对这类评论家来说,孔子在寻求与神灵世界建立亲密关 系这一点上,总是表现得静默,所以也就清楚地证明了孔子在乎的,是一种世俗的人文主 义(secular humanism)。这种人文主义解读,在《论语》另一段落,即当文本谈及孔 子的课程内容时得到强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段描述了他的教学体系所排除的内容。 在这一段,我们被告知:虽然孔子乐于把自己的见解灌注入已被接受并仍在不断发展的人 类文化,但他不愿意去推测人类的未来命运,也不愿意去推测宇宙的将来会怎样演变: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专注于探究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文化取得了什么成就,却似乎不太愿意冒险猜测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解释这些段落时,虽然有些人把孔子思想归类为去魅的人文主义(disenchanted humanism)。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进行另一种解读,以与孔子以家庭为中心的 宗教设想统一起来。例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孔子来说,真正的宗教信仰,并不在 于敬畏和祈求远古的神祗,而应该在邻里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另类的宗教信仰表现为一种 共享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精神性(spirituality),这通过追求一种家庭和社群之间的卓 越生活而实现。对孔子来说,一个人的成长总是围绕个人的自修展开,同时还应致力在紧 密的家庭和社群关系中不断地向四周伸延出去,以至于达到宇宙整体(cosmic totality) 的高度。在那里,有一个相互渗透的中心和外围,最自觉的集中具有最大的延展范围及影 响力,与此同时,最广泛的延展又被反射回来巩固最集中的东西。更具体来说,我们可以 这样推断:对孔子而言,在家庭道德生活中流露的自觉的尊重、崇敬和感恩,同与对祖先 的崇敬和一种自然的虔诚之表达相关联的那种静逸欢愉的精神性两者之间,具有直接而密 不可分的联系。或者更简单地说,这种儒家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宇宙归属感,是由我 们在最直接、最亲密的关系中获得的价值感所激发的。
如果拉丁文“ 宗教”(religare) 一词的本义确实意味着“ 紧密结合”(to bind tightly),那么,礼似乎就是理解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教的关键词,因为它是一种社会 语法(social grammar),能够在社会结构中产生有意义的联系并增强其强韧度。“礼”, 始于对家庭和宗族的仪式化奉献,然后扩展到社群,并同时把众人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 关系神圣化。在这一解读下,传承至今的传统春节应被视为一个意义深远的宗教事件。在 这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中,我们见证了主要移民城市人口大量向外流动的现 象。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会用尽一切可用的交通方式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进行持续一 段时期的庄重的道德“再创造”(re-creation)。这一再创造活动由一个终其一生都受 到道德教育的熏陶、十分尊敬培育了自己的家族、长辈、老师以及社群的人群参与,并且 他们会把自己的“老家”视为判别自己个人身份的一项主要决定因素。本着这种对家庭的 崇敬,他们回归自己的“根”,去续存他们最亲密的关系,在几周后蓄积了足够的力量, 又返回城市里去工作,如此这般,年复一年。
唐君毅先生将这一充分体现了以家庭而非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信仰的早期中国天道观 (cosmology)概括为“性即天道观”。这一主张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正在成为 什么样的人这件事从根本上被嵌入到我们无限的叙事中,因此,只能通过考虑我们全盘的 情境化关系来全息地理解之。这种对焦点 - 场域主体性(focus-field agency)的理解, 要求人们从最远的外围场域走近焦点然后进入中心点,同时又要从整体到特殊,从与我们 无关痛痒的各种因素走向与我们最相关的各项细节。这种焦点 - 场域主体描述了一个人的 自我意识显现为整体中或多或少有意义的决心的中心。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叙事场域,他的 后人可以在《论语》以及其他经典文献中看到这些故事。后学通过在孔子的大小故事里面寻找灵感来塑造自己独特的人格与行为习惯,而把孔子的叙事变成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子绝四之二——“毋必”(不武断绝对)。这样避免将固定的、终极的东西作为命令 或普遍法则是基于他对变化和新奇的基本尊重。它反映了孔子对置身于“生生不已”这个 宇宙法则之中的人类生命的开放式复杂性(open-ended complexities)的一种觉悟。“生 生不已”四字出自《周易》,有连续不断并且不可逆转地在变动的深邃意涵。在《周易》 的其他段落,这一生生的过程被明确表述为“天地之大德曰生”。这表明我们的出身、成 长、生活都在情境化的、不断发展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展开,在这一背景下,自我 意识的成长本身就是宇宙道德的实质。在这一个过程中,主体感首先出现在我们在不断展 开的个人叙事中,目的明确、深思熟虑地担负起至关重要的、常与人协作的角色时。焦点 - 场域的、关系性的主体性的这一典型特征,要求我们不仅要对这些角色的持续成长保持不 懈关注,还要具备足够的道德想象力,去意识到并且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不可化约 的复杂的人是生动而活跃的,在不断地尊重他人、与他人协作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保持 随机应变、知错能改以及乐于助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既没有终局也没有结束。
与此相关的是子绝四之三——“毋固”(不固执拘泥)。这一种灵活性,为明于自省 的人所必备,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经验交易、联合的性质,并坦然接受在周围其他 人的域境内自己身份之多重性,是多变而又确定的焦点。这种焦点 - 场域的主体,必须被 理解为在他们重要的关系模式之中自觉地去塑造或接受塑造的、不可化约的交易性的主体。 根本而言,这种主体性只能通过已然确立的认同和顺从习惯而议定。也就是说,虽然这种 行动在受到过去影响的意义上必然是被动的,即总是“承受”着他人的行动,但它同时也 必须在自觉性、灵活性、目的性、前瞻性几个方面找到适当的平衡。简而言之,我们只有 在定义我们身份的活动中灵活反应,才能过一种道德上负责任的生活。
子绝四之四——“毋我”(不自以为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主体有不可化约的社 会性,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随着通过在关联中塑造了他们的符号学过程、符号学能力而逐 渐适应于一种文化(enculturated),这些焦点 - 场域的主体从与他人的“内在”主观关 系(“intra-”subjective relations)中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自我反思和反省意识。这些既 是精神的又是极度物质的物活性主体(hylozoistic agents),必然以他们散漫却活力充 沛的血肉之躯,演活他们生命之中的多种角色。但是,当他们努力地在变化着的同样有机 的身体和社会关系(equally organic phys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结构中实现一己的 一致性时,他们的身体就像形成了多孔薄膜那样,不断地将经验内化为他们发展着的身份的一部分。
这些焦点 - 场域的主体必须施展他们通过学习得来的能力以应对所处环境,而同时在与 其他人共享的活动之中,非强制地展现出一种由关系定义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这些环境 当中合作关系的最直接结果——一个合作网络的价值和目的变成与每个协作者自己的相一致。
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道德生活,有着自己的一套特定、专门的词汇,但在另一种哲学背景下更好地理解这一学说,并更有效地与当代西方哲学家沟通 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是问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当代自由主义在讨论伦理学理论常用的专业术 语,例如“自主”、“选择”,我们能否将之重构,然后用来有效地解释儒家角色伦理学呢?
自主性(autonomy)一词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是“Gk autós”自我 “Gk nomos”法则,字面的意思为:对自己发号施令的人,或自我立法的人。在儒家角色伦理 学里,我们不能把“自主的人”理解为独立、理性的行动者;也不能把“选择”理解为人 们可以在的他们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之中,以独立行动者的身份进行自由选择。在儒家的 传统内,拥有自主性的行动者的选择,一定指的是受关系制约并且彻底嵌入其中的人,通 过投身他们自己特定叙事中的角色的特性而表达自己的偏好。我们所理解的“关系性自主” (relational autonomy)并不是指那些对自己特殊、独立的行动拥有操控权的个体,而 是指那些有自我意识但又有不可化约社会性的主体,他们通过在持续的交往中相互适应, 能够在非强制的情形下行动。同样地,我们所说的“抉择”(thick choices)并不是指 离散个体不受他人影响、不考虑他人利益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时,所作出的碎片式重大决定, 而是指具有批判性自我意识的社会性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表明了他对自己的角色和关 系中的某种行为模式一以贯之的坚持。
传统上,自由理论中的“自主”是指自我管治(self-governance)意义上的独立自 主,由一个被认为是离散、排他的自我开始。可以说,这种个体离散性的概念仅仅是一种 功能性的抽象,并且有时候所谓绝对自主对这一点的声称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却仍然具 有强大影响力的虚构。事实上,假如关联生活(associated living)是实情的话,我们表 面的离散,就不是一个初始条件,同时也不会排斥别人。相反,我们会变得独特甚至出色 恰是因我们一直以来能够与人相处而具有的特性。儒家的人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独特的、 相互依存的人的另一种动名词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关系性、独特性、社会性,正 是他们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来源及表现。而且,对他们来说,这种个性化——独特、 坚定的特质——非但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弊,反而是通过他们在构成自己的关系模式中所达 到的水平高低来衡量的。自觉的、关系性的自主所描述的是目的明确、非强制的活动,因 为这些活动在我们的角色和关系中实现圆满。有批判性自我意识的、不可化约的社会性的 主体的抉择(thick choices)描述了这些主体在其生活角色中所具有的决心和承诺。
由关系构成的人与他人相互依赖,彼此没有特定界限,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作为“自 我管治”的自主都需要一个集中但在程度上分散的个人身份,以及在交际中,它必须将所有相关的利益都作为其自主特性的组成部分。对以上这种相互依存的自我来说,关系性的自主要根据彼此之间的关联做出协调,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差异,以期在大家共享的明智做法中实现有意义的多样性。这样的一种关系性自主定义,跟一些表面上的独立自主的选择的说法大相径庭;它就是一种功能,在自愿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来达到自己的合 理目的,从而能够在常见的共同活动中把强制减少。事实上,那些被视为模范的人,他们的自主性比其他人更强,甚至变成了启迪别人的榜样——他们能够吸引人群,并且通过获得大家尊重的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影响和塑造了群体行为。以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纳尔逊·曼德拉三人的模范人格故事为例来说,他们都具备这么一种关系性自主,并且通 过作为榜样的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并且已经造成了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持续巨变。通过尊重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以及追随他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有人都与他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身份(corporate identities)关联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构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原则并不会剥夺人们各自的主体性或者选择权,而只是要求我们以与关联性生活的经验事实相符合的方 式重新思考我们所熟悉的如自主、选择这样的术语。鉴于基础个人主义 (foundational individualism) 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常识性看法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提及由关系构成的 人的概念,会常常被误解为要向我们提供一种被大大弱化的个人身份感。然而,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证明,在关系上建立的人观不但没有损害作为个人自主性表述而受到高度评 价的独特身份,实际上反而提升了它。例如,在希腊唯心主义人类范式中,个体身份是外部关联、个体分散式的,每个个体都被赋予一些相同的特征(eidos)。在这样的一个范式下, 人被视为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是偶然会有一点分别。在这个模型中,个人身份只能带有一 种相对残缺的独特感。相比之下,本构关系之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非凡、独特、 不可替代的,是且仅是我们自己的关系矩阵——中的一个学说即是一种彻底嵌入式的人的模型,这一模型反而将那些可被归于个人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放大了。
此外,通过说明个体身份自觉、专注、目的明确、有决心,并且同时在重要程度上扩散在我们的关系中,角色伦理学在生活的事件当中定位人,从而提供了一种经验上更有说服力的人的主体性概念。虽然我们焦点身份的独特性由这样的决心而得到确定,但这种独特性与我们对他人的意义相关,并且依赖于此。在我作为母亲的儿子这个角色中,我一直 以来的身份与行为必然受到我对亲爱的母亲的感情的尊重的影响。个人身份当然是特殊和独特的,但同时它也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其中包含了多段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是包括而 不是排除我们周边的其他人。如此理解我们的角色身份,那么它虽然是持久的,但也在不 断地变化;虽然非常自觉地富有目的性,但同时也非常包容和圆通;虽然出自主观个人, 但同时也尊重并关心其他人。
当我们转向儒家文本去证实这种关系性的自主而非个人性的自主,以及一以贯之的抉 择而非碎片化的选择,我们或者可以套用黄百锐从《论语》中引用的一段话作为说明。 黄百锐就是以它为例发展出他自己称之为“关系性的、自主的自我”(relational and autonomous selves)的微妙概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黄百锐对这段话的理解是:孔子比大多数人更“自主”,因为作为一个模范人物, 他是自己行为的唯一控制者,能够坚持一种理想的整体特质——“义”,而不受被他影 响的人的影响。这里表现出来的正义感,使得他能够不受那些在特定环境下由特定的人 触发的特定情境特征的影响。用黄百锐自己的话说就是:“似乎贵族阶层的部分成就就 在于这种保持道德卓越的能力,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和谁一起生活,他们都能对他人施 加影响。”
我们随即就会想到一些也许能够支持黄百锐上述说法的《论语》文本佐证。举例来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之风,必偃。”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我们也许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出与黄百锐的解读相关的一个类比:孔子是明辨是非的典 范,而东夷是蒙昧的不辨是非的人,这些人将不得不俯首于孔子的正面影响之“义”。
孔子在这一对话中想要表达什么?首先,身为国相兼三家之首的季康子,被孔子视为 篡夺鲁国王权的人。而从这个段落以及其他几个段落,我们知道孔子把这个篡权者看作是 一个无能管治国家的人。季康子想要把杀死一些自己的人民作为管治国家的方法这一事实 也遭到孔子谴责。对孔子来说,有效的管治,取决于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用以教化 人民的价值观的典范。但这些价值的来源又是什么?“善”在这段话中被解释成为统治者 努力达至行为上的“善”(good),而不是单从人所固有的某种先天的或更高层次的“善” (goodness)衍生出来的某种优越的品格特征;也不是某种通过指导一个人的行为而得 到践行的“善”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道德成长意义上的“善”始于连续叙事中散漫的 关系性活动。只有这样,它才能充当对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一般描述。“善”是通过相互“联系”(relating)和有效沟通来发展我们的关系并使它们变得“有意义”(meaningful) 的社交活动。要想真正做好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且使得这样的行为对我们的同伴也是善的, 需要尊敬和尊重。
一切行为那种不可化约的关系性质,以及“善”作为一种特性的事实,被理解为是在 关系本身中得到实现,而不是作为属于模范者的某种品质。以上这一点,在《论语》另外 一个相关段落中得到明确阐释:即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区别,与追求行为完满的人们所 要求的行为质量无关。无论是与家人、公众,还是与昔日的“野蛮人”打交道,完美的行 为都需要真诚的尊重、尊敬和尽心: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中这段提到德风草偃比喻的话,在《孟子》中也有出现。就一位国君之死, 孟子向其储子提出忠告,建议后者遵从孔子的训示,为朝廷设立一套新的守丧三年的规矩。 同样,这里的传达的信息一定是:统治者必须成为影响人民做出改变的榜样。但要指出的 重要一点是,模范人物的影响,来自他们与其他人交往时的尊敬和尊重,因为这种态度, 本身就是他们为“善”和做“在一定情况下最适当的事情”(义)的源泉。
孟子对这位世子的劝告,始于世子自觉地认识到自己过去荒废学业而没有受到朝廷官 员和亲人的重视。因此,作为新即位的国王他将难以获得他们在国家事务上的支持。世子 遵从孟子的劝告,注重自己的品格,故此能够提升和完善自己的行为,给人民树立榜样。 通过这样做,他赢得了朝廷的尊重并且能够改变大臣们的行为。如此一来,这种改变是并 行的:世子的品格,因为人民的期望而得到改善,而他的人民,也因为他现在的模范行为而相应得到改变。
下面我们按照解读《孟子》中这一段话的方式来解读《论语》中孔子想要与东夷一起生活的段落。对孔子来说,“义”有“做最合适的事情”的意思,这当然也是他 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将作为最终决定因素而援引的标准。不过, 对孔子而言,“义”的观念又肯定不是某种遥不可及的、前置的原则,凭借着明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相反,孔子认为:与夷人一起生活,那些渴 望成为榜样的人和夷人一样,通过相互迁就以及在人际关系中追求最适当的关系,彼 此都会变得越来越“意义重大”(significant,义 ) 。而在这个共同的叙事中,孔子 和“夷人”的身份都会发生重大转变。考虑到由关系构成的人,黄百锐所说的“理想 的整体特质”其实就是通过多数人的利益和典范人物的行为关联起来而实现的。这样, 由孔子行动随之而来的“行而宜之”(义),就会符合所有相关方(即孔子和夷人) 的利益。正是这种在多样性中实现的共享和谐(一多不分)构成了孔子的关系性自主。夷人受到启迪,向孔子学习并以孔子为榜样,他们的行为肯定会有所改变,使他们能 够戒除任何陋习。与此同时,随着夷人在他的影响下行为既得到道德上的提升又保留 了自身独特性,孔子也将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这段话并非期许单方面将 一个既定的标准强加于东夷,孔子与东夷必须以一种并行关系在携手合作中相互适应、 共同成长。
从孔子的角度出发,通过接触和学习另一种文化,他对“义”的理解(即什么是适当 的和有意义的)会变得更加丰富。事实上,当孔子的学说被接受并且适应于新人群的不同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孔子本人的地位和影响也将得到价值提升。榜样当然会激励那些效 仿他们的人,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效仿,他们也不能成为模范榜样,并且效仿者对榜样的 尊敬,也会引起这些榜样自身的重要变化。
作为理解上面这个段落的一种具体方式,我们或许可以思考儒家文化对“东夷”—— 即朝鲜、日本、越南这三个东亚民族历史的延伸。这种文化价值观与制度不是通过武力或 者占领强加给其他东亚国家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儒家文化一直都在以不同方式在 不同程度上,被这些不同的人群自觉接受和使用。而且,在此一转变过程中,被转化的不 仅仅是这三者,而其实牵涉到全部的四个汉文化传统。韩国、日本和越南的独特文化,以 及中国儒家文化自身的本质,全部都因为这一全息的焦点 - 场域过程而变得不同并且更加 丰富。在这种全息的焦点-场域过程中,每种文化都与其他文化相互关连。在这种模式下, 自主并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范本通过单方面超越其他文化影响并将秩序强加于他人, 从而控制他人。相反,关系性的自主需要同时结合非强制性的解决方案和回应性的尊重。 这是一个机会,让身处关系里的所有各方,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不断演变的文化 传统作出贡献;这种传统,同时也是“一多不分”的。如此一来,所有各方都在这个多边进程中得到转化。
在当前历史时刻,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这四种独特的儒家传统似乎都处于上升阶段,鉴于他们所信奉的儒家价值观,他们应逐渐成为当下不停变动的世界文化秩序的重要资源。本来,儒家作为东亚地区的一种整体性现象,对当下这个不停变动的世界文化秩序的塑造,应该是很有作为的,但随着他们自身关系的弱化,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秩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减了。
闪电新闻记者 王清宇 报道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