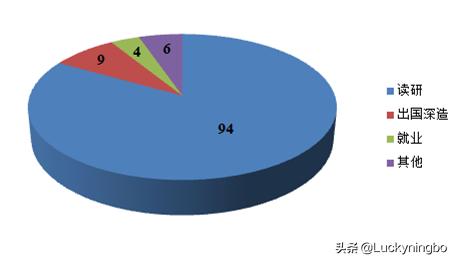回忆录感谢恩师(怀念我鄱阳街小学恩师们)
怀念我鄱阳街小学恩师们
1 难忘的第一个恩师——高小班主任刘玉兰
每当走过现在汉口大名鼎鼎的鄱阳街小学,我都会忍不住停下脉脉含情凝望。

90年代初拍下的母校31小大门教学楼
在我读书时,鄱阳街小学叫做汉口三十一小学。门口那栋标志性的大楼,当时就耸立着(现在改建装修后似乎变得高大上了一些)。我们的教室在三楼。大楼侧后是一个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操场,操场右手有几间平房,住着一些教师。后院当时还有一排平房,好像是教研室。我妹妹她们一年级也在那里占了一间上课。
我转到三十一小读高小的那年(1953年)冬天,“大寒”的前几天,汉口气温陡降,北风呼啸,天气奇寒。鹅毛大雪不停地下了多日,街道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凝成了冰块。我看见大人们用洋镐在中山大道挖开大块的冰块,足有半尺厚。
那年头大部分市民生活条件还谈不上“温饱”了。天一冷,冻手、冻脚、冻耳朵的孩子特别多。哪怕穿棉鞋(祖母怕我冻着让我带去换上的)上课,脚都会冻得生疼。我们使劲地跌着脚取暖,也无济于事。
可就在这种天气里,我们正好要在教室里进行期末考试。我记得,那天砚盘上的水成了冰,连墨都捱不动了。坐在前排的小女生有人都冻哭了。
忽然,我们的班主任刘玉兰老师仿佛天使般、捧着一盆熊熊的炭火到来了。教室里顿时响起一阵兴奋的小声欢呼,对于平日都把我们像自家儿女看待的刘老师,大家都觉得既然天这么冷,她会这样的。
她在前排放下火盆,后然马上转身又下楼去了。不一会,刘老师又端来一盆!原来她就住在学校。火,是她在自家用自家的板碳生的,火盆是她临时用家里的脸盆盛上灰临时“赶制”的。
每个孩子都感觉到了教室里明显而又特殊的温暖舒适!
那年头我的感觉是,每个老师皆如同父母般亲切。我们是二班,一班班主任柳老师也是这样在孩子们口中传颂。柳老师更年轻,长得也漂亮,天热时穿着长裙。而刘老师开始看上去并不美,就像一个武汉很多见的主妇一样,说话声音也大。但是用不了多久,学生就会把她当作母亲一样尊敬,给人留下的全是美丽和亲切的记忆。
我说过,当时一般孩子读书很少像我这样是六岁多就开始的,我属于年龄小,是小个子、小聪明、小调皮。我不属于那些喜欢打架惹祸的那一类男孩,却属于上课喜欢讲话、听讲爱打野、做小动作的那一类。如果套用现在“扰乱社会秩序”的格式,我恐怕属于扰乱课堂秩序的“惯犯”。但是偏偏我的学习成绩又很好,这让老师对我恨爱参半。不过,我居然从未受到过让我难堪的惩罚。
刘玉兰老师也和五女中附小的老师采用了一样的措施,让我和一个模范女孩王小珠(化名)——就是每个班都有的、最讨老师喜欢的那种——同桌,以减少了我对别人的妨碍。

31小校内:我们的教室在左栋三楼。大楼侧后就是个比篮球场大不了多少的操场
记得操场照片左手还有一栋三层楼房与几间平房,住着一些教师。从这张照片看左边那栋(只有一点点)好像就是。当时后院还有一排平房,好像是教研室。我妹妹她们一年级也在那里上课。照片中操场通向鄱阳街的小门(正中偏右)也还清楚可见。
1954年,武汉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江汉关水位最高涨到29.73米。那年武汉人民在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
我可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天天亲眼目睹的。
我们上学路经的中山大道、天津路、合作路、鄱阳街,以及我们放学常故意串绕的黄陂路、兰陵路和这边的北京路,满街都散落着黄泥。这是汽车、人力板车运泥土往江边加强堤防时漏下来的。那年大雨几乎没断过,每条马路也变得和乡间一样泥泞。我甚至以为,这些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干净如初了。
尽管洪水一天天高涨,但市内一切生活照常,人心和物价一样,十分稳定。学校离江边不到一百米,但是我们家长们每天都放心地让我们自己去上学。显然谁都相信政府肯定能战胜洪水,绝不会重演1931年的惨剧。
不过我们都听话,除了学校带我们去参观过一次,我们自己从未到江边去“看热闹”。

1954年防汛汉口场面
那些军民在堤上,泥脚腿、泥双臂,很多人赤膊上身,手捧着盛满泥石的竹编簸箕,排成长长“接龙带”的画面深刻印在了我的心中!
刘老师给我们讲述了1931年(她嘴里说的是民国二十年)武汉水位28.28米被淹水的故事,并让我们从心里相信:在新社会,武汉人防汛必胜。
她拿来一张漫画要我们临摹。
画中是两条拟人化的鱼在仰看着武汉关大楼:“小鱼说:‘妈妈,你不是说,大水来了,带我们去游“民众乐园”的吗?’
大鱼叹气说:‘孩子,那是1931年的事,现在不行了。’”
当时这张宣传漫画街上看到过多次。同学都喜欢临摹,我也画过几张,和同学们在鄱阳街散发。
我们听说了几次洪水如同猛兽冲刷江堤,武汉军人和筑堤工人挽着手、站在齐胸的水中组成人墙、保护江堤的故事。我们幼小的心里对他们肃然起敬,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危机感。
54年水位一度达到29.73米,但武汉战洪的胜利就这么豪迈地载入了史册,让世界刮目,让武汉人终生自豪。

1954年的武汉军民防汛大军
那年头,班上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不多,不少孩子都是家中“祖祖辈辈”的第一个“读书人”。有些同学家里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不少同学家长在做工,不能按时回家。同样,班上学习成绩也是参差不齐的。下午三四点放学后,男孩们便在街上“野”。好一些的,打球、到江边玩。糟糕的,打架、骂人,偷小贩的东西吃。
可刘老师办法多了,她连孩子们课余都不放任。我想:这是因为每个同学在她心里都是她的孩子。这个大学者们也许会不屑一顾、视作卑微的小学教师,以她呕心沥血的那种赤诚、那份爱心投身教育,是没有什么难倒她的。这也许就是我至今不把某些“教育家”放在眼里的缘故吧!高级别的“大师”们,你们差太远了!
刘老师把全班按住处、成绩(好中差搭配)分成了六七个“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在有条件的同学家里做作业。但有三个小组没有条件,她就将两个放在教室,一个放在她自己家里(她家就在学校楼下,是十来个平米的单间),揭了床单,让同学们并排趴在木床板上写字。
开始时,我被分到一个女生云集的小组,放学后去王小珠家“学习”。我极为愤怒,因为与这么多女生一组,让我很没面子,而我家里本来是有很好的学习条件的。
我找到刘老师申述,但是她回答说,需要我做到三条,就让我换组:第一,帮好两个女生(她们都大我四五岁,比我高一个头)学习;第二,今后上课不讲话、不做小动作;第三,跟王小珠的舅舅(一位我终生不忘的、我最早的音乐启蒙老师)学会一个节目(她已说好了),参加学校的六一儿童节演出。
我们听老师的话,向来都是超过听家长的。几个月后,我完成了所有三条。
王小珠的舅舅是武汉一师(位于赵家条)毕业的音乐老师,在他的耐心帮教下,我初步学会了简谱识谱。加上我自己家里良好的音乐条件,这几月,居然我得到了让我终身享用的进步。
王小珠的舅舅后来又到三十一小,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排练冼星海的《太行山上》二部合唱,以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等十几首歌曲,我都是在低音部。我们全班竟都爱上了唱歌。我也是此时初次体验了“和声”和“对位”。
几十年后,我听说王小珠成了武汉音乐学院的教授。
那年,我们年级被好几次安排到少年宫演唱。还由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后,在少儿节目时间播放。记得有一个歌由高我们一年级的、原三十小(北京路小学)的谢芳(当时她已经进了20中)领唱,她后来可是闻名世界的电影演员。
我父亲见我喜欢唱歌,便亲自给我讲了当年《太行山上》的诞生经过,我那时还小,不懂得我的家庭曾经那么幸运,怎么这歌作者冼星海原来是爸爸的朋友?只觉得好玩,爸爸“有板眼”!于是我就和同学一起看了《夜半歌声》,虽然吓得一年不敢一个人独自过夜,却迷上了盛家伦的歌声,于是父亲下班后亲自教我唱了这里面的所有插曲。1955年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学校操场举行的联欢会上,独唱了苏联歌曲《坦克车手》和冼星海为《夜半歌声》谱写的插曲《热血》。
刘玉兰老师兑现诺言,让我“自立门户”,组织了一个全部都是男生的学习小组。
我们的新学习小组就设在我家(汉口公新里六号),被我们自命为“莫让伊斯基学习小组”。 莫让伊斯基是俄国科学家,据说比美国莱特兄弟要先发明飞机。我们做完作业后,就兴高采烈地一起制作起飞机模型来(为孩子们预备的成套的材料是我父亲买来的)。做好了,就到江滩上去试飞。那成功的喜悦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了不起。
不过因“资金有限”,而当时成套材料又很贵,我们后来就没做模型飞机了。
但我们创造的欲望停不下来,便量体裁衣:先是用钢丝锯、三夹板来做中国地图拼图,这一成果很快受到班主任刘老师、地理艾老师的当众表扬。后来我们又做了很多房屋、船的模型,手工剪纸模型,每个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绘制各省地图,有的做石刻,我们还自制风筝到江边放飞,风筝做得很成功,我们在线放完后,用到处捡来的烟盒和天上的风筝一次又一次熟练地“打电话”……
量变终于升级为质变!不久,我亲手制作了幻灯机、显微镜、折光镜(潜望镜)等对大人来说技术含量都不算低的一些实用工具。
我的祖母最疼我,她把公新里六号二楼的一整间(冼星海原来在此工作过、父亲编辑《大家唱》的)房间(大约50多平米)腾出来,让我把制作的各种东西摆成展览状,请来老师、同学、戴文琦表哥、乡下来的亲戚同乡和同龄人,一本正经参观。我的童年在创造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也许正是我的小学,为我最终究成为多个企业青睐的开发型、创新型、顶梁型工程师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还制作了不少连老集邮者都看得上的“紧绷透明”的邮票本!还在画家姑父(张振铎)和姑母曾竹冰教诲下,学会了自己划好玻璃片,在上绘制幻灯片……素描基础也得益匪浅,特别是姑父教授的“质感”要害,对我后来帮助极大。
不过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学课的。当时在地理艾老师鼓励下,我又提前自学世界地理,绘制了全本的《二战后世界地图》,又让我的地理知识受益终生。
我们对学习充满兴趣,我不懂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只要分担我这其中一项都那么难?这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做的事,还不包括我们大量的书籍阅读!
2 当“坏”孩子遇到刘玉兰老师
还是在大防汛那年,刘老师给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讲了都江堰的故事,讲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让我对历史的兴趣大涨,甚至阅读起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志新编》来。
也就是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班兴起了孩子们互相交换书籍阅读的热潮。我读了一批少儿书籍,从张天翼的《秃秃大王》到翻译小说《维嘉.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在家里》等,印象很深。
进一步,我姑父李行夫不放过机会启发我和表弟,古典文学名著成了我高小的阅读上瘾书籍,至今还能背得《水浒》的回目和一百单八将的“石碣天文”!姑父带着我们有节奏地背颂着回目,围着家里的八仙桌“游行”玩。至今老母回忆起这画面都充满愉快。
那时我也爱上了集邮,除了我学会自制精美的邮票本,还对收集邮票发生了浓厚兴趣。我记得为了要收齐“纪1到纪30、特1到特13”以及“纪20错版”我挖空心思,当然主要靠我父亲的背后支持和投入,我渐渐达到目的。
在吉庆街的汇通路与崇善路之间有条巷子,进巷右手一家石库门房子一楼有个玩邮票的高手,我们都称他“秘密位址”,可以到他那里选择自己需要的邮票,拿自己多的“调”(第3声,汉口方言:交换)。
舍得下本钱一些,就到交通路旧书店(后来好像变成外文书店)门口的一个邮票摊子,叫做“断指嘠”(少一个指甲)的那里,一般都可以找到,但是因为贵,得慢慢来。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一个据说是兰陵路袁世凯后人的邻居邹文(化名),另一个是我们“莫让伊斯基学习小组”的、毛笔字写得比我好的周湘(化名)也经常和我在上海路邮局门口或者“断指嘠”那里相遇,他们邮票实力不如我。但周湘的大楷字写得很有笔力,我比不上他,便有些嫉妒。他呢,更加使劲要全面超越我,我们在悄悄较劲。
我们还一起去逛过两次周围的书店,特别是去了江汉路的新华书店。
男孩好动,能够创造性地学习,也能创造性地破坏?不过可以用来交换阅读的书毕竟有限,哪里去借呢?当时的阅读环境的确难比今日。
不久,他们两个的语文成绩忽然突飞猛进,我发现,他和另几个同学语文课的问题回答变得完美无缺,特别是“时代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几个教学要素很正规,连刘老师都有些吃惊。
周湘开始在我面前炫耀,嘲笑我。不经意间,他拿了一本书在我面前晃着炫耀。我一眼看到,是一本教师用的语文教学参考书,而更让我一眼看到吃惊的是:书背后没有盖章!
偷的书店的?
我觉得蹊跷,在一次和老师谈话时,我不经意讲出了这个秘密。哪晓得当天放学后,周湘约了那几个同学在半路等我,要和我算账,说是我“告状”,要教训我。
我当时不懂什么是告密,只是解释说我不是有意说出去的(其实多少有点受嫉妒心驱使)。不过那天我们并没有打架。可能周湘只是为了吓唬我。况且他比我大两岁,也更懂得社会上的名堂,多少理会“适可而止”、“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经典。他临走时留下狠话,假如刘老师对他“有么事”,他会搬“湖南伢子”带人来和我算账。
湖南伢子是当时汉口名噪一时的街头霸王,膀大腰圆,连大人都敢揍。说真的,我听后很害怕。更生怕那些人会侵犯刘老师。
不料,此事后来竟风平浪静、无声无息。他们几个居然都公开拿出那本书放到桌上来看了。就是教师专用的参考书。
又过了几天后,我才听一个同学告诉我,原来刘老师和他们谈话后,自己一个人到新华书店去交款买下了这几本书,送给了他们。
我们则很快把不快都忘了,又和好如初。又一起沉浸在无穷的、让人愉快的课外活动中。
回忆起来,到我们毕业时,我们班开展的小皮球、乒乓球、绘画、歌咏、旅游、阅读……不知留下了多少丰富美好的记忆,至今想起来,如同陈醇之香不去,让人不舍、难忘。
我敬爱的刘老师,写这篇会议时,她应是九十多高龄了。我想对她说:刘老师,请原谅我从没去看望过您!但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您!因为你指导我走上热爱知识的道路,让我度过了丰富多彩的童年。
3 艾老师和刘方老师
和刘玉兰老师一样,至今在我脑中能清晰地再现他们的音容身姿的老师,还有许多。
小学的记忆并不都是单纯和愉快,在年幼的心里,也留下过很多困惑和不解。我的老师不是圣人。可是,我的心里只记得了他们神圣的一面。
艾老师,她教过我们很多课,数学、地理、美术、音乐。我记得她很漂亮,有些像上官云珠。走进教室时一手托着讲义夹,粉笔盒、尺子都放在上面,很像佛教寺庙里常见的一个姿态。
孩子们觉得她走进教室时太美了,经常议论。周湘推测说,艾老师肯定以前当过“戏子”。
“艾老师,你以前当过戏子吗?”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没有。”艾老师答完,忍不住“扑哧”地笑出了声。
我数学好,为了保住领跑地位,出于虚荣心,五年级时,我便提前做六年级才学的文字题。有一次,我遇到做不出来的了,正好看见了艾老师,便去问她。艾老师帮我讲解得很清楚,让我知道怎样去分析文字题的含义,她教我的假设思维,现在想起来,就是代数学的思维方法了,在当时让我思路大开,受益匪浅。
“这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要先把现在的课学好。”她笑着对我说。
我学好了呀!我心里有点不服气。
有次,她在下课后叫我一个人去她教研室。这下,我以为犯了什么错误,心里忐忑不安地去了。
她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叫我坐下,拿出我的地理作业本在桌上打开,问道:“这幅广西省地图,是你自己画的吗?”
我说:“是的,是用您教的打九宫格方法画的。”
“怎么?”她得意地回过头对房里的其他几个老师说,“我说的他能画得到这么好吧!”她又车过身对我说:“画得真好,画得很准,地图就要这么画,颜色也填得好。但地图不能打满分,你自己说,我给你打多少分呢?”
“九十八分。”我贪心地说。一遍偷看站在一旁同样微笑着的刘方老师。
“好!”她答应了我,写上了98:“但是你以后还要继续这么认真地画。”她盯着我说。
我忍住内心的狂喜。一般有个70分就算得到“充分肯定”了!从此,我对地理兴趣大增。前面说过的制作中国地理拼图外,我又找我的表哥(秋哥)提前学画二战后世界地图。我因此有了不错的地图知识,一直记忆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
不料,一个假期后,我们回到学校里,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艾老师从学校(前面照片操场左边那栋)三楼跌下到操场,不幸去世!
我们难过极了。
那年月,不解的事情很多。关于她的死因,也有很多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在我心里一生都供奉着她。我要用鲁迅先生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那句话献给她:
“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刘方老师也教过我们的地理,教过自然、历史。教自然课时,他亲自放学后带我们到江边去拣石头,教我们认识花岗石、长石和云母(真没想到,我长大后参加工作最早到的地点就是丹巴云母矿,面对大渡河滩铺满的大片云母,我的脑中跳出的是刘方老师给我看的第一片云母的图像)。当时,十一二岁的孩子,甭提多高兴了。
不过,我记忆最深的是他给我们上历史课。
每当讲到帝国主义入侵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整个课堂气氛也变得庄严。在一次讲到十九路军上海抗战时,他竟当堂泣不成声。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觉得老师哭很可笑。他却没有在意。他平静下来后,便开始讲他当年参加抗战的故事,很快让我们入了迷。
刘方老师曾经是国军中的高射炮兵。从他口音听来,好像是川军的。他说,一次他对来视察的法国顾问回答说,做完瞄准动作要3到5秒,法国顾问听完哈哈大笑,然后斥道:“你太会吹牛了,连我们法国人都要8秒钟。”他的上师便跟着呵斥他,然后命他们演示一盘。结果他们3秒中就完成了动作。法国人激动得跳到工事里,握住他的手说:“太棒了,我们法国人……要……8秒钟。”
写到这里,他的音容相态都冲过我满含泪水的眼眶跳到我眼前。
从这以后,我们都盼望上他的课,并且要求他“讲快点”,好留点时间讲抗日的故事。他便给我们讲上海淞沪抗战,讲武汉保卫战,讲湘江之战,讲到失利、讲到中国人牺牲时,全班同学和他一起失声流泪。他在学生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宛如一个民族英雄。
不过有些事情是我当时的年龄无法理解的。大约是1954年底,一天,我们看见十几个教师被集中在操场上,刘方老师也在其中。他看见了我们——这些往日受过他鼓励和教诲的小学生们,很尴尬地低下了头。我们则都很难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很希望能有机会遇到领导,好去告诉他们,刘方老师肯定是个好人,因为他把抗日战士的爱憎深深植入了我们孩子的心里。
从此,刘方老师在三十一小消失了。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但说真的,我至今都很想念他。尽管我不知道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永远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教给我强烈的爱国情操的好老师。
这里我想起胡风先生的一句话:童年是一朵鲜花,它给我留下芳香的记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