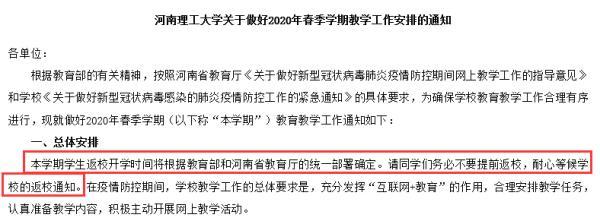敦煌的遗书印文特点(宾雍撰前言中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与敦煌绘画品)
读本:Laurence Binyon, The Tun-Huang Paintings and Their Place in Buddhist Art, A.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London, 1921,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敦煌的遗书印文特点?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敦煌的遗书印文特点
读本:Laurence Binyon, The Tun-Huang Paintings and Their Place in Buddhist Art, A.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Anci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 London, 1921
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1869—1943)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知名的“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史家,是欧洲研究远东绘画的先驱”。1893年,宾雍自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就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也就开始了他对远东艺术,尤其是中日绘画品的研究。两年后,宾雍转入英博版画与绘画品部(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当时的英博正在陆续扩充其东方艺术藏品,这也成为了他开展研究工作的良机。1904年,他发表了其第一篇讨论东方绘画的论文《一幅四世纪的中国绘画》,从此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到1908年,其《远东的绘画》一书付梓,随后一版再版,“至今仍为权威性著作”,短短四年时间内,宾雍的成长之速和成就之丰可见一斑。但宾雍的研究范畴不仅仅局限于绘画品,他同样对宗教艺术抱有兴趣。适逢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考察返英,宾雍就承担起了对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敦煌绘画品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他为此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例如1921年出版的《塞林底亚》中的《论敦煌的绘画艺术》(Laurence Binyon, Essay on the Art of Tun-Huang Paintings,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London, 1921)。同年,在斯坦因的另一本著作《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中,宾雍作了一篇导读性的前言《敦煌绘画品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对斯坦因的考察情况、英国对东方佛教艺术绘画的研究情况、佛教自印度东传的过程和佛教艺术的变化、敦煌绘画品的风格特色等进行了综合概述,属宾雍的东方宗教艺术研究成果中较为系统的一篇,对于了解他的研究路线与特色有一定助益。
一、《敦煌绘画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地位》的主要内容
斯坦因的第二次中亚考察在1908年左右结束,他随即返英,其在探险中获得的文物于当年年底运达英国,其中的绘画品于次年进入大英博物馆保管,并由宾雍、小约翰(S.W.Littlejohn)等英博工作人员进行整理和研究工作。由于斯坦因的本次中亚考察由大英博物院和英属印度政府资助,所以这些绘画品最终分为两部分存放在大英博物院和印度德里的中亚古物博物馆(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Museum),前者主要存放有中国风格的,共278件,后者接收有印度风格的,共280件。欧美中国书画研究者主要以海外收藏为研究对象,这是欧美研究的重要特色。这些斯坦因收藏品也构成宾雍开展佛教艺术研究的重要基础。
《敦煌绘画品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共有十页,分为四部分。囿于篇幅有限,不能逐字逐句翻译附后,因此下文将对这篇文章分章节进行简单的译介。
→A:路线
对斯坦因的探险历程及其获取敦煌文物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根据的宾雍的记载,斯坦因于1906年4月从克什米尔出发,途经喀什噶尔到达莎车,再到和田,后沿沙漠南缘向东,最终于次年3月到达敦煌。
斯氏已知的是,敦煌存在被称为千佛洞的石窟群,存有大量的壁画和佛教造像;但在他达到之后,经由一名回教商人介绍,他又得知了关于敦煌千佛洞内还藏有大量写本的传言,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之后,斯坦因探访了道士王圆箓,了解到王圆箓正是在修缮千佛洞的工程中发现了敦煌卷子,而当地总督府对此的保管并不如人意,按照斯坦因的描述,1907年3月他到达时,官府设置了一扇木门用以隔离出土的文书,随后他暂时离开了一个月,5月返回时,木门被一堵石墙取代,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措施用来保护文物。经过探访,斯坦因得知王圆箓的修缮工程仍出于资金缺乏的状况,便以此为契机,购买了大量的敦煌卷子。在他之后,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也到达敦煌,再次搜求了许多出土文书,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但精通汉语的伯希和带走的卷子更具学术意义)。政府在这以后才注意到藏经洞文物的价值,要求将其递送京师,但出于贪墨情状、保管不善,又有许多卷子在路途中遗失了。当然,出于各种考量,宾雍所述的斯坦因获取文物的过程并不十分清晰,省去了相当多的细节。
英国的工作人员的整理和前期研究工作:详细描绘了清理和装裱绘画品的场景,并记录了这些工作的参与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时任英博版画与绘画品分部主任的小约翰(S.W.Littlejohn)和他的日籍助手漆原由次郎(Y.Urushibara),以及来自英国皇家刺绣学院(the Royal School of Art Needlework)的温特(E.A.Winter)。小约翰在不久后到来的一战中去世,但他对这些绘画品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先导工作,通过敦煌绘画品与日本绘画在幡幢等上的相似性,他判定敦煌绘画品是日本绘画品的一些风格特色的渊源,宾雍的文章也就此为切入点进行论证。
→B:演变与图像分析
侧重于探讨佛教自印度传往中国经历的重要地点和佛教艺术的流变。宾雍经过研究认为,斯坦因搜集的敦煌绘画品呈现出了中国、印度、尼泊尔和西藏等多种地区的特色,这和以往欧洲学者作为样本研究的印度阿旃陀、日本奈良法隆寺等地的藏品有明显区别,宾氏认为这是由于“中西交流的通道,既是经济的,也是观念和宗教的”,因此斯坦因收集品体现的复杂艺术风格将为探查“从印度经由中亚到达中国的文化传播线索”提供巨大帮助:
- 宾雍首先讨论的是佛教从印度传播到犍陀罗的路线,指出英博馆藏的犍陀罗雕塑表现出了明显的希腊晚期风格,认为这是佛教艺术表现出融合性的开端。这种希腊风格不仅只出现在此处,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发现了被风沙侵蚀的于阗遗址,在此处出土了一些信件纸张,富有希腊特色,上绘有雅典娜、赫拉克勒斯等希腊文化中的神祗;斯氏在第二次中亚考察中,于伊循城也发现了一些存有希腊风格的石窟壁画。
- 除去犍陀罗和希腊风格之外,佛教传播沿线还有其他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一些佛教艺术形象中也有波斯风格的印记,部分敦煌写本中有粟特语的运用。
- 第三,中国风格出现在敦煌佛教艺术中与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有密切关系,政策是对外扩张亦或是向内收缩,对敦煌绘画品中中式元素的多少有重要影响,这也是敦煌一个重要历史特点。
在对佛教传播沿线的其他文化进行概述并探讨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反映后,宾雍开始讨论佛教本身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
- 当基督教和拜日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争夺控制权之时,佛教的东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复杂化程度远胜以往,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始的佛教发生了分化,部分教徒认为原始佛教只求自我解脱,而不追求普度众生,希望能使大众获得解脱,因此佛教分化为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 信仰与图像组合: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观音信仰出现并得到了广泛传播,记述了观音形象在敦煌绘画品中表现形式,以及观音菩萨与阿弥陀佛之间的关系(先后、并存、偏好)。此时的敦煌绘画品中,释迦摩尼的形象亦有出现,《灵鹫山释迦说法图》即是一例。由此,宾雍向读者介绍了一些佛教经典与艺术中的重要形象和概念,指出这些都是敦煌绘画品中的主题,例如文殊菩萨、地藏菩萨、弥勒佛、药师佛、四大天王、四圣谛、八正道等。
- 经过第二节的讨论,宾雍在节尾得出结论,即“佛教的体系是在不断吸收、添加传播沿线的信仰和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
→C:图像组合:中国与印度
纲要:敦煌绘画品的艺术风格、“印度风格是如何融入中国风格之中的”,以及印度与中国两种风格的差异。这一节也是宾雍着墨最多的一节。
本章节的前半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印度的宗教和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的情况,以部分斯坦因收藏品为例,有部分本生故事画,在建筑、人物、衣着等方面,均体现出明显的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与绘画习惯,但绘画品的叙事受到了印度和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宾雍进一步分析认为,造成这种融合表现的原因可能是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佛传故事先于艺术风格进入中国,导致中国画师按照自身的理解进行创作。
个案分析:对单一的中国传统风格进行梳理,旨在以此为线索展现中式绘画技巧的演变和对画作进行断代的难度。
- 他以英博馆藏的《女史箴图》和Freer收集品(Freer Collection)中的《洛神赋图》为样本,认为中国早期绘画具有描绘人物精准、对弯曲线条的有效的控制、对动作的表现力、景观描绘简单的特点,再将其与前文提到的绘画品作对比,指出唐代的绘画比例缩短且魁伟,对景观的描绘趋向复杂。
- 但宾雍在此处强调,单用艺术风格来为画作断代是有风险的,有一幅画作的线条、人物比例和简单的立体观均更趋向与顾恺之的作品,但其年代其实较四面观世音像(Four Forms of Avalokitesvara)要晚;另一幅比公元868年的绘画更古朴乃至粗糙的木板画,其年代应为公元947年。
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宾雍重申了他心目中印度风格融入到中国传统风格中的过程,即众画师和雕塑家在与佛教经典翻译进入中国同时段的学习了犍陀罗的美术艺术。他还在后文分析了中印两国的艺术区别,认为“中国画师擅长印度画师所欠缺的”,印度风格浓烈、满溢、情感丰沛,而敦煌绘画品更显克制、和谐、有气韵(rhythm),长于对线条和空间的控制,因此可以用留白的方式传达更多的信息。
→D:图像组合:内地与西藏
导读的第四部分主要讲述的是绘画品中存在的西藏风格。宾雍依旧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归属关系,认为这是构成两种艺术风格交织的一个原因,随后讨论西藏风格的特色和源流,认为藏传佛教中,密教经典及其对巫术的运用占据重要地位,这对其绘画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体现在绘画的构成和色彩上;而中国传统绘画风格也在西藏风格中发挥了作用。或许是出于学术偏好,宾雍在这一节的用笔要少于前三节。
二、宾雍的佛教艺术研究特点与二十世纪西方佛教艺术研究
a. 宾雍的核心探讨点应当是斯坦因搜集品中的绘画传达出的佛教传播路线、佛教艺术流变和具体的美术特色与技巧(图像组合和分析其实稍欠)。关注佛教的传播和艺术特色的转变,是宾雍研究工作的一个特点,他在其《长城与千佛》中也关注到了美术风格的流变,探讨了包括敦煌的绘画受到了中亚的影响在内的相关观点。
b. 比喻与比附:东方艺术知识与西方艺术术语结合起来,运用比喻等方式,更具体的、便于理解的传达佛教艺术的特色。例如他曾经用十五世纪意大利和荷兰的福音画中的人物身着符合东方习俗的装束,来解释敦煌绘画品中出现的线条、空间设计等中国绘画风格与印度和犍陀罗的故事、艺术特色之间的关系。文中出现的这类比喻大多准确、精到,综合运用了基督教等西方文化,这或许也和宾雍本身经过系统的古典学教育有关。尽管这种比喻或说比较方式容易被指出有比附之虞,但由于“就知者来说,任何已知的事物都一定是有系统的、经过证实的、可以应用的、显而易见的。而任何外来的知识系统都是矛盾、未经证实、不能应用、奇异和不可思议”,宾氏的这种述说对于读者的清晰理解非常有效。
c. 作为渠道和作为目的的中国美术:
提及外来文化和知识与本地视角的结合,《敦煌绘画品及其在佛教美术中的地位》中有一值得关注之处,即日本绘画的反复出现。在本文开篇,作者即提到英博的小约翰(S.W.Littlejohn)在世时将敦煌绘画品和日本藏佛教艺术绘画对照,希望能证明二者的源流关系。在第三节,宾雍还提出:
我们如何判定这些绘画品归属于(唐代的)中心传统呢?从日本寺院保留的日本的(或确是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绘画杰作来判断。即便我们不能确信早期的日本画家的艺术风格完全脱胎于唐王朝艺术大师的风格,部分敦煌绘画品与同时段的日本佛教艺术品(在艺术风格上)极度的接近,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很明显,宾雍认为,在对敦煌绘画品的风格进行分类以及对其断代的过程中,日本的艺术作品都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而日本佛教艺术绘画在英国更早获得研究的关注度和研究成果,也是和当时西方的文化氛围和科研环境相关联的。
皮特鲁西(Raphael Petrucci,1872—1917)也认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佛传故事、服饰、图案、建筑等都被整体地翻译、转化成了中国的形式”。 在佛教艺术研究这一门类方兴未艾之时,这些针对风格流变的研究和猜想为后世学者进行更细化的研究做了不可或缺的先导。(李玉珉:“纵观二十世纪初以来,和中国佛教美术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洋洋大观,成绩斐然。归纳其内容,大约可以分为四大类型:(一) 考古遗迹的发掘与考古文物的整理,建立佛教美术研究的基础资料;(二) 中国佛教美术风格特色的探讨,对作品的断代贡献良多;(三) 作品图像的解析和经典根据的追考,奠定佛教美术内容研究的基础;(四) 中国和印度、中亚佛教美术的关系的追溯,增进我们对亚洲佛教文化的认识。”)开展这些“通论性”研究以及学人对此的重视,为厘清佛教传播的基本概况和佛教艺术的基本特色做了重要工作,取得了相当大规模的成果,这也成为进一步发掘佛教美术新课题的做好了准备。
而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绘画的研究,成为了对敦煌乃至中国绘画认知和研究的中介环节。从十九世纪开始,伴随东西方交流愈发频繁,国际汉学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快速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例,英国于1823年就建立了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宗旨便是调查和研究与亚洲相关的科学、文学和艺术。从英国对亚洲的殖民战略考虑……通晓亚洲文化成为英国在亚洲地区取得支配地位的有效保障,也为亚洲艺术研究埋下了理论基础。”逐渐的,一些学者或是外交人员等与亚洲事物相关的人士出版了一些关于美术研究的作品,例如翟理斯(Allen Herbert Giles, 1845-1935)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的《收藏家笔记》(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 Book)等。
虽然不少著作都涉猎了中国传统美术,但日本美术研究才是当时的亚洲研究的重点,在大英博物馆,亚洲美术藏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威廉·安德森藏品。安德森“非常欣赏现代日本艺术的风格与技巧”,“其中大部分绘画都是绢本水墨或设色作品。花鸟小品、圣像画的比例相对大于山水。这恰好反映了日本收藏中国绘画的趣味” 。在科研工作上,英博“在研究中国绘画时都没有聘请任何中国专家”,而是更倾向于“取道欧洲学者与藏家,以及前来伦敦进行文化交流的日本专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艺术及其研究为西方学者研究远东艺术构建了一条认知的路线和范式,上文所提及的宾雍在研究敦煌绘画的过程中以日本绘画为依照也正是如此。
另外,不可避免的,这条认知的桥梁转变为观察的视角,许多研究成果表现出透过日本视角来看待中国作品的特点。翟丽斯曾经评价说:“中国人自己创作了大量有关绘画的历史和实践的著述,然而,就极少数非常简略地论及这个主题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人直接求助于中文原著,当然也没有任何翻译。些外国人总是用外在者的观点,你也可以说是用‘野蛮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绘画。”这可以想见会带来许多谬误,宾雍本人就曾表示:“最近几个世纪,中国的陶瓷、青铜器和刺绣,在西方获得了不错的理解和研究。然而,只要谈到绘画,一个流行很广的观点是:中国美术的唯一价值,就是给日本美术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基础或起点。”这一时代研究特征,也自然会出现在佛教艺术研究上,宾雍在《敦煌绘画品及其在佛教艺术中的地位》也提到,传统的佛教美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印度、日本奈良法隆寺等地的文物风格上。而斯坦因收藏品进入英博,给学者提供了弥补往日研究的空洞环节的机会,这也是宾雍反复称赞“敦煌所发现的绘画收藏品的艺术研究之重要性远胜于其他数次探险在中亚地区搜集的绘画品”的原由之一。而他本人在文章中表现的对中国绘画艺术的肯定和推广,也显得格外难能可贵。——他看到了“杨桃的另外一面”。如果我们暂时忽略萨义德和东方主义长久且绵亘的阴影的话。这一话题则需要另做他解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