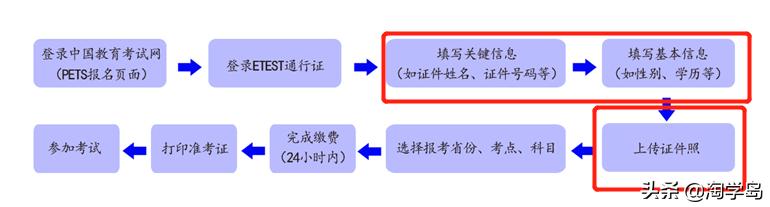20年前的家乡小河(大学生写家史跟水较劲)
王珂(北京大学)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爷爷说:“下一场雨,山里的水涌下来就涝;不下雨,留不住水,旱得厉害的时候吃水都难,更不用说浇庄稼了。雨来了躲水,雨过了缺水,这辈子就跟水较劲。”
爷爷名叫王德顺,一九四九年四月初七出生于现潮河镇林泉村一个中农家庭。“潮河”和“林泉”都是鲁东南山区五莲县的河名,林泉河是潮白河,也就是“潮河”的上游。潮河镇少雨缺水,从九仙山流出来的林泉河河床淤得厉害,存不住雨,一下暴雨就发大水,十年有九年非旱即涝。
爷爷出生的那一年,有省城里的知识分子带着学生来五莲搞经济调查,连带着弄了台“斯大林”拖拉机表演耕地,以此展示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恰好叫去赶集的老爷爷(爷爷的父亲)撵上了。原本只见过私塾先生的老爷爷自此大开眼界,把六岁的小儿子也就是爷爷送进潮河小学时,希望他也“造个机器出来”。可惜,当时的潮河小学几乎就是个放养孩子的识字班,尽管爷爷小时候聪明,识字比别的小孩都快,但才上了三年就从潮河小学退学,跑去县城大炼钢铁了。老爷爷看爷爷上学学的东西没啥实在用,也造不出机器,既然他能识字、会算数,已经不是“睁眼瞎”,索性不再管他。
之后林泉村被划进了五莲山公社,爷爷回村之后也没有继续学业,入了党后开始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一样种地挣工分,跟奶奶王玉荣成了婚。那几年五莲县天灾尤其厉害,不说旱灾涝灾,有一年下了六次冰雹砸死十多头耕牛,还有一年闹土蚂蚱把庄稼吃秃了,粮食几乎绝收。几个划成地主成分的老人说这是“作麻煞”(没事找事、背离天意),招了菩萨埋怨;“文革”的时候他们挨批斗,革委会拿着扩音喇叭对着他们耳朵高喊“人定胜天”。
五莲县是山区,蓄水费劲,就借着“大跃进”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大兴水库建设——却坡水库、墙夼水库、小王疃水库、长城岭水库都一个个建起来了,公社吃上了水不说,浇地也有了着落。但是潮河的水库不好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县里各来勘测了一次都说难办。但本着“创造条件、克服困难”的精神,龙潭沟水库工程终于还是在1975年轰轰烈烈上马,成立了水库工程指挥部。那年五莲山公社改名叫了潮河公社,爷爷27岁。

1970年代龙潭沟水库的建设场景
爷爷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修水库的时候管着五莲一中义务劳动的一群学生,当了个“工程建设突击队”队长。工地集结了全县的青壮劳力,包括贯彻“五七指示”的五莲一中所有师生,轮番扛着红旗唱着歌,步行40多里地去龙潭沟工地义务劳动。因为是“学工、学农、学军”的工农兵学校,编制是按照军队来的,一个班为一个“排”,三个班为一个“连”。爷爷带领的所谓“工程建设突击队”,就是学习五十年代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经验,挑又红又专、积极性高、能吃苦的青年组成英雄突击队展开劳动竞赛,弄得也倒像模像样。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每周能砸700多公斤石子;冷天的时候就得砸开冰,站在水里扒开石头填上黄泥,而填坝心的黄泥要十多个学生一组,男的拉车、女的装车,拿小车推上四五里推到工地。
爷爷在这之前闸过山沟、搞过水土保持,当时的队长——是村里的木匠,也是潮河小学的算术老师——收了他当徒弟,教他石匠木匠用得着的测算。爷爷捣鼓木头石头一把好手,主要得益于他脑子灵光;他之所以能当上队长,多半也是因为他是个“会算账的”、又是党员(五莲人把算术算得好的都叫“会算账的”),好歹能核算土石方,也能搞测量。爷爷最初是不情愿的:他想去炸山,点火放炮;但是人家怪他太粗心,而碾子磨硝铵、自制炸药、挖炮眼、放雷管都是细活,来不得半点马虎,户部修水库就炸死一个不当回事的,从此全县工地再不敢轻率怠慢。
好在爷爷很快就适应了他的任务,并且为他“会算账”无比自豪。当时随队劳动的一位一中老师周世明告诉他,“大跃进”的时候五莲县没有电工,农机厂工人宋效林造了土发电机还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夸他“你是个真正的土专家”,从此爷爷就开始以“土专家”自居。一次县里文宣队来工地唱样板戏,学生们把“土专家”介绍给他们时,一个青年颇为不屑地告诉他“学过工科的知识分子才叫专家”,他就跟人家急,拉着青年非得让大家评理、不让他走,直到文宣队队长出面来道歉,劝他“算了算了”才作罢。不过说实话,爷爷土办法还真挺多。举个例子,虽然看不懂图纸,但是他拿着一张1:10000的地形图能知道上面单位的面积,奇不奇?爷爷说,那是因为手指大约是一个平方厘米,手掌是一个平方分米,这不比拿着尺子量来量去、算来算去管用?
1976年潮河又旱了一次,四个月没下透犁雨,爷爷着急粮食和地,也焦虑水库能不能快点建好,山上刷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备战、备荒、为人民”、“腰斩龙潭沟,拉直潮白河”、“战天斗地”标语更让他焦急倍增。学生们积极倒是真的积极,有擦坏手的、铲破腿的,还有人拉平车拉得太满,坡陡跑得快,一不小心人仰车翻被摔断了腿,好长时间才养好。可爷爷口头禅是“反了你了”,管学生管得严,又要求中午吃饭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学生都有意见。一次一帮学生故意跟他对着干,硬是拖着不上饭,他好说歹说也没说动,只好跟着他们饿着肚子干活,恨恨地骂一句“红专个屁,这点苦都吃不得”。
爸爸叫王在刚,出生于1972年。因为爷爷是党员,执行七十年代初期“一对夫妇两个孩,两胎间隔四五年”的计划生育首当其冲,所以孩子只有姑姑和爸爸两人,在男丁数量代表家庭势力的农村可谓十分吃亏。而万人奋战龙潭沟如火如荼的三年正是爸爸的童年。爸爸现在留下的最早的记忆,就是一场暴雨几乎要把家里屋子给冲塌了时他在屋里哭叫,而爷爷却在工地守着水库——他想赶也赶不回来,工地离林泉村起码八里路,更何况爷爷觉得没必要回来:“得亏没塌,我要是回来了该塌的就不塌了不成?”

1970年代龙潭沟水库的建设场景
对爸爸和林泉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建设中的龙潭沟水库对生产队的吃水问题于事无补:几百号人吃水照样得围着仅有的一口井转,还有邻居因为下井舀水受重伤的。对粮食产量也于事无补:一强调向国家多卖粮、作贡献,就容易虚报产量,而产量报的越多,出力越大,缺粮食缺得越厉害。林泉号称亩产过吨,人均向国家交200公斤粮食,有时却要向外队借瓜干吃。
本来爷爷觉得这些抱怨简直毫无道理,毕竟修完水库这辈子就不用再跟水较劲了,可1977年过了年之后也没叫他们返工,当年春天修水库就没有下文了,“土专家”最后也没能“人定胜天”。水库最终停工的直接原因是清不了坝底,清不了坝底的原因是潜在的渗漏和岸坡坍裂风险。按照原来的施工方式,上游水位一抬高水压就大,要把土方掏出个空洞来,一往缝缝里钻水就要白白流掉渗掉。眼看着清底遥遥无期,钱和物资也批不下来了。虽然爷爷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不断地听人解释真正的“专家判断”,对龙潭沟的“破碎带”“断裂带”是全国罕见的难题一清二楚,但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干不了,而是因为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的几年后,一切都在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地、富、反、坏”分子摘帽了,大包干搞起来了,集体经济渐渐没人提了,大家也不大怕说话了,爷爷也回到了分到的一亩三分地上干农活,学了蘸糖葫芦的手艺到集上去卖,有时也会“重操旧业”,去帮着做做木工活、盖盖房子。当初爷爷没多生几个儿子,现在后悔了:计划生育政策一天严似一天,超生能把他罚到倾家荡产。
爷爷想让爸爸读工科,成为真正的专家,可爸爸讨厌与工科相关的一切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却喜欢语文和英语。爷爷觉得爸爸学不好数理化是不务正业,但爸爸非但没有不务正业,反而属于那种“不要命”的学生:所谓“不要命”就是只留一口气参加考试。和不少山区学生一样,爸爸也是每晚脸被煤油灯的烟熏得黢黑黢黑,早上洗脸鼻孔都是黑乎乎的;每次往返学校都要走十多里路,为了携带方便和省钱,主食是地瓜面子煎饼就咸菜疙瘩,吃多了烧胃,间接导致爸爸和他不少同学中年之后都得了胃病。小升初时爸爸以潮河镇第三的好成绩考进五莲一中,却整天想着怎么样赶紧考出去工作。中考报志愿时爸爸没有填报五莲一中的高中部,而是赌气报了潍坊师范学校。出录取结果的当天,书记见了爷爷就向他报喜,爷爷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回去拿树枝子把爸爸抽得嗷嗷叫,之后也无可奈何地放他走了。
爸爸上师范的时候正值对爷爷憋着一肚子火的叛逆期,觉得大修水库根本就不值当潮河镇费那个事,依据之一就是:潮白河的旱涝问题不是靠“文革”修水库解决的,而是靠改革开放后的小流域综合治理解决的。“文革”最后几年全县以粮为纲、砍了不少林子,什么石头地上都开荒,之前搞的水土保持工程也都荒废不算数了。再加上大包干之后集体经济变成单干,不少本来建的时候就匆忙的水库因为疏于管理也开始淤。最夸张的一次是1985年,一场大雨直接把薛村水库给淤平了。后来镇里也不修水库了,从林泉河开始慢慢干一系列小工程——裁弯取直、加深河床、砌石护坡,还建了气象站、水文站监测,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大涝灾了。不过当时爸爸没想到的是,潮河镇灾害缓解其实也跟退耕带来的生态改善有关——劳动力都往县城和大城市里跑,原本毁林开出来的坡耕地没人种了;而林泉农民吃尽了粮食广种薄收的亏,多数都不怎么种粮了,改种烟叶;爷爷虽然抽烟但不想种烟叶,就索性把原来的副业当成了主业,山楂下来的时候就蘸糖葫芦,要么就满五莲县窜找工地干活。
当然,最后爸爸也理解了爷爷的纠结和郁闷。爷爷觉得当“土专家”的几年是他人生最光荣的几年,村里的老汉却觉得爷爷迂得像个潮巴(傻子),他为此没少发脾气。一次过年吃饭时,二姑奶爷喝多了,席间大声说了一句“……噫,吃不了,穿不了!”爷爷脸一下黑了,重重地放下碗拂袖而去。还有一次爸爸从师范回来时,居然看见家里桌上摆着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问他哪里来的,说是从刘元坤(潮河小学老师)那借来的。爸爸不吃这一套,觉得爷爷怎么可能拉下面子去找小学老师借小孩看的书,再三问他之后才承认是去供销社买的。爸爸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觉得爷爷的文化水平能看进去才翻了天,不过也没怪他乱花钱这码事。
爸爸1993年参加工作,去县城职工子弟小学当了数学老师兼体育老师,带校篮球队训练,又在1997年与纺织厂工人的妈妈结婚,2001年当了爸爸。
爷爷知道妈妈生了个女孩的时候一度非常失落,并不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重男轻女,而是觉得女孩不是学理工的料。童年在老家的时候,爷爷就经常念叨我“学好数理化”,以至于耳朵已经听出老茧的我在父母面前管爷爷叫“数理化”。可能遗传了爷爷和爸爸的某些特质,小学中学的我一直成绩拔尖;然而相比分数,爷爷更关心我读了什么专业,即便他的孙女考上北京大学,还是因为读了文科而耿耿于怀。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之后,村里好事者怂恿爷爷赶紧请客吃饭,爷爷居然说了一句“知识越多越反动”。虽然知道他这是不想请客和对孙女的失望的双重作用之下说出的气话,我还是觉得有点好笑,问他“那你当‘土专家’是不是有知识?”答曰:“你那是假知识,我这是真知识,毛主席批的,是假知识。”

龙潭沟水库现景
2007年,也是我小学入学的第一年,县委县政府决定重启龙潭沟水库建设。这个项目再次上马的决定性原因,是争取到了山东烟草系统水利激进的专门投资支持——现在的潮河镇已经成了烟区,而龙潭沟水库的项目成了推动烟农增收致富的“烟水惠民”工程的一部分。这次的建设由葛洲坝集团三峡公司承建,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据说为了对付断层、进行混凝土灌浆还请了国外专家会诊,数易施工方案。当时爸爸还问过爷爷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大茂庄唱的《红灯记》——够吊呛。”
但不管爷爷怎么想,2014年龙潭沟水库最终还是落成蓄水了。第二年,龙潭沟水库改名叫龙潭湖,成了五莲县的备用水源,也成了九仙山风景区的一部分。每天电动船载着外地游客在水面上来来往往,一趟收五十块钱,景区停车场附近也像几十年前会战时那样刷着标语,内容却变成了县委书记马维强提出的“新时代五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挖山不止,拼命硬干。爸爸好几次提出带爷爷去水库看看风景,但爷爷每次都拿“蓄水之后我自己又不是没去过,又不是没见过水库,有什么看头?”来搪塞,也不知道他是真去过还是不想去。
爸爸在五莲一中上学的时候,前任校长韩俊三在宣布给刘少奇平反的师生大会上的两个非著名论断被传为笑谈:“什么是浪漫?浪漫就是吊儿郎当,就是耍流氓。”“什么是五莲人?五莲人就是实在人。”前者是他针对部分学生头发打蜡等现象大动肝火,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记忆,可后一个论断却称得上历久弥新。
高中时,地理老师觉得我是他有史以来见过做题最多的学生,这么拼命迟早得把脑子烧坏,于是为了给我们“调剂心情”,在一次水利建设的专题课上放了县里拍的龙潭沟水库的小短片。视频点开的瞬间,我感到某种奇妙的呼应感:三代实在的潮河镇人跟水较劲,最终把水驯服;就像我们跟彼此较劲,最终像水一样融入彼此的历史之中。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栾梦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