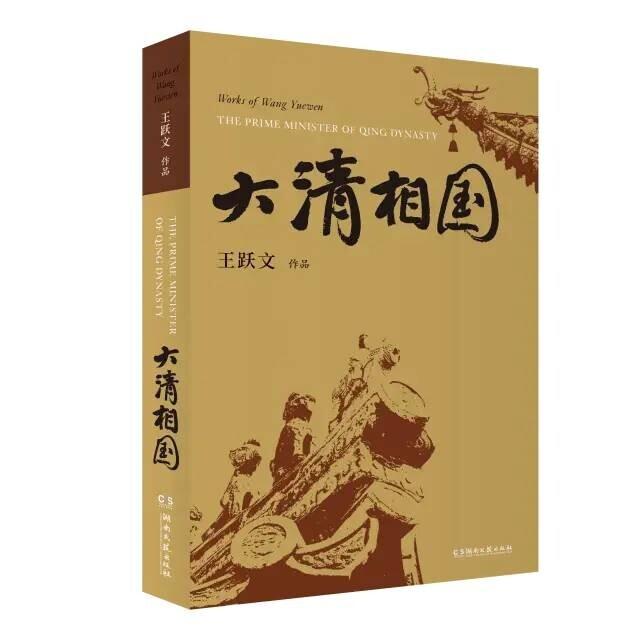(有关脏话你不知道的故事)
“每当遇上新词典,我都用‘fuck’这个字当基本测试。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找出‘fuck’,看看词典怎么说。如果书上的定义令人不满意,不符合我对这个字在现实生活中各种行动脉络里实际用法的了解,我会放下那本词典,另寻其他。因此,如果一本词典无法在这个字的定义上让我满意,我认为这表示它对其他字词的解释也不值得信赖。”
——鲁思·韦津利

鲁思·韦津利(Ruth Wajnryb)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语言学家。2004年,她出版了一本书《脏话文化史》(Language Most Foul)。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第一,从来没有这样详细研究英语脏话的书;第二,从来没有这么大胆将脏话当成一门学问去研究。有书评这样评价这本书:“本书对脏话研究详尽,引人入胜,笔调幽默,充满有趣的历史和好笑的轶事。若要在此引用例句,恐将难以避免用上不雅之词,所以各位还是快去买这本他妈的书吧。”所以说,这本书称之为脏话“文化史”是十分够格的。
我们从小就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要说脏话。但这种警告就像暗示一样,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如何使用脏话。人们小时候最先学会的语言除了一些常用语之外,恐怕就算脏话掌握的最快了。所以,脏话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我们认知这个世界。但是,作为一种语言中的另类,由于它在使用过程中的敏感与禁忌,很少有人能正视脏话,并且去认真研究它。它无所不在,但却总让人讳莫如深。脏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词汇是怎么诞生的,又是如何演变并赋予更多恶毒的指向,从来就没有人研究过。韦津利在书中也提到,想找一本专门介绍脏话历史的书籍很难。所以,作者能花时间写出这么一本书,确实是值得尊敬的——虽然内容涉及的都是最不值得尊敬的语言。
虽然这本书介绍的脏话来自英语语言范畴,但是从这些脏话发展史中不难看出,任何语言的脏话史都是相似的。比如,作者用了大篇幅介绍“fuck”这个词,《牛津英文词典》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才把英语里的“四字经”(比如fuck、shit、cunt)收录进去。而兰登书屋直到1987年才把“四字经”收进去。可见,脏话登入大雅之堂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
我顺手翻了一下我们出的词典,我手头上有两本《现代汉语词典》,一本是1996年版的,在这个版本中收录了“操”(cào)、“肏”这两个字,对“操”(cào)这个字的解释是同“肏”,而且还有“操蛋”一词的词条解释,不过这个解释词不达意,完全没有把“操蛋”的意思解释清楚,感觉十分操蛋。但是很奇怪的是,去年的新版本《现代汉语词典》则去掉了“操”(cào),我不明白“修现”后的词典为什么要倒退一步。我只好猜测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变得不操蛋了,或者变得更操蛋了,或者是编撰词典的人都是一些操蛋的人,比较忌讳这个词,抑或是编撰词典的人都不操蛋,有语言洁癖……总之让我浮想联翩的,但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随着时代的进步,“操蛋”一词怎么从词典里消失了,在新版本的各种宣传中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我又翻看了另一本《新华词典》。据说这本词典为了与《现代汉语词典》竞争,在某些词汇收录上十分前卫和大胆,但是当我翻到“操”这个词所在的页码时,它让我非常失望,居然没有“操”(cào),更别说“肏”了,这真是一本操蛋的词典。其实想一想也挺正常,英语词典里对一些脏词的收录都很慎重,更何况从来都是以道貌岸然为荣的中国呢。
韦津利把脏话分为如下几类(详见这里),这主要是为了便于阅读此书。不过,她在定义脏话的核心条件时,列举了这么几种前提:
第一、这个词必须有冒犯性,“桌子”“树”不能当咒骂词,因为冒犯不了任何人。
第二、咒骂词需要特定的冒犯性,不能太温和。
第三、该语句必须触犯一项禁忌,把任何一样被视为私密的活动拉到公众领域。
第四、咒骂词必须有意造成听者的震惊或愤怒或不自在。
第五、该字词必须实际存在。
第六、仅仅“实际存在的东西”并不够,它必须是众人广泛同意为“粘湿恶心的东西”。
具备了这些,基本上就是脏话了。
另外,古今中外的脏话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常用的最狠的脏话基本上都包含爆破音,比我们常说的“操”“靠”以及英文里的“fuck”“shit”“motherfucker”“cocksucker”等,因为是脏话,用于情绪异常激动或常用词难于表达自己情绪时用的一种词汇,所以爆破音有助于情绪的表达,能加重这个词的情绪份量。
在《脏话文化史》这本书里,作者列举了一打英语里最常见的脏话(她称之为“十二脏肖”),比如fuck、cunt、shit、piss、bugger、bloody、arse、damn、hell、fart、crap、dick。
在英语里,最活跃的脏词非“fuck”莫属了,韦津利说:“对于fuck的公开讨论,就像放在一旁炉子上小火慢炖,不时会沸腾起来表示激愤,但现在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若说fuck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它无所不在。有些人认为它的流行是由于道德的败坏,把它跟青少年未婚怀孕、毒品泛滥、识字水平每况愈下、同性恋婚姻等等归为同一类。另有些人则认为,这个字已经远离原来它指称的动作,使其力度大大减退。事实上,fuck似乎不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字义,而且,作为一个强化语,它也不再有强化语气的效果。换言之,如今要好几个fuck才能达到一个fuck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
再看看我们的特产“操”,命运跟“fuck”一模一样。比如“我操”,它基本上表示的是“惊讶”“感叹”“欣喜”“悲伤”……总之,任何在当时语境下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表达那一瞬间情感的词汇,都可以用“我操”来代替。英语里,因fuck衍生出的词义跟汉语的“操”也十分类似。韦津利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A:你有没有听说,18号星期六那天罗德甩了琴米?
B:操!不会吧。真的吗?
A:对啊,我是这么听说的。
B:我的天哪。操!谁告诉你的?
A:辛西娅。她当时在场。
B:操!真够烂的!操!
A:对啊,琴米真的很难过。
B:操,对啊!谁不会啊!
A:对啊。
B: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操,真糟糕。
在上面这段对话中,B用了好几个“操”,“操”在这段对话里发挥的功能是“惊叹号”,当然也有停顿功能,它没有任何该字实际所指的意义。这就跟老六平时说的那句“哦,天哪,天哪,天哪”意思差不多。同样,中国有这么一个笑话,讲的也是跟“操”有关系。说世界上举行一个讲故事大会,要求参赛者用最简短的话讲述一个最复杂的故事,结果一个中国人获得了冠军。这个中国人讲述了一个人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去郊外玩,骑车上山,看到了山上山下的风景以及看到风景是激动和开心的表情。下山时,由于自行车闸失灵,导致他不慎摔到了沟里。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有两个字“我操”。不信你可以用表情和动作给你的朋友讲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只用“我操”两个字,他们肯定都能听清楚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
还有,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个情节,马晓军拿着望远镜无意中看到了历史老师上厕所的过程。这时候,马晓军的台词也只有“我操”这两个字,他一共说了六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遍语气、重音、长短音都不一样,但是它比更多的语言都精彩,因为观众都能看明白马晓军的情绪与心理变化。你会问,这是为什么呢?“操”这个词在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太多意义,它已经像变色龙一样,不仅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词汇,也是随时可以赋予它任何意思的词汇,因为脏话每个人都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而自己的理解别人也恰恰都能明白。当一个脏词用到这份儿上,基本上也就不脏了。
不过,“操”字并非完全纯洁化了,有时候仍然能显示出它恶毒的一面,比如用在“操你妈”“操你奶奶”“操你姥姥”之类的词句当中,就会原形毕露。中国人的传统是长者为尊,所以骂人的时候,尽可能去侮辱对方的长辈,以达到侮辱的目的。所以,你很少听到“操你姐姐”“操你妹妹”之类的脏话。不过,北京人例外,他们造出了一个在全国其他地区都鲜用的脏话:“操你大爷”,这句话大概源于另一句程度较轻的咒语“你大爷”,前面加上一个“操”,实在是显得不伦不类。如果骂人的是一个女性,似乎挺合理,但是被骂的一方的大爷就占便宜了,平白无故的享受到一个女性带来的性交乐趣,估计被骂一方对此也无异议。但是如果骂人的是男性,就有点奇怪了,您是不是有同志倾向呢?事实上,中国人在骂人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怎么过脑子,怎么痛快怎么来,即便把自己搁进去,也在所不辞。当然,北方还流行一句脏话“完蛋操”,在这里,“操”是为了更进一步修饰“完蛋”的程度而已。
关于“fuck”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脏话文化史》里面也论证了很大篇幅,但是也很难考证出它的出处,甚至这个词可能源于拉丁语、德语、古荷兰语、挪威语或瑞士语。不过,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是“fuck”是“For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代表不合法的肉体知识)的缩写。还有一种说法,在中古世纪,偷尝禁果的女孩一旦事发,就会被处以游行示众,宣读公告的人会顿挫地喊出F.U.C.K,围观的人都明白这个缩略语的意思——“Found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被发现处于肉体知识之下)。不过这种解释也有点牵强。“fuck”在19世纪末还常常用于表达情绪的字眼,但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它的应用更加广泛了,甚至有家服装品牌干脆用“FCUK”(因为这家公司的名字是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起这个名字的人纯属故意。你说当你穿着这家公司的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知情者除了会心一笑之外,还会有厌恶的反应吗?
“操”不是脏话里最脏的,因为它太常用,而且语义变化太大,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纯洁了。真正脏的也不是“屎”“尿”之类容易引起人们心理反感的字词,而是“屄”这个词。通常我们像用“操”一样,鲜用“肏”,“屄”也一样,我们常用的是“逼”。
操与逼可谓脏话里的一阳一阴,它形象地浓缩了万物生灵的最基本特征。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不管脏话如何变化发展,“逼”这个字的肮脏分量一直没有改变。语言学家把这个字描述成“一个人能被骂的最难听的话”,性别歧视者称之为“一样恶劣的东西恶劣名称”。由于“逼”这个词从一出现就背负不誉之名,所以,追溯它的起源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很少有史料记载它的出现过程。虽然作者也在书中探讨了“逼”的起源,但是仍无法用史实来说明这个字的来龙去脉。18世纪的时候,“逼”这个字不能乱使用的,用了就是非法,除非重新再版的古代经典作品。直到1965年《企鹅英文词典》才收录了这个词。直到今天,这个词用起来仍就是那么咄咄“逼”人。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有一段对话:
“逼是什么?”她说。
“她不知道吗?逼!就是你下面那儿,我进去那儿时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它,整个儿的。”
“整个儿的。”她逗他。“逼!那就是跟操一样喽。”
“不对,不对!操只是做那档事。动物也会操。但逼不只是那样……”
劳伦斯用心良苦,他试图冲破一种禁忌,来为“逼”下一个定义。结果引起了一场有关猥亵定义的官司。
不过,关于这个最难听最狠的字眼儿,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麻木效果,韦津利写道:“我听说,在舞台剧《阴道的独白》演出过程中,演员要求观众一再重复念诵‘逼’字,以减低他们的敏感程度。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我听说数年前ABC的广播节目讨论一样名为《我的逼》的艺术品。可以想象,要讨论一样的艺术作品,很难不提它的名字。然而听众无法听出引号或者表示专有名词的大写字母,因此节目中的受访者非常尴尬地意识到,听众可能把这名称听成单指个人的‘我的逼’。然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访问讨论过程中,这个字被用了太多次——事实上是几百次——因此到最后,上节目的人对它的力道和效果都已经没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由于过度曝光,‘逼’获致了普通字词的性质和质地。事实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开庭审理时,前来作证的许多重要文坛人物中,有一人便曾说,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发现那些猥亵的字眼‘愈用就愈得到净化’。”
相比之下,“逼”这个字在汉语里面的命运要比英语里好的多,因为中国人在制造脏话方面的智慧远远要比外国人强,既然“逼”是名词,那么,我们可以在它的前面加上动词、形容词,于是,关于“逼”的汉语语汇就变得丰富了,比如“傻逼”、“牛逼”、“歇逼”,还有“得逼”“叨逼”“小逼崽子”以及专门形容周杰伦的名词“二逼”……关于“逼”的灵活运用,中国人已经远远超英赶美了。在汉语里面,“逼”这个字的禁忌程度也远远低于英语,因为这个字出现在我们日常话语中,多少跟女性生殖器没什么关系了,它逐渐转变成修饰性或加重某种情绪、语气的“虚名词”。不过,关于丰富多彩的“逼文化”,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尤以北京为甚),对于外地的逼是怎么用的,本人不太了解,想必是有其他类似的词汇可以替代的。
老罗给他自己的博客名字取名“傻逼老愤青”,很少看见有人自称“傻逼”。不过,老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名字:“我被一些傻逼逼的受不了了,就写文章批评他们的傻逼。我觉得因为大家本来就是观念对立的非同路人,所以互相觉得对方傻逼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结果我的读者中的很多傻逼问我,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傻逼?!别人这么说你你会怎么想?!为了让他们知道我怎么想,我就自称傻逼了。”这叫以逼还逼,但很明显,两种“傻逼”的意思是有差异的。
当然,上述说明只是“逼”这个字在使用种相对中性的一面,这并不能掩盖它在活跃的汉语脏话文化中恶毒的一面。我是东北人,在东北,“逼”这个字往往用在最狠的地方,比如“骚逼”“臭逼”“妈了个逼”“骂了个臭逼”“小逼养的”……相对程度较轻的一种说法是“妈了个疤子的”,这是张作霖的口头禅,实际上“疤子”仍然指的是女性生殖器。我记得一九八几年,中国足球队参加在西亚举行的亚洲杯比赛,当时的对手好像是韩国队(记不太清楚了),中国队的前锋是来自辽宁的马林。一次,他在对方禁区准备射门的时候被对方破坏,于是马林很懊丧。恰好这时候镜头对准了他给了个脸部特写,马林当时回头嘟囔了一句话,当时看球的有几个东北人,大家从他的口型立刻看出来他骂了一句东北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便异口同声地说:“骂了个臭逼的。”(关于这段典故,有心人可以跟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联系核实)。所以说,东北人在对“逼”的使用上,可以说是脏到了极致。从脏话的特征上也不妨能看出,为什么东北男人大男子主义的特别多。我想,如果《脏话文化史》的作者韦津利到我国东北去体验一下生活,采采凤,她又能写出一本书来。
有一次,我在北京的一个香烟店里买烟,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东北妇女,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打电话,另一个伙计在招呼客人,我从掏钱到拿到一盒香烟到最后伙计找我零钱,前后的时间不超过30秒钟,但是就在这短短30秒以内,我听到那位中年妇女说了一连串没有语法逻辑和实际内容的脏话,显然,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她诅咒的对象:“你这个杂种操的王八犊子什么鸡巴东西我告诉你这个欠操的王八羔子臭逼养的出门就让车压死混蛋玩意儿……”这是典型的东北人骂街的方式,从头到尾基本上脏话罗列,没有实际含义,用叠加的方式和简单的虚词过渡,来强调口腔快感,这种连珠炮似的骂街方式目的是坚决不给对方反击的时间。所以说,在东北,尤其是妇女骂街,如果不事先熟练掌握100种以上的脏话和巨大的肺活量,最好别开口。而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韦津利举的最复杂的例子也不过是“You fucking fuck,fuck you”(出自电影《蓝丝绒》中的一句台词),或者“我操他妈的要杀了那个操他妈的家伙。操他妈的王八蛋怎么敢跟我他妈的老婆性交?”这在我们东北人面前,算什么啊,脏话一点花样都没有。所以说,我们就能拍出《花样年华》,美国人只会花样滑冰。
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微软的Office字处理软件中得到证实,如果你故意把“cunt”打错,它会有提示,但是绝对不会在提示的正确词汇里出现“cunt”。韦津利说比尔·盖茨是拿肥皂洗全世界讲英文的人的嘴。其实不光是比尔·盖茨,我以前在《不许联想》这篇文字中也提到过,现今我们的各类输入法似乎都是删节版。每当我是用一个新输入法的时候,我就像韦津利拿起一本词典找到“Fuck”一样,我一定要先输入“傻逼”、“操蛋”之类的脏话,来检验这个输入法是否人性化,结果大多输入法让我感到失望。现今,很多英文出版物上都使用“*”来规避一些敏感词,比如“f**k”“s**t”“c**t”,这种用法最早出现在1785年,弗朗西斯·格罗斯编写的《标准粗口词典》第一次给脏词打上了马赛克。中国人智商也不低,你用“*”,我用“×”,异曲同工。这叫“落霞与孤鹜齐飞,星号共叉叉一色”。
其实,英语中的很多脏话和汉语中的脏话都很相似,前面介绍了“fuck”和“操”在很多地方相似之处,还有一个词也和我们的常用词(主要在北京地区)相似,这就是“bastard”,这个次我们可以翻译成“杂种”、“王八蛋”,这个词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非婚生子女”。《朗文当代英文词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①俚语,用来骂你所讨厌的人,尤其是男性。②口语,侮辱或开玩笑地说法,用以称呼男性。③英式用法,指造成问题的困难或事物。④旧式用法,指出生时其父母并未成婚的人。这个词跟北京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丫”“丫挺”何其相似啊。在旧北京,“丫”(或“丫挺”)实际上是“丫头养的”的意思,北京人说片汤话,很多字都给吞进去了,说快了就变成了“丫挺的”,更进一步就简化成了“丫”或“丫的”。但是,“丫”(或“丫挺”)的命运跟很多脏词一样,随着它被人频繁的使用,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它的咒骂与侮辱程度已经不如30年代老北京时期的效果了。如果说用十个“fuck”能达到十年前用一个“fuck”的效果,那么你要用一百个“丫”(或“丫挺”)也达不到30年代老北京人用这个词的效果了,因为它早就退化成一个清洁干净的虚词了。现在的年轻人更多不知道这个词的原意,只是听到别人使用,感觉时髦或是在表达某种意思的时候可以加重语气或渲染情绪,所以才频繁使用。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年15岁)在你父母前面使用这个词,他们不会感到震惊。但是,如果你在你爷爷奶奶面前使用这个词,估计能气的他们犯心脏病。
最后再讲一点,也是韦津利在她这本书里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脏话实际上在发展变化中都给赋予了很多性别歧视色彩,她认为,男人语义领域包含的大量词语意思多半是正面或中性的,比如guy、bloke、chap、fellow等,但表示女人的词汇负面的很多,尤其是充满性意味、非难的道德色彩或侮辱性的字眼俯仰皆是:马子、娘们、贱人、婆娘、情妇、小妞、母夜叉、泼妇、婊子、丫头、悍妇、蜜桃、祸水、浪女、破鞋、荡妇……韦津利指出,最早“破鞋”(wench)“荡妇”(harlot)在使用中并没有限定性别,也没有贬义,但是恶化语义使这些词汇不仅变成了贬义,还用在女人身上。这一点,跟中国男人称呼自己的妻子的词汇异曲同工,比如“糟糠”“贱内”“拙荆”“内人”……置于汉语脏话里面对女人所指的词汇一点不逊色于英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韦津利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变成骂人的话。”相反,在英语里,女人骂男人时使用的字眼十分有限,基本上是“鸡巴”“鸡巴头”“屁眼”“狗娘养的”“娘娘腔”“王八蛋”“种马”(这个词是在骂男人吗),指的也大都是对方的人格令人讨厌而已,而不像男人骂女人那样,会把女人分为恶魔般的女人(巫婆、母夜叉)、具有侵略性不像女人的女人(悍妇/泼妇)、被诅咒成禽兽的女人(母狗/母牛)、作为享用品的女人(蜜桃/骚货)、作为嫌恶对象的女人(脏货/淫妇)……这样丰富的语汇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世界不仅是男性统治的,连词汇都是由男性掌控的。比如我们常说的“肏”,这个汉字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动词的动作与从属关系,男性插入到女性的阴道里叫“肏”,女性在使用这个词是天生就是被动的,不管她说了多少个“肏”都无法改变这个词义的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事实上,是夏娃勾引了亚当,夏娃看似主动,但仍是被动。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时候实际上就造出了“肏”。
写得够长了,就此打住。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只是因为我跟你差不多,常常使用脏话,所以看了这本《脏话文化史》之后有些感触,写成了这么一篇文字,但愿这些刺眼的字眼不会冒犯你,如果我真的冒犯了你,我想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你赶快学会说脏话。
好,下面请欣赏名人脏言录:
★我他妈是怎么想出这个定理的?——毕达哥拉斯
★我想操他妈的不会下雨吧,你说呢?——圣女贞德
★这幅操蛋的画明明就很像她。——毕加索
★你让我在这操蛋的天花板上画什么?——米开朗琪罗
★有很多人要他妈的人头落地了?——安·波林(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之母)
★他妈的这么多水是哪儿来的?——爱德华·约翰·史密斯(泰坦尼克号船长)
★随便哪个操蛋的白痴都懂。——爱因斯坦
★他妈的我们到底在哪儿?——艾梅莉亚·厄哈特(第一位独立飞越大西洋的美国飞行家)
★你们他妈的都准备好了吗?——麦当娜
★为什么?因为操蛋的山在那里啊。——埃德蒙·希拉里(新西兰登山探险家)
★操他妈的谁会发现?——理查德·尼克松
★这不是他妈的真枪吧?——约翰·列农
★没关系啦,这里只有我和你,没他妈什么人知道。——比尔·克林顿
★他妈的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底在哪儿?——乔治·W·布什
★我他妈真想抽你!——冯小刚
★文坛是个屁,谁都別裝逼。——韩寒
★我操,我晕船晕的紧。——厉娜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