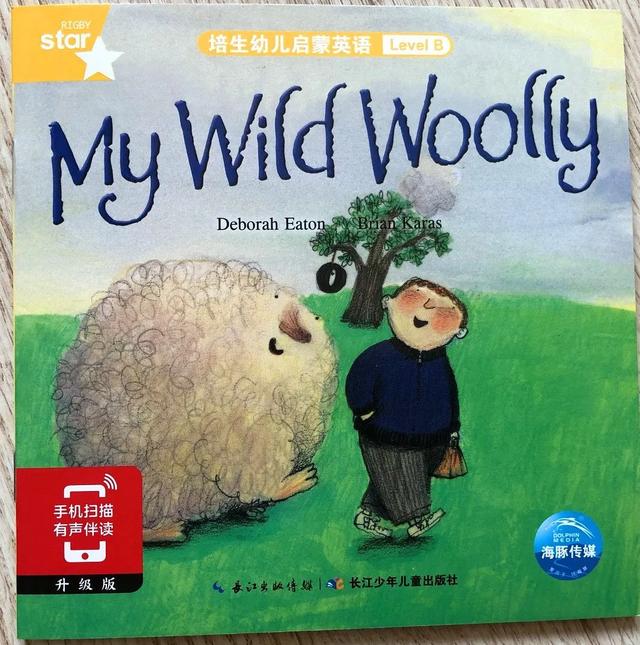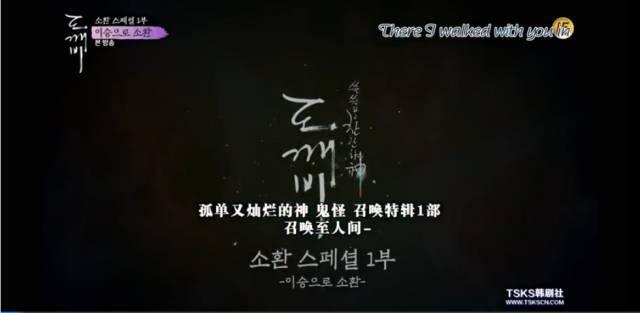庄浪的最新2022年(庄浪走笔四)
(四)

直至宋、金两季,庄浪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嬗变。嬗变的因子是因屯田而派生的弓箭手制度。
屯田制度是历代统治者为充实边陲常采用的策略。两汉以降及至宋、元、明、清都无例外地在西北边境地区实行了多种方式的军垦、民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地处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过渡地带的庄浪均受其影响,也由此发生了人口种群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宋、夏之争,边防多事,宋王朝在西边集结大量兵力,为了减少东粮西运,宋代沿用了两汉以来的办法,利用军士空闲时间开展营田和屯田。宋真宗景德二年九月,知镇戎军曹玮上言,“有边民应募为弓箭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其办法是: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时任陕西四路招讨使的郑戬也积极上言,建议在“田土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余万落”的水洛筑城,目的是“可得蕃兵三万五千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由此而引发了刘沪进驻水洛,继而筑城,以至发生一波三折的故事。
这种弓箭手屯田方式,实质是占有少数民族的牧场、变蕃民为编户、变畜牧为农耕。在庄浪,意味着从此告别了以往少数民族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开始了绵延至今的传统农耕文化。如果说,北宋之际的弓箭手屯田制度在庄浪土地上引发了由畜牧业向农业转化的趋向,金代则全面实现了这个划时代的生产方式的过渡。
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宁,无疑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先决条件。对庄浪而言,金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和平发展时期。与宋相比,金代在庄浪统治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因战争消弭,时局更为安宁,人口更为密集,史称“世、章盛世”的历史大环境,无疑对庄浪以深刻的影响。当时在庄浪境内增设了通边县、水洛县,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的人口增加和繁荣发展。毋庸置疑的是:因生产方式的嬗变,引发了在庄浪千沟万壑间进行的对处女地的大面积开垦,开启了原始式修梯田的先河。
后来,随着元蒙铁骑的纷拥而至,那些曾在庄浪土地上辛勤劳作了一百多年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受蒙古人欺压蹂躏,已很难立足,大多数被迫鸟举迁徙,悄然遁去。随之而来的另类人群 —— 蒙古“土达”,因元统治者实行的又一次大规模屯田移民而成为庄浪的新居民,他们居然在庄浪长期滞留下来。直至时隔二百多年后的明嘉靖年间,庄浪知县窦文有些诧异地写道:“文尝阅版籍,见民多蕃民,盖仍元之旧而未革也。又见土达军户,皆防御三边之卒,犹是元之种类,归附为民”。此中透露的消息证明:蒙古“土达”并未如某文所述那样“整体北遁”,而是部分滞留下来,他们的后裔成为至今庄浪人的组成部分。新编《庄浪县志》证言:“今南湖镇一带梁、杨、张、高、马、田、郭、程、王、蒙、蔡、杜等姓中,有‘土达’后裔。”至哉斯言。
笔者曾于民间多次听闻“正月十五杀达子”传说。然而这个不见头尾的传说叫人不明就里,这究竟在反映着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呢?真切的史实已无从深究,但细心推理,其大致的历史轮廓又不难显现端倪。
元蒙统治者在强盛之时所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族人野蛮的杀戮和残酷的压迫。这种久已聚积的民族矛盾和仇恨因元蒙政权的风雨飘摇而暴发。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狂飙席卷全国的当口,倾覆之势不可能理智地把暴虐的元蒙统治者与无辜的“土达”百姓分别对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势必对遍布于全国境内的蒙古人一股脑儿予以屠杀和驱赶,迫使“土达”百姓隐姓埋名,藏匿逋逃。
明人丘浚著文写道:“国初开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已多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望相化,而亦不易识别之也”。从丘浚与窦文两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蒙古土达入明之后,在庄浪和其它地方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丘浚的文章反映明朝初建之时,全国各处的“土达”已缩头缩尾,“更姓易名杂处民间”。而庄浪的番民、土达竟然在明建立二百年之后,堂而皇之地把名字登记在户口花名册上。没有人歧视他们,更没有驱赶、杀戮他们。关于“正月十五杀达子”的民间传说,可以认为是明初从异乡迁徙于庄浪的移民从故乡带来的历史传闻而已。在庄浪本土并未发生这桩惨案。其中昭示的意义再明白不过:因为庄浪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大融合的渊薮。庄浪从不欺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来自何方的异族人,外乡人,庄浪都会以慈母般的胸襟接纳他,使他以主人翁的姿态理直气壮地生存于这块土地上。即使时局风云骤变之际,庄浪仍会以宽厚的胸襟庇护、遮蔽那些异族儿女。在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庄浪人文历史中,无时不体现着这种包容并蓄的深厚底蕴。


一个群体共识近些年在庄浪渐渐明晰起来。
多数人认为:当代庄浪居民大多数是明、清两代移民。这个认知大体没错,因为现今大多数庄浪人家中都供奉着一部家谱,这些家谱几无例外地记载着某个年代流寓庄浪的历史,而且上溯的时间都没有超越明代。不仅如此,老百姓的口碑也是一个佐证。至今问起庄浪人的祖籍,几乎众口一辞:山西大槐树底下来的。这个话乍听起来似乎太有些漫无边际,其实,却是反映着一段历史的真实,反映着生命与生存的严肃话题。山西大槐树的故事源于明代“洪武大移民”。因元末农民大起义,全国战乱纷起,民不聊生,不知究竟什么原因,惟独山西没有战乱,于是各处的流民纷纷奔向山西避难。至明朝建立,山西土地上的人口压力已难堪重负。
山西巡抚频频呈奏,近似哀告的奏章使朱元璋下决心举行移民运动,于是分十批移民百万的“洪武大移民”的帷幕徐徐拉开了。这个过程进行得那样有条不紊:朝廷于山西洪洞县永济寺中设立了一个类似移民办事处的实施机构,移往全国各地的人群都要去该寺集中,办理有关的移民手续,领取一定的安家费或生产资料费用,然后由押官领队,一拨一拨地分赴各地屯田“就食”。

群体离土离乡之愁是一种弥漫天地的情绪。当时呼天抢地、哭天震地的场景一定会寸断肝肠。人们泪眼朦胧地回首看了一眼寺院前那棵参天大槐树——一个最明晰而永刻于心的标志。
在踽踽而行的旅途中,最难忘的则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实:为防止逃跑,移民被押差用麻绳将手臂一个个串联起来,途中有谁“内急”,报告一声:长官,解手。押差明白要干什么,于是解开绳扣,让其去路侧大小便。于是,“解手”这个特殊语境中最为默契的词汇,就约定俗成为人们至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口头语。
正如台湾作家杨明所言,“所谓故乡,不过是我们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后驿站”。又一批新居民在庄浪土地上安顿下来。迁徙此地的困境,迫使移民作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抉择,激发起人们生命底线下奔突的潜流。于是在庄浪的千沟万壑间又升起袅袅炊烟,鸡犬之声隐隐相闻,标明又一个充满生机的历史新纪元在这块大地上重新开启。锋利的犁铧翻起的滚滚泥浪中,移民们依然闻到了故乡土地一样的馨香——以自己粗壮的双臂打拼一盘属于自己的天地,不也一样圆着故乡创业的梦吗?且把异乡作故乡,大槐树来的人们不久就俨然成了庄浪的主人。
当推究“大槐树——洪武大移民”这段历史根源时,我们发现,除了疏散山西人口的普遍意义外,明代统治者对西部边陲地区,更有为巩固边防而实行的卫所屯田制度。作为历史上一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前哨的庄浪,更是被日益重视经营的地带。明初,统治者在这里全力推行“以屯养军,以军隶民”的屯田制度,实行“凡流民均给土地”的安置政策。但这种军屯和民屯同时进行的垦田活动,却有着悬殊的对待。明洪武时,“凡府郭四周平川地亩,灌溉有及者,俱属备卫”“凡军所占地,皆择膏腴之处”“军系屯住土户……军强民弱”。由此可以推想:为统治者效命的军户霸占了绝大多数平田沃土,而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移民和原有的蕃民、土达们只好在山间沟壑中耕种荒山陡屲,其艰辛苦楚自不贷言。
然而,我仍对庄浪这段移民变迁状况和县人的普遍结论多有疑窦:当代庄浪人的先祖,真的和绝大多数人自己认定的那样,都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走来而绵延至今的吗?真的是自明代起就是他们最后的驿站吗?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能允许他们安安稳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吗?由史实推断,可以部分否定这些论点。据史料分析,庄浪在明代一季,仍是一个苦难迭重、风雨飘摇的时代。虽然于明初因移民开发,使这块土地有了短暂复苏,但因卫所屯田制度造成的土地兼并,移民和其他旧籍汉人、蕃民、土达等少数民族被驱赶至山沟苦度日月,迫使将原有的森林、草地悉被垦殖。又加西北蒙古铁骑时来骚扰,为防止入侵,常于初冬草枯时节,采取“放火烧山”的对策,将远近茫茫林草付之一炬,为使蒙古铁骑来时无水草可侍,不攻自退。
这样大面积的垦殖和“烧荒”的结果,使草木俱毁,使原来良好的植被和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又加明成化四年(1468年)的满俊之乱的影响,及频频发生的饥荒、地震,使庄浪更加贫瘠、凋敝。翻开旧《庄浪县志》,赫然可见极为凄惨的记载:
“嘉靖三十五年,大饥。人相食,民逃几尽。”“崇祯十三年,大旱。人掇草根木皮充腹,甚或易子而食,折骸而炊,流亡殆尽。”
清康熙年间庄浪仕绅李敏盛也写道:
“自万历十年,十五年,屡生大祲,人民死亡殆尽,田地荒芜过半。崇祯初年,兵荒交加,寇贼屠戮,惨伤又不堪言。至九年、十三年,又遭奇祲,道殓相望,几无孑遗。”
康熙年庄浪才子柳翘才写道:
“……自明季迄今,逃亡十之八、九,仅存二里,丁只八百有奇,从无通完之赋,从少升任之官。”
清代《庄浪县志》中,知县王钟鸣《详平凉府文》中的一段文字真切地描绘了当时庄浪人的生活状况:
邑中不满百户,境内不过千人,乡无五家之聚,灶无十口之食。数十里断烟断迹,几十年无镇无集,耕凿而余,别无生理。士不亲笔墨,而尽力于西畴;女不习织纫,而悉事于南亩。即或稍殷者,仅有一、二牲畜,安济乃事?且田皆硗确荒凉,产多苦荞、燕麦,亢则苦涸,潦则忧浸,幸而事稳,而谷死金生。竭终岁之劳动,不足偿一年之维正;万一岁欠谷类,则八口之待哺无资,一夕之膳粥不饱。以故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况又复(掘)穴而居,撷草而茹,炕无片毡,仅赖粪糠之火;肤无寸布,徒藉碎羊之皮。严冬一敝裘,盛暑亦一敝裘,夫穿昼出,内则赤身。鹑衣鹄面,家无粒粮。”
如此致人死命的恶劣环境和背景下,人民非死即逃,“数十里断烟断迹”。即使苟活残留的人口,已是微乎其微。直至清顺治七年(1650年),全县人口才有2200多人,如果按后来合并南八镇时,人口基本对等的比量估算,庄浪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4500人。并且此后有不少人陆续迁出,邻县隆德至今仍有不少人声称自己祖籍在庄浪。由此推断,以这样小规模的人口基数,是不可能繁衍至今拥有43万之众的大县。至于现今庄浪绝大多数人自称先祖是“山西大槐树下来”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大多数人不大明了“山西大槐树”产生的年代和时代背景,误把清代以后的移民与明代混为一谈,以讹传讹,将历史传说化了的原因所致。

当我们寻寻觅觅,试图找到一条贯穿庄浪历史的线索时,但却往往象沙漠边缘的河流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坠入漫无头绪的空茫。尽管庄浪历史上确曾涌现出过几多光辉四射的英雄豪杰,丰富多彩的出土文物及其他历史物证,使我们触摸到远古庄浪人创造人文历史的生命律动,使后人为之神往而膺服。然而,一次又一次灭绝人性的浩劫,屡屡出现的断层,又使历史真切的面目杳无踪影。
长夜难明赤县天,庄浪人什么时候才能从苦难的梦魇中走出,让祥和的青鸟飞临这块土地,让生命的根须永久深植于这片热土?这个历史转折的契机何时才能出现呢?
经受了血与火、刀剑与犁铧、兵燹匪患与安宁兴旺交替磨洗的庄浪,终于走到了一个转折的路口。这个路口,似应定位在清康熙中叶。从这个时候起,直至清末二百多年历史中,应是庄浪全方位发展时期。几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奠定了其发展的基础。
首先是大一统的清王朝结束了重大的内乱外患,因蒙古与满清关系融洽,地处一隅的庄浪不再遭受来自战乱的侵扰;另外,清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予民生息、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并招徕流亡,由官府供给或借贷子种耕牛,奖励移民先山后川,择地占业。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发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个予民生息的政治因素和封闭偏安的地域环境,给庄浪以悄然复苏的机遇。
庇荫于陇坂之西一隅,地处群山深壑中的庄浪,此时唯一的财富是天荒地老的宁静。正是这种因闭塞而形成的宁静,恰恰成为疲惫的乱离人苟且偷安、聊以度岁的好去处。也许,他们中原大地或关中平原上的家乡,李自成造反的余波未息;也许,故乡瘟疫与饥饿的恶魔正在交替肆虐;也许因获罪而遭谪流放他乡……一千种、一万种的困厄不容他们在故乡立足,迫使他们辗转漂泊,远走四方,渴望找到一个宁静的港湾停泊栖息,以抚平他们躯体与灵魂的累累伤痕,希图再扬起生命的风帆。
他们终于找到了庄浪这个宁静的港湾。当踏入这块土地的那一刻,就认定这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时他们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状如乞丐。然而,他们眼中闪烁的是倔强的光芒,他们胸中扑扑窜起的是创家立业的火苗。立誓要把苦难、意志和智慧一起淬火,磨砺成一把不钝的锄头,在这块热土上开掘希望,以期收获明天的丰硕。
人类学家发现:人类种群的迁徙,常会增强其生命素质和生存能力。这个论点也印证了庄浪俗谚中“树挪死,人挪活”的认知。当命运之神又一次把来自天南海北的移民象撒一把芥菜籽一样散布于千沟万壑间的时候,标明庄浪又一轮 “创世纪” 的开始。新的拓荒者随便在一个僻静的山弯凿一眼土窑,或搭一间草屋,盘一台土灶,升起一缕袅袅炊烟,向天地宣告一个人家在此落根了。大山深沟,阻断了侵扰的马蹄,也阻断了奸吏皂役派丁摊赋的步履。安居此地的人们迎来每一个清岚笼罩的清晨,悠游地赶上牛儿、扛上犁铧,上山岗、下沟畔,耕耘西汉、或是宋、金先民原已垦殖的土地,播下希望的种子,祈求老天赏赐一个丰硕的金秋。
然而,所有的日子并非这样一如田园牧歌式的惬意。虽然乱离的阴影短时不再光顾,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得不冷峻相对。改朝换代、劫波之余的庄浪,一定是满目疮痍、备极凄凉。新的拓荒者面对的当是丛莽荆棘、狼奔豕突的景况,还有不时与旱祓洪涝、饥饿荒年搏斗。每一口饭食,每一寸衣缕的获得,都需付出生命极限的挑战。这种白手起家创业的历程是那样的艰苦卓绝和惨烈。
“石在,火种就不会灭绝。”只要老天不把倾覆的厄运降下,或只给一息的生机,这些饱经沧桑之变和颠沛流离之苦的庄浪人,这些操着各种口音、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批新移民,和少量留存的汉人、“番民”、“土达”组成的拓荒者,就会以空前创业激情让这块苦寂土地翻腾起来,让生命的绿荫覆盖这片热土。河南人、山西人、四川人、老陕们挈妇将雏来了,身怀薄技的五匠来了,走村串乡的货郎客来了,郎中游医、五行八做的异乡人都被这个宁静的港湾、被这个气爽风柔、土肥水润的息土吸引着络绎而来。
在庄浪,这是一个创造和激情燃烧的时代。经过几代人最窘迫、最艰辛的奋争,顽强地存活下来,繁衍生息下去。倏忽数十年、百多年过去,庄浪沟沟洼洼间到处已是绿树掩映、青岚笼罩、阡陌纵横、瓦屋鳞栉的村庄。
清初只有715个精壮劳力、2200多人的庄浪,至时隔200多年后的宣统元年,人口已发展到26281人,比清初增长近12倍。
未完待续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