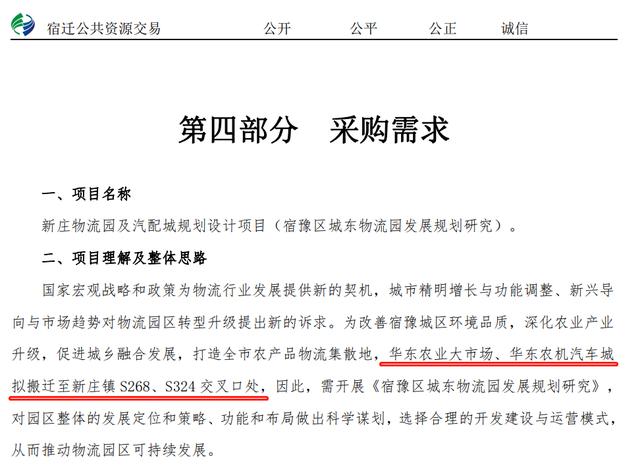肯尼基的灵魂音乐(那一首悠长的灵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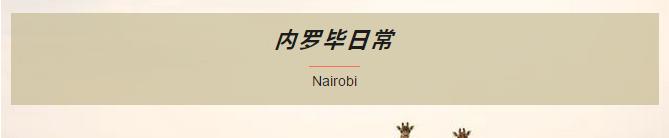
接机的是许久未见的朋友Y。他胖了大约有二三十斤,个子似乎也高了,据称是因赤道地区离心力较强。总之,可以确定这是块养人的沃土。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车速缓慢,沿街挤满了抱着各种货物的小贩。
定睛一看,全是贴着中文标签的充电宝、自拍杆、电蝇拍,甚至还有燕子图案的纸风筝。间或有人卖切好的水果、玫瑰与英文报纸。
天色渐暗,我们有点心慌,毕竟注意事项上明白写着:“在市区搭乘车辆时,请不要开着窗户打手机,请妥善保管自己的物品,钱物随身,以防被抢”。左臂上不久前接种的黄热、霍乱疫苗似乎也隐隐作痛起来。


路过某个中东国家大使馆时,端着AK的保安把车拦下,一脸严肃地叽里咕噜一番。Y操着还算流利的斯瓦西里语,连说带比划算是过了关。路上也有警察偶尔拦车,我们问Y这里治安怎么样。“别提了,这儿的警察,下班脱了制服基本就是强盗。”他恨恨道。于是我们更坚定了决心,天黑后绝不能离开酒店。
我们在市区流连了几日。Y抽空带我们去了博物馆、市政厅等地标,包括一家据称是总统弟弟开的烤肉店——也只是几间扎得较结实的草屋而已。还有一间开在希尔顿大堂的小珠宝铺子,老板是个犹太老先生,留一把雪白整齐的胡子。他从保险柜深处摸出几颗夺目的坦桑蓝与祖母绿,用口音很重却十分好听的英语,试图兜售这些漂亮的宝石给我们。当然回答他的只有一连串的No No No。

一天早上,Y和朋友邀请我们去打高球。顺便一提,肯尼亚的气候非常宜人,并非想象中几小时就能被晒脱一层皮的状况。因东非草原海拔高、气温低,这里是热带草原气候,虽然紫外线很强,但早晚甚至要穿厚外套御寒。
清晨五六点钟,我们到了球场,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在开球了。我们跟着他们慢慢散着步,太阳一点点升起,天空从清冷的蓝色一层层变暖。球场边围着高大的香料树,有些结满了绚丽的黄色花朵,啄木鸟敲击着树干,晨雾、露水在那有节奏的“笃笃笃笃”声中慢慢消散。第一次走进高尔夫球场,居然是在东非草原,这经历倒很是值得纪念。



在市区流连了几日,我们驱车前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一路上经过了大大小小的村庄,向来路上爱打瞌睡的我几乎全程抱着相机大张着眼睛。一切都是奇妙美好的。
天空,云,风,甚至空气的颜色。一家三口在远处的山坡上摆弄一架红绿相间的联合收割机,身后是乌沉沉的天空。



一群小孩子光着脚在草甸子上追逐一个瘪了的足球。满头卷发的双胞胎站在妈妈浑圆坚实的屁股上朝我们张望。破旧的公交车被漆上缤纷的颜色,头顶着一大包行李的阿姨叫嚷着让司机停车。留着山羊胡的老人赶着羊过马路,他的手掌、脚掌都是白色的。
司机沉默地开着车,Y告诉我们,一个好司机是很重要的。因为进入保护区后,并没有什么固定线路,全靠司机的经验带我们去寻找大象、长颈鹿、狮子等的活动区域。


门票价格不菲。然而踏入园区的瞬间你就会明白,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个时节的草原并不是苍翠的。大片金色的长长的草颈交缠着,像绵密的海浪。斑马与小羚羊在我们的惊呼中成群结队地出现,斑马有肥壮的大腿,羚羊有浓密的睫毛。它们平静地吃着草,甚至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




快到酒店时,我们遇到了一群长颈鹿,三只大的,两只小的。它们很慢很慢地踱步,用舌头卷下金合欢树的叶子吃。我知道金合欢树的嫩枝上是长满了软刺的,那么大概长颈鹿的舌头很是坚韧。
当车子在路边时,这群长颈鹿转过身来看着我们,一动不动。距离大概有接近二十米,清灰色的天空下,有风穿过旷野,大家都不再讲话,只是呆呆地呆呆地看着它们,那一个个修长的、温柔的剪影。


第二天一早,司机就催促我们出发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深入马赛马拉腹地。天灰蒙蒙的,阳光还埋在厚厚的云雾下。万籁俱寂,只有车轮碾过泥土和晨风吹拂草尖沙沙的声音。司机开了大约十分钟,靠边停下了。他指着前方,小声对我们说:“Wildebeest”

角马,成千上万只角马。它们飞快地掠过草脊,腹部与四足被晨露沾湿,变成很深的褐色。上万只角马数十、数百一群,随着领头角马的节奏,或忽然发足狂奔,或在疾行中迅速改换方向,或在越过平缓的土坡后瞬间顿足停止——仿佛无数安静而汹涌的洋流一般,纷乱却有序。
它们的筋肉像铜铸的一般坚实有力,鼻尖咻咻地喷出暖烘烘的白雾。这宏伟的洋流让人汗毛直竖,手脚僵硬。你张开嘴,却很难发出声音——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

太阳挣脱了云层。从地平线开始,天空被染成七八种颜色,靛蓝、水绿、绛紫、胭脂、绯红、鹅黄、鱼肚白。角马像流云一样飞快地四散消失了。五彩斑斓的天空下,只剩下一棵孤独的金合欢树。我们离开了这片区域。
水边聚集了许多动物。各种各样的鹿,大的、小的、斑点的、条纹的、直角的、旋角的,它们的足尖仿佛永远不着地,总是轻快地点过草尖,几个急速的跳跃,就消失在草丛深处了。斑马、瞪羚、长颈鹿、成对的疣猪、带着幼崽的猴子、三五成群的大象。

和先前的大群角马一样,这些动物偶尔看向我们的眼神中充满的安然,毫无惧色。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小水坑旁,指着前方说:“Hyena"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冷僻的名字是什么,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原来是一窝鬣狗。
记得小时候读《哈尔罗杰历险记》,里面对鬣狗的描写是有点恐怖的:一只饥饿的鬣狗咬碎了主角煎肉用的铁质平底锅,并把自己割得满嘴鲜血。
这种长相凶残的小动物什么都吃,受伤的同类相食更不在话下。然而此时我们看到的,大概是鬣狗世界中难得的温情瞬间。几只成年鬣狗带着幼崽,在水坑附近悠闲地晒着太阳。

小鬣狗身上还没有长出斑点,嘴部也较尖,毫无邪念的黑眼睛仿佛汪满了湿漉漉的溪水。清晨的阳光给它们柔软的毛发镀上极浅的金色。
大鬣狗有些警惕地看着我们,但终究也没露出利齿。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Pi第一次在父亲的动物园中见到Richard Parker时的情景。当你直视对方眼睛的一瞬间,你的确会隐隐觉得它是不会伤害你的——猛虎也有细嗅蔷薇时。

接近中午时,我们回到了酒店。动物在气温过高时是很少出现的。餐厅是半封闭的设计,远处可以眺望平缓的草原。
许多羽色鲜亮的小鸟在大厅穿来穿去,甚至直接停在你的午餐盘子上。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鸟,翠蓝、雪白、朱红、极耀眼的金色……它们纷乱又和谐地披在这些小精灵身上。大厨不耐烦地一遍遍驱赶着飞来争食的鸟儿们,并对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外地人报以略带无奈的嘲笑。



再次出发,司机决定带我们去寻找狮子。向导之间有互相通报踪迹的电台,我们与几台越野车并行向草原深处走去。转来转去开了大约半小时,远远看见几辆熄了火的车,从车窗伸出几只长枪短炮。司机示意我们千万不要大声讲话:到了。
我们静静等前几辆车离开了观察点,才缓缓开了过去。几只母狮散在草丛里,似乎是睡着了,尾巴偶尔跳起来驱赶蚊虫。唯一的一只公狮歪头半卧着,它金色的眼睛缓缓看向我们——那是怎样的一双冷酷而镇定的眼睛。

想起来时别人告诉我们,不久前某个庄园的主人带着女儿在自己的围场打猎,忽然被埋伏在附近的狮子袭击。庄园主受了重伤,眼看救不回来了。女儿忍痛逃回车上,为了结束父亲的痛苦开了枪。自此那个区域的狮子再看到人类,眼神就完全不同了。
正当我胡思乱想时,那公狮与身边的母狮厮闹着忽的恼怒起来,发出一声爆裂的嘶吼,犹如平地惊雷。惊慌之下手里的相机差点掉了,临车的游客也被吓得惊叫起来。这就是百兽之王。Richard Parker的影子早已被抛诸脑后。我们赶紧开离了这片区域。

当晚我们住在园区内。不远处是乞力马扎罗山,月色明亮时,能看到那锥形的轮廓,还有围在山腰上厚实的云。漫天星光下,开一瓶TUSKER啤酒,放上周杰伦欢快的老歌,不知不远处隔离围栏外的动物们是否能听到,做个跟我们同样色调的梦。

离开马赛马拉,我们驱车前往博格利亚。每一个看过《走出非洲》的人,大概都不可能忘记邓尼斯带着凯伦,飞过落满火烈鸟的湖面的场景。
崎岖的山路上,能看到一群群绯红色的羽毛,柔和而温暖。偶尔有一小群还未成年的幼鸟,羽毛是浅浅的灰色。随着年纪渐长,它们食物中的鱼、虾、藻类所含的虾青素会使羽毛呈现越来越鲜亮的红色。

我们来到一大片据称可以近距离观察火烈鸟的水滩前,然而它们仍在很远的地方。脚下泥水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实在走不了更远。这时候,一个小男孩走过来,用简单的英语比划着表示可以让远处的火烈鸟飞起来,代价是一美元。这大概是他做熟了的小生意。
他脱下鞋子,飞快朝滩涂深处跑去,不一会儿,只见一片粉红的云霞忽地腾起了:几千只火烈鸟悠悠地飞了起来,我们像傻瓜一样欢呼惊叫着,被它们美丽的脖子、修长的双脚和翅膀下一小块心形的红斑所折服。它们有的越飞越远,渐渐去了另一座山峰被夕阳点亮了的地方,有的用脚飞快蹬着水面,落在不远处的湖上。

小男孩已经跑回来了,看着我们少见多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塞给他一块大白兔,他紧紧握在自己黝黑的小手里。

离开肯尼亚的前一晚,忽然想起看到角马的那个清晨。它们从吉普车两边缓缓流过,有些会在车窗边停下,仔仔细细地盯着我们看。那眼神中没有任何恐惧或挑衅,仅仅是在端详几个钢铁怪物中的小人儿。
是的,在这辽阔无边的草原上,我们才是局外人。肯尼亚大概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此生一定要再来的地方,只为在那无边草原上的某一刻,你忽然意识到人类并非这世界上唯一的、最重要的生物,那一刻你的心纯净无杂念,只想抱一抱脚下的大地母亲。
“如果我知道一首属于非洲,属于长颈鹿,属于非洲新月的歌,属于田地的犁头,和采咖啡工人的歌;
那么非洲是否也知道属于我的歌,颤动的平原上空,是否正有我的色彩,孩子们是否会发明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新游戏,满月抛下的阴影,落在碎石的车道上,是否像我的身影,尼冈山的鹰是否会看顾我?
再会了,肯尼亚,那一首悠长的灵歌。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