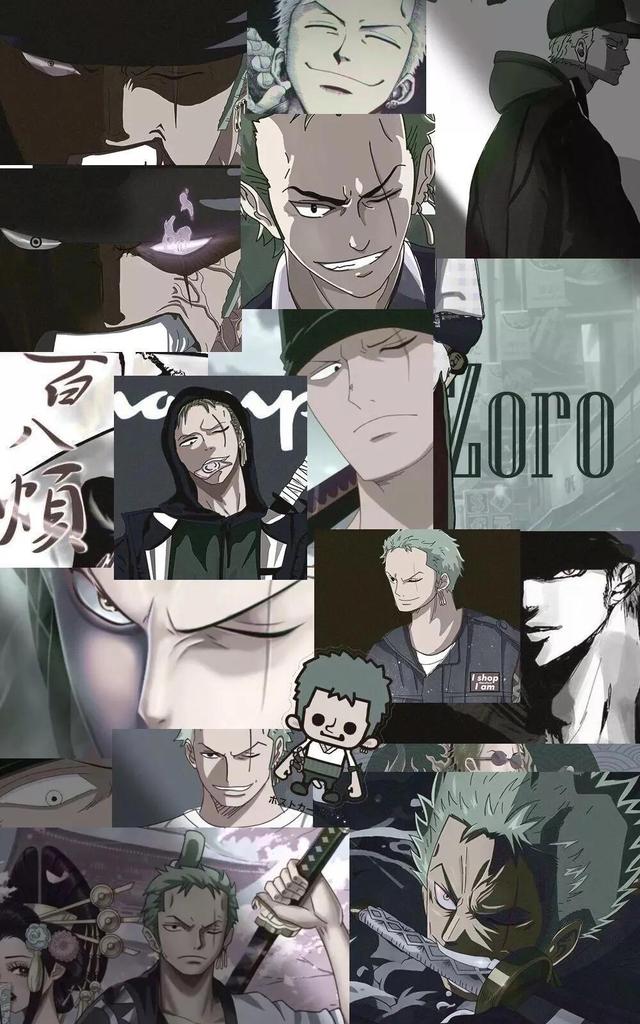(在罗江就一直纳闷)
伍松乔/文 雁子/编辑
十月黄金周在德阳采风,分组而行,我是主动报名去罗江县的,原因只有一个:再去瞻仰李调元。
城东纹江之滨、古太平桥首玉京山上,身后是刚刚看过的李调元纪念馆,眼下是"文山"黄沙岩大型深浮雕,高35米,总长72米。李氏"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指李调元父亲李化楠以及李调元、李调元堂弟李鼎元和李骥元,他们中榜皆在29岁),四个顶天立地的巨大头像让人过目难忘。

不能不佩服罗江人的崇文精神与先知先觉,占尽一座山风水宝地的李氏园林,1989年便已竣工,1990、1994年先后定为县级、市级文保单位。新世纪以来,罗江文化在我耳朵、眼睛里络绎不绝:博物馆、诗歌节,李调元学会、研讨会等等,难能可贵在于,这一切都是自选动作。
风和日丽,凭栏远眺,古城尽收眼底。
一堆罗江、德阳的文化图书,五六个本地学者、作家老朋新友,喝茶、放眼,摆不尽的李调元龙门阵。
当年北京四川会馆里,有副大名鼎鼎的对联,传诵一时:
此地可停骖,剪烛西窗,偶语故乡风景:剑阁雄,峨眉秀,巴山曲,锦水清涟,不尽名山大川都来眼底;
入京思献策,扬鞭北道,难望先哲典型:相如赋,东坡文,太白诗,升庵科第,行见佳人才子又到长安。
这对联是清乾隆蜀中大才子、罗江李调元写的,可谓巴蜀地灵人杰的精华版,李调元历数汉、唐、宋、明的巴蜀文人标杆,一朝一人,到"本朝"就戛然而止。
最初读到这对联的时候便曾心生一念:选择清代的"一个代表",会不会就该是李调元本人呢?遥想调元先生风流倜傥指点江山挥洒蜀国英雄榜的时候,
心头或许也潜伏着一个自我呢,呵呵。
以李调元为清朝蜀人代表,不是没可能。
李调元与遂宁张问陶(张船山)、丹棱彭端淑,早就被合称为"清代蜀中三才子",而李氏"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一向被视为眉山"三苏"现象异代重现的佳话。

暂且搁下"代表"的事,李氏一生到底是热闹呢还是寂寞?真是不好说。
1990年代在媒体上盘点巴蜀文化的时候,就一直纳闷,干嘛李调元身后老是声名不显、高开低走?在李调元的传说故事中,他常常给别人(从牧童直至皇帝老倌)解疑释惑、指点迷津,轮到自己,谁来盖棺论定?
嘉庆本《四川通志》154卷《人物》介绍李调元时说"其自著诗文集,不足存也。"光绪本《国朝全蜀诗钞》卷14评价李调元:"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识者宜分别观之。"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12《李调元兄弟词》如是言道:"绵州李雨村观察(调元)所刊函海一书,采升庵著述最多,惜校对未甚精确。其自著《童山诗文集》亦不甚警策,词则更非所长。"
凡此种种,李调元最终未能进入《乾嘉诗坛点将录》与《清史稿·文苑传》。1949年以来,多种版本的中国高校古典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几乎皆不提李调元。流风所及,四川文苑对李调元也就渐渐疏远乃至回避了,直至今日,巴蜀学界主流大抵也如此,这就整得有点离谱了,外人不知道,自家祖宗自家也不知道?

这不能不说是蜀中文坛、学苑的一大憾事。
其实,同时代名声如雷的诗坛盟主袁枚对李调元推崇备至,他不止一次地评价李调元"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今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诗话》精妙处,与老夫心心相印,定当传播士林,奉为矜式"等等。
李调元诗文为时所重,可见一斑。我只读过调元先生留迹巴蜀的一些纪游诗,印象颇佳,尤其他56岁所写的《登金顶》,极其喜欢,上世纪90年代便拜托泸州乡贤倪为公先生写成一堂屏,朝夕相处,深感其妙:
拾级登天路又分,混茫浑不辨氤氲。人言峰顶真如月,我见峨眉尽是云。四壁银光千古雪,两廊铜锡万年文。昨霄风雨何方降,夜半龙归隔寺闻。
我后来发现,对李调元的无视与贬低,不过是在所谓主流文学界或"纯文学圈"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与主流的评价大有不同,在民间,在大众,在不那么"雅"、很有些"俗"的戏剧界、通俗文艺界、餐饮、谜语对联诸界,其人其文其事,真是热闹得很,持续时间也长,影响所及,远非四川盆地所能局限。种种内容,虽不乏附会,但实在也堪称集川人幽默之大成。
或许是还没找到衡量李调元的标准?他过于传奇过于庞大,以至于我们的好些正统研究者、评论家一直吞咽不下、消化不良。
关于李调元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李调元穷其一生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有待深入发掘,其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应当从新估量,获得应有的公允评价。

尤其是,李调元为家乡四川作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文化建树,超越包括苏东坡等在内的所有历代先贤,每一件都是其它人倾其一生难以完成的,哪一桩不胜过即便是华章墨宝的优秀诗词?
简而言之——李调元是继司马相如、扬雄、苏东坡、杨升庵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巴蜀文化巨人,不可忽略。
在我看来,"山(书山)呼海(《函海》)啸",可谓李调元的惊天伟业。
李调元生活在清朝雍、乾、嘉盛世,但他所面对的家乡四川,却是天灾人祸的明末清初大劫难之后,天府之国土荒人稀、十室九空。虽经清初移民入蜀,恢复生产,但四川文化的大窟窿岂是一下子"填"得起来的。文脉中断、书院寂寥、蜀学不振、科举题名甚少,一个最大的制约便是图书尤其乡邦文献的缺失。读书人、读书事,没有图书,犹如皮之不存。
"念日月之以逝,恐文献之无征。"李调元自青年时期即有志于蜀中文献的搜罗与整理,担负地方文化传承重任。具体说来,是要在家乡建设一座笑傲天下的大型书库。

这座后来被叫作"万卷楼"实则藏书十万卷的书库、书山,有着清晰的几大来源。
两代人的悉心购藏:乃父李化楠,乾隆七年进士,先后在江浙、京畿担任知县、知府,他以俸禄遍购珍贵书籍,不辞千山万水运回故乡。李调元自云"酷有嗜书癖",年轻时就受父亲熏陶,博览、泛购群书,在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公余之暇,犹手不释卷"、"遍访异书",虽遭逢生活拮据,仍千方百计、孜孜不倦。
抄录国家秘藏:李调元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诏修《四库全书》,入馆任纂修。借参修《四库全书》之机,李调元煞费苦心,"每得善本辄雇胥抄录之"。"各书中于锦里诸耆旧作尤刻意搜罗",汉至明代四川名人的上百种在本土业已失传及罕传秘籍尽入囊中。之后,他利用在吏部任职的机会,同样勤奋披阅、抄录,"于是内府秘藏,几乎家有其书矣","御库抄本,无一不备"。
此外,通过交换,以书易书;从全国交往的师友那里得到馈赠;以及自刊而藏的图书等等,都是藏书来源的方方面面。
十万余卷,就是李调元数十年精卫填海般锲而不舍、坚韧努力的结果。

李调元在两度出任广东学政后,擢升直隶通永道,奉旨护送一部《四库全书》去盛京(今沈阳),因途中遇雨沾湿黄箱而获罪,被流放新疆伊犁。旋经名儒袁守侗搭救,以母老纳金得释,途中召回,发回原籍,"赢得生还入剑门"。
罢官返乡后,他在今罗江镇北20里的云龙山下调元镇其父李化楠修建的醒园居住,就此悉心经营,乾隆五十年(1785),"万卷楼"拔地而起,大功告成。楼四周"风景擅平泉之胜,背山临水,烟霞绘辋川之图,手栽竹木渐成林。"李调元不无得意地写到"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楼都已经跟山一样高了,可见其雄伟气势,面积之大,藏书之富。李调元还专门编辑了《万卷楼藏书目录》和《赝书录》,每天都要"登楼校雠",还要时时迎接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访书、读书人。
比"万卷楼"更早开始、同时进行的另一桩"名山事业"浩大工程,也于嘉庆五年(1800)全部完成,这便是李调元所编辑的大型丛书《函海》。该丛书共收书152种,大部分为巴蜀先贤著述。分30函,1至10为晋至唐、宋、元、明世人罕见之书,11至16专刻明代杨慎专著,17至30为自著之书及各家已刻而流传不广的书籍。另编书目《西川李氏藏书簿》10卷,分经、史、子、集4门。

《涵海》是集巴蜀文化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涉猎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诸多方面。它是一介书生独力完成的巴蜀文化的灾后重建,雪中送炭,功德无量。
《函海》出版历经艰难。它先后共有6种版本,1782年的初刻本只有20函、是因为李调元含冤被捕,刻版工头向李夫人索要工钱未果而毁版以致。初刻本在国内已经见不到,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
《函海》倾注了李氏半生心血,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校勘,多有序跋记其原委。全书后又经其从弟李鼎元再次校勘审定。其后数十年,调元先生又多加修正改订,所收书增至两百种。该书一经流布即为世所誉,李氏亦自叹此生无恨矣!
李调元回老家时51岁,其后十八年间,他不仅成为百科全书型大学者,还纵情巴山蜀水,"玩"出"川剧之父"、"现代川菜之父"的两个大名头。
李调元是个美食家、美食研究者,他整理了父亲收集的江浙烹饪资料,加上自己在京、粤、疆了解到的烹饪方法,写成一部两卷本《醒园录》,记载了120多种调料、饮馔及食品的制法。所收菜点以江南风味为主,也有四川的,还有少数北方风味,甚至有西洋品种。书中记载的菜肴制法简明,尤以山珍海味类有特色,是研究清代中叶烹饪的重要典籍。1980年代初,商业部组织专家注释烹饪古籍,《醒园录》注释本一版再版。

《醒园录》关于川菜的部分,是川菜历史上的第一部食谱。川菜的自成体系、现代川菜(清初"填四川"后,移民与巴蜀本土饮食文化融合发展起来的川菜)得以形成,首先归功于李调元,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川菜第一人实至名归。
《醒园录》出版时间为乾隆四十七年(1783),对四川这个内陆省份吸收外来烹饪文化具有开创性作用。直到现在,蜀中烹调燕翅鲍鱼、糟醉鱼虾海产,《醒园录》所载方法,犹时有所见。
李调元的诗文中,不少是"形而下"的风物作品,包括写四川饮食原料、菜肴、点心、小吃的作品。《入山》《题青社酒楼》《食芋赠君章》、《落花生歌》等,对民间烹饪翔实记录,赞誉有加;《峨眉山赋》将这天下名山的花木果树、鸟兽谷蔬、山珍水族尽收一卷,为今人研究川菜原料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李调元对中国戏曲颇有研究,不仅关注戏曲理论,更是个戏曲大玩家。他把省外剧种引入川内,使其本地化,成为业界公认的"川剧之父"。
文士李调元与艺人魏长生相交甚厚,携手为川剧艺术发展作过重大贡献。川剧弹戏的四大本《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经李调元润笔整理,文采斐然,也更适合弹戏演唱。此举开文人写作川剧剧本之先河,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赵熙,成为川剧艺术的一项重要传统。
李调元不仅喜欢看戏,还自己组建一个"家戏"班子,在四川各地巡演。

时至2011年迎春之际,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廖全京、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四川戏剧》杂志副主编尹文钱等齐聚罗江,集体朝拜"川剧之父",为先生故里打造临江仙川剧会所、组建调元翰林演出班致贺。
调元先生集大雅大俗于一身,如此非常之才、非常之功,只能说是天造地设的山呼海啸了!
如今传统文化复苏,前度"乡贤"又重来。
什么是乡贤?李调元就是。
巴蜀历史上,像李调元这样呕心沥血回报乡邦、奉献巨大,而且是终其一生、非在一时的,实在不多。
书山起,《函海》毕。品川菜,唱川戏。"草堂溪水清,照见溪上屋。幽人正著书,灯光映修竹",如此晚年生活,正是万千书生的梦境。
就这么下去,李调元可能活出中国文人家园故事的精彩之最。

可上天似乎不乐意世间事有这般圆满,李调元的人生也终遭浩劫,未能快乐到底——天地大戏场,以悲剧告终。
万卷楼建成15年后,嘉庆五年(1800)二月,一夜间被打劫一空,化为灰烬。
起火原因有多说:一是四川白莲教起事,"忽被土贼所焚";一是遭李调元过去的政敌串通盗匪放火;清人王培荀则认为"贼人"就是李氏族人。
正在成都友人家中避难的李调元闻讯悲恸欲绝。
赶回故居后,他将残书片和书灰捧起用黄绫包好,埋入土中,在万卷楼遗址用青石砌起高2米、长2.67米的墓堆,亲笔写了"书冢"二字,刻石碑立于冢前,以诗相哭,泣不成声:
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人火同宣谢,藜燃异石渠。不如竟烧我,留我待何如?云峰楼成灰,天红瓦剩坯;半生经手写,一旦遂成灰。獭祭从何检,尤杠漫逞才。读书无种子,一任化飞埃。
(同治四年《罗江县志》卷三十五《外纪》)

万卷楼被焚后,李调元"意忽忽不乐",两年多后,终在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撒手人世,时年69岁。
我想,在此之前,垒起"书冢"、埋葬书灰之时,李调元实际上已经把自己一起埋葬了。
逝者如斯,调元先生如山似海。
说高说矮也罢,说深说浅也罢,其实,——山在那里,海在那里,调元先生就在那里。
伍松乔简介
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巴蜀文化中心研究员。2017年11月因心梗不幸去世。
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中国报纸副刊特殊贡献者荣誉称号获得者。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四川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散文学会、四川文艺传播促进会副会长。
出版有散文集《姓甚名谁》、《随遇而乐》《记者行吟》《四川散文名家自选集伍松乔卷》《十字岭,识字岭》,评论集《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传记《中国书生宋育仁》、人文地理《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即删)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