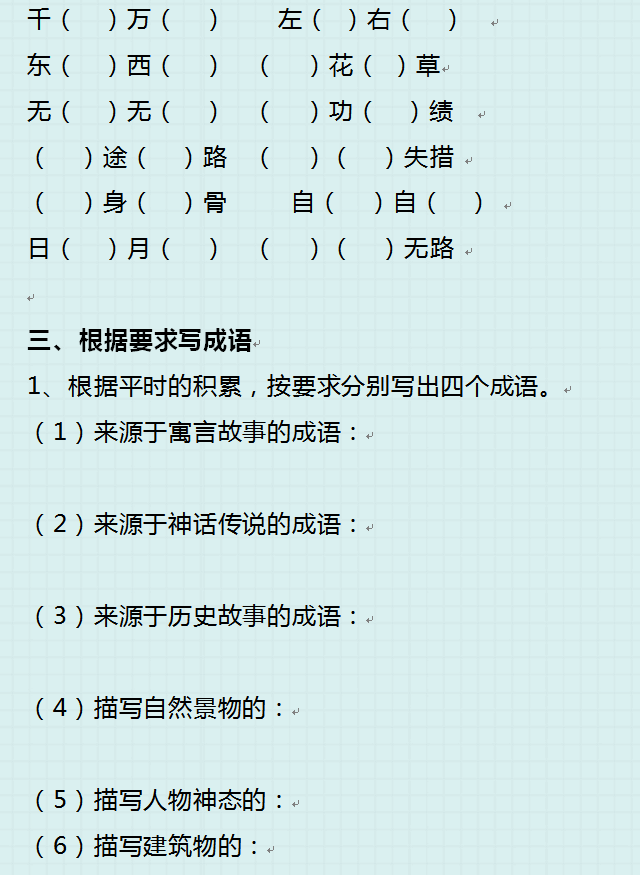应该怎样写读书笔记(怎样写读书笔记)
关注:西安君翰 公众号,领取免费学习资料
写读书笔记最大的好处是能贮存著书立说的资料。常言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做学问必须依靠准确可靠的资料,如果读书不记笔记,单凭一些模糊印象来写论文,当然不可能获得成功。正因为写读书笔记是我们积累资料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人们干脆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梁启超还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有用者,立刻钞下来。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为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子。(《治国学杂话》,《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一《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中华书局1936,24页)凡卓有成就的学者都在写读书笔记方面下过苦功。顾颉刚之子谈及其父时说:
父亲一生治学,留下了一部分极富特色的文字,这就是他从1914年至1980年记了六十多年的、积累了约二百册四百万言的读书笔记,它们已成为父亲全部著述的重要部分。父亲生性遇事注意,并勤于动笔,或写下直接的闻见,或记录偶然之会悟,总之不放过每一个思想的火花,使其留于札牍,把笔记簿当成随手可稽的工具,为作文著书打基础。(《关于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特色》,《文史哲》1993年第2期)记笔记还可以节省查资料的时间。现在虽然也有目录索引之类的工具书,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研究课题,这些工具书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研究的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将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以及资料线索随手记下来,使用起来当然会既方便又实用。
一边读书,一边写读书笔记,对书的印象将会更加深刻,对书的理解将会更加透彻。清龙启瑞说:
愚谓今日诸生,读史必须手边置一札记,随其所得,分类记之。记古人之嘉言懿行,则足以检束其身心;记古人之善政良谋,则足以增长其学识,以至名物象数,片语单辞,无非有益于学问文章之事,当时记录一过,较之随手翻阅,自当久而不忘,且偶尔忆及与蓄疑思问,其检查亦自易易。此为读史要诀,诸生所宜尽心。(《经籍举要》史类《资治通鉴》提要)龙氏所说,当然不局限于史学著作,而具有普遍的意义。梁启超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经学、子学尤要,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读书分月课程·学要十五则》,《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中华书局1936,4页)他还谈道: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来。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它抄下来,那注意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得来的实况。(《治国学杂话》,《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中华书局1936,25页)记笔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迫使你在读书时思考。谁都不愿多写一个字,什么该摘录,什么不该摘录,都是四考的结果。严家炎说得好:
读书要有效果,一定要做笔记。笔记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不仅是为了记下读书的当时产生的那些闪光的思想和精彩的语言,使之不要被遗忘;它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即可以促使我们在整理自己原始想法的过程中把思想系统化和深刻化,促使我们摆脱那种“学而不思”的状态,不做思想懒汉。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一些本来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思想,经过做笔记过程中的加工整理,不仅明确了,而且丰富了、升华了,于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记下一大篇东西来,犹如从蚕茧上理出一个丝头,能得到一大堆蚕丝一般。这就是记笔记的好处。我们应该养成这个习惯,不要偷懒,不要把它看做可有可无的事情。(《严家炎自述》,《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473页)写读书笔记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有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都是读书笔记汇辑而成的,如洪迈的《容斋随笔》、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钱锺书的《管锥编》。顾炎武《日知录·自序》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逐削之。”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明显受到了《日知录》的影响,其曾孙钱庆曾称:“公弱冠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后著各书,即于其中挹注,又去其涉于词华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编定,题曰《十驾斋养新录》。”(《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3页)还有依靠写读书笔记从事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蔡尚思曾举一例:
资产阶级方面,在世界上也出了一个最博学、最多写笔记最多产的小说家,他就是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他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写出此类小说近一百种。他每研究一个科学问题,都要看大量的资料,以便写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他亲自摘录的笔记,就有两万五千多本。他为了写一本《月球探险记》,就研究过五百多册图书和资料。(《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08页)怎样写读书笔记胡适在《读书》一文中讨论过写读书笔记的方法问题,指出:
札记又可分为四类:(a)抄录备忘。(b)作提要,节要。(c)自己记录心得。(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6页)显然,第四类已超出了写读书笔记的范围,或者说是写读书笔记的最高阶段,兹不具论,仅对前三类略作介绍。
抄书这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法。郑板桥曾对儿子说:
凡经史子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得。阅书时见有切于实用之句,宜随手摘录,若能分门别类,积成巨册,则作文时可作材料,利益无穷也。(《潍县署中谕麟儿》,《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500-501页)王筠在指导学生读书时也是这么要求的,尝云:
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编》本)如果自己时间紧,当然也可请人代抄,当年蔡尚思在南京国学图书馆读书就是这么做的。
不少古书都是抄录纂辑而成的。汪辟疆归纳道:
窃以抄书亦有六等:一曰全抄,基本书全抄全读,如巾箱《五经》是也。二曰节抄,读书时随所嗜而节抄之,如《群书治要》、《意林》是也。三曰撰抄,每阅读一书将其书中精要,撰次而抄之,如《九经要义》、《文选理学权舆》、《说文段注撰要》是也。四曰比抄,两书皆有相当地位,比合抄之,如《班马异同》、《新旧唐书合抄》是也。五曰摘抄,随所阅览,摘其字句而抄之,如《两汉博闻》、《两汉蒙拾》是也。六曰类抄,与摘抄略同,但分类隶属,以便挦撦,如《文选类林》、《楚骚绮语》是也。抄书至此,似为最下,然取便记忆,本无不可。(《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1-72页)梁启超说:“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20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汉纪》提要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复云:“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
不少学者都将抄录资料作为写作的基础工作,如顾炎武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称其:“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梁启超评论道:
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钞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他“以钞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钞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钞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钞而不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1936,60页)近人著述,如钱穆之《国学概论》也复如此,“正文仅为纲要”,(《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1页)主要内容是所称引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当然都是抄录而来。
写提要这种方法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所读书进行把握,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根据提要、节要所提供的线索去寻求原文当然也比较方便。现存最早的读书提要当推《书》序、《诗》序。因为单是从篇名还不容易看出各篇诗、书的内容,所以阅读和传播《诗》、《书》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们加上了内容提要。如《诗经·鄘风·载驰》的小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再如《尚书·虞书·舜典第二》的小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汉成帝时,刘向父子整理图书,整理完了,往往写一篇提要,介绍书的作者、整理情况、书的内容,并且作出分析和评价。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然是这么做的。近人张舜徽读清人文集,每读一部就写一篇提要,一共写了一千多篇,后来选了八百篇编成《清人文集别录》出版了。他写提要的方法是尽量辑录原文,并标明出处,挺实用。现代出版的书发表的学术论文多有内容提要,对我们了解这些论著的内容和特点当然是有帮助的。
写心得体会这种方法难度又要大一点,因为读书真有体会,还将体会写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代吕祖谦《吕氏读书记》中的部分内容大致属于这种情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书为“吕祖谦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阅之书,随意手笔,或数字,或全篇,盖偶有所感发,或以备遗忘者”。上面提到的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大抵也是这类读书笔记。今录洪迈《容斋随笔》两则为例。
其一,《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舆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處。”与字云:“赐予也,与舆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其二,《喷嚏》: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这种心得体会偏重于资料考证,还有一种心得体会着重于对思想内容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学术短文,如朱自清的读书笔记《<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作者首先介绍了将《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前一书任中敏先生主编,民智书局出版,后一书任夫人王悠然女士编,大江书铺出版,都是散曲选本”。接着分析了《元曲三百首》内容上的特点和缺点,并结合诗歌中“归隐山林”这一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诗人的“归田”,大概是说说罢了,心里总还想着做官的。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正可描写这种人,这种诗。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作底子,道家思想做幌子。散曲家身份本不甚高,无甚远志;他们只图个自己快活,说想归隐,倒是真的。可谓一针见血,辨析入微。作者还论述了体裁与主题的关系问题,并指出:“散曲这东西似乎只够写写儿女之情,用来言志,总觉得有种俳谐气而不切挚。宋词除苏、辛一派外,似乎也是如此。……词这个体裁似乎根本上并不宜于言志。”作者最后道出了《荡气回肠集》“专取私情之作,以尖新为主”的特点,但是又指出:“在礼教高压的时代,读了痛快淋漓的,现在时移世易,却也觉得有点辽远了。”从而说明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道理。这则笔记虽然不长,但闪光的地方却很多。
做索引如果我们自己有书,或者该书常见,容易找到,不需要摘录的话,还可以做题录和索引。题录可以只记录论著的题名与出处。索引可以写关键词,或主题词,或用最少的词句撮其要点,然后再注明出处。其优点是节省时间,中心突出,便于查找;其缺点是不如抄录原文那么直接了当,内容完整。
读书笔记写在哪儿写在书上最省事的方法是干脆买一本书,就在书上做记号、加批语、移录有关材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读书笔记附书以行,不易丢失;读书笔记可以和原文比照,容易收到直观的效果。所以,从事学术研究最好买一些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书。胡适说:
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86页)将读书笔记记在书上的方法起源甚早,汉代的郑玄似已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毛诗正义四十卷》提要称:“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
王季思介绍过古人常用这种方法,指出:
最简单是在书上作记号,最先他们所用的记号是划、是抹。《朱子语录》:“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朱笔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全与原看时不同。”又朱子论读书法说: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所谓抹,所谓划,都是在文章的紧要处或精采处,划一条线。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迂斋评注古文》,也都是用这个方法指示读者的。现在学生看书,遇到应该注意的地方,大都用铅笔、自来水笔或颜色笔划出来,不知这正是八百年前人的读书方法。稍后一点,是用圈点。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方回的《瀛奎律髓》、罗椅的《放翁诗选》,边都是附有圈点的刻本。(这圆点不是标点的符号,而是鉴赏的符号。)这种方法从元、明以来,日见流行,直到现在才渐渐的少用了。(《语录与笔记》,《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2,322页)王季思还谈到人们常在书的天头地脚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称为“眉批”。不少线装书的天头地脚,都留得特别宽大,以备人们写批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称为文学批评,也由此而来。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脂砚斋批本《石头记》,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前辈学者都喜欢采用眉批的方法。殷孟伦在《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文中说:
他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现在看到他存下的批点过的书有百余种,集录下来一定对后学启发不少。他批过《文选》,他的学生曾传抄过。所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几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说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广韵》也是如此。这三部分整理出来就是很可传世的名著。他又批过《资治通鉴》,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同志在陆宗达处借去一部分采入标点本。 (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43-44页)有的学术著作就是利用批在书上的读书笔记写成的,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谈到了他的杰作《十七史商榷》的写作过程:“凡所考者,皆在简眉牍尾,字如黑蚁,久之皆满,无可复容,乃誊于别帙,而写成净本,都为一编。”沈祖棻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宋词赏析》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两本书,程千帆在整理时,用了沈氏读书时的批语。程千帆在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中说,有四分之一取自沈氏平日批在各种诗集上的评语。“旧释二十三首,也是她在各书上所加的评语。这些评语,除了已经改写为《浅释》的各篇之外,还有一些较为精审的。零璧碎金,弃之可惜,就又选抄了一部分,附录于后。”(《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00页)程千帆在《宋词赏析·后记》中复云:“姜、张两家词札记是从她手批的四印斋本《双白词》中辑录出来的。她的批语有的很简略,有的则比较详细。现在只能把较详的录出,因为这一部分对于读者的帮助可能大些。(《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0,245-246)
还有移录可同本书比较参证的材料的。如果书上的空隙处写满了,可再买一本,或另用纸写了贴在相关部分。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就是这么做的,柴德赓说:
陈先生(陈垣)搜集了很多清代学者的手稿,其中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手稿。从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孙是如何搞学问的:他著《广雅疏证》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再发现再贴,而用到书上去的,就是那最新、最可靠的材料。有些后人不懂王念孙做学问的这种方法,往往找到一条材料,一看现在的《广雅疏证》上没有,就批评他不全面,要给他补,实际上王念孙早已有了,而没有用上。(《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37页)很多学者都用方法积累资料,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专著也都是依据眉批写成的,如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程千帆《史通笺记》等。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之史部补证《跋》介绍道:“某案头初置此书一部,辄就知见,随手以硃笔补注眉上,积久上下眉无隙地,更置一部注之,如是者两三部,窃自比于桥西札记所载邵位西标注简明目故事。乙卯闲居,遂取数部审择迻录,合为一帙,成《补正》五卷。”(《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61页)当然,写学术论文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如季羡林介绍道:
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季羡林自传》,《文献》1989年第2期)写在卡片上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调动自如,有利于分析排比。宋人已普遍使用卡片,王季思说:
以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 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书成以后,存在洛阳的残稿还满两屋子。后来李焘作《续通鉴长编》,他的方法更精密了。据《癸辛杂识》说:“李焘为《续通鉴长编》,以木橱十枚,每橱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乙记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这种方法是合乎科学的。(《语录与笔记》,《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2,322页)《金史·元好问传》称元好问“构亭于家,著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缀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金史》,中华书局,1975,2743页)既然用寸纸细字来写,当然也是用卡片的形式写读书笔记了。祁承㸁称宋人“陈莹中好读书,至老不倦,每观百家文及医卜等书,开卷有得,则片纸记录,黏于壁间,环坐既遍,即合为一编,几数十册”。(《澹生堂藏书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9页)从“片纸记录,黏于壁间”几个字看,陈莹中也是用卡片来记读书笔记的。
今人当然也爱用卡片。如王利器说:
读书要全靠记忆,哪里记得住许多。除了我在家塾里读的那些死书,至今尚能背诵而外,我全是利用卡片来帮助记忆力之所不及,来处理所搜辑的第一手资料。十几二十年来,我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卡片。十年内乱中,我蒙受的损失最大的要数这批卡片。(《王利器自述》,《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210页)郁贤皓也自我介绍道:
我决定把李白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考证李白生平事迹及其交游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与难点。当时在阅读李白作品时做了不少札记,同时将诗文中提到的交游全部制成卡片,然后查稽各种典籍和石刻资料,发现有关材料即写入卡片,通过对资料的排比研究,如有心得或有所发现就写文章,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我与唐代文学》,《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168页)他研究李白的成果汇集成《李白丛考》一书,后来他撰写《唐刺史考》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他说:“从1973年起就有意识地搜集刺史(太守、尹)的材料,制成卡片,几年以后积累的卡片竟数以万计。”终于完成了这部二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我与唐代文学》,《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171页)
目前图书馆用的卡片,多为7.5厘米×12.5厘米,我们用来摘录资料的卡片可以大小不拘。刘乃和介绍陈垣搜集资料的方法时说:“他抄资料都是用大纸的稿纸,有时也随手用‘另纸’,即零散纸头上,也就是我们所用的卡片。写在稿纸上的材料,无论字数多少,都是一个问题另起一页,一纸不抄两段材料,将来用起来方便。”(《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141页)季羡林钞资料的纸头似乎更随便一些。他介绍道:
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寅恪)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黾勉从事。(《季羡林自传》,《文献》1989年第2期)吕叔湘的卡片则是长条纸,后人回忆道:“吕先生当年做的例句卡片,是用毛笔写在裁成长条的粗纸上,然后分门别类粘贴在废书页上。字作率更体,方正挺峻,字如其人。”(刘坚《吕叔湘先生学术述略》,《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裘锡圭用的卡片是自己用废纸做的,他说:“正规的卡片很贵,我极少购买。我的卡片有些是用大张白纸裁成的,有些是用反面无字的废纸裁成的,还有一些是用印刷厂用纸时剩下来的边角料裁成的。正规的卡片盒我更买不起,只能用较浅小的放罐头等物的集装纸箱代替。直到今天,我还在用废纸裁成的卡片。”(《我和古文字研究》,《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458页)
剪贴图书或复印资料,也可算做变相的使用卡片。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陈澧》谈到:“先生治学之法:凡阅一书,取其精要语,命钞胥写于别纸;通行之书,则直剪出之。始分某经,继分某章、某句、某字,连缀为一,然后别其得失,下以己见。如司法官之搜集证据,乃据以定案也。余因阅《学思录》与《读书记》,而悟其法如此。”(《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0页)周本淳也谈到过一个故事:“张晓峰先生攻人文地理,当时买书极易,凡遇到有用材料则剪下,床下有两巨箱皆所分类剪下之书,此法在当时不失为科学省时之作。王先生(王瀣,字伯沆)曾与之戏言:《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君则‘为书日损’。张先生一笑而已。”(《如是我闻》,《文教资料》1994年第1期,60页)
写在本子上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便于保存,如果每个笔记本只记录某类材料,则检索起来也不困难。宋人叶廷珪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收集资料的。其《海录碎事》原序云:“始予为儿童时,知嗜书。家本田舍,贫,无书可读。……每闻士大夫家有异书无不借,借无不读,读无不终篇而后止,尝恨无资,不能尽得写,间作数十大册,择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录》;其文多成片段者,为《海录杂事》;其细碎如竹头木屑者,为《海录碎事》……”(《四库全书》本《海录碎事》卷首)《海录碎事》流传下来了,还保存了不少资料。
宋末王应麟撰《玉海》,是一位很博学的人,他主要也是靠本子来积累资料的,元人孔齐《至正直记》称其“每以小册纳袖中入秘府,凡见书籍异闻则笔录之,复藏袖中而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于该书提要中对《玉海》的文献价值作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如杨树达、柳诒徵、汪辟疆等采取记日记的形式积累材料,也可算作将笔记写在本子上。如柳诒徵之孙柳曾符曾谈到:“先祖遗稿有《劬堂日记抄》数十百册,皆平时读书时编摘材料,间加按语,以备著述之用。”(《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1页)汪辟疆介绍道:“余年十四,随侍梁园。时五经甫毕,先府君日督课读《资治通鉴》、《三国志》、《文献通考》、《文选》诸书。日有定程,夜则疏记一日看读所得于日记册。日必三四百字,文事日进,即始于此。”(《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01页)
输入计算机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储存量大,检索方便,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
西安君翰
注意事项1、一定要注明出处
我们写论文要言必有据,注明引文出处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写读书笔记时就应当不厌其烦地详细注明出处。谢伯阳曾经对笔者说,他和他的岳父凌景埏花了数十年时间编成《全清散曲》,起初未注明出处,出版社的同志要求他们一一注明出处,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重查资料来源。我们应当记取这一教训。我们在注明出处时还要做到详细而准确。文献名称、文献作者、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报刊名称、发表时间,乃至页数都要写明,否则复查起来非常困难。
2、来自实践中的信息也可以写入笔记
我们做学问的信息,一部分来自文献,一部分来自社会实践,所以我们既要读有字书,也要读无字书。我们的读书笔记既可摘录文献资料、也应记录来自社会实践中的有用信息。《论语·卫灵公》云:“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御,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可见这种做法,起源很早。后来的各种各样语录,大抵也是学生们将老师的言行记下来汇编而成的。
近人夏承焘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学生蔡义江回忆道:“夏先生手边有一本小笔记本,在谈天中,他时而拿起来写上几句。不论是我转述读过的书,文章中的话,耳闻别人的谈吐,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见, 只要夏先生觉得有点意思的,他都会记下来。老师们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的,不但从来未遇到过,实也闻所未闻。”(《忆夏承焘师》,《文史知识》1992年第8期)李灵年也将听来的有价值信息写成笔记,其《闻学琐录》,文前说明云:“予从事学术研究有年,与众多前辈学者有不少接触,或论学术,或谈逸事,随时恭录,散见于日记之中。自愧不敏,不能窥其堂奥。只是陈迹惟恐湮没,雪泥鸿爪,可飨后来学子,故一鳞一爪,不嫌其琐屑,摘取发表,公诸同好。”(《闻学琐录(一)》,《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今举一则为例:
施孝适先生问我《鬼神传》《巫山艳史》各家目录有无著录,他在整理这两部小说。我仿佛记得查过书目,印象中无记载,于是便顺口说:“无。”后萧相恺同志来,我向他请教这两部书的著录情况。他说,孙目、柳目都有著录,《鬼神传》又名《终须报》,全名《阴阳显报鬼神传》,国内存有几个本子,一曰丹桂堂刊,四卷十八回;一曰丹拄堂刊,四卷十八回;又有二十回者。阿英藏书的一部分现藏芜湖图书馆,有咸丰年间广东省城刊本《鬼神传》,萧曾去查阅,为丹桂堂刊本,究不知二刊本有何区别。丹桂、丹拄二堂在清代均为广州坊刻处。《巫山艳史》一名《意中情》,孙目有录,北大图书馆和日本千叶菊香有藏。由此事可知勤于请教的重要。萧同欧阳健搞了四年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跑遍全国各大图书馆,历尽艰辛,遂成专家里手,对小说版本异常熟悉。(《闻学琐录(二)》,《文教资料》1995年第4、5期)吕叔湘说过“朱(自清)先生身边经常备个小记事本,听到别人说一句话他认为值得注意的,马上记下来,积累多了,自然从中发现好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刘坚《吕叔湘先生学术述略》,《文史知识》1997年第11期)可见听来的信息记下来对选题也是大有帮助的。
3、应当有指引卡或编索引
资料积累多了,不便检索。为此,要给资料卡片做指引卡,要给书本编制索引,用电脑贮存资料,一般都会预先设计好检索途径。所谓指引卡,就是在卡片盒中高于普通卡片的卡片。其高出部分是用来写关键词或类目名称供检索用的。王云五说:“关于利用卡片的方法,凡就所读的书,对其内容某一段落认为足供将来参考者,可以卡片列其标题及所见书籍的页数,再将积累的卡片分类排列,则于应用时一检有关的标题,便可以在已经读过许多书籍的某些页中同时搜集许多有关的资料。”(《漫谈读书》,《谈读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42页)王氏所说的分类排列,其类目就是写在指引卡上的。王氏强调了用卡片来做资料索引,其实也可以用卡片来摘录原材料,或写自己的体会。
4、最好单面写
为了节约纸张,一般人都会在一张卡片或一张纸的两面摘录资料,这会给我们写论文时排比与剪贴资料造成一定的困难,而单面写笔记就会避免这一缺点。
5、一张卡片只抄一条材料
刘乃和称陈垣:“他抄材料都是用大张的稿纸,有时也随时写‘另纸’,即零散纸头上,也就是我们所用的卡片。写在稿纸上的材料,无论字数多少,都是一个问题另起一页,一纸不抄两段材料,将来用起来方便。”(《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141页)
6、要勤笔免思
我们在读书时常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读书读得非常起劲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停下来摘录有关资料。而书读完了,时过境迁,往往又找不到想摘录的资料,或者没有兴趣去摘录有关资料了。刘乃和介绍陈垣的一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他凡是看到有用的资料,马上就写,随手抄录,决不耽搁。在思考问题时,也是偶然想起什么,或有何心得,也即刻写在“另纸”。他经常教导我要随手写,“勤笔免思”,不管是材料或想法,有时稍纵即逝,不及时记下,考虑的问题就会忘掉,翻到的东西,当时未写下,再找时会很久也找不到。(《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141页)郑天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收集史料如捉贼,稍纵即逝,不可放过。”(刘泽华《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436页)最好的办法是随读随记,或者一边读一边写上需抄资料的页码并用铅笔做上记号,待读完了再摘录。胡适云:“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吴淞月刊>发刊词》,《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43页)
7、将引文与自己的话严格区分开来
我们在摘录材料时,往往写上自己的感想,或者为了文从字顺,而加上自己转述的话,如果不用引号,或采用其它方法加以区分,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将难以反映引文的原貌。
8、用什么方法应当先具体分析一下
譬如自己有书就可以将读书笔记写在书上,再做个索引就可以了。需抄的资料又多又零碎,最好用卡片。已经有了书、论文或文稿,就可以将新获得的材料就批在书、论文或文稿上,如果再抄成卡片放在卡片盒里,就很难找到了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