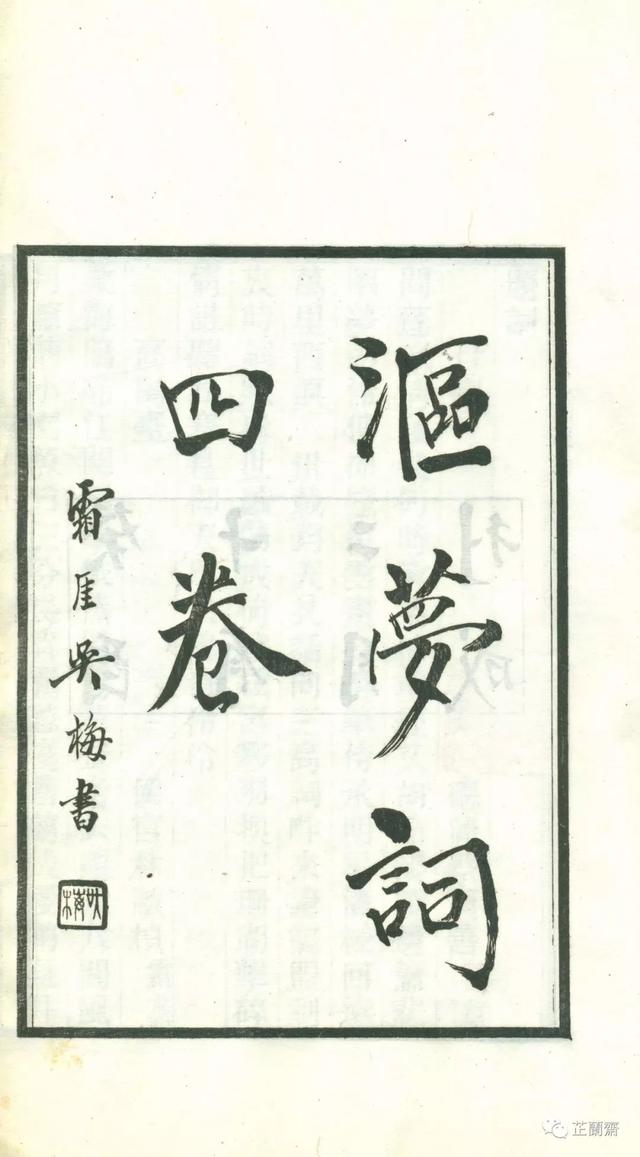王小海的情深似海 王小海晚熟之思念
《义门村的故事》特别说明:从今天开始,将向大家分享文学创作爱好者王小海的作品《晚熟》的全部内容,希望得到大家的喜爱和关注!
思念之前言在我婆病重的时候,宝宝告诉她:海燕要给你写文章,在你下葬的那天,贴满咱家的墙,让大家都知道婆是多爱娃娃。你说好不好?我婆轻轻地说:好。
我写文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纪念我婆,不管我婆离开我们多少年,她的精神和轶事将和文字一样长长久久地留在纸上,不会消失,我也再不会忘记。我写文章的第二个目的,饱含着我的愤怒、不平和冤屈。我婆活地卑微,无权、无势、无钱、甚至无儿,她忍受了多少羞辱和欺负,她像是需要讨好所有人。她的勤劳、善良、忍让、和蔼等等,所有的品质,都让我想冲老天质问:凭什么?我婆就必须做一个任劳任怨的好人才能活?我要为我婆讨回公道!我要给她著书立传,让她比乡长、县长都风光,让她像名人和伟人一样永垂不朽。我写文章的第三个目的是记录我的成长过程。容纳我的村子和生活在我身边的乡邻,是我成长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既宽松又天然。我婆润物细无声的爱护和教养,是我成长的小环境,我感激大环境和小环境,让我自由自在地长成一个健康、有益于家庭和社会的人。
我的文章看起来零零碎碎,仅仅是我将脑海深处的记忆都原原本本复制下来,因为这就是我经历的真实的生活,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婆,一个平凡的农村娃,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从中读出长辈对孩子深重的亲情、孩子对家庭真挚的爱和依赖、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孩子天真却敏感的心理活动。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懂得珍惜家庭、体恤老人、爱护孩子,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用心的。
思念我婆不到80岁,直到去年脑梗住院后,才不再干活。她的身体迅速恶化,现在躺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也含糊不清。眼看着我婆如风中残烛,余日不多,我专门请假回家几天伺候我婆,以免日后我只有无穷无尽的伤心。王二的假期比我还长,我走后她一直给我发信息。一天她给我信息,我婆给她说,你快没婆了。我突然泪如泉涌。无论何时何地,我只要想起我快没有婆了,我就忍不住大哭。有谁能知道我对我婆的依赖呢?
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我婆吃、睡、走亲、串门、干活......回到家,我首先是叫我婆。如果她不在,我就要挨家挨户找她,直到看到我婆,才觉得踏实。我婆给别人说,她不去亲戚家住,要不然娃回来看不见她,恓惶的。
我曾经是个有婆伺候的娃。有婆,再冷的冬天我都是睡热炕,还从不要烧炕;有婆,每天起来,厨房的锅里总是冒着热气,灶膛里总有暖和的火苗,从来不知道冰锅冷灶的凄凉;有婆真好,我婆用有限的条件想办法给我们做好吃的;我婆干净、整齐、有无穷的精力,是我的依赖------现在,我给躺在病床上的婆按摩,她的胳膊细地我手都抓不满,我想着以前她的胳膊比我的粗;我给她揉肚子,她的前胸肚子只有一层皮了,我想着她以前肚子的肉还往下垂,我总捏她肚子上的肉;我帮她换衣服,拉衣服时她人都跟着动,我在想那个曾经给我帮忙脱棉裤、套裤罩子的婆;我握着我婆瘦的如一把柴火的身体,心里知道我再也靠不上我婆了!我曾经认真祈求过老天,把我的寿命给婆续上,我不想没有她了后还活很长很长。有一个爱干活爱娃娃的婆,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娃,那就是我今生最幸福的时候,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我婆吃、睡、走亲、串门、干活......回到家,我首先是叫我婆。如果她不在,我就要挨家挨户找她,直到看到我婆,才觉得是回到家。我婆给别人说,她不去亲戚家住,要不然娃回来看不见她恓惶的。
1.跟着我婆走亲戚无论我婆去哪个亲戚家我都要跟,我最喜欢跟着去梁家洼(指澄城县寺前镇人和村,也叫梁家洼,地势低洼,大多人姓和、梁,我婆的娘家)二老舅家。二老舅是村干部,有办公桌,我能玩红印泥,有时候偷偷挖点带回去。办公桌的台历,每一页上都有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日常生活的好点子、全世界全国各地的景点、笑话------有一页日历上是做面酱的方法,老妗子还让我给她念。办公桌上的黑色的拨码电话,特别诱惑我。提起来能听见听里面的滴滴声,我忍不住总想乱拨一拨,又害怕打通了。民民叔和芳芳姑有很多书我都能拿走,有一本是唐诗宋词的注释,还插着简笔画,真是诗情画意。我爱不释手,整天拿着读,也照着画描。老舅还给我一本后史记,是他的一个朋友编写的。我读这本书已经到了高三了,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段,给枯燥的高三带去了些许调剂。
我婆去老舅家,一般都是先去老姨妈家约上老姨妈,两人一起回妈家。有一天,我知道我婆要去梁家洼,我就操着心,我婆不想让我跟也操着心。我等来等去,突然意识到我婆已经背过我偷偷走了。我判断不出她已经在路上了还是在老姨妈家,就在洼底的路口等着。不管她在走一队的西辽坡还是走三队的洞子坡,都会经过这里。她们俩居然真的被我等到了!老姨妈很不满我不听话非要跟大人,她说我婆,她的那些孙子就没有人敢不听话跟着她。我婆好像是让老姨妈说的伤脸的,或许是没有摆脱我失望的,她一路都不理我。我的脸皮厚,她们都不理我,我还是跟在她们后面。小时候觉得我婆走的真快,我一路小跑才跟得上。
每年阴历初二,我们都要去梁家洼老外家拜年。同学都不再去老外家,我们家却还和老老外家(我爷爷的外婆家)来往,我觉得特别骄傲。我们家过年,总是很热闹,要去两个老外家拜年,要去东头婆家拜年,还要招待老姑、姑、一些不认识的老亲戚给我家拜年。用我的话说,吃完别人家,就该别人来吃我家。在梁家洼拜年总是从二老舅家和三老舅家来回跑,因为两家离得很近。有一回我从三老舅家向二老舅家走地好好的,有个人突然喝住我问:这娃,你爸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想过,愣神想了一会。后来我听说三老舅是从小就送给了东头的,因为我婆一提起她兄弟给人了,就心疼地哭。我劝说:大老舅没有给人,可是离得更远,几年见不上一次。别家兄弟两个结婚后都是要分家过的,即使三老舅不给人,也要重新划院子盖房子分家啊,可能离得比这还远。我婆说她知道,可是想起来还是难过。
我婆总是惦记她兄弟。西瓜熟了,就要我跟着她拉着架子车给我老舅送瓜。去梁家洼的路被拖拉机碾的坑坑洼洼,特别难走。我驾辕拉车,我婆跟着帮忙推。我喜欢去老舅家,也因为老妗子做的饭好吃,还会做面酱、西瓜酱和腌青辣子,我们从梁家洼回来都能带些。我婆也跟着老妗子学着晒面酱和西瓜酱,可没有老妗子做的好吃。
老姨妈好像是1990年去世了。她病了后住在她大女儿家。我婆带我去看她,她的头上有一个很大的洞,一直都在渗水。我听他们说,女怕戴帽男怕穿靴,意思可能是女人头上有病的话,肯定是活不成了。1991年我婆的妈病了,我跟我婆去看她。姥姥已经80多岁了,大家给她喂点人参水活命,因为等着我北京大老舅。二老舅家的民民叔,喜欢和他几个姑坐炕上守着他婆。韩家洼老姨打发民民叔去灶房看面起来没有,民民叔也不想去,说不要看,丢不了。惹得大家都笑了,我觉得民民叔还幽默的。
韩家洼老姨家一有事,我婆就提前去了,家里没有了婆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要是不用上学我也跟我婆去老姨家住下。永青叔结婚后第二天,我婆没有回去,我也不回去。原来结婚第二天是还要吃饺子。提起老姨家,就记得吃席,似乎老姨家席特别多,老姨的公婆去世是两顿席,过三周年又是两顿,这就四次席了。老姨家还有三个叔,每个叔结婚这又是三次席,三个叔生三个娃,看娃席又是三次。老姨家席超级多,把人吃糊涂了。有次在老姨家吃埋人席回来,村里人问我,你老姨的公公去世了还是婆婆去世了?我竟然不知道是老头去世还是老太太去世。
我婆不爱去她几个娃家停(停的意思是多住几日),尤其是她不去大荔我彩姑那(彩姑是我妈妈的妹妹,王彩莲,在大荔县城居住很多年,现定居西安),理由让我觉得特可笑。她嫌单元房小,说她在厕所唰唰尿,我姑父坐在客厅都能听见,她觉得难为情。她不去我新姑家停,因为近在一块,不需要停,再是她觉得停在我新姑家愧疚,又没有管过我新姑(新姑,我妈妈的妹妹王新莲,小时候送给我外爷的大哥,我婆照顾我新姑的时间不长,就在一个村里,很近)。等她病得时候,必须有人跟着她时,在雷家姑妈家住几天。(雷家姑妈,是我妈妈的姐姐,我婆的大女儿,嫁到雷家,大荔县高明镇王彦雷村,和我村王彦王是邻村)姑妈说,我婆每天都是混混沉沉睡觉,天天等学生放假。龙龙(我弟弟)放假回来去雷家接她回家,我婆来了精神,自己开始收拾行李,秋裤没有干,我姑妈说再等等,可我婆一分钟都不等了,装上湿秋裤要马上走。
2.最远的亲戚我婆走的最远的,就是北京大老舅家(大老舅是我婆的弟弟,和麦胜,年轻时候很爱学习很有出息,一生致力于中国航天事业,现居北京度晚年)。1999年我考上大学,要在北京转车。记得离家那天,9月2号,南党姑妈(我爸爸的大姐,嫁到澄城县寺前镇南党村)还有婶婶他们都来我家了,我爸爸买了肉招待大家在家吃饭。吃完饭后,对门荣荣哥找车送我们去韩城坐火车。我坐在车里扭头看家门,家人都站在门口看着车,我心里居然有点酸。离开农村,这一天我已经苦等了很久很久,考上大学对我们农村娃不是锦上添花的荣耀,而是唯一的活路,不值得欣喜若狂也就不值得依依不舍。到了韩城有民民伯(我妈妈的堂兄王新民,时任韩城市副市长,2000年任期内突发急病离世)接我们,我们先去伯住的地方——政府分配的单元房。然后去饭店吃饭,我娘(民民伯的妻子)从家带饮料,有一盘菜是长豆角,全切成大约十厘米(一乍)长,整整齐齐放在盘子里。把我婆看得稀罕,说咱每天都吃长豆角,可就知道切成短的。我伯开玩笑说,切成长的放整齐就要X块钱了。杨若琳(民民伯的外孙女)才几岁,却大方,懂礼貌,长的甜美,特别招人喜欢,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小孩。伯的秘书,他先帮我们买好了两张卧铺,又去帮我买硬座票。他走了后,我伯说。这个娃文章写的好,西北大学毕业的。
去北京的火车是绿皮车,我婆和我爸爸坐的卧铺,我坐的硬座。上车后我一直在我婆的卧铺车厢,对面的人吃煮黄豆角,还让我们吃。我婆觉得真稀罕,咱种了多少年多少亩黄豆,都没有煮过绿豆角吃。到熄灯,列车员让我去硬座车厢。我婆说:娃在这照顾她。列车员说有事就找她,按规定我不能呆着卧铺车厢。火车在北京西站停下,我看见大老舅夹个小包,在窗户外面张望,他来接我们。老舅认识车站的领导,所以我们没有走旅客通道,而是走的员工通道。老舅的司机,也帮我们搬行李。出站的时候,要上很长的台阶,我爸爸搬着我换弟姑(我妈妈的小妹,王焕弟)给我的大箱子---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不知道他生过病能不能搬这么重的箱子,但我没有吭声。
老舅专门叫了车,陪着我们逛北京,其实北京老舅也很多年没有逛过北京。出去逛的时候,老妗子灌了凉白开带着。她说她穿的衣服和凉鞋还有老舅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我们坐在车里走过长安街,看天安门。我婆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很想去毛主席纪念堂。那几天,刚好碰上毛主席纪念堂修缮,没有能去看毛主席。我们逛故宫,故宫门票才30。我们一行人,老弱病残的,都没有那么好的体力,只沿着故宫的中心线上走。很多宫门都是锁着,我和我婆就隔着门上的缝隙,看看皇上用过的东西。老舅带我们吃北京烤鸭,吃饭的时候,给我爸爸、我婆和我各要了酱油颜色的饮料,好像是野梨汁,真好喝,酸甜的,还是凉的。我很快喝光我那瓶,我爸爸喝啤酒,我又喝了他的一瓶。我婆说太凉,她拿瓶又给我喝。我喝了一瓶又一瓶,其实我心里知道不能再喝了,再喝就成二球了。但是太好喝了,我知道我很丢脸可是就是控制不住,从来没有喝过任何饮料的人啊。
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婆坐在和燕姑(大老舅的女儿,和燕)的房子里,一个人在悄悄流泪。我问她怎么了,看我老舅过的这么好,怎么还哭啊。我婆说她看见她兄弟过的这么好,就放心了。
3.我婆的娃放学回家,我进门首先叫婆。如果她不在家里,我就挨家挨户一直找她,直到看到我婆。我、我婆和换弟姑,一起睡觉,一直到我五年级时候我姑结婚。我睡觉的时候要和我婆搂着,还要把腿搭在她身上。我姑一直有意见,嫌我那么大了还要和我婆搂着。我现在睡觉只有蒙着头缩成一团才能睡着。那是小时候有时候我婆去了我老外家或者别的亲戚家晚上不回来,我一个人睡觉,特别害怕,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哪怕是大热天,捂的我大汗淋漓气喘嘘嘘也不敢出来。
有了我婆和我爷,我小时候过的非常无忧无虑。他们总是满足我那些小要求。当然,聪明的我从来就没有提过过分的要求。夏天上学要灌水,我婆就把开水凉好,给我装瓶子里。有时候还是面汤。我爷还喜欢过问我的学习,考完试,他都爱问我考得咋样,我都骄傲地说,差不多。如果我爷活到看见我考上大学,该多欣慰。
晚上睡觉前,我们坐在炕上教我婆认字,用窗门当作黑板。我婆爱学习,却是文盲。她小时候,家对门就是学堂,她抱着娃只有听学生念书的份。她经常用古老的歌谣鼓励我们读书,可惜我记不清了,似乎有一句是:学文化学下文化本事大。我婆给我们讲扫盲趣事,我们都笑得不行。晚上开会学习的时候,有的妇女就坐在墙角纳鞋底,孟娘一开会就睡觉。农民没有文化,根本不理解念的是啥。老师念: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大家问,毛主席来了还停两天?在哪儿停两天?老师念:避战避荒为人民。大家跟着念:闭门闭窗怕来人。我婆虽然不认识几个字,对学习却还是很有见解。很多娃学不动,家长就说:我娃灵是灵,就是不知道学习。我婆认为:你娃灵咋就笨地不知道学习?对于认字,她认为不认识字是看的少,就和认人一样,你天天见的人,自然就认识了。我婆认为懒人就是笨人,因为笨的不知道干活。又想起我爷,我们小时候,我爷也是看见字就带着我们念。比如纸箱子的字:二级酱油 茉莉花茶。年画上的字:舞龙灯 踩高跷 划旱船。
有时候坐在炕上我婆给我们讲鬼怪的事,吓的我们挤在一起,都不敢去方便。我觉得很奇怪,我婆一点都不害怕。有时,她给我们讲她小时候的事。大老舅小时候就爱读书,寺前镇办了初中,大老舅要念中学,说学校都开了家门口了不让人念书。婆给我讲了很多有作为的亲戚从小都是自觉地要求念书,用功念书。民伯17岁已经是民办老师了。公叔为了考学,几个月点了十多斤煤油,每天早晨起来他的鼻孔让煤油灯熏的黑乎乎。我和我妹都爱学习,也许和我婆的思想倾向有关系。她还给我们唱她小时候的曲子,都特别有趣: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文明?------我们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哎嗨哎嗨呦就是那毛泽东---张妈妈来说媒,我和她反了对----轻了就骂重了就打,你说那当媳妇的可怜不可怜?----
记忆中,冬天总是特别冷。每天放学,我婆先给我端一盆热水洗脸,然后让我上热炕,我坐在热炕上后,再给我一碗粘稠的小米饭暖手。那时候,饭桌就搭在炕上,和我爷一起吃饭。我经常和王二比赛吃“净碗”——小米饭很稠,等稍凉凝固后,就能整块在碗里滑,我总是能做到吃完米饭后碗像洗的一样干净。王二从来比不过我。
冬天上学很早,天还没有亮就要起床。我婆还得跟着我们早早起来梳头。我们都羡慕别人的长头发,也要留头发,可是我两还不会梳头,所以再冷我婆也得起来。王二说,她自己扎的头发半天就松了,我婆给她扎的一整天都是紧的。
小学时候每次考试,我婆都要给我们烙馍吃,我考完一门,王二就给我送来坨坨馍。她考试的时候,我又给她送。其实现在想来小学考试时间很短,没有必要准备吃的,更不用送好几个,小女孩根本吃不完。
我婆还给我们炸麻花,准备做之前还要秤面和油的重量——惭愧我硕士学历还不认识杆秤。她总是琢磨着怎么既能省钱又上我们吃好。我幼儿园前还很老成地说:这贼老婆做的饭,没有一点油星星。孩子们总是嫌油少,我婆总是说,看你爸爸干得来呀。我婆平时精打细算过日子,等到来客人或者管老师饭时候才做丰盛的饭菜。六年级管张玉田老师的饭,我吃上了菜盒子,我婆做的,特别好吃,可惜和老师吃,特拘束,影响食欲。平时家里来客人,就会有好饭菜,小时候贪吃不知道伤脸,总要上吃饭桌子和客人吃,但是总是被喝止住,让我蹲灶房吃剩下的。
小时候特别喜欢煮整个鸡蛋。每年只有一次啊。清明的那天,我婆擀细面,煮熟用凉水过一遍,拌上熟油,做成凉面,装碗,碗底卧个鸡蛋。这就是上坟面。我爷带着我们几个去上坟,给我爷爷的父母(我的男女姥姥)烧纸,还要给我爷爷的哥(我大爷)烧纸。上坟后,拔一把麦苗,挂在大门上。清明的凉面似乎更好吃,尤其是那个鸡蛋,我等了大半天了,就是为了把它从碗底找出来,装到学校,一点一点吃完。
上初中以后,基本都是我婆给我做菜,在宿舍吃饭,别的同学都是说她妈给她做啥,我都是说我婆给我做啥,初二时候,一个女生给我说,初一时她以为我没有妈。后来,星期三送的菜总是很少不够吃,我给我婆提意见,可她却说,她切不出来了,嫌少让你妈切。
初三夏天,我补课,王二来给我送饭。新蒸的馍,还有一瓶芥末。我婆做芥末的方法是,把芥末颗粒磨碎,再用火烤熟(我不清楚怎么弄熟的)倒上醋、油、盐等,蘸馍吃,特别的过瘾!那瓶芥末我放在桌子上,结果瓶子滚掉地上,碎了 ,我一口也没有吃上。心疼的牙根都难受啊。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初三每个周末只有半天时间回家,就那一会儿时间,还要装馍装菜,洗头洗脚,还有做作业。就没有时间洗衣服,也不怎么会洗衣服。我婆看我时间紧张,总是让我扔下,她来洗。
初三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晚上回家,第二天早晨再去学校。那天早上,天还很黑,风特别大,带着哨子一样。我心里非常害怕,但还是得上学。我推着自行车寸步难行,走出大门一百米的时候,似乎听见谁在遥远的地方喊我。是我婆,我忘了带啥了,她就追到门口喊我。她看不见我,但她知道我还没有走远。由于是逆风,她喊我很多声我都没有听见。那一刻,我心里特别感动。还有谁会黑天里顶着大风追着我喊着我呢?
4.跟我婆干活我婆一天到黑都在忙,早晨我还在睡觉,她已经在院里刷刷刷扫开了,要是冬天她就是爬地上烧炕。等我睡起来,我婆饭都做一半了,柴堆在灶火口、火烧的很旺、锅里的饭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电壶是满的。吃完饭,我婆又洗碗洗锅,看水还清,她还得把锅盖、锅台、案、篦子等都洗洗。洗完又给中午饭做准备。等她出了灶房,就快做中午饭了。一天里有半天她都在灶房,把灶房的活干完了,她才坐到大门口,手也不停,剥豆子、剥花、拆旧衣服------她经常说:屋里这活多得能把人绊死,你咋就眼里看不着?晚上睡觉,她要么弄豆芽罐要么弄酵面盆。我看不见活可我话多,总是嘴不停地说话,她说我像话山倒了。
我婆带着我们挖野菜,教我认识了很多野菜。洋槐花开的时候,她带着我去折槐花。去韩家洼的路上,有很多野生的槐花,都是很矮的树,不像村子里的槐树那么高,够不着。我们用钩子折了很多。槐花生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婆一般都是拌上面粉做蒸菜。我又想起我爷了-------有时候,是我爷带我们去钩槐花。
我婆看我回来,就说咱包煮饺吃。我说吃面。她问,你还不爱吃煮饺?我说:包煮饺你又叫我帮忙,擀面你一个人就做了。她带点笑带点惊讶看着我,好奇我咋这么怕干活。听大人说,我不记事时候爱做饭,嘴里还说:我爷擀“鞋底”,我捻“捻捻”。我婆做“捻捻”就让我帮忙,她会两个拇指一起动,我爷也是,我左手动就会忘了右手。我婆打底子右手拉风箱左手添碳,很快火就大了,我搭碳时不会拉风箱,所以底子不是火不旺就是干脆灭了。我提起打底子就怕,软塌塌的麦秆,要把湿漉漉的碳块烧着,太难了。不知道谁还唱了个口诀:歪女子,打底子,打不着,叫王哥,王哥来了才打着。打底子还没有蒸馍难,因为蒸馍要提前做酵子。经常看我婆在太阳下晒酵子——黄黄的玉米面粉和核桃大的面疙瘩,摊开在吃饭桌上,还总有一双让面粘一起的筷子,用来搅酵子。每次蒸馍后还要留一块面放在面粉瓮里作为酵面。和蒸馍面的时候,我婆就在面粉里加上这些酵子酵面,撩一点水,再用拳头按按,和上大半盆面。要等面起了才能蒸馍,冬天面不好起,我婆就叫我把面盆抬到热炕上。面要是起过头了,蒸出的馍就发酸,所以要留心面。我婆蒸馍我给她揉面,一大盆面,我婆搬到案上,切成一块一块,我出点蛮力揉个头遍。我婆把我揉过的面再揉揉、搓条、剁馍、丸馍。等馍搭锅里,我婆就让我出去,怕我热。她坐在灶火前,火烧的很旺,伸出的火舌舔着灶火口,把她留着汗水的脸照成金红色。等气圆我婆做菜,我就帮忙剥蒜、踏蒜、择菜。我爷说剥蒜要剥净,吃了蒜皮腿就会像他的腿,走路跛。我最爱吃我婆烙的馍,小的圆的厚的是“坨坨”馍,大的圆的薄的是“学学”馍,吃时候切成一角一角。烫面油饼,吃着不筋,我不太爱吃。包煮饺包包子时候我婆都给我们教怎样包,王二还学会一点,我就不想学,只擀皮。包煮饺能包成两种样子,一种圆圆的疙瘩,那是肉饺子,一种扁扁的像耳朵,那是菜饺子。我婆包“疙瘩”时候包的特别快,似乎就在手里一挤就好了。包 “耳朵”还简单些,把面片一圈捏一起,留个小口,在手掌中将饺子里的气从小口挤出,再将小口捏一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婆包的饺子吃起来馅多还瓷实,硬硬的一块,我包的又软又薄,就像个耳朵,吃的时候就能看出这个是谁包的。包圆包子是把面皮一圈的边收成包子摺,留下个小口吃的时候灌辣子蒜水。包长包子和“耳朵”饺子的方法差不多,但是要捏出摺子而且不用留放气的口。我婆包的包子摺都是整齐好看的,我喜欢挑好看的馍吃,不吃歪歪扭扭的。有一回我们说我婆做的馅味道太淡,不香。我婆就说她舍不得放那么多油,她看我琴凤娘和馅倒了一大勺子油,难怪琴凤做得包子好吃。有时候蒸馍剩点面我婆还参点盐,搓成小棒棒,在灶火上给我烧熟,那就是烧馍。这些麻烦的饭其实平时很少吃,因为做起来费事,再是吃得多,一顿吃了好几顿的粮食,我婆舍不得。吃馍吃厌烦了,我婆给我们蒸篦底子、烙油饼、摊椒叶煎馍、做嚷皮子、包茄子煮饺、南瓜包子、辣子油花、凉面------我再也没有婆给我做好饭了。
端午节时候要给嫁出去的女子送“端午”,其实就是送粽子。快到端午了,我婆带上我去梁家洼摘芦苇叶子。梁家洼村头有一片洼下去的芦苇塘,我婆挑些宽宽大大的叶子,回家了洗干净,准备包粽子。有一年双喜叔家的婆帮我婆在院子里包粽子,她们旁边洗干净的一碗红枣,吸引着我。我婆给老姑家送粽子,老舅又给我婆送粽子。后来人图省事送端午就买一包晋糕,现在卖晋糕的不用黄色的芦苇叶子,而是白色一次性塑料饭盒。小学放学回家,惊喜地看见柜盖上一包黄叶子包的晋糕,这样的幸福再也不会来了。
放忙假的时候跟着我婆和巷里的老婆拾麦,因为学校总是以勤工俭学的名义收麦,我得交麦啊。我提着篮子,我婆提大点的竹笼,去上北坡、西洼里拾麦。我婆一会功夫手里就整整齐齐握一小捆麦杆,然后分出一小撮麦秆把所有麦秆缠紧,摆在笼里——这让我想起鲜花店包装好的一束鲜花。我也许是手小,也许是没有耐心,手里才很细一把就让我婆给我缠住,她就把她手上的与我的合成一把缠成一捆,放我篮子里。我蹲在地里,慢腾腾往前挪,离地头还远着哩,太阳还高着哩,离天黑还早着哩。我婆说,你弯下腰,拾得快。我说腰疼。她说碎娃没有腰。我就说碎娃没腰那弯啥?有时候拾麦不要杆,带上剪刀,只把麦穗剪到笼里。拾麦最不敢看见邻家地里没有收割的麦,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麦穗,让人有一种冲动,那就是跳进去,咔嚓咔嚓一分钟就能剪一笼,省的我在空地里满来回寻不到麦。拾来的麦不和自家的麦搅,都是在院子里,我爷我婆用棍打出来。这些麦用来交学校,拾的多了还能换桃。收假给学校交麦的时候,我婆按学校要求的分量,称好。可我总是嫌少,和她抢着布袋,要多装些。她气地说她称过,只多不少。还说我拾麦不好好拾,交麦总要多交。
我喜欢和我婆打背子。光是寻烂布,就让我很兴奋。因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翻箱倒柜,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搜寻一遍,掌握住哪儿都藏着啥宝贝。爬上我婆的炕,踏上枕头,拉开箱子门,把箱子里的袱子挨个打开看一遍。有一个袱子里是我的新衣服,只有走亲家才能穿,我先看看。有个灰蓝色的布烟袋,里面是我婆收集的各种纽子。箱子口还有我婆给我剪的衫子,到底也没有缝成。那是我给她抱怨我没有好看的衣服,她就找了一块粉红的新布,照着我合适的一件衣服剪了。 翻了我婆的箱子,还得翻我爷的柜——我总觉得箱子是我婆的,柜是我爷的。柜很深,我爬在柜边,头伸进柜里,柜的袱子里有我换弟姑的新衣服,柜里的抽屉有我爷一点雄黄、黄连、胡刀片,有我婆染布用的颜料小纸包——印着一个女人抱一个白色的羊娃,还有很多小零碎。箱子和柜里的东西,我只能是翻一翻,不能拿,罗柜的东西我要看上了就能拿。罗柜里主要是不经常穿的衣服,旧棉袄、烂绒衣、别人淘汰的衣服等,全是破烂。我拉出来一件旧衣服,我婆就舍不得拆,总说这好好的还能穿,只要衣服不烂个洞她就说是好好的能穿。我婆把旧裤子旧袄烂单子拆了、剪去锁边、洗干净、拉平,熬一盆子面汤,桌子凳子在院里摆好,就开始打背子。她刷一层面汤,铺一层布,布都是破布,总是这里长一块那里短一角,我们几个娃娃围在一圈,积极地给婆找大小形状合适的碎布片补空。背子一般是十层布或者八层布,十层做鞋底,八层做鞋面。背子层数够了就整个揭起来,粘墙上晒干。院子的砖墙上都是绿绿红红的背子,一个挨着一个。我婆一边找碎布片,一边说打背子要棉布和粗布,渗上面汤能粘住。料子布光溜溜的,不粘。
我婆身体好的时候,有空就织布,做洗碗布、单子、门帘甚至衣服。她常常取一块新洗碗布包上豆子给亲戚拿,尤其喜欢给城市的亲戚拿手工洗碗布,就好像城市人没有洗碗布一样。我婆炕上铺着蓝色细条纹的单子,老婆都把这个花型叫“狼尾巴”。咋这样叫呀,我看着不像尾巴?我婆的门帘都是织的粗布,我喜欢站在门帘下,拉门帘,或者用门帘把自己包住。柜里放着我一个粗布红格子衬衫,不知道为啥,基本上没有让我穿过。织布的第一步应该是纺花。冬天我婆把纺花车子搭在炕上的窗户底下,她盘腿坐下,右手摇纺车,左手拿棉花,只听见轮子转起来唔-唔-唔的风声,她左手的棉花就抽出细线,一圈一圈缠在轮上了。我有时候在她身后睡觉,有时候趴在炕墙上写字,有时候就很好奇盯着她手里的棉花,看看为啥棉花能和吐丝一样不停地抽出线,有时候还用手挡正转的轮子,轮子就会突然停下来。有时候我婆给我说的她小时候的“花花”,“花花”就是歌谣。有一首“花花”我还记得:说花花,套车车,对门子死了他干妈,有心白哭,够不得哭,有心黑了哭,蝎子蛰了眉棱骨。纺花车上的线咋样变成织布的线?肯定要从纺花车子上取下来吧,还要做成一个宝塔样的线穗子,还要拐线,拐线好像是用一根筷子上穿个核,把线一层一层缠在核上,缠成两头尖中间粗的梭子型,这就是织布时候梭子里的线。我记得我婆织布的时候,要把线梭子的一头用嘴含住,一头泡在水碗里,然后吸水。为啥不直接泡水里啊?织布要织出彩色的条纹或者格格,就要在织布前染线,我婆的做法是在做饭的大锅里用颜料煮线,她的手好几天都是蓝色的。我在四队勾娘家见过他们家的单子还有黄色的条条,我婆只染成枣红色和深蓝色,为啥就不能染成黄色?织布机子搭在文娘家,我就跟着我婆到文娘家,听他们一边说话,看我婆左手麻利地把梭子扔到右边,脚下配合着蹬一下,右手又扔左边,再蹬一下。据我观察,梭子走一次,布就长了一根线的宽度。也就是说,我婆织的几丈布,是她一根线挨着一根线摆出来的。晌午我婆织布困了,就会睡在文娘家。文娘家没有碎娃,安静,也干净,她小房子里炕对面还有一个窄床,有时候我跟着我婆也睡午觉。文娘去世了不去文娘家了,织布机子搭在孟娘家大门口。我婆去孟娘家,我自然就跟到孟娘家,只要满伯不出来我就半躺在满伯的躺椅上。满伯一边咳嗽一边抽烟,黑瘦的就像他手里的卷烟,满伯爱问我话,他用河南口音叫我“盐烟”。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上高中了,村里流行用毛线织单子。王红婶婶她妈还给我东头婆织了个窄的,铺在炕沿上。我婆也给我家织过,不过,我婆没有钱买新毛线,都是用我们不穿的旧毛衣烂毛裤拆下来的线,颜色搭配不能赶人的心来,线子粗细长短也都是凑合,所以我婆织的布条纹宽窄不统一,也不平整。再后来,村里流行用买来的彩色细线织布,织布的人不再是老婆们了,而是手巧的年轻媳妇。这种线织的布和买的布一样,要啥颜色就有啥颜色,很好看,还比买来的布厚实一些。我婆没有织过这种布,她老了,织布机上她坐不了。
农村嫁女要做花馍——蒸个超级大的馍,直径大约一尺。先做个大花卷作为馍的芯,蒸熟后,切去周围多余的,再包一层面,接着蒸。蒸熟后的夹心大馍和一般的馍一样,又白又大又光滑。用彩色的面做各种各样的花样,扎在牙签上,然后把这些小花都插在馍上,大馍扎满了花,就像唱戏的凤冠一样。其实我觉得这和生日蛋糕一样,先烤个大蛋糕,蛋糕周围涂上一层白奶油,然后再在白奶油上用彩色的奶油裱花。我婆是做花馍的高手,掌握这个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不管谁家蒸花馍都要请我婆,我特热衷于跟上婆去左邻右舍蒸花馍,因为大花卷切下来的边角料很好吃。有时候我还能混上炕,和老婆们一起揉面捏花子,我就喜欢做这个手工。可是大人们都很烦小孩子,比如我婆不管去谁家,都是偷偷的,让我跟不成。我就在脑子里把家家户户过一边,谁家要过事了?然后去要过事的人家去找我婆。曾经我婆给双喜家蒸花馍,还真让我找到了。等过完事,主家拿上几个大花炸果谢我婆。有一回我带着理明把炸果偷吃完了,婆掐我的大腿。第二天,我的大腿上有个紫色的印,两个指头掐的圆片,像个小鸡。我不知道怎么来的,觉得稀罕,叫我婆看:我腿上有个鸡娃。
我婆经常去文娘家和文娘一起糊花圈,所以我就喜欢去文娘家。只要回家我婆不在,我就先去文娘家。她家的大门没有固定好,我每次经过都怕大门塌下来。文娘和我婆都爱糊花圈,我也喜欢颜色,喜欢那些不同质感的纸,皱纹纸、油光纸、普通的白纸、彩色纸。我喜欢看皱纹纸扎成花子,白纸剪出锯齿再用线扎成花子。但是她们都不喜欢我加热闹,觉得我是捣乱。我其实只是坐在旁边给她们帮忙,或者剪她们不要的碎纸。有一回文娘笑着给我婆说:三婶,你借了我两毛钱是不是忘了?我和小燕嘟囔说文娘真小气,才两毛还要。我婆笑,说借了钱人家要有啥啊。
我和我婆去磨面,我拉着架子车,我婆跟后面。那时候磨面人还得在机器的出口用桶接着粗面粉,倒进机器再次细磨。我不明白,就这样接啊倒啊,最后却分出黑面和白面。黑面含麸皮多,就是现在珍贵的粗粮,白面是精粉,蒸的馒头白、筋、香,只有在过年或者走亲才能吃上。我爷和我婆教给我的歌谣:打箩箩,胃面面,胃下麸子喂骡马,胃下黑面哄娃娃,胃下白面献爷爷。磨面是按照麦子的重量收费,我记得一百斤麦子收几块钱的加工费。算账的事,我婆管。我虽然学习非常好,但就是不会算账。有一次拉着磨好的面回去,走到大队门口那个十字路口,我终于算清账了,给我婆说,少给咱几毛钱,我婆当时就问我为啥不早说,哎,早我还没有算出来呢。她要返回去要钱,我不让她返回去,因为感觉几毛钱很少,不值得回去,再就是我对我的计算结果没有信心。

王小海 陕西大荔人,大学毕业,现供职于郑州市某单位。热爱文学创作。
王小海自述:
我热衷“演说”(这似乎是个讨人厌的毛病),经常神采飞扬地讲述有趣的笑话,慷慨激昂地点评时事,却总是敏感地想是不是听者无心感受?于是我决定闭嘴,把我想说的都写下来。摸着键盘,我却犹豫写还是不写?我是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写自己的简单经历和单调的感受不怕被人嘲笑?我是如此碌碌无为,有记录与阅读的价值吗?然而,我的“小宇宙”总是要爆发的,那就写给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孩子们看,献给走过我记忆的每一个好人。
文章来源:作者
原文作者:王小海
整理编辑:义门村的故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