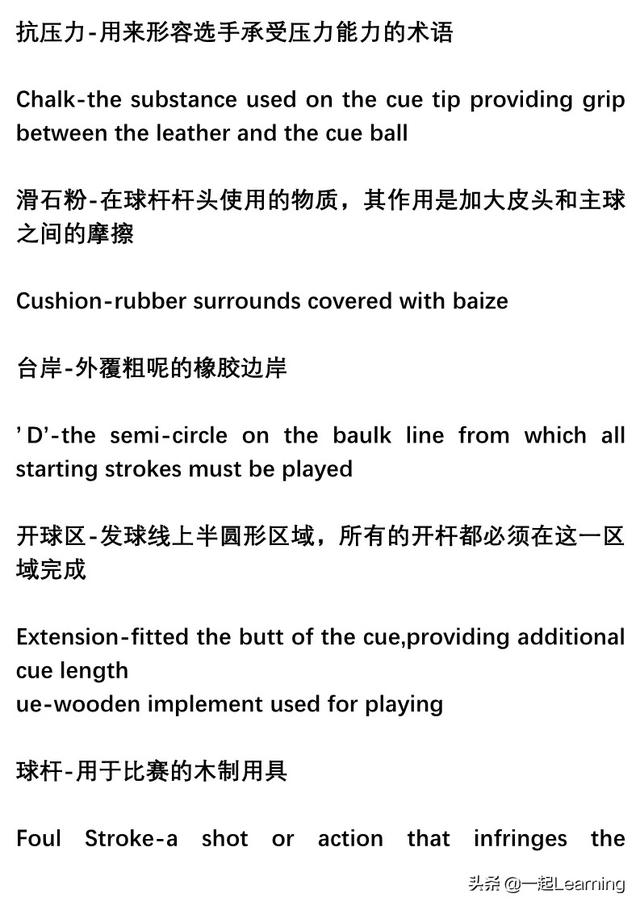抗磷脂综合征属于哪科疾病(抗磷脂综合征诊疗规范)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以反复血管性血栓事件、复发性自然流产、血小板减少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有抗磷脂抗体谱(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s)持续中、高滴度阳性的自身免疫病。通常分为原发性APS和继发性APS,后者多继发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干燥综合征等结缔组织病。APS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全身各个系统均可受累,最突出的表现为血管性血栓形成。APS病因未明,病理特点为非炎性、节段性、阻塞性血管病变。
实际上APS并不少见,有研究显示,年龄小于45岁的不明原因卒中患者中25%的患者aPLs阳性,反复静脉血栓事件患者中14%的患者aPLs阳性,反复妊娠丢失的女性患者中15%~20%的患者aPLs阳性。由于临床医师对该类疾病认识不足,APS的平均延误诊断时间约为2.9年。APS通常女性多见,女∶男为9∶1,好发于中青年,原发性APS与继发于结缔组织病的APS在发病年龄、临床特点等方面无显著差异。
在既往十余年里,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对APS的认识和诊治理念已发生显著改变。现结合临床中的常见问题,借鉴国内外诊治经验和指南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范,旨在规范APS的诊断方法、血栓及病理妊娠风险评估与治疗方案,提高临床医师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实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最终改善患者预后。
一、APS的临床表现
(一)血栓事件
APS血管性血栓形成的临床表现取决于受累血管的种类、部位和大小,可表现为单一血管或多血管受累(表1)。静脉栓塞在APS中更常见,最常见部位为下肢深静脉血栓,亦可累及肾、肝、锁骨下、视网膜、上腔和下腔静脉,以及颅内静脉窦等。动脉栓塞最常见的部位为颅内血管,亦可累及冠状动脉、肾动脉、肠系膜动脉等。
表1 抗磷脂综合征血栓形成的临床表现

少数APS患者可在1周内出现进行性多个(3个或3个以上)器官的血栓形成,累及脑、肾、肝或心脏等重要脏器造成功能衰竭和死亡,并有病理证实小血管内血栓形成,称为灾难性抗磷脂综合征(catastrophic APS,CAPS)。
(二)病理妊娠
APS是导致病理妊娠的少数可以治疗的病因,妥善管理APS可有效改善妊娠结局。然而,目前产科APS的诊断和治疗存在诸多争议,认识不足与过度诊疗现象共存。由于既往研究中可能与APS相关的不良妊娠结局的定义不同,导致有关aPLs阳性患者妊娠结局的研究结论不同,甚至存在矛盾。为解决该问题,2006年国际血栓止血学会提出了APS悉尼修订分类标准,确定与APS相关的病理妊娠主要包括三种情况,具体内容见表2。
表2 2006年抗磷脂综合征悉尼修订的分类标准

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aPLs可能会导致女性不孕的假说,但直至今日,在该领域依然存在明显争议,目前尚无足够循证医学证据证实aPLs与不孕症以及辅助生殖失败之间有关联。
在临床实践中,部分患者具有产科APS的典型临床表现,但抗体检查结果达不到APS分类标准,如仅持续低滴度aPLs阳性;亦有部分患者具有标准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但临床表现未达到分类标准,如连续2次不明原因流产,或3次及以上非连续不明原因流产,或晚发型子痫前期,或胎盘血肿、胎盘早剥、晚期早产等。这些患者存在再次出现病理妊娠的风险,且应用产科APS的标准治疗(阿司匹林联合低分子肝素)可改善妊娠结局,被归为非标准产科APS。
(三)分类标准外临床表现
2006年悉尼修订APS分类标准会议上专家组即已提出,APS可能存在血栓事件、病理妊娠外的aPLs相关临床表现,包括网状青斑、浅表性静脉炎、血小板减少症、aPLs相关肾脏病变、心脏瓣膜病变(瓣膜赘生物、瓣膜增厚和瓣膜反流等)、溶血性贫血、舞蹈症、认知功能障碍和横贯性脊髓炎等。这些均非血管性血栓事件所致,但可能与aPLs的促凝或促炎状态相关,通常称之为“分类标准外临床表现”,其与血栓事件、病理妊娠风险、疾病预后存在密切关联,具有额外的诊断价值,并可能在诊治过程中影响治疗决策。APS临床试验及国际合作联盟的一项关于APS患者临床特征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52%的APS患者存在分类标准外临床表现,甚至可以独立于血栓事件、病理妊娠之外单独存在。因此,对APS患者应详细询问病史及体格检查,评估有无分类标准外临床表现;对出现上述临床表现的患者需积极筛查aPLs,警惕APS可能。
血小板减少是APS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发生率为20%~53%,通常SLE继发APS较原发性APS更易发生血小板减少。APS患者血小板减少程度往往为轻度或中度,可能的发病机制包括aPLs直接结合血小板使血小板活化和聚集、血栓性微血管病消耗、大量血栓形成消耗、脾内滞留增加、以肝素为代表的抗凝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等。由于血小板减少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因此临床医师对合并血小板减少的APS患者应用抗栓治疗存在一定顾虑,甚至会错误地认为APS血小板减少可降低患者血栓事件再发风险。事实恰恰相反,有研究显示,合并血小板减少的APS患者血栓事件再发风险显著增高,因此更应积极对待。
瓣膜病变是APS最常见的心脏损害表现,部分研究报告发生率最高达30%,合并aPLs阳性的SLE患者瓣膜病变发生率增高3倍。aPLs相关瓣膜损害临床表现包括瓣膜整体增厚(>3 mm)、瓣叶近中部局限性增厚、瓣缘不规则的结节或赘生物(Libman-Sacks心内膜炎)及瓣膜中重度功能异常(反流、狭窄),二尖瓣最为常见,其次为主动脉瓣,但需除外风湿热和感染性心内膜炎病史。病变早期临床可无明显相关症状和体征,多数患者出现瓣膜严重损害或动脉血栓事件筛查病因时才发现。通常经胸超声心动图或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即可证实。其具体发病机制未明,可能的机制考虑受累瓣膜在免疫复合物沉积损伤基础上继发纤维素-血小板栓子形成。治疗方面尽管规范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瓣膜病变有可能仍然会持续进展,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亦不明确,1/3患者会最终需要外科手术干预,且在随访12年中动脉血栓事件发生率增加8.4倍,特别是卒中。
APS相关肾脏损害不仅限于肾脏大血管栓塞事件,亦可累及肾脏中、小动脉及肾小球毛细血管丛。急性APS肾脏损害可表现为难以控制的高血压、肾功能急速下降和不同程度的血尿、蛋白尿。微血栓病变常同时累及其他器官,出现灾难性APS。亦可表现缓慢进展性血管病,主要表现肾小球滤过率缓慢下降以及高血压,大量蛋白尿通常不常见,多数患者只有<1.5 g/d的尿蛋白。典型的病理表现为血栓性微血管病,即肾小球内皮细胞损伤,如内皮细胞增生、肿胀,毛细血管腔内出现破碎红细胞、纤维性或血小板性血栓,基底膜增厚,出现双轨征,毛细血管腔狭窄或闭塞,肾血管管腔内血栓或纤维素样坏死,管腔狭窄或闭塞,甚至形成“葱皮样”结构等。同时可能伴有肾小球基底膜重复增生,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动脉内膜增生或急性肾小管坏死,提示APS相关肾脏损害的可能机制不仅限于高凝及血栓形成。
(四)CAPS
1992年,Asherson等首次报道,少数APS患者可在1周内出现进行性多个(3个或3个以上)器官的血栓形成,累及脑、肾、肝或心脏等重要脏器造成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并有病理证实小血管内血栓形成,称为灾难性APS。其发生率约为1.0%,但病死率高达50%~70%,往往死于卒中、脑病、出血、感染等。其可能的发病机制为短期内形成血栓风暴及炎症风暴。
二、APS的辅助检查
aPLs是一组以磷脂和/或磷脂结合蛋白为靶抗原的自身抗体总称。aPLs主要存在于APS、SLE、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病患者中,是APS最具特征的实验室标志物,亦是APS患者血栓事件和病理妊娠的主要风险预测因素。其中狼疮抗凝物(lupus anticoagulant,LAC)、抗心磷脂抗体(anticardiolipin antibody,aCL)及抗β2糖蛋白Ⅰ(β2GPⅠ)抗体作为APS分类标准中的实验室指标,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亦成为临床实验室最为常见的自身抗体检测之一。然而,不同实验室采用的aPLs检测方法差异及其异质性,实验室检测存在重复性差、标准化困难。2019年,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自身抗体检测专业委员会等发布了《抗磷脂抗体检测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建议各实验室以此统一检测方法。对可疑APS患者,建议同时检测LAC、aCL和抗β2GPⅠ抗体,以明确诊断并全面评估血栓事件或产科并发症的风险。
与aCL、抗β2GPⅠ抗体相比,LAC与血栓形成、病理妊娠间存在更强的相关性。LAC是一种功能性试验,是基于LAC在体外能延长磷脂依赖的不同途径的凝血时间来确定机体是否存在LAC。LAC的检测方法包括:(1)筛查试验:包括稀释的蝰蛇毒时间(dRVV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硅凝固时间法、大斑蛇凝血时间及蛇静脉酶时间等。目前,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CLSI)等国际aPLs检测指南均推荐,对LAC采用两种不同凝血途径的方法进行检测,其中dRVVT和APTT是国际上最常用的检测方法,通常dRVVT作为第一种选择的方法,敏感性较好的APTT(低磷脂或二氧化硅作为活化剂)作为第二种方法。(2)混合试验:将患者血浆与健康血浆(1∶1)进行混合,以证实凝血时间延长并不是由于凝血因子缺乏所致。(3)确证试验:采用改变磷脂的浓度或组成来确证LAC的存在。接受华法林、肝素及新型口服抗凝剂治疗的患者可能出现LAC检测结果的假阳性,因此,对接受抗凝剂治疗患者的LAC检测结果,应谨慎解读。
随着新的生物标志物不断被研究发现,极大拓展了对aPLs的认识。许多新型aPLs已证实可存在于APS患者中,且这些新型aPLs与患者血栓事件或病理妊娠等临床表现具有一定相关性,亦被称为标准外aPLs。目前已知的新型aPLs主要包括aCL IgA型、抗β2GPⅠ抗体IgA型、抗磷脂酰丝氨酸-凝血酶原(PS/PT)复合物抗体、抗β2GPⅠ结构域Ⅰ抗体、抗波形蛋白抗体、抗膜联蛋白抗体(主要为A5)等。对临床高度疑诊APS,但LAC、aCL、抗β2GPⅠ抗体检测均阴性时,可考虑检测新型aPLs以协助诊断。但其临床意义仍有待长期、前瞻性研究及临床实践深入探讨并验证。
三、APS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1. 诊断:当患者出现如下情况疑诊APS时,应尽早完善aPLs检测:(1)不明原因的血栓事件;(2)反复发作的血栓事件;(3)肠系膜、肝静脉、肾静脉、颅内静脉窦血栓等非常见部位的血栓事件;(4)青年(<50岁)卒中、心血管事件;(5)难以解释的神经系统症状:舞蹈症、横贯性脊髓炎、早期血管性痴呆;(6)SLE及其他结缔组织病合并血栓事件者;(7)难以解释的血小板减少症、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8)反复流产或伴有早产的妊娠并发症;(9)网状青斑或其他血栓事件相关的皮肤表现;(10)实验室检查意外发现APTT延长,梅毒血清检测假阳性。
1999年国际APS专家共识会首次提出了APS分类标准,即札幌(Sapporo)标准。2004年在悉尼进行第二次专家共识会,对该标准进行了修订。APS悉尼修订分类标准包括临床和实验室两方面,须同时符合至少一项临床指标和一项实验室指标方能诊断APS(表2)。
应注意,专家共识会上亦强调如果临床工作中患者不符合该分类标准,仅意味着不适合纳入临床研究,但不能排除APS诊断。临床工作中,APS亦应包括存在网状青斑、血小板减少、心脏瓣膜病变等aPLs相关临床表现的患者,以及符合临床标准同时伴持续低滴度aPLs阳性者,该类患者同样存在血栓事件和病理妊娠风险,应在管理与治疗上等同于APS患者。
临床中有很少部分患者存在典型的血栓事件、复发性自然流产、血小板减少等临床表现,高度疑诊APS,但常规检测aPLs抗体均为阴性,因此有学者提出“血清阴性APS”的概念,类似于“血清阴性类风湿关节炎”。辩证看待风湿免疫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血清阴性APS”的提出亦在情理之中,但做出该诊断应慎之又慎。通常出现aPLs阴性的可能原因包括:(1)患者存在其他先天性易栓症(如抗凝蛋白缺乏、凝血因子缺乏、纤溶蛋白缺乏)或其他获得性易栓症可能,不能诊断为APS;(2)既往病史中曾经aPLs阳性,随着病程和治疗改变,少部分患者出现aPLs转阴,亦非血清阴性APS;(3)患者典型aPLs均阴性,但新型aPLs检测阳性,如aCL IgA型、抗β2GPⅠ抗体IgA型、抗PS/PT抗体、抗β2GPⅠ结构域Ⅰ抗体、抗波形蛋白抗体、抗膜联蛋白抗体等,患者血栓事件和病理妊娠再发风险亦显著升高,应按照确诊APS进行管理与治疗。
2. 鉴别诊断:APS的鉴别诊断主要依据不同的临床表现加以鉴别。多种获得性或遗传因素亦可导致妊娠丢失,和/或血栓栓塞性疾病。静脉栓塞需与遗传性或获得性凝血功能异常(如蛋白C、蛋白S、V Leiden因子缺乏)、抗凝血酶缺陷症、恶性肿瘤和骨髓增殖性疾病、肾病综合征等鉴别。动脉栓塞需与动脉粥样硬化、栓塞事件、心房纤维颤动、心房黏液瘤、感染性心内膜炎、脂肪栓塞、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系统性血管炎等鉴别。同时或者先后出现动脉和静脉栓塞时需与肝素诱导性血小板减少症、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或纤维蛋白原活化因子缺乏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骨髓增殖性疾病、真性红细胞增多症、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华氏巨球蛋白血症、镰状细胞病、系统性血管炎及反常栓塞等鉴别。
四、APS的病情评估
及风险预测
(一)血栓事件再发风险评估
APS的血栓性病变常呈间歇性发作难以预测。既往临床实践及多项研究均已证实,APS患者血栓再发风险显著增高,其中“三阳”(即aCL、抗β2GPⅠ抗体、LAC三种磷脂抗体均阳性)患者尤为突出。新近有研究证实,aPLs滴度本身并不能反映血栓事件再发风险,aPLs阳性种类越多,其血栓再发风险越高。同时合并吸烟、肥胖、高脂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肾功能不全等其他血栓高危因素患者,血栓事件再发风险亦显著增加。如何精准评估和预测血栓再发风险尚未得到公论。2013年,Savino等首先提出全面APS评分(the global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score,GAPSS),评分标准在SLE和原发性APS队列研究中均显示能较好地反映血栓再发风险,评分标准包括高血压1分,高脂血症3分,LAC阳性4分,aCL IgG型/IgM型 5分,抗β2GPⅠ抗体IgG型/IgM型4分,抗PS/PT抗体3分。GAPSS≥10分为血栓再发高危人群。由于部分医院尚无法检测抗PS/PT抗体,不包含该抗体评分的修订GAPSS亦能较好地反映APS患者血栓再发风险。GAPSS有待进一步在大规模前瞻性临床队列研究中进行验证。
(二)病理妊娠风险评估
目前产科APS风险评估尚未建立较为理想的模型,公认危险因素包括三种磷脂抗体阳性、既往病理妊娠史、血栓史、合并SLE等其他结缔组织病、基础高血压、肾功能不全、低补体血症、血小板减少症等。法国关于产科APS相关病理妊娠危险因素分析研究发现,APS相关的早期复发性流产、≥≥10周的胎儿死亡、子痫及先兆子痫各自具有不同的危险因素,进一步证实三者可能病理生理机制不同,因此建议在病理妊娠风险评估中应根据不同的不良妊娠结局单独构建风险预测模型,方可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五、APS的治疗方案及原则
APS的治疗目的主要包括预防血栓和避免妊娠失败。治疗应个体化,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临床表现、病情严重程度及对治疗药物的反应等制定恰当的治疗方案。除了药物治疗外,亦应包括加强患者教育改善依从性及生活方式调整。
(一)血栓性APS的治疗
长期充分抗凝是治疗血栓性APS的关键。常用的抗凝药物包括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林及肝素或低分子肝素,可单用亦可联合抗血小板药物阿司匹林。具体个体化方案详见表3。一般情况下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在APS患者无需使用,但当合并严重血小板减少、溶血性贫血、发生CAPS或有严重神经系统损害时可以应用。
表3 2019年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关于成人血栓性APS的治疗推荐意见汇总

(二)产科APS的治疗
根据不同妊娠临床表现,以及既往有无血栓病史和病理妊娠史,可考虑选用小剂量阿司匹林、低分子肝素,或阿司匹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通常经合理的治疗后,超过70%的APS妊娠妇女可顺利分娩。
1. 既往无血栓病史的早期反复流产或晚期妊娠丢失的APS患者:通常建议在尝试受孕时开始应用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每日50~100 mg),并在证实宫内孕后开始应用预防剂量的低分子肝素治疗。与单用阿司匹林比,肝素联合阿司匹林能显著降低妊娠丢失风险,并增加新生儿活产率。但妊娠相关并发症(早产、子痫前期、胎儿生长发育迟缓)的风险两者间无显著差异。
2. 既往无血栓病史的胎盘功能不全相关早产的APS患者:建议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每日50~100 mg),孕早期开始,并持续整个孕期,建议同时联用预防剂量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当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失败或胎盘检查提示大量蜕膜细胞炎症或血管病变和/或血栓形成时,建议低剂量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
3. 既往有血栓病史的APS患者:对血栓性APS的非妊娠女性,建议长期接受华法林治疗,并在妊娠期接受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如患者既合并亦符合2006年悉尼修订APS分类标准的病理妊娠史,建议在妊娠期采用治疗剂量低分子肝素联合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
4. 临床无相关表现的aPLs阳性携带者:如何处理尚缺乏相关证据。该类人群在不接受任何治疗情况下超过50%的女性会成功妊娠。根据欧洲APS指南推荐,可考虑单用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每日50~100 mg)。
5. 难治性产科APS患者:通常指经过规范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联合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仍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APS患者,目前尚无高级别循证医学证实有效的二线治疗方案。建议在妊娠前使用阿司匹林和羟氯喹的基础上,于妊娠期前3个月考虑加用小剂量(≤≤10 mg/d)泼尼松或同等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小样本的难治性产科APS治疗干预研究结果显示,静脉应用丙种球蛋白、治疗性血浆置换可能为有效的治疗手段,但尚需大样本的设计严谨的临床研究来证实。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和其他细胞毒性药物(如环孢素A等)等治疗该类患者均被证实无效且有副作用,对aPLs滴度水平的改变影响小,很少有证据显示这些药物能改变高凝状态。并且糖皮质激素治疗增加产科不良事件及母体后遗症的风险,包括胎膜早破、早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感染、先兆子痫、妊娠期糖尿病、母体骨量减少等。
6. 产科APS患者围产期和产褥期管理:APS患者孕36周后可以随时停用阿司匹林,理想情况下需要在分娩前7~10 d停用。分娩前12~24 h需停用低分子肝素,分娩时尽可能减少分娩相关出血。产科APS并非剖宫产指征,如无其他产科并发症,通常推荐在孕38~39周进行计划分娩(催产或剖宫产),从而便于控制抗栓药物的终止时间。如果合并子痫前期和胎盘功能不良的临床表现,可根据产科指征处理。既往合并血栓事件的APS患者建议终生接受华法林抗凝,不建议停用抗凝时间超过48 h。在产褥期应尽早恢复抗凝。对无血栓事件的产科APS患者,建议产后继续预防性抗凝治疗至少6周。
(三)CAPS的治疗
CAPS是APS的急性严重类型,以广泛小血管及微血管血栓形成为特点,短期内发生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情危重,因此早期诊断和积极治疗是处理CAPS的关键。积极早期控制感染、尽量避免抗凝治疗中断或强度减低有助于预防CAPS发生。CAPS的一线治疗方案为肝素抗凝,联合糖皮质激素及血浆置换和/或静脉应用丙种球蛋白治疗,同时积极寻找并控制诱因,明确有无感染源及筛查恶性肿瘤。难治性CAPS可考虑应用利妥昔单抗清除B细胞、依库珠单抗阻断补体活化通路治疗,但尚缺乏大型对照研究,仍需更多的临床证据。
六、预后
APS患者整体预后相对良好,10年生存率约为90.7%,主要死亡原因为血栓事件、出血事件及合并感染。血栓性APS如未规范治疗,5年血栓事件再发风险超过50%,长期规范抗凝治疗能显著降低血栓再发风险。未经治疗的产科APS妊娠成功率仅为10%~30%,经规范治疗后活产率可显著升高至70%~85%,但早产率仍近40%,且母亲妊高症、子痫、子痫前期及围产期血栓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健康人,容易出现羊水过少、胎儿出生低体重等,产科APS患者长期血栓事件风险尚不明确。
诊疗要点
1. APS是一种以反复血管性血栓事件、复发性自然流产、血小板减少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伴有aPLs持续中、高滴度阳性的自身免疫病。
2. APS是导致病理性妊娠的少数可治疗的病因,妥善管理APS可有效改善妊娠结局。
3. 在临床工作中,APS亦应包括存在网状青斑、血小板减少、心脏瓣膜病变等aPLs相关临床表现的患者,以及符合临床分类标准同时伴持续低滴度aPLs阳性者,该类患者同样存在血栓事件和病理妊娠风险,应在管理和治疗方上等同于APS患者。
4. APS的治疗目的主要包括预防血栓和避免妊娠失败。治疗应个体化,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临床表现、病情严重程度及对治疗药物的反应等制定恰当的治疗方案。
执笔:赵久良
诊疗规范撰写组名单(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白玛央金(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曹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曾小峰(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柴克霞(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陈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池淑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风湿免疫科);达展云(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戴冽(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风湿免疫科);戴生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丁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风湿科);董凌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风湿免疫科);杜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段利华(江西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段新旺(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樊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冯学兵(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风湿免疫科);高洁(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高晋芳(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白求恩医院 风湿免疫科);耿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古洁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郭江涛(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何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何岚(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黄慈波(深圳大学华南医院风湿免疫科);黄烽(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黄文辉(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黄新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黄艳艳(海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姜德训(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姜林娣(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风湿免疫科);姜振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靳洪涛(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彩凤(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风湿科);李芬(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娟(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风湿病诊疗中心);李龙(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李梦涛(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李芹(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李懿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风湿免疫科 湖南省风湿免疫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厉小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栗占国(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林禾(福建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林金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林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林书典(海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林志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林智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刘冬舟(深圳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刘升云(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晓霞(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刘燕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风湿免疫科);刘重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鲁静(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路跃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风湿免疫科);马丽(中日友好医院风湿免疫科);马莉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风湿免疫科);米克拉依·曼苏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莫颖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风湿免疫科);潘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戚务芳(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青玉凤(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沈海丽(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沈敏(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沈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湿科);石桂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史晓飞(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帅宗文(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宋立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风湿科);苏娟(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苏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孙红胜(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田新平(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彩虹(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丹丹(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王静(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立(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丽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培(河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王迁(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王晓冰(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燕(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王永福(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友莲(江西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王玉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风湿免疫科);王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王悦(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志强(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风湿免疫科);魏蔚(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风湿免疫科);吴歆(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风湿免疫科);吴振彪(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免疫科);武丽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夏丽萍(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向阳(湖北民族大学医学部风湿病发生与干预湖北省重点实验室);肖会(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谢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风湿免疫科);徐沪济(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风湿免疫科);徐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薛愉(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严青(福建省立医院风湿免疫科);杨程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杨静(绵阳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杨念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杨娉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叶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风湿科);张风肖(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奉春(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张辉(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张江林(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张莉芸(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白求恩医院 风湿免疫科);张缪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娜(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风湿免疫科);张文(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张晓(广东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烜(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临床免疫中心);张学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志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张卓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赵东宝(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赵久良(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赵丽珂(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院);赵令(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赵岩(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赵彦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赵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风湿免疫科);郑朝晖(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临床免疫科);郑文洁(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周京国(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邹和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邹庆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左晓霞(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风湿免疫科 湖南省风湿免疫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本文来源:中华内科杂志, 2022,61(9) : 1000-1007.
本文编辑:胡朝晖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