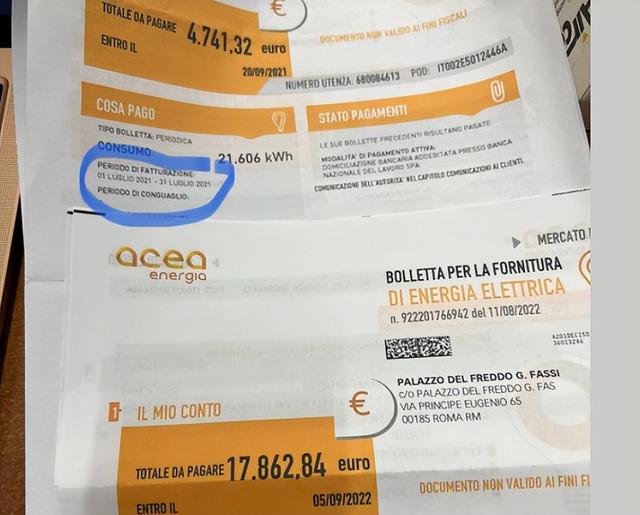还是昨天的你 还是昨日的宁静

搜寻童年的记忆(散文)
——太和碗厂旧址记
那片山崖,还是那般的翠绿;那条小溪,还是昨日的宁静,只是昨日已然成追忆,昨日的少年,已混浊着昨日的记忆。
少年时代的记忆,多已随风而逝,残篇断章,难以回忆。眼前的风景,残存在脑海中只有那遍布着碓状石窝子的画面,清晰着。只是一别三十余年,当年的少年,转身间,已进壮年,只是毫无壮志可言。
应该是八十年代中期,跟随盛年的父母,从柑子区徒步进入太和乡,目的大竹县神合乡。一路走走停停,沿途多有亲戚接待,太和乡与老家,隔着一座巨大的山梁,人称——擦耳岩。
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那是一个细雨纷飞的八月,一大家人清晨从太和的亲戚家出发,开始翻越那翠绿的山梁。当农家的炊烟在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田野与山岗间升起时,我们已远离了村庄,在一片陡峭的山脚下开始了第一程的歇息。
仰视的山梁,在细雨中愈发碧翠,时有风过,那翠绿便结成大滴大滴的,晶莹的水珠子,高高低低从树冠下扬洒下来,缭乱而美丽。远处,一片不毛之地在这满山的绿色里显得有些突兀,只是童年的我并不经意于那间杂于满目苍翠间的一片黄白斑点。
随着断续的小路攀爬,陡然发现刚才的不毛之地,就在咫尺眼前,竟是那么的怪异,奇奇怪怪的大大小小的石窝成阶梯状布满那一小片多是碎陶的陡坎,令人不解。残存的水积于那层层叠叠的碗状窝子里面,有水虫游弋。这必是人类留下的痕迹,只是与我第一次谋面,令我茫然不知眼睛所见为何物。
父亲见此,讲与我们,说这是当年太和碗厂捣泥的石碓,从山上挖来的一种黏性极好,又极细腻的泥,要放入这石窝子里,靠人工用长木槌捣散捣细,再层层滤下,沉淀,沉淀下来的泥浆,待半干时取用,用于制碗盆鑵等陶器……
之后的山路崎岖而陡险,一大家子顶风冒雨在山路上前行,虽是有些艰辛,但童年的欢乐也许正是暗藏于这份辛劳之中吧!以至每每回想起那段山路,总是满怀欢喜。
擦耳岩丫口风助雨势,禁不住有些寒颤,只是,脚下的土地已是故土了,远远的看得见那巨大的水库,父亲说,家就在水库边。
之后的路,已在记忆中模糊,只记得那高高的牌坊,歪歪斜斜的老屋,还有老家叔爷们的热情。
那时,祖母还在,最为高兴的莫不过她老人家了,他一遍又一遍的念叨着我的孙子呢,我的孙子呢,因为她已无法看见了。
许多年过去了,祖母早已在轮回的世界了,严厉与慈爱的父亲也已去见他敬爱的马克思了。时不时想起那段远足,总是浮现起那山梁下遍布的石头窝子,总是想去再看上一看。

终于,从朋友处打听到那个70年代就搬迁走了的国营碗厂的遗址,周末约上三朋四友前往。
当年用了数天才抵达的山崖,现在用时不过一小时的时间,想来真要感谢社会的飞速发展。
通村的公路蛇一样蜿蜒,已没有一处风景能让我找回儿时的记忆。我不知道此刻的我是不是行走在当年的道路上?只是当年决没有这水泥的路面。终于在一片茂密的山林下停了下来,一弯小溪清澈而浅浅,溪边有鳞次栉比的木楼瓦房,只是多已残败不堪,也都无法与远去的记忆相重叠了,我努力的去搜寻那已然模糊映像中的那片石窝子。
现实的世界,让这搜寻徒劳着,无果。
一条窄窄的水泥道路缓缓而上,有旧日的挡墙隐于野藤绿蔓中,更有只剩梁柱的大厨房,孤零零伫立在一片齐人高的野草丛中。天光自由的洒落在那昨日的灶台,石水缸、磨盘已沉寂了多年了,尘灰与青苔斑驳着,野草窜生在屋子中间,那画面有些荒诞,当然,眼前的一切必是荒凉的。
只是,我还是未见到那儿时所曾见。
无人问询,也就懒懒散散的穿行在那当年的村落里,沿山麓而建的上百间穿斗架子房,层层叠叠分布在这大山脚下,虽多已无人居住,但半个世纪的风雨竟未能彻底的摧毁它,它们——那一栋栋错落有致的木楼瓦房,组成的大村落,似乎并不屈服这半个世纪时间的摧残,依然抗拒着自然法则的淘汰,多保持着当年的姿态,只是再不能重现昨日的辉煌了,鸡鸣犬吠已远去,人声鼎沸已远去。
信步由缰的脚步,迂回在那山坡上旧房的檐前屋后,野草齐腰,瓦砾遍布,也有不见踪影的鼠类窜行其间,只有这迎春的桃李,一如昨天,怒放着,映红那荒芜的世界,虚化这眼前的破败,不在乎赏花人的更迭变换,甚至无人再来。
遇有老者荷锄归来,老人见有外人巡游其间,有些诧意,但更多的是善意的笑脸。
与其相摆谈,知这碗厂当年有数百人居于此间,制陶耕田,栽桑养蚕,也有鸡犬声相闻,也有小儿追逐嬉戏于房前,也有牛铃遥响树林间,一如世外桃园。
他的眼神已然浑浊,只是,在他讲到那回不去的从前时,脸上的笑,如同他身后怒放的桃花一般,灿烂。
只是,那份醉心的笑,太短。
70年代厂址搬迁,虽随厂搬走了许多人家,但依然居住着本地的村民,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状态,虽是清贫,也还自在。只是改革开放之后,年轻一代再也经受不住这份清贫了,多外出闯世界,而今当年外出的年青一代也多已老去,他们的后代更是分散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多数人早已忘记了这个曾经的家园,这个他们走出去之前的世界,这个叫指南寺的地方。
再问起当年

再问起当年我所见的石窝子呢?老者有些惊讶,他遥遥的指了指我们刚才经过的地方,说那条水泥路就经过那片当年捣碗泥的石窝作坊,只是修公路全都挖填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我随着他的手指所向,空自抬头看了看那穿行于丛林间的水泥道路,心里有些失落,也有些无奈。
看不见了!果真看不见了!
2020年3月22日
(图片:作者拍摄)
【作者简介】
张伟,男,从警于四川。喜收藏、阅读、旅行,喜欢将自己的见闻安静的倾吐于笔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